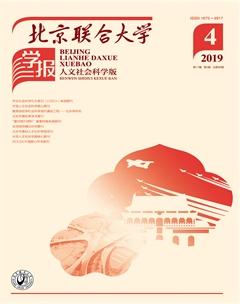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文化资本的转化逻辑
蒋淑媛 李传琦
[摘要]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化资本的理论内涵有所延伸,文化资本的生产积累方式也得到了拓展,并促进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碰撞和审美趣味的交流。随着新媒体平台功能的不断强大和开发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方式实现了创新,打破了文化资本在特殊阶层内部循环、并不断巩固的传统认知。但资本转化过程中存在的身体商品化倾向、非理性文化消费、文化资本造假以及挑战道德底线博取注意力等社会问题更值得反思。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资本;资本转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4003807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引入社会学领域,从考察法国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入手,提出了“场域”和“资本”的概念,旨在分析家庭出身、教育水平、文化品味、社会关系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力。他将“场域”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人们的实践活动均是在一定场域中进行的,每个人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低,决定了其在场域中的地位。而“资本”的含义更加泛化,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原则。”[2]也就是说,资本是经过长期积累、与社会形成的一种嵌入关系和控制能力,不仅仅包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的经济资本,同时也包括以社会名誉和社会地位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的社会资本,以及以个人品味、作品和文凭为符号,以学位证书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另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都具有象征性,都可以以象征资本的形式呈现,象征资本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和其他资本中的一种或几种共同发挥作用,各种形式的资本成为个体维持地位、社会维持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科技的进步,文化资本渗透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结构和运行规则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成为学界考察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重要切入点和理论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推广,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知乎为代表的知识问答社区、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社区等新兴媒体的社会功能从信息传播拓展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应用,不仅变革了传统的传播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结构、知识储备和生活形态。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媒体语境中,文化资本的内涵、生产积累方式都出现了新的社会特征,而在文化资本、社交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凸显,成为影响场域结构及运行机制的初始动力和核心原则。本文将紧密结合我国互联网技术带动下各种新兴媒体平台的实际应用,聚焦于凭借新媒体实现了文化资本——社交资本——经济资本快速转化的网络红人和网络大V这一典型群体,对文化资本的理论内涵、积累和再生产方式、转化路径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解读,并反思文化资本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商品化倾向和道德困境。
一、文化资本理论内涵的延伸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标志行动者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3]文化资本是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指标,在特定场域内,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成为行动者赢得社会资本进而获取经济资本的“入场券”,于是合法化的文化形式、品味标准成为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也成为巩固和提升阶层地位的重要手段。文化资本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3.体制形态,这是一种被区别对待的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的那样),教育文凭完全是在文化资本的一种原初特质下授予的,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认定。”[4]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成为当代社会主要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的生产和运行规则直接影响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心态的变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文化资本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领域,不论是对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是对人们的心态结构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当下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知识社会中,互联网技术裹挟下的文化资本更加深刻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三种形态文化资本的内涵均有所延伸和深化,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中,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也有创新性的延展。
第17卷第4期蒋淑媛等:新媒体语境下文化资本的转化逻辑
北京聯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0月
(一)具体形态文化资本:从长期累积到短期速成
具体形态文化资本是嵌入个人身体状态中的技能和修养,是精神层面的外化和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爱好品味、谈吐水平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形态的文化资本是与身体融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知识储备、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都是通过外在的身体呈现出来的,获取的过程是不断积累的过程,个体必须亲力亲为,投入精力和心血,所以极费时间。“衡量文化资本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获取收益所需的时间的长度作为其衡量标准”。[5]194具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情况下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取,是长时间学习积累后由文化塑造出的身体,个人的外表、状态和活动都是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具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十分漫长,而且最终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即时性地传递。”[5]195而凭借新媒体平台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的优势,部分网络红人进一步放大了身体作为文化资本载体的作用,通过外在的宣传包装、以身体化特征作为标签,不断调动人们在视觉、听觉等维度上的感官体验,在短期内迅速走红,大大缩短了具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时间。从早期因网友将照片上传到网络中而以清纯形象走红的“天仙妹妹”羌族女孩尔玛依娜,到在选秀节目《创造101》中歌舞技能平平,凭借运气和外表胜出的锦鲤女孩杨超越,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仅仅接受过短期的技能培训,主要以身体外观来打造“人设”,成为建构的形象符号。另外,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以身体为主要形式的文化资本实现了批量化生产,“锥子脸”“网红脸”就是当下根据用户需求设计生产出的具体形态文化资本,不仅体现在一个特定的个体身上,而且成为当下很多女性审美的风向标。
(二)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从物质性产品的占有使用到虚拟性产品的应用
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在物质层面上表现为经济资本,在象征层面上表现为具体形态文化资本。占有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只需要支付经济资本,但是要了解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象征性的文化含义,则需要个人去学习、掌握。例如,人们可以用金钱购买一本实体性图书,但需要具备一定的识字能力和知识储备才能阅读、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人们能够用金钱购买占有一台机器,但需要通过培训才能真正操作使用机器。“在物质和媒体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绘画、纪念碑、器械等,在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承的。”[5]198互联网技术催生出来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和特质。第一,不同形式的新媒体中生产了大量的内容产品,各种虚拟性的网络应用软件深度介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中,这成为新媒体平台中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主要形式。微信公众号生产的各种文字性信息、短视频网站中播放的娱乐内容,都是当下人们能够便捷获取的新型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从购物、订餐、出行、支付到医疗、教育、娱乐等,在电脑或手机等终端设备上,不同的应用程序有着不同的操作步骤和流程,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阅览了有关信息,才能真正习得这种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同的新媒体平台网络红人和网络大V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就在于他们对于网络直播、短视频拍摄、知识社区运行程序的熟练使用。第二,新媒体平台中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所具有的虚拟性特征使其无法在物质层面呈现,人们只有通过实际应用才能获取其象征层面的文化属性。第三,网络应用软件附着于电子设备中,而电子设备更新换代的频率使得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在物质性层面的传承价值较低。
(三)体制形态文化资本:从官方的学历证书扩展至标签化认证
体制形态文化资本的主要呈现形式是由权威机构授予的学历证书和资历认证。“它在官方认可的、合法化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的差别,而那种简单的文化资本则需要不断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看到强迫他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5]201体制形态文化资本超越了具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生物局限,通过合法化的集体认可,确立体制形态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价值,从而保证了拥有者的经济利益。
官方认可的学历证书等体制形态文化资本在新媒体语境下仍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储备和学历水平仍然是个体在新媒体平台上获得关注和认同、进行自我价值标榜的重要手段。同时,传统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也成为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标签化认证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例如,知识问答社区“知乎”采用体制形态文化资本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一是账户认证。“知乎”通过社区内的规章制度认可了体制形态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合法保障价值。根据用户提交的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划分为官方机构账号、认证个人账号和普通个人账号三个等级。认证成功后,用户名后面会有蓝底白色对号的徽章,与未认证用户进行区分。增加了认证用户的认知度和可信度。二是标签说明。一种方式是用户在个人主页上可自行添加教育经历和职业经历,也可以编辑关键词,如烘焙爱好者、养猫达人等,说明自己的身份及擅长的领域。第二种是官方统一的标签说明。如用户获得的关注人数、点赞量、被官方收录的回答次数以及在社区内的活跃程度而获得的徽章数等。不同的标签说明也将直接决定其在社区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文化资本生产积累方式的拓展
文化资本的生产积累指的是文化资本后天习得以及不断增殖的过程,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生产积累的途径主要来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根据文化资本离学术市场要求的距离的远近,家庭往往会做出某种反映,一种是进行具有肯定性的早期家庭教育节省时间,提前开始,一种是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早期家庭教育浪费时间,并且是双重的浪费时间, 因为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改正早期家庭教育所产生的效果。”[5]195家庭是文化资本生产积累的首要场所,儿童学习成绩、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不同社会阶层自身的文化资本和重视教育程度有关,原生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平等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区隔的重要原因。学校教育是文化资本生产的主要环节,“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學机构,就成了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争夺的关键。”[6]学校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并以一种强加和灌输的专断方式迫使人们接受的场所。学校教育不但垄断了学历文凭等体制状态文化资本,而且也垄断了客观状态文化资本,并且对于具体形态文化资本产生作用。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迁、文化资源供给和获取方式的变革,文化资本的生产积累方式相应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一)途径:从家庭、学校到网络平台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仍然是社会个体获取和积累社会资本的主要方式,但不再是阶层固化的桎梏。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从经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从乡村到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家庭内部文化资本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世界的日益开放,学校教育资源也日益丰富,社会分工的细分化程度也不断促使文化资本的评价标准日益多样化。同时,“互联网+”逐渐渗透至教育领域,不断缩小不同区域间教育投入和师资条件的差距、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曾引发热议的新闻《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报道了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和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准。另外,互联网是各种知识和信息的集散地和资源库,以技能培训为主旨的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成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有效补充。而新媒体所具有的社交属性使得有共同志趣的人们能够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建立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分享学习方法和资源,不断消弭阶层之间的知识鸿沟。
(二)生产:从特权阶层到普罗大众
另一方面,粉丝社群在打造明星、培育偶像方面显示出了社会资本强大的号召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粉丝从大众媒介主导下被动的“追星族”和“过度的大众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新媒体平台中的“生产型消费者”,他们有意识地参与到对偶像知名度的打造和维持环节中,粉丝与偶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粉丝团队的社会资本规模扩大后建立起了层次清晰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粉丝站、后援会、投票组、宣传组等内部机构分工清晰,各司其职。偶像不再依靠个人实力而成名,而更多地依賴于粉丝的社会资本所支撑的投票数据和曝光度,尽管粉丝力量主导下养成的偶像短时间内也能够获取一定的经济资本,但表现出投机性和短视性,产生更多的不正当竞争,并影响了整个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知识付费+打赏模式
“在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若想获得收益,他必须凭借一定程度的教育资历(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11]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需要市场对其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兑换率进行识别。在注意力稀缺与互联网信息超载的悖论中,受众对优质内容资源的诉求愈发强烈。网络环境中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集中体现在不同形式文化资本吸引用户注意力、经济变现的能力。
1. 知识付费:对文化资本的直接售卖
对知识付费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消费者支付相应的费用获得相应的知识。这里所购买的产品大多是无形的,产品提供者持有的文化资本决定了经济资本的收益率。例如,社会领域中的知名学者和文人,在新媒体平台开设专栏或注册自媒体账号,在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曾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薛兆丰在“得到”新媒体平台中开设了知识付费专栏,每天用10分钟左右音频讲授经济学常识,订阅用户超25万,销售收入近5 000万。有数据显示:“知乎Live的相关课程达到了7 000场以上,而喜马拉雅上付费内容高达31万条,得到也在31个付费专栏的基础上,增开了精品课。”[12]知识付费已经成为知识型网络社区的核心服务内容。
2. 打赏模式:对文化资本的认可馈赠
打赏模式是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平台的创新性盈利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于在街头卖艺和梨园界的唱堂会,由特定观众对其呈现的文化资本进行定价,以各种形式的礼物或数额不一的资金进行支付。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成熟,打赏模式很快在文学网站、游戏以及网络视频聊天室得到普及,用户通过赠送虚拟性礼物、网站充值打赏或者直接以金钱形式赠予文化资本的提供者。赏金的多寡也与文化资本持有者的产出内容的质量息息相关,但用户的打赏行为在一定层面上具有炫耀性消费的特征,以表现个人对文化资本的认可程度。
四、文化资本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布尔迪厄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对文化资本存在形式进行划分,从具体形态到客观形态再到体制形态,这种渐进的过程体现出了不同形式文化资本获得的难度和由此带来的经济资本数量。但在视觉文化为主导的新媒体平台中,以身体为依托的具体形态文化资本成了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化的主要形式,并由此出现了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和谐的文化现象。
(一)身体的商品化倾向日趋严重
在消费社会,身体异化为商品的现象一直被学界所诟病和批判。“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能量的、动作的、性的)‘实用价值向唯一一种功用性‘交换价值蜕变。”[13]新媒体平台的应用进一步加剧了身体的商品化程度,为了在网络直播中获得高关注和打赏,网络女主播会故意穿着暴露从而引人注目。与传统社会中强行异化女性身体的“裹小脚”审美方式不同,网络主播自愿通过医疗整容等手段加工、塑造一个“商品化的身体”,使身体退化成为一种媒介工具。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凯瑟琳·摩根认为整形美容手术是消费市场“对女性身体的殖民化”,女性一旦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审美机制中,身体就不为自己所控制,成为“驯服的身体。”为了实现身体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化,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自愿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身体容貌的展示。例如,“口红一哥”李佳琦以帅气的男性外表对女性产品进行推广,身体和推荐产品的巨大反差,吸引了大批女性用户的关注,直接带动了口红产品的销售,进而获取可观的经济资本。
(二)刺激人们进行非理性文化消费
为了实现文化资本快速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很多网络红人和网络主播以娱乐搞笑、新奇怪异甚至色情挑逗的内容来吸引用户,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影响下,新媒体平台中充斥着大量浅层次、停留于感官层面的文化产品,尤其在网络打赏这种新型付费机制的促动下,使用户形成了娱乐式消费、成瘾式消费。网络打赏介于“免费”和“自愿付费”之间,打赏方式的任意性和金额的随意性使得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同时对于网络主播来说也是获取高收益的机会。由此,网络主播会通过言语、文字和各种音视频形式不断制造猎奇内容来刺激用户心理,诱发打赏行为。根据对四家主流直播平台前1万名主播的统计显示,“2016年,2名主播收入过千万元,45%的主播收入在5万~10万元之间。”[14]“网络打赏”的金额纪录屡被刷新。未成年人“天价”打赏主播的行为层出不穷,因编造、夸大事情真相获得高额经济资本的新闻事件也不时公之于众。由此,网络打赏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规范。
(三)文化资本的造假行为频出
由于新媒体平台的虚拟性特征,部分网络红人和网络主播进行着虚假的自我呈现。自我呈现的核心在于对自我印象的控制与管理,“人们生活在一个表演社会,表演者内心渴望能够给观众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印象。” [15]在网络直播中,滤镜的设置美化了主播的容貌,声卡的设置使主播的声音可以任意改变。技术手段的升级为人们带来了良好的场景体验和审美享受,但同时也制作出更多虚幻的媒介形象,欺瞒蒙蔽了大众视线,使部分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产生偏差。例如,网络主播“乔碧萝殿下”用卡通图像挡住脸,以甜美的声音和大家聊天,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但一次直播时因软件故障遮挡图像没有显示,其真实相貌曝光,由此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于主播颜值真伪的舆论之争。被封为女神的知乎用户“童谣”,个人主页上写着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学历,曾在投资银行工作,头像是一个颜值颇高的女性,在获取高度关注以后,在知乎上用“ck小小”与“童瑶”两个账号互动,谎称自己身患重病来博取同情,诱使网友捐款,事情败露后发现,这位高学历女神只是个专科毕业的普通男性。
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中,买粉丝、刷数据等造假行为更是屡禁不止。在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上,存在着以销售粉丝为主业的店铺,对不同层级的粉丝进行明码标价,如5元就能购买9 999个“初级凑数粉”, 50元可以购买1万个“超级真人粉”,并提供转发、点赞、阅读、评论等付费服务。在社交网络社区中活跃着一些组织粉丝进行点赞、评论的兼职小组,通过制造虚假的社会资本来推高流量,从而获取经济资本。2019年,社会生活分享社区“小红书”因存在通过代写虚假“种草”文、刷单刷量、销售违法违禁产品等问题被各大应用市场下架的事件引发网民热议,并促使“小红书”启动了对站内内容的全面排查和整改。
(四)文化资本缺乏者的残酷表演
新媒体平台将文化资本转化经济资本的巨大作用力,使得少部分并不具备文化资本的人群也盲目跟风,采用极端的方式尽可能地博取网友的注意力,攫取经济利益,这就造成越来越多“吃人血馒头”的事情发生。在短视频网站中存在的未成年人抽烟喝酒、自虐式吃病猪肉、鞭炮炸裤裆等视频内容都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部分网友的关注、围观和评论,反而激发了一些网民对种种病态行为甚至于危险视频内容的效仿,“学‘抖音挑战高难度动作,爸爸失手致使2岁宝宝头部着地”“为当网红在马路飙车”等新闻令人反思,尽管新媒体技术为资本转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但只靠博取眼球获取经济资本的方式并不可靠,反而会弄巧成拙,不仅对表演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五、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化了文化资本的理论内涵,也改变了文化资本积累的方式,并且为文化资本向其他资本的转化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但不能忽略的是,新媒体平台仍然是资本之间博弈、争夺权力的场域。在新媒体语境下,尽管文化资本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强势地位,但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依然反映出经济资本在以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更新迭代、粉丝群体等社会资本的快速聚集和巨大号召力、关注度、点击率等能够换算成经济资本的各种数据驱使着人们不断上演一幕幕的愚昧表演和集体狂欢。新媒体还处于动态发展的演进过程中,还将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入的影响。只有全面深入地把握新媒体的运行规律和文化本质,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强化内容治理,平衡好现代科技与个体成长、社会良性运行之间的关系,洞察网络用户的审美诉求并给予积极正向引导,才能提升社会宏观层面的文化资本,促进资本之间的科学理性转化,以此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資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3]张意:《文化资本》,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4]P.Bourdieu:The Form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Greenwood Press,1986,P.244.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第9页。
[7]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3页。
[9]陈峰:《文化资本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
[10]Dalls W.Smythe:Communication: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
[11]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2]搜狐网:《知识付费热潮后,用户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https://www.sohu.com/a/216253479_286651。
[13][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
[14]36氪网:《中国独创商业模式,网络“打赏”该如何定性?》,https://36kr.com/p/5082580。
[15][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JIANG Shuyuan, LI Chuanqi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 Design Arts, Beijing University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has been extended, and the way of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has also been expanded. It has, therefore, promoted the cultural collision and the exchange of aesthetic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strata. With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new media platform function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to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has achieved innovation, and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that cultural capital circulates within special classes and is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However, th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tendency of physical commercialization, irrat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capital fraud, and challenging the moral bottom line to attract attention are worth reflecting.
Key words:new media; cultural capital; capital conversion
(责任编辑孙俊青)2019年10月第17卷第4期总66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Oct. 2019Vol.17 No.4 Sum No.66
[收稿日期]2019-09-20
[基金项目]2018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环境下北京公共文化资源的合作共享机制及其效能研究”(项目编号:18XCB008);2017年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基金课题“粉丝文化视域下的网络剧现象研究”。
[作者简介]蒋淑媛(1974—),女,山东冠县人,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重点实验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