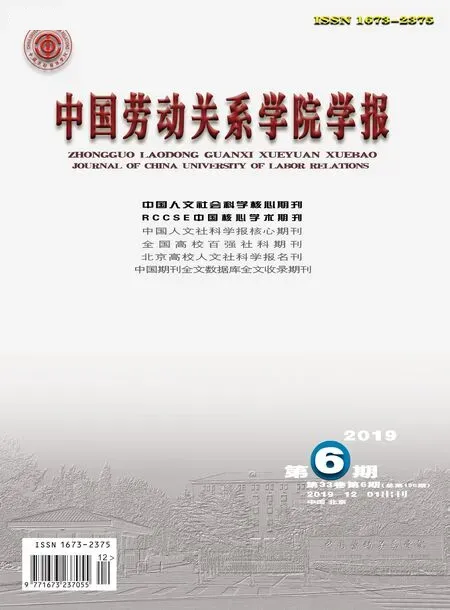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及其重构*
刘乐明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一、导语
随着大规模工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销声匿迹,“自为”的工人阶级似乎消失了,学界关于工人阶级或工人政治消亡的论调大行其道。然而,工人阶级“拉萨尔主义”式的维权抗争并没有随之消失殆尽。有学者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走向沉寂;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罢工,从来没有休止过”。[1]而且,全球产业结构的转移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人数量的剧增,工人的罢工与抗争也在这些国家兴起。因此,工人政治研究的传统议题并未消失,工人政治仍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工人维权的策略、方式、手段及其与资本和国家所发生的关系成为后革命时代工人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职业健康作为工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劳动权益,是劳工抗争的主要诉求目标,因而工人职业健康是工人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①文中所言的职业健康指的是权利范畴意义下的职业健康权益,工人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工人群体,既包括我国传统产业工人,也包括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农民工群体。因此,工人职业健康指的是广义工人群体的职业健康权益。为了表述简洁,本文统一使用“工人职业健康”表达“工人职业健康权益”的意涵。
工人职业健康研究并非一门显学。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工人职业健康研究影响深远,但学界迄今少有关于工人职业健康的系统性论著,相关研究只是散见于职业卫生与预防医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社会医学以及抗争政治等研究领域。由此导致,一方面,学界对以往研究文献的类型与脉络未能清晰的把握,缺少对工人职业健康研究的全景观察;另一方面,以往研究未能建立系统的分析框架,传统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赋权理论均未能搭建起理解工人职业健康的系统框架。因此,通过梳理国内外已有成果,归纳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本研究提炼出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进而搭建分析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系统框架,以期推动工人职业健康研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
二、理解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
对于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研究,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英国工人阶级身体普遍衰弱状况的深刻揭露使得工人职业健康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2]并启发了后来诸多对工人阶级健康状况的研究。①工人阶级状况相关研究可参见: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M].陈瑞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M].梁光严,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汤普森 E P.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M].钱乘旦,杨豫,潘兴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早在公元前4-5世纪就有关于工伤和职业病的文字记载,[3]这是关于工人职业健康的最早研究。正是这些公共卫生、职业病与工伤史学研究为人们科学认知职业健康问题奠定了基础。②国内外学界在此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可参见:ROSNER D,MARKOWITZ G E.Drying for work: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ROSNER D,MARKOWITZ G E.Deadly dust:Silicosis and the politic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M].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MCIVOR A,JOHNSTON R. Iners' lung: A history of dust disease in British coal mining [M].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7.GROB G N. The deadly truth:A history of disease in America [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ABRAMS H K.A short history of occupational health[J].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2001,22(1):34-80.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资料集(一九四九—一九八六)[G].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2.刘翠溶.尘肺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及其意涵[J].台湾史研究,2010,17(4):113-163.NG K T. Pneumoconiosis in Hong Kong:Its epidemiology,control and compensation[D].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7. 陈黎黎.1900-1969年间美国的尘肺病治理历程及其启示[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2-16. 户佩圆.试论美国黑肺病运动(1968-1978)[D].开封:河南大学,2013. 张凯.美国历史上的煤矿矿难及其治理[D].重庆:西南大学,2009. 江文娟.20世纪英国煤工尘肺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经过漫长的探索,该领域研究使得人们摆脱了以往对职业病与职业健康的混沌甚至错误认知,逐渐认识到工作环境是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重要因素,并确立了“工作-健康”(work-health)的基本解释范式。[4]在此基础之上,社会科学开启了对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探索,并确立了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四种基本理论模式。
(一)社会医学模式
在1848年魏尔啸(Rudolf Virchow)医生提出“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概念之后,[5]研究者开始突破对劳动者疾病的单纯医学解释,探寻劳动者疾病的社会意涵。社会医学先驱弗兰克(Johann P. Frank)在他的演讲中已注意到工作场所之外的居住环境对工人健康的影响,[6]赛里科夫(Irving Selikoff)则直言“矽肺病是一种具有医学面向的社会疾病(social disease)”,③尘肺病的种类较多,主要有矽肺、煤工尘肺、石墨尘肺、石棉尘肺、滑石尘肺、水泥尘肺、云母尘肺、陶工尘肺、铝尘肺、电焊尘肺和铸工尘肺等。文中所言的矽肺病是尘肺病的一种,下文所言的黑肺病即煤工尘肺病。强调尘肺病的社会医学特征以及尘肺病产生的复杂社会背景。[7]随着研究者逐渐加入各种影响要素,工人职业健康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最终需要用“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这个术语加以概括。德比(Allard E.Dembe)建构了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综合的职业病分析模型,认为分析理解雇佣关系与医患关系的情境是全面解析职业病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工会、政府、保险公司、研究者以及社群等又是向两大情境施加影响的主要力量。[8]罗斯纳与马科维茨也强调“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对职业病认知的重要性,认为“对疾病的专业认知并不必然归因于医学的进步与流行病学的变化。疾病是由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以及科技创新所共同形塑的。没有理解疾病的社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疾病的历史。这些社会语境包括疾病出现与消失的社会因素”。[9]艾布拉姆斯(Herbert K.Abrams)在对职业健康进行历史考察后认为,“要想理解职业健康的历史,必须将之放到劳资关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与工作相关的疾病(workrelated disease)是社会化的产生。”[10]而现代医学社会学的研究更是明确指出,社会阶级是健康和疾病最有力的决定因素。[11]
总体来看,社会医学面向的研究不再将职业病或职业健康问题限定为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将其影响因素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开始寻求阶级、住所、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等更广泛的影响因素,突破了职业病与职业健康史学研究所确立的“工作-健康”的解释范式,丰富了对工人职业健康的社会学解释。
(二)经济环境模式
宏观经济、经济周期、政治经济模式等经济环境也是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重要因素。华莱士(Michael Wallace)的研究发现,煤矿工人的职业安全与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繁荣会提升工伤率,而经济衰退则会降低工伤率。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煤炭需求量的增加会从两方面影响煤矿工人的职业安全:一方面,煤炭需求量的增长会导致矿主不断提高产能标准,而产能标准提高与矿业生产安全事故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另一方面,煤炭需求量的增长还会带来大量小型煤矿死灰复燃,小型煤矿不仅自身的安全防护技术低下,而且国家对小型煤矿的监督难度大,从而导致煤矿安全事故高发。[12]但也有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会导致政府为了促进与激活经济而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如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卡特政府不断减少对社会的管制,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在劳资纠纷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劳工立场,从而导致矿业生产安全质量下降。[13]因此,不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工人职业健康存在着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的工伤与职业病问题开始凸显,对此问题的理解不能脱离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这个大背景。在市场化改革后,权力与资本的联盟成为不争的事实,[14]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与“嵌入型自主”的政府特性激发与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5]另一方面,“地方国家统合主义”与地方政府掠夺型行为的大量出现,[16]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特征与工厂“失序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的存在。[17]前者催化着后者的恶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大旗下忽视工人职业健康保障,并纵容企业逃避保障工人权益的责任。卢晖临、张辉等学者就把中国严峻的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归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赶超型发展”等国家战略引导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18-19]聂辉华、蒋敏杰的研究也发现,政企合谋是导致煤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当煤矿的生产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正相关时,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之间的合谋必然会导致产权清晰的国有重点煤矿死亡率很高和安全投入不足,以及证照不全的中小煤矿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屡禁不止。”[20]
(三)社会抗争模式
20世纪以来,国外关于工人职业健康的研究更多从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的视角进行阐释。诸多研究认为社会运动与社会抗争是改善工人职业健康的重要推动力量。德里克森(Alan Derickson)的研究发现工团主义(trade-unionism)是推动19世纪英国政府开启矿业安全立法的重要因素,与之类似,富有战斗性的基层斗争与黑肺病运动对改善美国煤矿工人工作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21]史密斯(Barbara E. Smith)的研究认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科技创新带来的大量机械化应用彻底改变了煤矿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伤残工人的失业率剧增与矿主经营的日渐萧条导致黑肺病运动的爆发,进而推动了工人职业健康权益的保障。[22]罗森伯格等人(Beth Rosenberg et al.)的研究也总括性地指出公共健康运动是推动美国工人尘肺病得以控制的关键因素。[23]
华莱士的研究则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进一步阐释了社会运动与抗争产生的原因,认为社会运动即“弱势或被排斥群体(disadvantaged or excluded groups)如何通过利用组织化的资源(比如人、金钱等)获取政治、社会权利”。[24]工人手中掌握着控制劳动过程、反抗雇主剥削的两大重要资源:组织工会与罢工的权利。20世纪美国煤矿工人正是利用手中的制度性(工会)与非制度性(罢工)资源,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定量分析结果也表明工会与工人罢工显著地降低了1930-1982年美国煤矿的工伤率。[25]其中,工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美国矿工联合会(UMWA)为矿工更安全的工作条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第一,促使联邦与州政府出台更严格的法律管制工矿企业的安全标准;第二,促使矿主遵从与执行现有的安全生产标准;第三,联合会保证矿工有权抵制不安全生产条件且不用担心遭到矿主报复。[26]同样,德里克森的研究较早认识到矿工联合会在为工人争取权利与福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工人职业健康上升到了工会民主甚至政治民主的高度。[27]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工会在促进工人职业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①相关研究参见:KERR L E.Occupational health:A classic example of class conflict[J].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1990,11(1):39-48.CLARK P.The miner's fight for democracy:Arnold Miller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SELTZER C.Fire in the hole:Miners and managers in the American coal industry[M].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WYSONG J A,WILIAMS S R.The UMWA Health Care Program for miners:Culprit or victim?[J].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1984,5(1):83-103.而罢工则充当了工人最后的安全阀,也是与资本家抗争最有力的武器,不仅使得工人可以拒绝危险的劳动条件,而且还可以迫使企业与政府改善劳动条件。
总体来看,较之社会医学与政治经济面向的工人职业健康研究,抗争政治视野下工人职业健康研究实现了从“社会情境”“经济情境”向“政治情境”的扩展,将工人职业健康的影响因素扩展到国家、政府、议会、工会等政治要素,丰富、深化了对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解。
(四)赋权理论模式
农民工在数量上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28]因而农民工问题成为当今中国工人问题研究的重心。职业健康是工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劳动权益,因此与工人职业健康相关的问题大都可在劳动权益保障,尤其是农民工劳动权益这个更为宽泛的主题下加以考察。
国内存在诸多关注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分析范式上正从“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向“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过渡。[29]“生存-经济”叙事模式以农民工的生存道义为逻辑起点,从人道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下推演出政府承担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利的道义责任,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更为本质的农民工“权利”问题。②相关研究参见:黄平.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权利贫困与赋权理论成为重要的分析概念。诸多研究认为工人(农民工)权益受侵害主要是由他们自身的权利贫困所造成的,要保障该群体的职业健康权益就必须向他们赋权,即把平等的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赋予他们并使之具有维护自身应有权利的能力。③相关研究参见:王小章.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9(1):121-138.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J].社会学研究,2005(3):99-118.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王春光,单丽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陈映芳.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31-132.陈峰.罢工潮与工人集体权利的建构[J].二十一世纪,2011(4):18.洪朝辉.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J].江苏社会科学,2003(2):120.王雨林.对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4(9):1-7.操家齐.合力赋权:富士康后危机时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动力来源的一个解释框架[J].青年研究,2012(3):40-52.苏黛瑞就认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实质上是“争取公民权”(contesting citizenship)的问题,[30]陈映芳则更直白的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31]郑广怀的剥权理论进一步厘清了伤残农民工维权困境的根源与机制。该理论认为,在伤残农民工的维权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与国家对农民工赋权所相反的剥权(de-powerment)过程,即通过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以及弱化社会支持四种制度连接机制,逐步剥脱制度(法律)文本所赋予农民工的权利。[32]
在国内研究中,赋权理论对于工人职业健康保护与改善的解释似乎成为某种共识。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不断地通过政策、法规向工人赋权;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工人的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问题非常突出,伤残工人的维权困难重重。这表明国家赋权对保护工人职业健康的效果有待提高,也表明了权利贫困与赋权理论在工人职业健康解释上的乏力。
三、问题内核:劳动关系与工人职业健康
工人职业健康是劳动关系三方主体——国家、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博弈品,①国家、工人与资本的三方主体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政府、劳方与雇主劳动关系三方主体,它不仅仅是由代表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劳方的地方总工会、代表用人单位的企业代表组织(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商会等)三方协调主体,还应包括三方协调主体所代表的宽泛的主体与力量。为了能与更多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话,文中使用“国家、工人与资本”这个外延更为宽泛的表述。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在于对这三方主体关系即劳动关系状况的把握与剖析。毛丹、张洪认为,无论是阶级实体还是阶级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对工人阶级状况和性质的研究需要从工人、国家与资本三方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入手进行考察。[33]而通过上文对以往解释工人职业健康理论模式的梳理可以发现,以往研究最大的问题或不足便是未能建立涵盖分析国家、工人与资本三方劳动关系主体的系统框架。
首先,社会医学模式与经济环境模式更多关注的是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宏观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作为宏观背景要素对工人职业健康固然或多或少存在着影响,但经验事实表明,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不同国家的工人职业健康水平却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在解释工人职业健康问题时,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只能作为背景性要素加以考量,不能作为核心的解释变量,而应进一步关注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制度性关系以及内在机制与过程。
其次,既有研究未能建立涵盖国家、工人与资本三方力量的分析框架。赋权理论模式强调国家(政府)对工人职业健康的影响与作用,主要包括国家对工人的赋权与国家管制两种方式,突出国家在影响工人职业健康方面的自主性;社会抗争模式强调工人本身以及普通大众对工人职业健康的影响与作用,他们主要通过社会运动、罢工等抗争形式实现对工人职业健康保护的改善,突出工人自身的能动性作用。赋权理论模式呈现的是国家与工人之间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社会抗争模式虽然可以隐约看到国家、工人与资本三方主体的影子,但主要呈现工人与国家之间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两种理论模式都未能将三方主体全面涵盖。
最后,以往研究没有呈现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机制与过程。社会抗争模式强调社会运动、罢工等抗争活动对推动政府改善工人职业健康保障方面的推动作用,但社会抗争的动力及其抗争过程未能充分揭示。赋权理论模式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它强调国家自上而下赋权的重要性,但国家赋权的动力来源以及赋权后的运行机制是个黑箱。因此,不论是社会抗争模式还是赋权理论模式,都未能揭示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机制与过程,而这又是深入理解工人职业健康的关键和核心。
为了弥补以上三方面在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上的不足,这就要求构建一个分析工人职业健康的系统性框架。如图1所示,显示的是一个整合三方主体力量的三角分析框架。一方面,可将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劳动关系三方主体(国家、工人与资本)都整合到一个框架之内;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国家、工人与资本三方力量之间的双向互动博弈(A与a、B与b以及C与c),可以揭示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此外,建基于劳动关系之上的分析框架,还能影响工人职业健康的变量从外部因素向内部关系与制度变量推进。

图1 “国家—工人—资本”三方互动关系
显然,图1这个分析框架是建基于劳动关系之上的。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使用者和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与劳动相关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34]从劳动关系的定义来看,劳动关系涉及工人与资本,或者说劳动者与管理者两方主体。但是,由于在“管理者与劳动者两方博弈中,博弈双方的利益差别和效用函数不同而选择不合作战略和各种斗争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没有外在力量的强制下,劳动关系博弈的‘囚徒困境’现象难以避免。这就是说,和谐劳动关系很难在管理者与劳动者双向互动中最终实现。因此,必须加入政府一方参与劳动关系的博弈,发挥政府在劳动关系博弈中的特殊重要作用。”[35]李亚娟、杨云霞认为,“劳动关系的平衡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相互协调,否则绝对的市场化会导致三方利益冲突的激化,而政府行政权力的绝对干预会遏制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发挥,降低经济活力和效率。”[36]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石地位的合约关系,其正常运转离不开政府的恰当干预和支持。因而,学界通常所说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涉及国家、工人与资本三方主体。

图2 “国家—工人—资本”三方博弈图
如图2所示,工人职业健康是劳动关系三方主体国家、工人与资本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基本要素是局中人、策略与收益,局中人的收益取决于局中人的策略选择,而策略选择又受制于局中人所掌握资源的多寡。掌握资源越多的局中人,其策略选择的空间就越大,从而获得预期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国家、工人与资本作为工人职业健康博弈中的局中人,三者有着不同的策略选择与目标收益。在目标收益方面,工人的首要目标是保护自身的职业健康权益,维护自身的正当劳动权益;资本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资本的增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为了减少投入、缩减成本,资本家会试图违背国家制定的劳动生产标准,忽视给工人提供基本的劳动保护;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稳定则需要通过给工人提供基本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换取。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相斥或矛盾的,所以国家经常在这两个目标上左右徘徊。
劳动关系三方主体目标的实现需要它们各自掌握相应的资源。概括来看,这些资源包括政府的权力、工人的权利以及资本的发展能力。在工人的权利方面,工人职业健康与劳动权益的保护需要工人掌握选举权、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与罢工的权利。选举权是工人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力量,而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权与罢工的权利则是牵制资本的有效力量,两者共同保护着工人的职业健康;在资本的发展能力方面,资本增值的实现是因为资本掌握了经济增长、提供就业与交纳税赋等发展经济与福利的能力,这些能力是资本在劳动关系博弈中的重要筹码;在国家权力方面,国家掌握着合法使用暴力(强制力)、资源配置以及政策制定的权力,国家正是通过这些权力的使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大核心目标。
简言之,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在于对劳动关系三角结构的把握,工人职业健康研究不能脱离劳动关系三方主体所构成的三角结构关系。通过劳动关系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从整体的劳动关系状况判断工人职业健康保障的总体水平,还能通过对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之间的目标与资源的分析,切入三方主体之间两两互动博弈的机制与过程,从而更深入、系统地剖析和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
四、结语:迈向均衡劳动关系
工人职业健康作为一种零和博弈品,国家或资本力量的过强不利于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而工人力量过强则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其自身职业健康水平的提高。因此,基于保障工人基本劳动权益的理想劳动关系形态应是工人、资本与国家三者两两之间均能达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均衡状态。如图2,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劳工政策以及强制力影响工人权益(A),工人也可通过手中选票等力量影响国家决策(a);国家可以监管企业安全生产(b),资本在发展和纳税方面的功效影响着国家决策(B);资本给工人提供了生存机会并可在劳动过程中对工人加以规制(C),工人也可通过集体谈判等手段牵制企业生产与资本增值(c),如此达成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现有研究也已表明,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失或弱小,容易形成其他两方联合压制一方的局面,从而破坏稳定的三角关系结构,导致劳动关系的失衡。①相关研究参见:毛丹,张洪.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J].社会,2017(1):97.赖特.阶级[M].刘磊,吕梁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李锦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J].社会,2013(3):204-241.
因此,均衡劳动关系可以成为判断工人职业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有相关研究论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华莱士关于矿难的研究指出,均衡的劳动关系是促使国家加强管制,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关键性要素。[37]均衡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类型之一,程延园按照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对比等因素,将劳动关系划分为均衡型(相互制约)、倾斜型(资方主导)和政府主导型。[38]巴德提出的“劳动关系平衡论”认为,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应寻求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个雇佣关系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既注重效率带来的经济繁荣,也应重视尊重人的尊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39]换言之,均衡劳动关系对于工人职业健康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均衡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各国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所追求的目标。然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始终处在不均衡状态之中,“弱劳工”现象非常普遍。蔡禾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尽管我们国家的各种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总体上看,在政府、资本、劳工三者关系上,是一个强国家、强资本、弱劳工的状态,而农民工更是处在弱中之弱。这种弱不仅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弱,也是在利益受损时,体制内利益诉求能力的弱。”[40]刘林平也指出,“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格局非常稳固,在这种格局下,工人较少渠道维护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劳资关系处于极度的不平衡中。[41]而经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资强劳弱的不均衡劳动关系中,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逃避劳动保护职责的伎俩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的“赶超型发展”与“碎片化权威”的政治经济模式下容易监管失职,从而导致我国工人职业健康状况堪忧。这也是我国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数量惊人,工人职业健康维权困难重重等问题的根源所在。
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高度重视和支持,[42]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为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整体部署。[43]而均衡劳动关系正是迈向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董保华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造成了对劳资关系调节的矫枉过正,企业与劳动者只有互利才能共赢,建议修法时回到《劳动法》的平衡点,使劳动关系调整更平衡。[44]那么,我国如何才能达成均衡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三方主体的行为并非在真空中发生,受到现在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尤其关涉工人、资本与国家之间博弈的初始制度或资源是更为本质的因素。如上所述,工人所掌握的选举权、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等是工人与资本进行博弈、抗衡的力量之源。因此,要改变“弱劳工”的劳动关系,迈向均衡劳动关系,充实或完善工人的权利成为必由之路。陈峰指出,“制度化的工人集体权利(工业公民权)是国家、劳工和资本关系平衡和稳定的基础。”[45]郭于华认为,“要改变极不均衡的劳资关系,必须向工人赋权,包括‘劳工三权’的逐步合法化与真正落实,即工人享有团结权、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如此才能有可能建立起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使工人有能力参与工资共决、集体谈判等保护自身权益的过程。”[46]常凯的研究指出,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能使劳动关系双方的力量获得相对平衡,因此我国劳动关系转型的方向是完善集体劳动权利,实现劳动关系由个别向集体的转型。目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尚处于零散残缺的状态中,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立法核心理念应是确认和保障“劳动三权”,这是劳动者在劳动法中最重要的基本权利。[47]因此,结合以上研究可以认为,集体劳动权利的保障与确立是达成均衡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与转型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