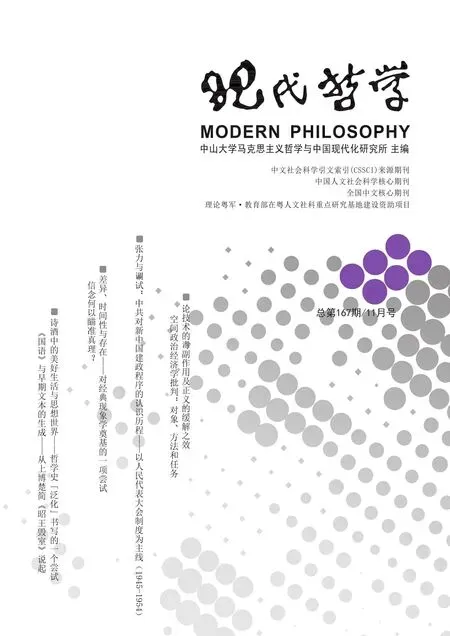胜军比量与《增一阿含》
孙劲松
胜军生为西印度苏剌佗国人,著名的佛教居士。主要生活时代是公元七世纪,曾从贤爱、安慧等人学习因明、声明及大小乘论,后追随戒贤深研《瑜伽师地论》,博学广闻、名重一时。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胜军“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惟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年百岁矣,志业不衰”(1)[唐]玄奘撰、[唐]辩机编次、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他在七十岁至百余岁的三十年中,常年在杖林山集徒讲学,从学僧俗常达数百人。玄奘西游时,曾在其门下二年,学习《唯识决择论》《瑜伽师地论》以及因明等方面之义理。
一、玄奘对胜军比量的批评与修订
玄奘翻译了商羯罗主所造之《因明入正理论》,窥基对其进行注释,成《因明入正理论疏》一书,世称《因明大疏》。据该书记载,胜军通过四十余年的深思熟虑,立一比量:“诸大乘经皆佛说(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2)[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高楠顺次郎等编校:《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21页。在当时“时久流行,无敢征诘”(3)同上,第121页。。
这是典型的共比量三支量式,一般来说,“宗”由前陈、后陈(又称“宗依”)组成;前陈与后陈需要立论者、敌对者共许,但由此二者所成的宗体则必须是立论者认可,敌对者不认可。此比量的核心论点(宗)“诸大乘经皆佛说”“诸大乘经”作为宗的“前陈”是大小乘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佛说”作为“后陈”所表达的佛陀曾经有所说法,也是一个大小乘人都承认的事实。但是前陈、后陈之间加了一个“皆”,变成“诸大乘经皆佛说”,就明显成了大乘人认可、某些小乘宗派不认可的一个论点。
其“因”支用了“两俱”“极成”四个字。所谓“两俱”,就是论辩的敌我双方都承认的前提条件;“极成”指至极的成就。“两俱极成”就是敌我双方都认可的、丝毫不容置疑的“前提”。因明作为论辩逻辑,立正破邪、战胜对手是其目的。所以,因明家特别强调论辩前提的“两俱极成”。而此论题两俱的对象是“非佛语所不摄故”,意指不仅小乘佛教教理超越所有外道理论,大乘佛教也超越各种外道的理论,只有佛陀才能说出大乘佛教教理。其“喻”支则举了《增一阿含经》作为例证(阿笈摩即“阿含”)。
玄奘到杖林山向胜军求学期间,认为胜军比量的“因支”犯了“两俱不成”“随一不成”“自不定”等过失。玄奘法师主要用小乘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以及该派别的代表作《阿毗达磨发智论》对胜军的因支展开辩难。根据窥基《大疏》记载,玄奘展开质疑的角度如下:
1.胜军比量犯有一分两俱不成过。“且《发智论》萨婆多师自许佛说,亦余小乘及大乘者,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岂汝大乘许佛说耶?”(4)[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卷,第121页。玄奘指出,当时非常流行的小乘佛教流派萨婆多部自认为《发智论》的观点是佛陀所说,但是大乘佛教和其它小乘派别都不许可这个说法。此时,大乘佛教与小乘萨婆多部在《发智论》是否“非佛语所不摄”的问题上已经存在分歧,这对大小乘“两俱极成”说形成一个挑战。玄奘进一步指出:“若以《发智》亦入宗中,违自教,‘因’犯一分两俱不成。‘因’不在彼《发智》宗故。”(5)同上,第121页。“两俱不成”是“因十四过”之“四不成过”的第一过。指“因”不周遍于“宗”的“前陈”,而成为立论者、与问难者共不许之量。据《因明入正理论疏》记载,“两俱不成过”又以“因”体与“宗”关系之程度而分为“全分”与“一分”。熊十力在《因明大疏删注》中指出:“此极成非佛语所不摄之因,既对《发智论》无简别,汝若立‘《大乘经》《发智论》者俱是佛说’以为宗者,此‘因’对小乘之许《发智》是佛说者而言,大乘但有违自教失,以大乘本不许《发智》是佛说。今成此宗,故违自教,若对小乘之不许《发智》是佛说者而言,此因即犯一分两俱不成过,立敌共许此因,于宗中一分《大乘经》上有、一分《发智论》上无,故言一分两俱不成也。”(6)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1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在胜军比量中,论辩的“问难方”若包含信奉《阿毗达磨发智论》萨婆多部,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大乘佛教也不承认《发智论》是佛说;但大乘与小乘的矛盾也不是全面性的,大乘佛教承认《四阿含》是佛说,小乘的某些派别也不完全否认大乘,所以说此命题可能导致一部分的“两俱不成”,在因明学中称为“一分两俱不成”。
2.胜军比量犯随一不成过。玄奘认为:“又谁许大乘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是诸小乘及诸外道,两俱极成非佛语所摄,唯大乘者许非彼摄。因犯‘随一’。”(7)[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卷,第121页。玄奘指出,小乘和外道都认为大乘佛教不是“佛语”所能包含,除大乘佛教自身外,没有哪个派别“两俱、共许”大乘是佛说。所以,这一比量的“因”支犯有“随一不成”的过失。“随一不成”也是“因十四过”之“四不成过”的一种。指立论者与问难者的某一方以对方不承认之因(理由)来立“量”时所造成之过失。此一过误复分为两种情形:若立论者自身认可其因,而他方不予承认,称为“他随一不成过”;若立论者自身不认可其因,而他方予以承认,则称“自随一不成过”。此二过皆可因冠上简别语而免除之,如“他随一不成过”用“自许”之简别语以作自比量,“自随一不成过”用“汝许”之简别语以作他比量,即不犯此过。玄奘认为,胜军比量的“因支”所犯的是“随一不成过”中的“他随一不成过”,需要将此比量由“共比量”修订为“自比量”,将“两俱极成”修改为“自许极成”来避免过失。
3.胜军比量犯有自不定过。玄奘认为:“因不在彼《发智》宗故,不以为宗,故有不定。小乘为不定言,为如自许《发智》,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汝大乘教非佛语耶?为如《增一》等,两俱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汝大乘教并佛语耶?若立宗为如《发智》,‘极成非佛语所不摄’,萨婆多等便违自宗,自许是佛语故,故为不定言。为如自许《发智》‘极成非佛语所不摄’,彼大乘非佛语耶?以不定中亦有自、他及两俱过,今与大乘为自不定故。”(8)[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卷,第121页。“不定过”是在因明论式中,具有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9)商羯罗主造、[唐]玄奘译:《因明入正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第11页。中之第一相,而缺后二相,所立之宗义不定所生之过失。
所谓“同品定有性”是表明因与宗后陈之关系。凡与“宗依”的后陈同类的,都称为同品。所谓“定有性”是说宗的同品中必定具有因的性质,但并不需要同品都具有该性质,只要有些具有该性质即可。所以,只说“定有”,而不说“遍有”。胜军比量的“后陈”是“佛说”,而“因”中“两俱”二字含摄有“小乘萨婆多部”,但大乘及小乘其他宗派认为其并非“佛说”;同理,“小乘萨婆多部”也不同意“因”中“两俱”二字含摄的“大乘”是“佛说”,这样就不能具足“同品定有性”,就形成“不定”的过失。
“异品遍无性”指“宗”的异品须普遍没有因的性质。所谓“异品”,亦即某物只要不具有“宗”的“前陈”所表述的性质,即可用来作为异品。异品分宗异品与因异品两种,凡与“宗”的“前陈”相异的,叫做宗异品;凡与“因”相异的,叫因异品。由于“宗”的“前陈”的外延比因法大,所以凡与“宗前陈”相异的宗异品,也都是与因相异的因异品。所谓“遍无性”,是说所有的宗异品都与“因法”不发生关系,因为凡宗的异品应该都是因的异品。由于此异品遍无性是用来从反面制止因法之滥用,所以要求宗的异品必须全部不具有因法的性质;如果不是全部宗异品同时都是因异品,那就不能制止因法的滥用。在胜军比量中,“大乘”作为“宗”的“前陈”,其异品可以说是“小乘各派别”,但是大乘佛教以及其他小乘教派认为“萨婆多部”理论与外道的“非佛语”相类,不在“非佛语所不摄”的范畴;反之,萨婆多部也认为大乘不在“非佛语所不摄”的范围内。所以,胜军比量也违反了“异品遍无性”,玄奘认为其犯了“自不定”小乘各派别的过失。
根据窥基《因明大疏》记载:“由此大师玄奘正彼胜军因云:自许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简彼《发智》等非自许故,便无兹失。”(10)[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卷,第121页。将胜军比量的“两俱”改为“自许”,将“萨婆多部”等小乘宗派排除在外,以避免过失。玄奘修订后的比量如下:“诸大乘经皆佛说(宗);自许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11)同上,第121页。
二、玄奘法师没有注意到“喻支”是胜军立论的关键
因明作为印度佛学以及各宗派、教派共同遵守的论辩逻辑,依立、敌双方对所使用概念或判断是否共许,其论式可以分成三种比量:自比量、他比量和共比量。一个没有过失的共比量,必须是立、敌双方共许;除宗体是立敌对诤的标的外,所使用的概念和因支、喻体都要得到双方承认;既是真能立,又是真能破,功用最大。他比量限于破敌之论点,不申扬自宗。自比量只申扬自宗,限于诠释自己的理论,无力破他。玄奘在运用“简别”的方法,对胜军经过四十多年深思熟虑而立的一个比量却有过失加以辩难,将其共比量改为自比量。但玄奘的辩难过程没有对“喻支”加以论述,笔者认为这个喻支恰恰是胜军比量的关键。
窥基在书中引用《摄大乘论》所立的另外一个比量云:“诸大乘经皆是佛说(宗),一切皆不违补特伽罗无我理故(因),如《增一》等(喻)。”(12)同上,第121页。。其喻支所用的是《增一阿含》等经,胜军比量也是用《增一阿含》为喻支。那么,《增一阿含经》到底是一部什么经?里面有什么内容能支撑大乘是佛说的观点?这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增一阿含经》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四部阿含之一。这部经典明确记载了佛教有“三乘”,信徒有声闻部、缘觉部(辟支部)、佛部(菩萨部)等三部大众,大乘法中的“六度”“菩萨”等词语也频繁出现,还记载有大乘佛教中广泛出现的弥勒、文殊等事迹。
①如是《阿含增一》法,三乘教化无差别;佛经微妙极甚深,能除结使如流河。(13)[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第550页。
②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持此誓愿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复持此八关斋法,用学佛道、辟支佛道、阿罗汉道。(14)[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3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第757页。
③今此众中有四向、四得,及声闻乘、辟支佛乘、佛乘。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当从众中求之。所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众。(15)[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4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第792页。
材料①已经出现“三乘”一词。材料③明确指出佛教不仅是声闻、缘觉二乘,还包括阿罗汉道(声闻乘)、辟支佛道(缘觉乘)、佛道(佛乘、大乘),共计“三乘”。
《增一阿含经》还有大量关于菩萨、六度的记载。如,
④如来在世间,应行五事。云何为五?一者当转法轮,二者当与父说法,三者当与母说法,四者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五者当授菩萨别。(16)[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第622页。
⑤若菩萨摩诃萨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17)[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第645页。
材料④指出,佛在人间示现应该要做这五件事情,要建立菩萨行,让佛弟子们遵循而修,并为诸菩萨受“记别”,即受记何时成佛。材料⑤记载了佛与弥勒菩萨的对话,这里出现大乘“六度”的概念,并提出大乘佛教修行的目标是“无上正真等正觉”。《增一阿含经》卷44,还有与大乘佛经相同的授记弥勒将来娑婆世界成佛的文字。可见,《增一阿含》作为小乘佛教尊奉的佛陀所说之根本经典,确实可以看到大乘佛教的只鳞片爪。这也正是胜军等人反复引用《增一阿含》与小乘人论证大乘是佛说的关键原因。
现代学者对《增一阿含》的产生年代以及是否为佛说提出质疑。此质疑若成立,将对胜军比量形成致命伤。一些学者提出大乘佛教是佛灭度后数百年间,为大乘佛教徒编创,并以此为根据,将《增一阿含》所涉及的大乘部分也列入后世“编造”的范围。台湾的印顺法师说:“四部、四阿含的成立,是再结集的时代,部派还没有分化的时代。”(18)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他认为佛灭度后,第一次五百结集中只完成“杂藏”,而《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都是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的第二次七百结集时才完成,这为伪造、掺假提供了可能。但是,即便是印顺信奉的《杂藏》也指出四阿含在第一次结集中全部完成了。《杂藏》的《佛般泥洹经》卷二指出,佛陀涅磐后不久,“大迦叶贤圣众,选罗汉得四十人,从阿难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19)[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卷,第175页。。这说明四阿含都是在第一次结集完成的,并且都形成文字,记载在“疋素”之上。由此可知,印顺等人的考证并不准确。另外,龙树《大智度论》云:“佛灭度后,文殊尸利、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集是摩诃衍(大乘)。又阿难知筹量众生志业大小,是故不于声闻人中说摩诃衍,说则错乱,无所成办。”(20)龙树撰、[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卷,第756页。根据传统说法,不仅四阿含为第一次结集形成,大乘经典的主要部分也应在佛陀灭度后不久,由大乘弟子另外结集而成。可见,胜军比量的关键,不在因支,而在“喻支”。在胜军生活的时代,各佛教教派都共许《增一阿含》是佛说,所以,胜军比量以此为“喻支”并没有问题。
三、胜军因支“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并无重要过失
1.大乘经“非佛语所不摄”并无过失
“非佛语”与“佛语”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概言之,佛所语者是出世间法,而非佛语者都可以归属于有生有灭的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有情世间,也称众生世间,指由五蕴假合而心识的一切有情生命,包括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界的众生;其二是器世间,也称国土世间,指由地、水、火、风四大积聚而成的山河、大地、国土、家屋等,是一切众生所居住的地方与空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其三是五阴世间,又名五蕴世间,即色、受、想、行、识之五阴,包含有情世间与器世间之全体。无论是有情世间、器世间还是五阴世间,都是迁流变化的现象世界,一切众生皆有生壮老死,一切物质世界都有成住坏空,“五阴”定有聚散离合。佛教之前的各类宗教体验,都不出六道轮回;一切世间的哲学、玄想、教义,都不出“世间”。
佛陀因众生根器之不同,从浅至深施设三乘法教,都是出世间法。其先说声闻法之八苦、四谛、四念处观、八正道,后根据时节再说缘觉乘之十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小乘僧众依靠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理论来思维与观行,明白缘起性空、缘起无我之理,明白缘起之法必归于灭,其性必空,故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性空,由是体悟缘起性空之理,断除我执、烦恼,不再受业力与无明牵制,达到证得阿罗汉四果、辟支佛果,断我见与我执,舍寿而灭尽十八界法,由此而出离三界、“世间”,证小乘解脱之无余涅槃。然而,无余涅槃之本际为何?阿罗汉并不知晓。此无余涅槃若是绝对的“无”,就是“断灭”论者,成了断见外道;若是一个具体的“有”,必然落于三界的“世间法”,成为常见外道。所以,《阿含》中佛陀多处说明无余涅槃内有本际,《四阿含》常用“实际、我、如”甚至“阿赖耶”等代指真心本际。但此说都是略说,并非详细解说,恐小乘众生“执此为我”,反生羁绊。阿罗汉虽无实证无余涅盘之本际真心,然依佛圣教量的开示,确知“无余涅盘”非断灭后,故可于内无恐怖、于外无恐怖而安住于其修证的境界。可见,小乘声闻、缘觉之法以大乘法为根本而方便宣说,若离大乘法所宗的“真心实际”,小乘涅槃将无异于“断灭见”。
真心的亲证是在佛陀宣讲般若、唯识系大乘经典时才详细解说。小乘声闻人虽于结集前亦曾参与二三转法轮般若唯识诸会,因无实证,不得现观验证诸佛所说法要,唯能记忆一些名相,此亦是大乘经典中所说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21)[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卷,第218页。。此“本际、真心、阿赖耶”是“真际之有”,此“有”与“世间万法之有”不在一个层面,而是作为所有世间万有之体的“有”。近代学者见大乘佛教描述“真心体性”有“常乐我净”之语,便说大乘佛教等同于印度外道“梵我”,可谓荒谬之极,此“我”非彼“我”,岂可混淆一谈。“真心”“阿赖耶识”是三界万法之所依,出世间与世间法不二,一切众生本来常住涅槃, “心”与“三界万法”如水与波之关系,三界万法如梦幻泡影、生灭不息,但是其所依之“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只要契悟此心就可证知轮回只是表面现象,真心本不生灭、本来不入轮回。体证这个自性清净之常住真心以后,还需要高杆进尺。如《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云:“有二法难可了知,谓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唯信佛语。”(22)[唐]玄奘译:《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卷,第222页。证悟自心自性清净只是“见道”,而自性清净之心为烦恼所染,证悟自心之后仍需要反复体证五蕴十八界的空相(这是小乘修行的核心内容),生生世世广修六度万行,断尽烦恼障习气种子随眠,以及所知障无量随眠,圆满具足一切种智的智慧功德,方能成就究竟佛道。可见,大乘佛法含摄小乘佛法,两者都以“本心真我”作为理论基础,都超越所有描述世间法的“非佛语”。
2.“两俱极成”可以成立
《增一阿含》等小乘经典有明确的三乘、菩萨、六度等大乘名相的出现。胜军运用“《增一》等阿笈摩”作为“喻支”,与小乘人辩说“大乘是佛说”。小乘教徒看到《阿含》确实记载有“声闻、缘觉、佛乘”的三乘概念,虽然他们只能理解声闻、缘觉的教义,但不会贸然否定大乘教义。而大乘佛教徒也承认声闻、缘觉乘的经典是佛陀因机教化众生所说。所以,大小乘根据《增一阿含》等经典的记载,共许大小乘“非佛语所不摄”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可以推出“大乘是佛说”的概念。
萨婆多部又称“说一切有部”,约于佛灭后三百年出现,此派以迦湿弥罗国为中心,于健驮罗、中西印度及西域等地,曾盛极一时,玄奘西行印度期间,此派实力相当大。创始者为迦多衍尼子,著有《阿毗达磨发智论》,其主要教说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三世实有”指过去、未来与现在相同,皆有实体。“法体恒有”指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五位(细分七十五法)均有实体。这一主张明显误解了佛陀在《阿含经》中灭尽十八界方入无余涅槃的教导,若“涅槃”与世间生灭法都是“实有”,则其“涅槃”必然不能脱离“三界”,是“假涅槃”,不能摄属于佛陀所言之“出世间法”。萨婆多部认为佛教唯以八正道为正法轮之体,认为佛之说法中有无记语,将不利于自己的体系的佛陀言教说成“无记语”,而且说佛陀化缘尽时永入寂灭,将佛陀等同于其错解的阿罗汉乃至断灭论外道。玄奘作为通晓三藏的杰出法师,当然知道《发智论》的观点误解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教义,在辩难胜军的论述中,明确指出大乘不承认《发智》的观点是佛说。由此,我们可以为胜军比量提出两点辩护:
其一,从理上说,萨婆多部没有真正宣扬佛陀的“出世间法”,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小乘佛教团体”,自然不在“两俱极成”的含摄范围内。“佛教团体”的界定若没有严格的标准,都由自己说了算,那么玄奘改成“自许极成”也会出问题。后世许多附佛外道及邪教都自称是真正的“大乘佛法”,若把他们都算成“大乘佛教”,那么“自许极成”就将纳入这些附佛外道的理论,同样会落入玄奘责难的“两俱不成”“随一不成”“自不定”等过失。所以,玄奘用自己都认为是“非佛说”的教派作为佛教派别来辩难胜军,有些牵强。
其二,即便承认“萨婆多部”是佛教团体,但“萨婆多部”也承认《增一阿含》的地位。玄奘在《成唯识论》卷三指出,“说一切有部《增一经》中,亦密意说此名阿赖耶,谓爱阿赖耶、乐阿赖耶、欣阿赖耶、喜阿赖耶”(23)护法等撰、[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1卷,第12页。,还专门引用说一切有部所流传的《增一阿含》,并且说此经有大乘经典的“阿赖耶”等名相。无著所撰《摄大乘论》也认为“声闻乘中亦以异门密意,已说阿赖耶识。如彼《增一阿笈摩》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欣阿赖耶、喜阿赖耶”(24)无著撰、[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1卷,第134页。。胜军比量所引用的例证是《增一阿含经》,“经”的地位当然高于迦多衍尼子所造的《发智论》,即便其以《发智论》来辩难,也可以用《增一阿含》的论述让其落到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可能才是胜军比量“时久流行,无敢征诘”的关键原因。
《增一阿含》可以作为可信的小乘佛教经典,虽然在传译过程中有不同版本,但都记载了小乘人听闻大乘法时纪录的大乘名相,只是由于小乘人不能深刻领会大乘佛法,不能详细记忆、背诵、记录;但其中的大乘名相已经充分说明佛陀确实演说过大乘法。真正具信或实证声闻解脱果的小乘信徒,可以据《增一阿含经》接受“大乘经是佛说”的观点。从大乘经典看,大乘佛法含摄小乘佛法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小乘佛法深广,真正的小乘圣者阅读大乘经典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思想不是仅仅描述世间法的“非佛语”所能包含的,真正的大小乘信徒在此问题上可以“两俱极成”,胜军比量是可以成立的。另一方面,萨婆多部在当时信徒众多,大家都认为其为“佛教”,而且其教理并非一无是处,其“五位七十五法”之说,经无著大师等修正为“五位百法”,对唯识理论的细化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从当时印度佛教弘传的事实情况看,玄奘以萨婆多部为假想敌,对胜军比量进行修订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