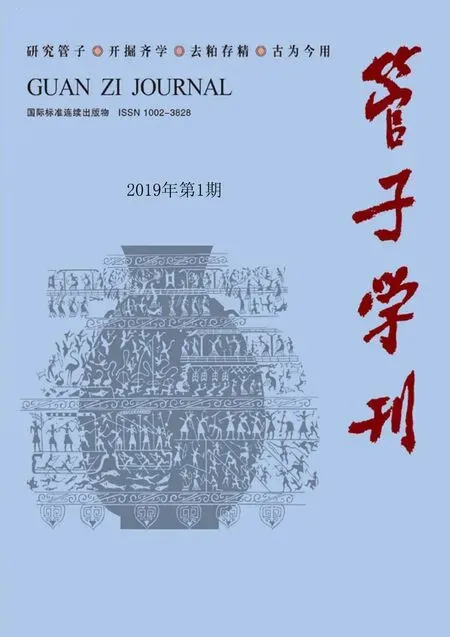上博竹书《景公疟》再探
袁 青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据科学测定,上博竹书的年代距今时间为2257±65年[1]3,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与郭店竹书的年代大致相当。上博竹书《景公疟》与传世本《晏子春秋》相关篇章大同小异,这又是《晏子春秋》早出的一个有力证据。《景公疟》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曾著文对其作了初步的研究[2],此文我们拟在拙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景公疟》与传世本《晏子春秋》的关系、《景公疟》的思想特色及其所反映的战国齐楚关系等方面对其进行探究。
一、《景公疟》与传世本《晏子春秋》的关系
上博竹书《景公疟》与传世本《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七·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第七》(以下简称《景公有疾》)、《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第十二》(以下简称《景公病》)类似,同时也杂糅了传世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以下简称《景公信用谗佞》)相关内容[3]。上博竹书《景公疟》的面世,使我们可以通过将其与传世本《景公有疾》《景公病》《景公信用谗佞》等作对比,以更深刻地认识《晏子春秋》文本的形成。
关于《景公疟》与《景公有疾》《景公病》的比较,梁静已经有所论述[4],笔者试在此基础上加以申说。据梁静的统计,《景公病》有370字,《景公有疾》557字,而简本《景公疟》现存484字,其中重文一,合文二。根据竹简形制可以推测出,此篇残缺240字,则全文共有大概724字。《景公疟》的字数将近是《景公病》与《景公有疾》章的总和[5]。不过梁静并没有算上《景公信用谗佞》章,其实将《景公有疾》《景公病》与《景公疟》相对照,可以发现《景公疟》文句更接近于《景公有疾》,而《景公疟》第6简和11简显然出于《景公信用谗佞》,所以比较《景公疟》与《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谗佞》的字数,更能说明问题,据笔者统计,今本《景公信用谗佞》229字[注]据《四部丛刊》景印明活字本统计。,这样与《景公有疾》557字相加,更接近于《景公疟》的字数。由此似乎可以推断,《景公有疾》与《景公信用谗佞》当是将《景公疟》一分为二而成的。
由于《景公疟》主题思想与《景公有疾》《景公病》是一致的,都是景公想杀祝、史来治愈疾病,晏子加以劝谏,最后景公打消了这个念头。故而我们先来比较三者之间的差别:
其二,《景公疟》记载了高子、国子劝谏景公杀祝、史的故事,这是《景公病》与《景公有疾》章所没有的。
其三,《景公病》中晏子的劝谏更为直接,没有拐弯抹角,通过揭露出“祝为有益”这个命题的荒谬性来讲明杀祝、史无助于治愈景公之病的道理;而在《景公疟》与《景公有疾》,晏子详细论述政治与祝、史的关系,指出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影响祝、史的命运,而祝、史则影响不了政治,劝谏景公要想病痊愈,就要“修德”或“明德”,《景公有疾》说:“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景公疟》第9简说:“明德观行。”这是《景公病》所没有的内容。
其四,《景公疟》和《景公病》都记载在听了晏子的劝谏后,景公罢免了梁丘据等人的官职,然后景公之病得以痊愈;而《景公有疾》则是景公采取了“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等措施后,景公之病才痊愈。并且《景公病》在景公病愈之后,还有景公欲赐晏子以封邑,晏子辞的故事,而这是《景公疟》与《景公有疾》所没有的。
其五,《景公疟》和《景公有疾》天人感应的色彩很浓厚,《景公疟》载“旬又五,公乃出见折”,《景公有疾》则记载景公采取了一些政治措施后,“公疾愈”,《昭公二十年》虽与《景公有疾》章基本相同,但惟独没有这三字。《景公病》的记载是“改月而君病悛”。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景公疟》和《景公有疾》都有景公一采取措施就马上痊愈的意味,而《景公病》像是客观记载景公痊愈的情形。
其六,《景公疟》糅合了今本《景公信用谗佞》的内容,因而文意相对《景公病》和《景公有疾》而言更具复杂性。
我们再来看看《景公疟》与《景公信用谗佞》之间的关系。《景公信用谗佞》主要讲景公信用谗佞,导致赏罚不公,晏子加以劝谏,粗看起来,这似乎与《景公疟》《景公有疾》《景公病》三者之间的主题[注]主要都是记载晏子劝谏景公不要试图靠杀祝史二人来取悦鬼神,说明“诅为无伤,祝亦无益”。不一致,但《景公信用谗佞》的内容可以作为晏子在劝谏景公时的论据,说明景公平时行为不端,用来说明景公得病的原因不在于祭祀的物品不够丰富,而在于自身行为不合正道,由此引出“诅为无伤,祝亦无益”的命题。
刘向《晏子叙录》说:“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景公疟》杂糅了传世本《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谗佞》等章的内容,这或许是后人将其分开以合《汉志》之数。当然,由于《景公有疾》与《景公信用谗佞》内容相差较大,而且《景公有疾》在《外篇》第七章,而《景公信用谗佞》在《内篇谏上》第十二章,两者并非相互临近的两章,这与银雀山汉简是不同的,所以最可能是刘向校书时所分。《景公疟》杂糅了《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谗佞》等章的内容,这一事实或许意味着《景公疟》可能是刘向校书时所删去的“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之一。不过由于材料太少,我们对于《景公疟》与《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谗佞》等章的关系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二、《景公疟》的思想特色
关于《景公疟》的思想特色,笔者曾著文指出《景公疟》等文献否定祭祀可以求福,是战国时期一种重人事、轻神事思想倾向的具体体现[2]。但当时对《景公疟》的思想特色认识不够,还必须得进一步做出说明。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各地难免会遇到新挑战和“硬骨头”。虽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较大,但后者更需直面困难,迎难而上,不能找理由推诿敷衍。地区差距不是“喘口气”“歇歇脚”的借口,恰恰是奋起直追的动力。乡村振兴要克服“懒政”思维,与其心动,不如行动。
《景公疟》否定祭祀可以求福而认为求福的关键在于行德政,这种思想与孔孟荀等儒家有相通之处。帛书《要篇》载孔子之言:“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一五上】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6]243孔子认为君子要靠德行来求福、仁义来求吉,而非祭祀、卜筮等手段。孟子更是提出“祸福自求”的观点,他说:“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自求多福”的观点完全否定了通过祭祀、卜筮等手段来求福。而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更是直接否定了天(鬼神)有意志,故而更不可能通过祭祀、卜筮等来向天求福了。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景公疟》等篇虽然是重人事,但也没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认为靠祭祀是不能取悦鬼神的,但人事做好了自然能够符合鬼神之意,如果人事做不好的话也会招到鬼神的制裁。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谏第六》载:
齐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谏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益〉……”
在此,晏子提出“天道不谄,不贰其命”的命题,“天道不谄”即“天道不疑”“天道不谄,不贰其命”,也就是说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不会因为人事活动而改变。这颇有荀子“天人相分”的意味,然而《晏子春秋》并没有将像荀子那样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底。《荀子·天论》提出“天行有常”的命题,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分,天人不相干,所以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完全否定了天对人事的干预。《晏子春秋》虽然否定人通过祭祀等手段求福等,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天对人事的作用,《晏子春秋》认为人事如果做得不好,天是会有所反应的。《景公疟》简9说:“明惪观行。勿(物)而未(祟)者也,非为媺玉肴牲也。”物指鬼神,鬼神作祟不是为了美玉肴牲,那是为了什么呢?前一句是“明惪观行”,虽然有阙文,但我们可以推测出,鬼神作祟是为了敦促君主“明惪”。《景公疟》第12简说:“祭正(贞)不获祟,以至于此,神见吾迳〈淫〉暴。”“以至于此”指的是景公之病不见好,这也就是说神看到景公的淫暴,才导致景公之病不见好。《景公欲求福》在描述景公一系列暴政之后,也说:“是以民神俱怨。”这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如果人事做得不好的话,天(鬼神)会惩罚君主。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与后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相较起来,也有所不同,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醒,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夹杂着“灾害”“怪异”等“谴告”之说,具有鲜明的阴阳家色彩,而《晏子春秋》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相对朴素得多。
由此,我们可知,《景公疟》等篇章在思想上虽然否定通过祭祀等就可以求福的观点,认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天也会惩罚君主,具有一种较为朴素的天人感应色彩。
三、从《景公疟》看战国齐楚文化的关系
众所周知,《景公疟》是用楚文字抄写而成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其具体出土地点,但它出土于楚国却是无疑的。楚竹书《景公疟》的面世,显示出战国时期《晏子春秋》的相关篇章已在楚国广为流传。不仅如此,上博竹书(四)中有一篇《柬大王泊旱》,主要记载了楚柬(简)王的两件轶事,其中一件就是楚简王因天气干旱而患病,与《景公疟》记载齐景公“疥且疟”类似,其文曰:
简大王泊旱,命龜尹罗贞于大夏,王自临卜。王向日而立,王汗至【1】带。龜尹知王之庶(炙)于日而病,盖仪愈夭。釐尹知王之病,乘龜尹速卜【2】高山深溪。王以问釐尹高:“不穀骚,甚病,骤梦高山深溪。吾所得【8】地于莒中者,无有名山名溪欲祭于楚邦者乎?尚言必而卜之于【3】大夏。如,將祭之。”釐尹许诺。言必而卜之,。釐尹致命于君王:“既言必【4】而卜之,。”王曰:“如,速祭之。吾骚,一病。”釐尹对曰:“楚邦有常古【5】,安敢杀祭?以君王之身杀祭未尝有。”
王入,以告安君与陵尹子高:“向为【7】私偏,人将笑。”君陵尹、釐尹皆辞其言以告太宰:“君圣人且良伥子,将正【19】于君。”太宰谓陵尹:“君入而语仆之言于君王:君王之骚从今日以瘥。”陵尹与【20】釐尹:“有故乎?愿闻之。”太宰言:“君王元君,不以其身变釐尹之常古;釐尹【21】为楚邦之鬼神主,不敢以君王之身变乱鬼神之常古。夫上帝鬼神高明【6】甚,将必知之。君王之病将从今日以已。”[7]192-197
楚柬(简)王患病之后命令釐尹速祭,釐尹不肯,太宰告诉不“速祭”符合礼制,上帝鬼神会保佑,君王之病自然会好。《柬大王泊旱》这则故事与《景公疟》情节很相似,只不过将故事中的主人公由“齐景公”换成“楚柬(简)王”,“晏子”换成“太宰”,两则故事中齐景公与楚柬(简)王都相信祭祀可以医治自己的病。只不过在《景公疟》中晏子认为只要为政之措施得民,自然就能符合鬼神之意,景公之病也就会好;而在《柬大王泊旱》中太宰认为坚持祭祀的礼制,不因君王之故而有所减省就能得到鬼神的庇护,简王之病也会痊愈。《柬大王泊旱》作为楚人的作品[7]203-207,与成于齐人之手的《景公疟》故事情节之间的相似,以及《景公疟》在楚地的流传,这一事实启发我们思考战国时期齐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除《景公疟》与《柬大王泊旱》之外,齐楚之间还存在许多内容相似的文献或故事。上博竹书(四)中还有一篇《昭王毁室》,主要记述楚昭王新宫建成后与大夫饮酒,有一位身穿丧服的人进入宫内,告知楚王他的父亲就埋葬在新宫的阶下,现在宫室建成他就无法祭祀父母了,昭王闻此而毁室[8]181-186。这则故事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谏而许第二十》《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七景公台成盆成适愿合葬其母晏子谏而许第十一》情节十分相似,后二者主要记载逢于何或盆成适之母死,而其父恰恰早就葬于景公所修的路寝之台下,逢于何或盆成适想要将其母合葬于其父所葬之地——经景公之台,景公不许,经过晏子的劝谏,景公同意逢于何或盆成适将其父母合葬于路寝之台下。《昭王毁室》与《晏子春秋》二篇都涉及君主所建之宫下有其他人的墓地,结果楚昭王毁掉了宫室,而齐景公也同意别人将其父母合葬于宫室下。此外,《史记·滑稽列传》所载齐威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而已,一鸣惊人”与《韩非子·喻老》所载楚庄王“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不仅故事情节一致,而且用语也一致。《史记·滑稽列传》所载楚庄王欲以棺椁大夫之礼葬其爱马,楚国优孟谏之,这则故事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所载之事也有雷同之处。
齐楚之间如此之多的情节相似的故事,预示着齐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定存在密切交流的关系,否则很难解释这些故事之间的雷同。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史籍是否记载齐楚文化存在密切交流的时期呢?我们知道,楚国在历史上属于文化落后地区,以致于楚王多次自称“蛮夷”:据《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楚曰:“我蛮夷也。”楚国文化落后,自然要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和齐国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而齐鲁与楚国在地理位置上也相距不远,为楚国与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文化落后的楚国理应大量吸收了齐鲁文化。从楚地出土的文献看,也确实如此,近年出土的文献如上博简、郭店简等大多数齐鲁两国的文献。王葆玹早已指出,楚国与鲁国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认为楚国在文化上承继了鲁国文化,以致于他将其称为楚鲁儒学[9]19-27。王葆玹这一看法固然不错,但从近年楚地出土文献来看,我们也不应忽视楚国文化与齐国文化的关系。从现存史料看,齐楚的交流应始于楚成王时期,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齐楚这次会盟为两国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楚成王三十九年(齐孝公十年,公元前633年),“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齐桓公七子奔楚,并在楚国都做上了上大夫,而桓公七子都受到了良好教育,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在楚国传播齐国的文化。楚威王七年(齐威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这使得齐楚两国边境更为接近了,有利于两国文化的交流。而至楚怀王时期,齐楚的交往就更多了,楚怀王六年(齐威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齐”。楚怀王十一年(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在这六国中,齐楚当时是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两国的来往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致于“楚怀王十六年(齐宣王七年,公元前313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楚怀王二十年(齐宣王十一年,公元前309年),楚国“合齐以善韩”。《景公疟》等楚简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刚好与楚怀王时期吻合,这都表明当时齐楚两国交流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就更为密切了。现存史料也直接记载了齐楚文化的交流,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国稷下先生就有“环渊”一人,而“环渊,楚人”;齐襄王时期,荀子在齐国“作为老师”,并“三为祭酒”,后到楚国,并死于楚国兰陵。
需要指出的是,齐楚两国的密切关系在楚怀王时期达到顶峰,也在楚怀王时期形势发生逆转。楚怀王二十四年(齐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05年),楚国“倍齐而合秦”,以这件事为转折点,齐楚从亲关系开始破裂。楚怀王二十六年(齐宣王十七年,公元前303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怀王二十八年(齐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01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至齐湣王十七年[注]《史记·田敬仲世家》所载是年为齐湣王四十年,误,此依杨宽改,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1页。(楚顷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燕、秦、楚、三晋合攻齐国,最终导致齐湣王出亡而后为楚使淖齿所杀,淖齿与燕国共分齐之侵地与鹵器。随后,齐国便进入齐襄王和齐王建时期,大概是由于齐国在齐湣王末年受到六国的攻击已经元气大伤以致于差点导致灭亡,齐国从此倒向秦国,史载齐襄王王后、齐王建母后君王后,她在齐襄王时期以及齐王建初期对齐国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史记·田敬仲世家》载:“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齐国“事秦谨”,以致于齐王建六年(公元前259年),秦攻赵,齐国虽然与楚国表面上去救赵,但赵国断粮,请求齐国支援,齐王不给,最后导致“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秦攻打齐国,齐国竟然不战而降。而反观楚国,自从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卒于秦,秦楚绝,之后秦楚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如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等,秦楚已势同水火。齐楚的不同外交政策当然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从楚怀王之后,齐楚便不像以前那样密切了,自然会影响两国的文化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齐楚文化交流至楚怀王时期达到顶峰,但也正在此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由盛而衰。
结语
以上我们比较了上博竹书《景公疟》与传世本《晏子春秋》相关篇章,通过《景公疟》我们对《晏子春秋》的成书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景公疟》虽然否定通过祭祀等就可以求福,认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同时又认为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天也会惩罚君主,具有一种较为朴素的天人感应色彩。从《景公疟》为楚简这一事实看,我们又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齐楚文化存在一个密切交流的时期,两国文化交流在楚怀王时期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