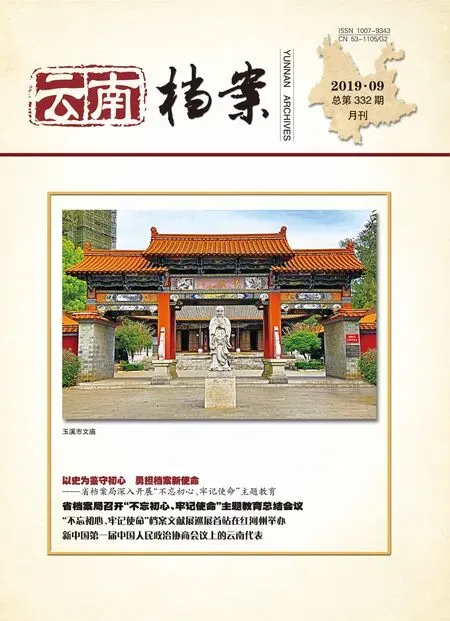社会记忆建构视域下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研究
■ 梁思思
云南省的“非遗”数量不胜枚举,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云南省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为109 项,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第一批34 项,第二批共38 项,第三批共21 项,第四批16 项,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大多数,四批中包括民间文学(如阿诗玛)、传统音乐(如彝族海菜腔)、民间舞蹈(如傣族孔雀舞艺)、传统戏剧(如玉溪花灯戏)、曲艺(如傣族章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如彝族摔跤)、传统美术(如纳西族东巴画)、传统手工技艺(如白族扎染技艺)、传统医药(如彝医药- 彝医水膏药疗法)和民俗(如傣族泼水节)等十个种类。
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社会记忆的传承
云南省“非遗”档案大都是以神话传说或者是民间说唱和民间民谣形式传承以往的社会生活,对这些“非遗”档案的保护无疑是对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延续,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诗玛,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揭示了光明终将代替黑暗、善美终将代替丑恶、自由终将代替压迫与禁锢的人类理想,对这些以民间故事或者神话传说方式流传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建档保护,是传承社会记忆以及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有利于社会记忆的建构
“非遗”档案的保护具有在活态性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证实和纠正作用,云南省“非遗”档案的保护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可以发挥形象展示与传播功能,例如傣族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独龙族卡雀哇节、怒族仙女节、傈僳族刀杆节等“非遗”节日,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式的保护,可以将少数民族“非遗”作为云南省的特色产品,并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从而建构云南记忆。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的优势分析
(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档案的保护已引起高度重视
2011年,在第一批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的文章中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是亟待重点保护的文化类专业档案。档案部门开始意识到,必须承担起文化类专业档案的监督指导职能[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七条也明确规定:“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3]。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非遗”及“非遗”档案的保护日益重视都为“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与名录体系的建立
随着2001年第1 批入选名单的公布,“名录制度”开始从物质文化遗产转向“非遗”。我国也开始建立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与名录体系。根据国办发[2005]8 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4],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和审批工作于2005年开始。随着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建立,云南省“非遗”代表作名录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共建立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
云南省“非遗”档案保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云南省的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是最主要的表现。云南省各个档案部门的传统专业优势尚未成为云南省“非遗”保护的迫切需求。在云南省目前的“非遗”实际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诸如“非遗”档案收集不齐全,整理不规范,保管不科学,开放利用不及时等现象。“非遗”档案保护的安全风险还没有在实践中对专业的保存体系形成迫切要求,这也造成了档案部门的专业优势不能在具体的“非遗”保护中发挥作用[5]。
(二)全民保护意识弱,民众参与度低
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兴趣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年轻人在外上学、工作,加之受到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兴趣,认为传统文化都是落后过时的东西,全民的保护意识不强。此外,由于“非遗”与民俗紧密相连,这使得民众的认知容易出现偏差,无法正确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经过笔者在云南省的调研显示,民众对云南省传统古村落的保护,有一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在保护落后的东西”。
(三)传承人的缺乏
“非遗”的传承主体就是传承人。这些“非遗”在父与子、师与徒之间通过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等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现代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冲击,很少会有年轻人再对传统文化感兴趣。随着一些云南省优秀民间艺人因年老而去世,使得云南省很多“非遗”传承主体缺失,从而导致一些传统技艺濒临失传。此外,对于身处云南省贫困落后地区的“非遗”,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水平的落后,在学习传承“非遗”方面就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并且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许多“非遗”的传承还面临着不通少数民族语言,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非遗”本身所蕴含文化内涵的困境,以及在具体掌握“非遗”技巧方面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了传承主体的缺失,导致云南省有不少“非遗”面临着无人传承的状况。
四、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路径的优化
(一)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档案馆是长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社会各方面开发利用档案资料的中心。我国的《档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管在机关档案室的档案,要定期向本级综合性档案馆移交[6]。因此,云南省各级综合性档案馆要定期接收机关档案室已经分类整理好了的,包括“非遗”档案在内的档案。对于云南省各机关档案室移交到档案馆的已经分类整理好的“非遗”档案,本级档案馆应先将其按“项目”区分全宗,然后按全宗顺序编号上架便可。如果移交的档案没有经过分类整理,或者整理质量不符合要求,档案馆就要对其进行重新分类、编号、编目等整理程序。
(二)提高社会意识和参与意识
“非遗”档案保护本质上需要公民参与的,只有传承人和保护部门参与形成的“非遗”档案是不完整的,“非遗”档案护中不仅在于丰满社会记忆,更在于丰富民族特色。社会意识是“非遗”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基础,“非遗”及其档案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内涵与特征带着特定社会意识时期的烙印,如傣族章哈的唱词内容是历史故事或歌唱劳动、生活、爱情等,都能真实地反映傣族先民的生产劳动、居住环境和社会风气。通过利用云南省“非遗”线上线下的表演、档案的展示展览等方式进行宣传,激活社会的基础感知和精力投入,并且吸引云南省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事业当中。
(三)重视建立传承人档案
“非遗”传承人档案,因其类似人事档案,是传承人人事档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事档案的性质,故对其分类可参照人事档案的分类标准设类。但传承人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人事档案分类中“十大类”,而是要体现“非遗”传承人档案的特点灵活设类,对于云南省“非遗”传承人档案而言,可以保留反映传承人基本背景信息的类别。另外,又可增设传承人“教育培训”、传承人“艺术作品”、传承人“表演场所和道具”、传承人“口述档案”、与传承人“相关文献报道”等类别。因云南省为少数民族大省,还可根据云南省少数民族归类后,再对传承人档案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