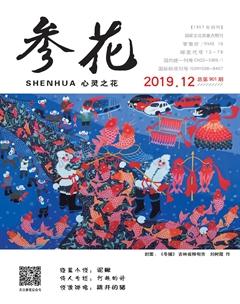陆羽是怎么火起来的
现在的天门,陆羽是最大的网红和金字招牌。不仅有以陆羽命名的社区、街道,还专门开辟了陆羽公园,修筑了意欲跻身江南名楼的茶经楼。可是在解放初期,天门知道陆羽的人其实很少,也鲜有人了解他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什么名气。
我有幸在未上学的时候就晓得有个陆羽,是因为我们住在雁叫关外婆家时,对面通往河边的巷子口,有一个跨街阁楼,上面供着陆羽的牌位。当时人们都称陆羽先生,也不知道他是算命先生还是教书先生。每逢初一、十五就有人去阁楼上烧香,可见人们将他当作菩萨了。我们这些孩子常去阁楼上抽“香签子”,拿回来作为打“珠果洛”的赌资。当时对陆羽的了解仅此而已,那些鸿渐关、雁叫关、古雁桥与陆羽有什么瓜葛,平民百姓基本上不知道。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左右,天门刮起了一股求佛水的风,说陆羽先生在三眼井显灵了,每天去求佛水的人络绎不绝。
很早就知道有个三眼井,在照墙街以西一个叫北坛的湾前面,但老人们讲的三眼井传说似乎与陆羽毫不相干。老人們说,不知是哪朝哪代,也不知是“长毛”还是什么土匪队伍,攻破了天门城,人们纷纷弃家“跑反”。照墙街一富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害怕遭土匪蹂躏,跳进了这口井里。几天后人们从井里捞起了小姐的尸体,同时惊动了官府,旌表为烈女。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民间出资修了一个青石板井盖,凿了三个不能让人掉下去的很小的井眼,只能用特制的小桶提水,三眼井因此出名了。后来,我知道了这口井是陆羽汲水煮茶的“文学泉”,但为什么一定要在井盖上凿三个眼呢?可见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在还没有建起县招待所的那块荒场地里,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说是一个来三眼井求佛水的京山妇女在洋生姜林子里生了三胎,全部是男孩,是生产街积极分子、接生员鄢家阿巴接的生。待我们这些爱看热闹的小屁孩闻讯赶到时,产妇已经走了。因为来不及送医院,又是早产,三个婴儿都死了,街道安排人予以掩埋。我们只看见了草地上的斑斑血迹,只见戴着红袖章的鄢家阿巴正在向人们津津乐道这段奇闻。说这个妇女由于“怀相”不好,经常闹病,丈夫听说天门有菩萨显灵,就用马驮着妻子百里迢迢来求陆羽先生保佑,没想到一路颠簸动了胎,白白糟蹋了三个还没发育成熟的儿子,作孽啊!
过了不久,西门火神庙又腾起了妖雾,陆羽又在那里显灵了。这次求的不是佛水而是丸药,信徒们将黄表纸折成三角形放在用破砖块垒成的“香案”上,烧纸叩头祷告后,纸包里就“飞”来了一粒粒如芝麻大小的黑色丸药,有求必应,能治百病。据说陆羽先生很忙,白天在北门三眼井上班,晚上到西门火神庙执勤,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傍晚,我和形影不离的发小安二、毛二从四牌楼经天门中学来到雁叫关以西的火神庙旧址。还没走到,就远远看见荒场地上星星点点的火苗,像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来到场地上,每个“香案”前都有一个人躬着屁股磕头作揖,妇女尤多。在朦胧的火光里,我们发现一个白发老太婆不断地摇头晃脑,就像汉剧《徐策跑城》里的徐大人为救人于水火,心急火燎,不断地摆动着苍髯白发。“摆头疯!”精明的毛二一眼就看出了老太婆的病症。
老婆婆摆了好大一会儿头发,作了几百个揖后,颤抖着双手十分虔诚地将黄表纸包放进了衣服的大襟处,摇晃着脑袋慢吞吞地离去。纸包里有没有丸药,我们当然不可能看到,反正她得到了陆羽先生的灵气,心满意足地走了。
“惊蛰开河,团鱼挪窝”,蛰伏了一千多年的陆羽,终于通过“显灵”展示了他的存在。
果然在一九五六的丁酉年,陆羽开始出名了。那年五六月份,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不知是谁带头,同学们发疯似的跑到北门一间破牛屋里拓陆羽像。又是我们三个一起来到北坛西边一间关牛的破庙里,地上满是牛粪。东边墙壁上嵌着一块约八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的青石小碑,右边是阴刻的头戴便帽、身穿飘逸长袍、右手端着一个茶杯的陆羽坐式像。人物面目清秀,线条十分流畅,可能出于名家之手。旁边一行篆字“陆鸿渐小像”,左边还有不少字,不太认识。我们立即拿出准备好的纸和铅笔将画像拓了下来。我拓了三张,回家后进行了加工,用墨笔将实处涂黑,就成了一幅黑底白线条的“神像”。房东老板老妖婆十分迷信,要了一张,恭恭敬敬地贴在房里墙壁上,每天烧香叩拜。可见,陆羽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
一天没事,我仔细看了看拓片左边的那几行字,确实有很多不认识,特别是题字人“范禹偁”的那个“偁”字,从来没见过。我自小就有对不认识的字刨根问底的习惯,但家里很穷,连《新华字典》也没有一本;问老师吧,当时的语文老师经常读错别字,他能认识这种不常用的字吗?好在同屋的熊春舫大伯是一部活字典,他七十来岁,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当过几天日文翻译。于是我向熊伯请教,他说这是“称”的异体字,还说范禹偁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五代十国时期蜀国的翰林学士,简州刺史,是有名的大诗人。啊,这么大的人物为陆羽的碑题字,陆羽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五代十国离现在一千多年,这块碑多么古老啊!
没多久,文化馆在大门口出了一个“文化专栏”,将近期《人民画报》刊登的介绍“茶圣陆羽”的图片及文字贴出来让人们观看。画报上也没有多少内容,好像有“茶经三卷”和挂着“陆羽遗风”招牌幌子的江南茶楼的照片,这时候人们才知道陆羽是茶圣。旁边还贴着一张如我等所拓的“陆鸿渐小像”,肯定是文化馆的专业干部拓的,比我们的拓印水平高多了。
每天都有不少人围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议论,有的说陆羽虽然在天门默默无闻,在江南、两广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名气很大。有的说得更邪乎,说是农业农村部寻找这个“茶博士”,经过调查,才有了《人民画报》的介绍。啊,这下子天门出名了,天门人高兴了!
扯白如“扯闪”,闷雷滚滚来。可这次不是“干打雷不下雨”,还真“纷”了几滴毛毛雨呢。不几天,陆羽亭开工兴建,听说是拨的专款。工地在北坛,我们隔三岔五地去看看。一些高水平的木匠挥凿舞斧,精雕细刻,镂刻出了诸如带有金瓜的木柱,有浮雕的斗方。那些曾经修过祠堂、庙宇有着雕龙镂凤绝技的老师傅派上了大用场。那间牛屋也不关牛了,进行了打扫清理,堆放着材料和半成品。一个老师傅说,这是“陆公祠”,很有些年头了。
几个月后,陆羽亭建成了,建在三眼井边,是个只有立柱没有墙壁的六角凉亭,虽然没有盖琉璃瓦,飞檐斗拱也显得十分气派。三眼井台也用水泥护砌,磨得很光洁。还有一块镌有“文学泉”三个大字的古碑立于井边,据说是农民挖藕时从北湖里挖出来的。
在杨柳依依,绿荷掩映的湖边有了一个仿古建筑,给封闭单调的县城增添了一道风景。每天都有不少人“来此一游”,特别是诸如彭响之、熊春舫等民国遗老和一些堤街上的大商户老板来得更勤。
“河里无鱼虾也贵。”天门确实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什么南禅寺、城隍庙等不是毁于日本鬼子之手,就是拆掉盖了学校、仓库什么的。陆羽亭的兴建,满足了部分有“思古之幽情”的人们的精神寄托。
进入八十年代,天门建立了“陆羽研究会”,翻箱倒柜地挖掘陆羽文化,撰写、汇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资料,分期出版,人们对陆羽开始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为了扩大陆羽的影响,重修了金碧辉煌的陆羽亭,包装了古老的三眼井,终于恢复了被摧毁的名胜古迹,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一些研究陆羽的外国特别是日本学者“丹凤朝阳”般地向天门涌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日本研究陆羽的学者,时年六十七岁的东京医科大学教授诸冈妙子遵父遗嘱,将四十年代其父诸冈存博士到天门寻访陆羽遗迹,时任县长胡雁桥赠送的《陆子茶经》完璧归赵,郑重地奉还给天门。二〇〇六年,妙子的女儿风间清子沿着祖辈的足迹访问了天门,参观游览了有关陆羽的火门山、西塔寺、三眼井等名胜古迹,受到了天门地方领导的热烈欢迎。
进入新世纪,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气候中,又新修了陆羽纪念馆和高耸入云的茶经楼,耗资之巨,动作之大可谓前无古人。
西湖边,绿荷掩映的茶经楼确实造型别致,古朴典雅,比岳阳楼还高大。我围着茶经楼转了一圈,观赏了金光闪烁如龙翔凤翥的匾额和楹联,但我没有登楼造访。因为我去过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里面陈列的尽是现代人撰写的简介和古人咏楼的诗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硬通货”,每次下楼都后悔不该上楼。茶经楼定然如法炮制,不会有什么新名堂。陆羽文化留下来的“硬通货”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几本再版的《茶经》,就是“文学泉”古碑和“陆鸿渐小像”石碑,这些笨重的石碑是不会往楼上搬的,倒不如去逛逛博物馆。
一千多年来,国内外对陆羽如此推崇,一直没有降温,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对陆羽贡献的认识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我认为陆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保护了人类的健康,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曾元迈说的。如若不信,请认真看看曾元迈的《茶经序》,现摘录几段:
一、酒之为物,能乱人心志。求其所以除痟去疠,风生两腋者莫韵于茶。
二、公诸天下,后世岂不使茗饮远胜于酒。
三、茗饮远胜于酒,而与食并重之,为最初切于日用者哉。
这几段文字说明茶这种饮料有益于人的健康,比酒强多了。并强调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老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没有“酒”。这是陆羽的观念和学术思想的生活化,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促进了人类的健康。
“然禹恶旨酒,先王避酒祻(祻者,祭祀也,笔者注)。”曾元迈旁征博引,谈到了酒的危害,说大禹厌恶美酒,祭祀不用酒,尽力避免酒祸。
酒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目共睹,而茶则能清心明目,醒脑提神,涤污除秽,润肠生津,有益无害。陆羽对茶的研究与推崇有利于人类的健康,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是毋庸置疑的。
天门人曾有豪言,誓将茶经楼打造成江南名楼,以期居“四大名楼”之一。水汽以晶核聚之,风雨兴也;俗物赖高人点化,声名盛焉。且不说天门位于长江之北,但凡能称名楼者,除人文地理优势外,高人的“点石成金”很重要。滕王阁靠王勃的“序”名震四海,岳阳楼赖范仲淹的“记”誉满华夏,黄鹤楼的出名则得力于崔颢的那首令李白都哀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黄鹤楼》。诚然,天门的茶经楼有着茶圣故里的人文地理优势,其缺憾是没有高人“点化”。行文至此,猛然忆及,曾元迈的“序”能不能算是“高人点化”呢?曾元迈,天门人,康熙年间翰林,出任过御史,官不大,名气也远不及王勃、崔颢、范仲淹。但他的《茶经序》却是序里的名篇。历史上为《茶经》作序的人难以数计,可只选上了陈师道、皮日休、曾元迈等十六篇,连明朝中晚期“后五子”領袖之一,官居礼部尚书的李维桢的“序”也落选了,说明曾元迈的“序”是名篇。
曾元迈的“序”不仅是一篇很美的散文,更可贵的是他能以独特的视角,从“养生”和“社会”的角度,阐述《茶经》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果请高水平的书法家泼墨,以鎏金的行草将曾元迈的《茶经序》制成一块屏风陈列于茶经楼,定然会产生轰动效应,那就可以与那几个名楼一比高下了。
物之为物者,烨然其表,何如质其里耶?没有一点“硬通货”,仅靠外表的光鲜,是不可能跻身于名楼之列的。
我没有登上过茶经楼,估计天门的众多专家学者及诸父母官比我高明多了,应该想到了曾元迈的“序”,其举措肯定比我的建议更好。
2019年9月4日
作者简介:尔也,本名曾凡义,湖北天门城关人,年逾七旬。种过田,做过水库工作,当过民办教师。在国家及省、地报刊发表散文、杂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近20万字。
(《鸿渐风》微信公众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