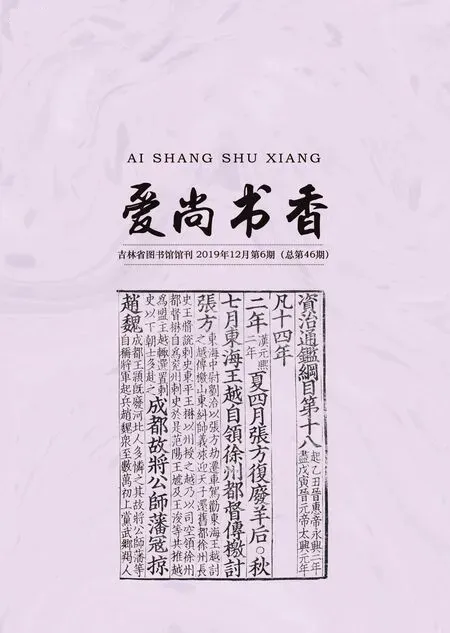爱在高原
——读陈晓雷的散文
周东平
我和陈晓雷是多年的朋友,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草原煤城——大雁矿务局相识。当时陈晓雷是大雁矿工报社记者,以笔名“田雨”写的文章常见诸于报端,而我在矿务局办公室任职,因工作关系,两人时常接触。后来,晓雷到办公室做调研员,我们成了同事,都从事文字工作,又互相欣赏对方的写作特长和风格,决不“文人相轻”,倒是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味。再后来,晓雷调到“东煤公司”去往长春,我本人也因故离开大雁。在以后的岁月里,偶有信息互通,但还是由于空间拉大而渐行渐远,以至中断了联系。直到去年暮秋,我通过大雁几位朋友打听到陈晓雷,才得以重新建立联络。
在和朋友们的谈论中,有人对陈晓雷如今的地位和名气艳羡不已,我也为朋友的进步感到欣喜,但更对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赞叹有加。私以为: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机缘巧合,得机缘而成就人生辉煌者有之;失机缘而碌碌终生者亦有之。而“写作”则不同,它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人生阅历、感悟,以及驾驭语言艺术、把握文字技巧的能力,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在他的职衔中,我最看重的是“作家”头衔。
一
翻开晓雷的《大地童谣》便被深深吸引。书中的生活场景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作品的距离,和作者心灵的距离。我似乎听到了山林的阵阵松涛,嗅到了牧草的悠悠芳香。
1967年冬,我们举家从辽宁庄河县徙居呼伦贝尔阿荣旗,在大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落户,开始了“土里刨食”的农家生活。后因工作调动移居大雁,直到2001年回迁庄河。三十年的时光涵盖了我的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阶段,给我深深地烙上了大兴安岭的印记,直到现在常以“呼伦贝尔人”自居。
晓雷的散文大多是写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活,与我那一段的生活轨迹完全契合,文中的生活场景就像电影片段一样历历在目。
读着《香酱谣》,感觉就是自己正手握“酱耙子”在搅动酱缸,鼻翼间充溢着诱人的酱香。读着《河畔木屋》,眼前浮现的是一排排低矮的土坯草房,和弥漫在晨曦中的缕缕炊烟。读着《风雪暖冬》,想起自己和小伙伴们在冬夜里手拿电筒,肩扛木梯,沿着各家房檐掏家雀,引得全屯吠声一片。
在读《渴甜谣》时,眼前晃动着挂满果实的山杏树、山丁子树、稠李子树,还有酸得人直皱眉头的酸木浆。透过《野菜谣》,让我看到了自己在炎炎夏日满山割灰菜而湿透衣衫的身影。还有,春阳下鸣叫着钻上蓝天的“鹅了”;盛夏里林间淌出来的冰冷山水;秋风中金黄的田野;寒冬里凌冽的“白毛风”,随风蜿蜒游动的雪粒子。
读着读着,似乎我就置身于他和他的伙伴中间,我就出现在他的描述里。不可名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挥之不去。
二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生活中,肯定都有几件记忆深刻、值得回味的往事,抑或糗事。晓雷把他儿时记忆中的故事,用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活灵活现,感人至深。他并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融进了时代的背景,融进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揉进了人性和感情,赋予作品以文学的力量,让人们在灵魂深处产生共鸣。
《风雪暖冬》中的老信差郭爷爷,腾出自家屋子给一个“右派”劳改犯夫妻团聚,让这对夫妻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这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为促成这短暂的团聚,老人不知拜了多少“庙门”,说了多少好话,可能还拍着胸口作保。“明年冬天再来,大叔的老屋暖和着呢!”送别时的暖心话,让谁听了不如沐春风?这是一个山里老人质朴的善良,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任,是一种人性的美,一种人间大爱。
在《沉默山脉》中,晓雷的父亲面对四个民工对其生命的威胁而不屈,最后让首恶“李大疤痢”黯然溜走,昭示的是“邪不压正”的人间正道,让人钦佩不已。《白桦谣》里老丑婆和母狼的故事,表现了母性的伟大,揭示的是“善有善报”的道理,给人以生活启迪。《橘瓣糖》里吃到田奶奶奖励的橘瓣糖时的甜蜜;《渴甜谣》里品味只有在大城市才有的“懈粮糖”(口香糖)的喜悦,和尝到“高粱果”滋味时的惊异;《香酱谣》中蘸着大酱就把平时难以下咽的冻卜留克、冻萝卜缨子吃得津津有味的情景;还有《河畔木屋》中住进新房时洋溢在全家人脸上的幸福和满足……这些正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年代,人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人们努力创造幸福生活的高涨热情。
晓雷就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给看似细碎零星的、平淡无奇的小故事赋予了真、善、美的意味,和深邃的生活内涵,读了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回味无穷。
三
年轻的晓雷朝气蓬勃、好学上进,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盎然的兴趣。
1997年初春,我去大连,途经长春在晓雷家小住两日。短短的两日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经典名著,晓雷在人生的积累阶段,摒弃那种浮躁之气,狠下了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惜时如金,埋头读书。如此,“文学如雨露滋润了我年轻的心田”,文学“让我的情感丰富起来”“文学像多情的种子,悄悄植入我的心灵,融入我的精神”。正是广泛的阅读,为晓雷最终踏进文学艺术的殿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在他的《巴别尔的文学永恒》《映现广袤精神世界的窗子》等篇,以及诸多散文中信手拈来的名家、名作、名言就是最好的体现。可以说,阅读的乐趣融进了他的精神家园。
书架上除了图书,还有许多笔记本。出于好奇,我随手翻检几册。那里记着他的读书笔记、学习心得,还有所见所闻的趣事等。
晓雷是个善于与人沟通,极具亲和力的人。记得在大雁共事时,有一次闲聊,他让我讲点“农村的事儿”。我讲了阿荣旗农村漏粉条的情景,和几位男女社员边劳作、边戏谑的故事,听得他哈哈大笑。
他的散文中就有许多是通过这些听来的故事写成的。《沉默山脉》里,他的父亲勇斗“四条恶狼”,应当是乃父给他讲述的;《卜留克高原》中,尤里一家带着种子逃亡的传奇,想必也是听来的故事;《听来的草原往事》,更是把从钱姓老者口中听到的发生在俄罗斯人阿廖沙和老者娘舅身上两个关于金子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还有《根河的传说》中,极有魅力的月拉姑娘唱着《唤母歌》投身巨涛,变成“一条银光闪闪的细鳞鱼”,最终化身为“白鱼公主”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事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而记者出身的晓雷却不同,他有着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视角,更加敏锐的“嗅觉”,他好奇心强烈,喜欢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追根溯源。他是一个乐于听故事,善于讲故事的人。在《晚霞映红冬牧场》里,他描述自己蓄意躲开同行伙伴,留在冬日的巴尔虎草原,通过向牧人学习蒙语,拉近距离,取得信任,进而交流,终于从牧人嘎拉图口中得到了另一个牧人阿里木斯失去草场后的遭遇故事。被他收入“囊”中的诸多故事,大概都是通过“交朋友”获取的吧。
他就是这样扎根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汲取文学营养,挖掘生活内涵,使植入这些故事的散文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文精神。
阅读名著和深入生活,给晓雷的创作插上双翼,让他在文学艺术的天空得以飞翔。
四
他在《人生与文学——我的精神告白》中写道:“在我心里贮存着两种爱,即生活是终生的爱,文学是精神的爱。在生活的长河中,我爱亲人,爱朋友,爱工作,爱自己的祖国,爱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是朴素的心灵、高尚的爱”。正是有了“爱”,让他的心充满阳光,激起他讴歌生活的热情。
因为爱,他写外婆的慈祥、勤劳和简朴,写郭爷爷的善良、忠厚和质朴,写父亲的干练、正直和不屈。因为爱,他写小乌娜偷偷放走了捡回来的小鹿;写老丑婆掩护了被猎人追杀的怀孕母狼。因为爱,他写女儿赛汗的拼搏、刻苦和勤奋;写妹妹晓波与病魔的抗争和生命的顽强,以及自己的紧张、焦虑和渴望与祝福。因为爱,他写热情的老额尼玛丽娅·索和她的烤列巴;写鄂伦春林杰老奶奶的老当益壮和矍铄精神。
还是因为爱,他写了珍惜草原的牧人嘎拉图;写了真诚待客的蒙古族主妇索伦托娅;写了同学二燕送来萝卜时体验到的被关怀的温暖;写了与发小诤友金河几十年来的情谊。更可贵的是,他还写了对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李林军的追念,令人为之动容。
除了这些人物,他还热爱故乡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在《故土芬芳》中,满怀着感恩之情写道:“我的精神中激荡着那片山野的灵气,我的肉体里融汇着那片土地的养分,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山岭赋予的刚毅……我虽身体离开大兴安岭三十余载,而我的精神却一刻未曾离开大兴安岭。故乡是我放养精神的牧场。”他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他永远是大兴安岭的儿子。带着他对大兴安岭、对呼伦贝尔草原的挚爱和眷念,这些散文作品,就像一条条涓涓的小溪,透着清新,带着欢快,从大兴安岭深处流淌出来。
“爱”,始终是他创作的主题;“爱”,是他埋头写作的原动力;“爱”,让他的散文作品充满暖意。陈晓雷在他的散文中对“爱”的诠释告诉人们:“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前进的根本。没有“爱”,人类社会将被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