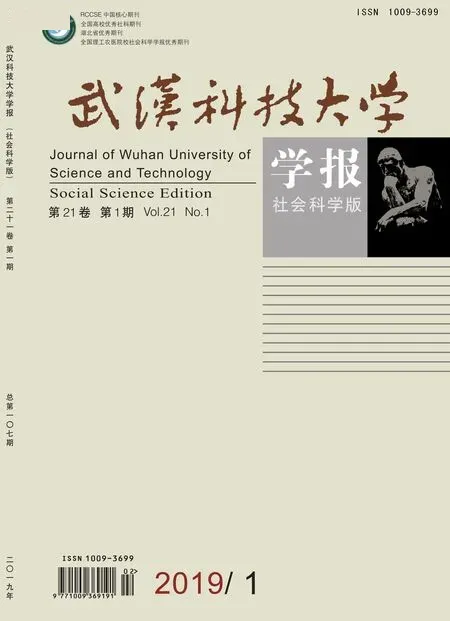法治社会建设的本土资源和中华法系
——殷周金文的法制思想与当代价值
黄 震 云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殷周金文题篇上万,内容富丰,特别是周代金文,细致、准确、生动地记录了出纳王命与立法、司法、执法的情形,反映了我国大道之行的轴心时代的法制思想和法治方法,是当代法治建设最珍贵的本土法律资源之一。由于文献是陆续出土,加之文字识读等原因,至今没有全面研究和开发。笔者对殷周金文中的法制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深入理解我国法制的形成、形态以及对当代法治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部分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一、以史为鉴、加强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是周初立法的基础理论
殷商灭亡的原因很多,周代人认为主要是对天不敬、对下不关心百姓的喜怒哀乐、乱罚无罪、公务人员酗酒等。《尚书·无逸》说:“乱罚无罪”,“其监于兹”[1]60-61。因此,周公教导成王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代初年成康时期的四十多年里刑措不用,显示了周公设计的政治制度及其成效的完美。 “殷鉴”不远是西周政治的实践基础和前提。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诗经·大雅·荡》也有类似的表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979明确指出,历史不是一面镜子,而是很多面镜子,殷商初期还以夏代灭亡为鉴戒,后期则自己成为鉴戒了。
周人认为“酗于酒德”是殷商灭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周公发布了《酒诰》昭告天下:
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1]51
《酒诰》对于工作期间饮酒作出了明确、严厉的规定,将饮酒定性为大乱丧德行为。康王时的《大盂鼎》有相同的记载:
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敷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矣。[3]1517
根据《大盂鼎》,周康王训诫盂酗酒亡国:殷商不仅朝廷君臣牛饮,连边缘地区的地方官员也嗜酒如命,因此亡国。传世文献强调酒德,但究竟是什么程度和规定并不清楚,据《大盂鼎》我们知道周文王、周武王滴酒不沾。西周以殷商为鉴,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社会长治久安,是一个成功的治国范例。强调非必须情况下不得饮酒,而文王武王则滴酒不沾,作出表率。另一方面,西周强调勤政,并进行必要的考核制度,有效地提高了行政效率。《诗经·大雅·既醉》说:“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酒诰》规定,官员只有在行大礼如祭祀时才可以饮酒,但祭祀者既饱以德,就是酒礼对应人品,不喝醉是酒德标准。
二、敬畏天命、明德慎罚是西周治国最重要的原则和执法的指导思想
西周以多元神取代殷商的一元神,以道为核心,将神权通过道德表现出来,强调人最根本的生活价值就是德的培育和实践,明德慎罚思维由此产生。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的《逨盘》记载:
逨曰:不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召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竝(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逖)不享,用奠四国万邦。雩朕皇高祖新室中,克幽明厥心,柔远能迩,会召康王,方怀不廷。雩朕皇高祖惠中(蠡)父,盭(戾)龢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雩朕皇高祖零白,粦明厥心,不惰□服,用辟龏王懿王。雩朕皇亚祖懿中(设),谏谏克匍保厥辟考(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雩朕皇考龏叔,穆穆趩趩,龢询(均)于政,明济于德,享辟 厉王。逨肇缵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事,肆天子多赐逨休,天子其万年无疆,耆(?)黄耈,保奠周邦,谏乂四方①。
《逨盘》叙述了逨的高祖单公随文王、武王夺取天下的事迹,克明慎德是对单公的评价,慎德是赞美做人的原则或人品纯粹高尚。父亲龏叔明济于德,因此得到天子的表彰。我们看到,其对四代祖先的评价都集中在道德和功德上,这也是逨恭敬和骄傲的地方。由此可见,敬天尊王、修德勤政是官场风气也是家风。因此,西周的道德建设是其政治思想和法制文化的体现。又西周中晚期的《史墙盘》记载:
西周宣扬天命,但并不迷信天命,将天命道德化,天命类似于后代理学家的天理。对过去的成功往往归结为天命对道德的奖赏或者说应然,而当下主要是道德的实施。“史”应该是殷商的遗民,因此其“用肇彻周邦”,先祖投奔周武王,在周公麾下,随文王武王夺取天下、平定四方,成康以来南征荆楚、恪守本分、日夜操劳,因此天子发布命令进行褒奖。西周对于人心的向往十分重视,不仅家族内部,对殷商移民也是如此。武王翦商以后立即进行分封,承认殷商联邦的合法地位。《论语·尧曰》记载,尧能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因此天下之民归心。这些优秀的传统管理措施和方法,在周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挥。按《何尊》记载:
《何尊》是周成王亲政五年后对下属的训告,表现了敬畏天命、君权神授但必须秉德慎行的主张。又《大盂鼎》记载: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又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匐有四方,畯政厥民,在于御事……汝妹辰又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令汝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3]1517
《大盂鼎》强调执政要秉德用经、奔走不息,并培育子弟、重视小学,通过教育进行明德的培养,避免成为法盲或糊涂官员。《周礼》记载周人对于人才的培养采取选拔制度,选拔的唯一要义就是德的有无,不再坚持尧舜时代只要是贵族子弟就必须造就的策略。
三、敬明乃罚、治心为上的法权体系是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和运作逻辑
三代以来的圣贤治国主张王道,因此强调敬明乃罚、治心为上,认为人心美好与和谐自然就不会有犯罪行为发生。治心的方法导致了礼乐制度的产生。西周强调王权的至高无上,唯皇作极。《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2]796王权高度集中,再通过五服形式构成封建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宗法体系和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三轨并行,又互相作用,直指内心以规范言行,因此周代历史长达八百年。目前出土的书写金文的器,绝大部分是感谢君王赏赐的产物,主要内容包括王命,说明奖赏钱财、物品的原因,然后是作器的目的,即为了感谢君王的恩德,而且要作为传家宝子子孙孙传递下去。家族观念、门阀思想、敬天礼人传统皆因此形成,而这一切的逻辑起点和根本是对人心的治理。

牧牛违背自己的誓言,以师讼,按照周律,违背誓言是重罪,但王要求他可以通过再誓免除处罚,并让五夫作为证人。按照律应该鞭打千,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赦免他五百,罚三百寽。负责执行的伯扬父让他发誓,不再滋事,不再因小事纠缠不休,控告行政长官,类似今天的和解。但是,如果行政长官来告你再度违背誓言,随时还可以按律执行鞭千。最后牧牛交了罚金,案件了结。按《周礼》说,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周王利用盟誓方式,恩威并施,化解矛盾,成为制度。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法律智慧和司法艺术。周人的法律制度,有清晰的法理支持,法以济礼,是周代法制的基本特征。
王曰:“牧,汝毋敢弗帅先王作明刑用,雩迺讯庶右邻,毋敢不明不中不刑,乃贯政事,毋敢不尹人不中不刑,今余唯申就乃命,赐汝秬鬯一卣。[3]2748(《牧簋》)
牧在先王时代担任司士的职务。按《尚书·舜典》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牧担任的应该是司法首长,王任命他为辟百僚的官。“有炯事包迺”句子后面的“多乱”“不用先王作刑”,虐讯庶民,结果是“不刑不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不刑的后果是刑罚不能体现价值功能。不刑的后果是罚,也即是刑罚,而刑罚要“用中罚。”[1]69这里的中罚指惩罚得当,是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厥罪厥辜指按照其习惯审理案件的事情。王给牧提出了系列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先王的规范要严格遵守,通过敬神、实用、实施,实现政通人和。尹人应该是管理人。《论语·子路》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42《礼记·大传》曰:“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爱护百姓,刑和罚才能够发挥作用,刑罚发挥作用才能安定社会。“中”指有效用。这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法律的制定和司法都要建立在爱护百姓的基础上,不能简单粗暴。《史记·乐书》解释了乐教对治理的作用:“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5]191司马迁指出乐教对于预防犯罪的价值原理。治理国家以人心的教化为根本,而不是简单地用律来规范。

四、法权下移、维权再审和私人公共领域搭建的意识自觉
夏代开始的世袭制标志着国家的全面私有,土地作为固定的财富自然成为私权。周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彻底废止殷商的一元神制度,而是建立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神学体系,因此往往借助神灵的名义管理社会、治理百姓。西周封神时设立社神,命令25家一社,随着井田、社田、千亩这些形式的推行,法权分解下移。《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周礼·地官·小司徒 》《孟子·滕文公上》 等都有记载,如:“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256公田并不是天子田,而是国家的田。西周到春秋时期,井田制度客观存在,神社和井田构成了周代宗法制度的双重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司法不仅要对人负责还要对宗族神灵和土地神负责,因此审理案件时,需要北向和对神盟誓这样的仪式。《小盂鼎》记载:

又《大克鼎》记载:
善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3]1515
大廷、大室都是祖庙中最重要的宫室,北面供奉的都是主要的神主,一般为始祖,所以北面就标志着虔诚和神圣。北面与天罚神断不同,北面表示对鬼神负责,而不是让他们尽职,体现言行需要对祖宗负责。在家的监督氛围中,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避免矛盾激化,同时,培育了耻辱感和孝敬心理。
周代规定具体的职事官拥有立法、司法自由的权力。如《周礼·秋官·司盟》记载,“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授权司盟特别的法权,其他的官职也大多相同或者相似。法权的下移最突出的优势是了解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相对容易作出客观的裁定。
随着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在利益驱动之下,宗族亲亲关系开始削弱,而利用宗法制度干预司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曶鼎》记载匡众的家丁二十人,在荒年的时候抢劫了曶禾十秭,秭的数量一般作数亿,有的认为是十亿、千亿,总之数量巨大。因此曶将匡季提告到东宫,但是匡的手下早已逃匿。怎么办?东宫的第一道判令是要求寻人,如果匡众找不到偷盗的人,那么要加重处罚即罚大。匡众提出调解和曶商量,愿意赔偿五田,也就是五百亩地,同时附加众和臣等家丁四人。协商未果,曶拒绝了匡众,继续上告。东宫下达第二道判令,要求加倍偿还,如果拖延到明年,再加倍惩罚,即需要赔偿四十秭。因此,匡众决定赔偿,计赔付七田和五夫,相当于三十秭,也算是折中了一下,曶也接受了。通过诉讼,曶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并将利益最大化为三十秭,以十秭损失获得三十秭的赔偿[3]1520。从理论上说,这一判决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其中对匡臣不至于加罚十秭,对其拖延又加罚十秭。这就是周代法律的公平方式和尊严体现,这样的公平考虑了对方对审判的诚意和执行的决心。曶和匡的官司没有盟誓的情节,说明彼此内心的纠结难以调和。在利益的驱动下匡和其仆人形成私人关系空间,利益关系对宗法制度构成了破坏,而这种破坏形式多样,最终导致了王室衰微,社会关系重新建立。又《曶鼎》其二记载,王四月丁酉这天,邢叔在異爲□,曶使小子代表他向邢叔起诉被告叫限的这个人,是效父的家臣。我用一匹马和束丝赎买五个奴隶,完成了交易。限说:当地的官员某□使我偿还马,效父把丝给了某□。这样,交易并没有完成,但曶的马和丝都没了。因此,曶的小子在王的三门都树立了木榜,祈告上诉。一般认为,榜木不可解,将榜分为木、冖、方三块来理解,或推测这段话的意思是双方在王宫外的三门悬挂着交易法令的木板下,用货币进行了交易,于是买了这五个人,付出一百钱。如果补交出五个人就要上告,于是某□上告并希望索回赎金[6]。所谓三门交易法令不符合文意,但是也感受到三门的榜木和官司之间的密切关联。接着邢叔发话,这样的交易在王廷才合法,于是彼此到王廷进行协商,希望和解,将陪等五夫交给曶,而曶将百寽钱给付,某□也同意。曶将酒、羊和三寽用致丝人,即给付负责运送帮助完成交易的人。曶让某□交纳了囗矢五秉作为诉讼失败的费用。同时提出,五夫要住在原来的地方耕种原来的田。如果没有意见,可以复命,对方表示可以。
木榜就是榜木,《曶鼎》和甲骨文、篆文衍化关系清晰。上诉者将榜木(华表)放在通往王宫的大门口,表示上告。按照周代的城市格局,三门指应门、皋门、路门,其中应门为外面的正门。《尚书·顾命》说:“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诗经·大雅·绵》说:“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路指路寝之路,指直接向王申诉。
《五年琱生簋(曾称召伯虎簋)》记载,琱生和召伯虎家族关系密切,琱生吃了官司,去找召伯虎商量,召伯虎送给君氏一把壶,并说,君氏已经发话说他老了,你那个(仆庸)土田多谏的官司,弋白(伯)氏答应你的要求,利益分配为公三,你二,公拿二,那你就拿一半。我为了得到君氏的帮助,送给他一个大璋。召伯虎将送一把壶说成一个大璋,欺骗琱生,行贿过程的舞弊耐人寻味。召伯虎说,我既然负责审理,而我的父母已经给我提出,我不敢违背,还要把结果告诉他们。琱生从外面拿来圭送给召伯虎。让召伯虎父母为其官司疏通关系,打一场人情官司的琱生是王室子弟[3]2636。这个案子明显具有徇私枉法的特征,应该是我国最早记录的贪腐案件,而又发生在王室和重臣那里,宗法制度的弊病十分明显。宗法制度以血缘为基础,因此有着先天的认同,所以又利于彼此的和解。

1975年于陕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裘卫四器记载了经济利益交往及其不平衡对礼法制度的破坏与挑战,显示了周代国家治理的一个明显弊端,就是缺少调节功能,或者说法制方式没有应然进步完善。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成康四代刑措不用的局面,但是之后虽有调节,也只在美刺范畴,没有实质性改变。《卫簋》说:二十七年三月,王盛服出现在周太室,南伯陪着裘卫前来,立在中廷,面对神祇。王赏赐给裘卫巿、朱黃(衡)、(銮)物品。裘卫制作了簋,作为感恩纪念品[3]2478。司裘官员负责君王的服饰和裘毛产业,地位并不是很高,但伺候王左右,因此容易得到王的关照。《九年卫鼎》记载,恭王九年的正月,王在周的驹宫太庙,隆重接待眉敖者□的使者。为参加这次礼典,矩伯取车、车的配套设备和若干车马饰具,给了矩伯妻子矩姜三两帛。矩伯于是把自己的□里给了裘卫。裘卫给在王室的颜林两匹军马,给颜的妻子颜姒一些物品。矩伯发话立下将林□里的树林和田地交付裘卫的文书[3]1505。我们看到裘卫在矩伯困难的时候,通过交换获得了山林土地。这表明,原来的封建秩序已经通过交换实现了调整。那么,随后的利益之争必然更加激烈,礼制转向法制成为历史必然,而这些新阶层的利益获得者和失去利益者形成了彼此矛盾交错的公共领域。
又《裘卫盉》说,恭王三年三月,王将在豊举行爯旂礼,矩伯让庶人到裘卫那里买瑾璋。按照《周礼》和《诗经》的记载,王举行大礼时官员要举璋参加,而矩伯没有这个东西,因此矩伯向裘卫购买。矩伯用赤虎(琥)两、两鞈一折合二十朋,又用舍田三田作六十朋来购买[3]4973。根据《周礼》,王田不鬻,禁止田地买卖,只允许内部交换。《礼记·王制》有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厘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5]73因此,矩伯和裘卫告于伯邑父,荣伯,定伯,亮伯,单伯,乃令(命)参(三)有司,司徒微邑,司马单舆,司工(空)邑人,服遝受田。燹、(走甫)、卫小子瑶逆者(诸)其卿(飨)。三有司具体承办这个事,到最后还祭祀了土地神灵,表示置换交易完成。裘卫为他的父亲惠孟做了一个盘,也就是盉,希望传给子孙。盉似乎是纪念品,但同样也具有法律文书的功用,尽管是自己制作的。这种自制文书记录的方式在青铜器中普遍存在,说明得到社会认可。按《五年卫鼎》记载,裘卫提告邦君厉,理由是厉负责水利工程,在王室东面我的田地里开挖两条水渠,答应过五百亩田作为补偿,但是没有给付。负责审理案件的是五伯,传厉质证,厉对事实表示认可,五伯要厉宣誓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然后令三司执行,划出厉的四田,又划出部分其他的田地,勘定四至,给付裘卫,还请来荆人等几方面代表作证,举行交割仪式。《五年卫鼎》记录了诉讼到定谳执行的过程,程序分为六个步骤:告、讯、誓、履、付、飨,详细完备[3]1507。《九年卫鼎》中明显省略,只有履、付、飨三个步骤。“□(履)付裘卫林□里”“卫小子家,逆者(诸)其□(剩)”。裘卫的土地权官司,表明法律对财富调整的制度保障。
五、教而诛之,是积极预防犯罪的仁政思想
比较起来,西周法律强调法的价值,将律放在次要的位置,而法的精神又通过德的积累完善。明德慎罚、德主刑辅是周代安定社会的大政方针之一,明确指出只有乱世才用重典。“为政之法,当先施教令于民,犹复宁申敕之。”[4]194《孟子·万章下》举例说,如果有能行王道的人出现,会将眼下这些多少都有些放肆无礼的诸侯都杀掉吗?还是教化他们让他们改正,如果坚决不改正再杀呢[4]319?《荀子·宥坐》与《孔子家语·始诛》都强调对于犯罪的人要“陈之以道,上先服之”,“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金文《训匜》[3]5541-5542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又《师旂鼎》记载,师旂因为他属下的许多仆官不跟穆王去征伐方雷,便派其友弘把这件事告到伯懋父那里,说:在□的时候,伯懋父曾罚得、系、古三人三百锾,现在没有能罚得。伯懋父命令说,依法应该流放这些不跟右军一起出征的人,现在不要放逐了,应该交罚款给师旂。孔伯把这事告知内史记下来,旂为对扬伯懋父的判决,要求将此事铸刻于宝彝上[3]1478。这是另一种从轻处罚的例子。
积极治理、预防犯罪是周代最为成功的治理手段之一,礼乐制度建设的同时,将文王作为万邦学习的楷模。《论语·子路》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4]142。朱熹言:“范氏曰:‘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4]142按《礼记·大传》说:“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这里的刑是仪刑示范。周人树立的仪刑是周文王。按《诗经·大雅》说:
上天之载 ,无声无臭。 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文王》)[1]117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棫朴》)[1]120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皇矣》)[1]123
《诗经》是西周的礼乐作品,仪刑文王就是以文王为刑,文王作为万邦之方,因此说礼乐不兴,那么仪刑和惩罚就失去了基础。再向前推,按照《礼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礼乐发生机制,那么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其中,礼乐指制礼作乐,亦即礼和乐。
按《师虎簋》记载,师虎接任其祖父的职务,王在册命的时候要求他要今余隹(唯)帅井(刑)先王令(命)[3]3421,“帅”就是率,刑就是执行照办的意思,也带有范式意味,刑的对象是王命。仪刑,可以是好,也可能是坏。甲骨文中就有“兹人井(刑)不”。“不”就是丕(表示大、很好、尊奉的意思),刑不,语义类似仪刑,与刑辟无关。按《师望鼎》说:克的文祖师华父对王室十分忠诚,恩惠万民,出入王命十分到位,得到很多的奖赏。王让尹氏册令为善夫,并告诉他必须对执行王命高度负责,赐给田地等财富[3]1515。从王言看,更重视王命的发布和实施。
根据《尚书》,大禹曾经询问过皋陶如何施行德政教化,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大盂鼎》③记载:九月,王在宗周给盂发话说,当年文王受天命安排,开始显赫,周武王建国打击犯罪,安抚四方,因此拥有天下。以美好的政治奉献给人民,工作期间滴酒不沾,就是祭祀的时候必须饮酒也没有喝酒,因此得到了天的尊重。法是四方安宁的保障。殷鉴不远,那么你要像文王学习效法,掌控正令、修德敬业。像你的祖父南公那样,对王室真诚,以和善的态度对待边民,不要动不动就动用刑罚征讨,只要记得对我负责就可以了。我赏赐给你人才、礼器,你去封地任职吧,一定不要忘记我的命令。为了表示对王的忠诚和感谢,以纪念祖父南公的名义,制作了这个宝鼎。
任职前赏赐和训诫是周王长期坚持的工作方式,目的就是为了长治久安。
六、西周的土地制度的建立和契约精神
田产交易一直被认为是春秋时期才有的典型现象,土地买卖关系的形成一直被看作是土地所有权即私权的形成标志[7]。《诗经·北山》关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句以及《礼记·王制》“田里不鬻”的记载皆非虚构。那么,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换记录作何解释?是否可由此认为西周时期已经存在土地私有?然而,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才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私有化的标志性事件[7],为什么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
从时间顺序来看,西周土地交换由中期的共王时代已经开始,由《卫盉》铭文起,宣王时期的《吴虎鼎》止,期间历经了懿王、夷王以及厉王三个时期,其中以记录共王和厉王时期的土地交换为最多。而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共王时期起,周王室已经开始显现颓势。“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四世,周政乏善可陈……王室多故,诸侯干涉王位继承……王威陵夷,也由夷王开始。”[8]203到了厉王时期,更是“西周崩溃的开始”[8]318。由此可见,西周的土地交换正是周王室不断衰微的背景下而逐渐兴起的。土地交换与王室衰微在时间上的契合并非巧合,相互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 西周中后期内忧外患所导致的王室存在的起起落落,必然伴随着各项制度的破坏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金文资料所记载的土地交换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卫盉》《九年卫鼎》《五祀卫鼎》《鬲从簋》《倗生簋(格伯簋)》《吴虎鼎》记载的金文资料中的土地交换的情形,除去个别篇目的当事人身份不易考察,综合各篇还是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土地所有权下移的脉络。无论是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还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土地交换,都是贵族宗主对土地享有处分权能的表现。金文资料中有六篇显示土地交换的流向是由上往下的,说明西周中期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开始了由上往下的转移趋势。这无疑是周王室对土地控制权力减弱的一种表现,即随着周天子可处分土地的减少,贵族阶级甚至平民对土地处分自由的扩大,土地离周王室越来越远。
金文资料中所出现的土地交换并非全部都是基于意思表示而产生的(也即自主决定的土地交换),部分土地交换现象是基于法律规定,如侵权后土地被当作赔偿物进行赔偿。首先,来看共王时期的四篇金文:
矩或取赤虎(琥)两、两鞈(韦合)一,才(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卫盉》)
厉曰:“余执龏(恭)王恤工(恤功),于卲大(昭太)室东逆□(营)二川。”曰:“余舍女(舍汝)田五田。” (《五祀卫鼎》)
矩迺(乃)(暨)(濂)(邻)令寿商啻(意)曰:“顜(讲)。”履,付裘卫林里。(《九年卫鼎》)
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取良马乘于(倗)生。(《倗生簋(格伯簋)》)
矩伯用土地分别换取的是马车等实物和朝觐用的物品,邦君厉则是为获取两条河流而以土地进行交换,格伯是为获取马匹等而用土地换取。以上土地交换的产生都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进一步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贵族阶层对于土地的处分已经相当自由。而土地交换发展到后来,其产生原因又有了新的变化:
唯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并叔在异为,(曶)厥小子戴以限讼于井叔……
昔馑岁,匡众氒(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曶鼎》)
凡復友(贿)復友(贿) 鬲从田十又三邑。(《鬲从簋》)
《曶鼎》中匡的家臣和农夫偷盗了曶的禾,于是曶告到东宫那里,也就是说土地交换产生的原因在于侵权引起的诉讼,侵权赔偿中土地是作为一部分赔偿物的。而《鬲从簋》中土地用来贿赂鬲从,并且达四次之多。土地既然可以当作侵权后的赔偿物和贿赂,说明贵族阶层享有的土地处分权能进一步加大。虽然土地当作一般等价物来进行交换说明土地国有制度的式微,但却并未将其全盘否定,即便是土地交换发展到西周后期,周王对于土地的控制还是存在的,《西周十二年大簋盖》记载的土地更换产生的原因在于周王将本属于睽的土地转赐给了大。由此可见,即便是土地交换发展到夷王时期,周王对于土地并非完全没有控制权。所以直接将土地交换等同于土地私有观点是不正确的。厉王时期同样也存在类似的土地转赐(见《鬲从鼎》)。土地交换的产生由合意交换发展到后期的当作侵权赔偿以及贿赂等是交换原因不断多样化的表现。我们可以推断,现实的西周社会土地交换的原因可能并不止于金文资料中所涉及的,多样化的土地交换原因是各级宗主对于土地的处分权能不断加大的表现。
根据《卫盉》《五祀卫鼎》记载,西周中期开始的土地交换规定了比较严苛的程序,当中的各项程序可以类比大陆法系民法中的物权登记制度,这些程序的规定或可说明中国的土地登记制度从西周时期起就已经存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不经登记不转移所有权,但是物权登记制度是为确定权利归属以及便利所有权转移,而西周土地交换中的不经程序不转移土地所有权则更多的是周王对土地所有权控制的表现。周王通过程序规定将土地交换的过程控制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之内,以保障自己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交换发展到后期,懿王、夷王以及厉王三时期的土地交换,金文资料中再无程序性的表述。

土地交换发展到懿王和厉王时期,周王及其官员要么完全消失于交换过程中,要么在当中起到的是中立性或可有可无的作用。从《卫盉》《五祀卫鼎》记录看共王时期有官员参与监督土地,到《九年卫鼎》中并未有官员参与,仅靠双方合意和程序来完成土地的转移,说明共王时期,周王就已经在土地交换中逐渐式微。而共王之后王室官员多数是作为土地纠纷的调解员或者记录员而出现的,其参与到土地交换中是在侵权、转赐得不到执行等纠纷出现之后才被动参与的。周王及其官员在土地交换过程中的参与度不断减弱是周王室对土地控制权减弱的最直观的表现。然而如《鬲从鼎》《吴虎鼎》中所记录的,虽说西周土地交换过程中周王和官员参与程度总体上是呈减弱趋势的,但其并未完全从土地交换中退出,其出现在部分土地交换事件中,说明西周土地国有制度即便发展到后期也并未完全崩溃。
判断土地制度的公或私,应更多地从权能的角度进行分析,而非从权利归属上进行简单的切割。西周土地王制破坏的根本在于土地处分权能的下移,虽然与西周时期的土地公有有很大不同,但是这样制度前提下的土地交换却可以给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提供很好的类比,不妨碍我们运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我国现有的土地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发生的各类土地现象,诸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这样的土地交换现象的发生,守住土地处分权能不能够转移这一底线,便不会有土地私有化的危险。而所谓土地交换应当是土地使用权能、占有权能及收益权能的转移,这符合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却也并不会破坏土地公有制的大前提。
殷周金文提供的法律思想和案例,体现了大道之行的轴心时代我国法律的成就和价值,关于治心、综合治理、法权下移、契约精神等司法理论与实践,是我国法律自信的基础和法治宝贵资源。
注释:
①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②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