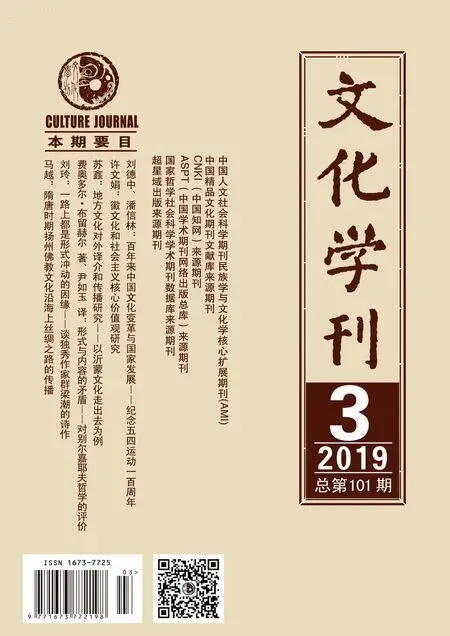阿特弗尔德生物中心主义思想的理论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杨 澜
罗宾·阿特弗尔德于1941年在英国伦敦附近的圣奥尔班斯出生,他是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学习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自1968年1月以来,他一直在卡迪夫大学讲授哲学,还曾在尼日利亚(1972—2003年)和肯尼亚(1975年)任教。他的威尔士博士学位于1972年完成,从1992年开始担任哲学教授。他是英国皇家哲学学会理事会成员,直到最近,他还是英国哲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作为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卡迪夫分校的主席,他积极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环境伦理学国际工作小组。
阿特弗尔德学术成果丰硕,截至目前,出版了4本著作和100多篇论文,最近的著作是2012年由Ashgate出版社出版的《伦理概述》,另外几本经典著作有2003年由polity出版社出版的《环境伦理学 :21世纪的概览》,2006年由Ashgate出版社出版的《创造、进化和意义》和2008年Ashgate出版社出版的《环境伦理学》。由此可见,尽管阿特弗尔德的学术研究涉及广泛,但环境伦理是其主要的学术关切。在上述几本著作中,阿特弗尔德较为系统地提出、论述了其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想,主要包括生物的道德关怀等级、生物内在价值和生物利益的公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选择等方面,具有个体论、生物利益选择的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动物道德关怀的扩展三大特征。
一、个体论
阿特弗尔德的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想较奥尔多?利奥波德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持个体主义与持整体主义。阿特弗尔德反对环境伦理学上的整体主义。他的观点是生态系统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个体事物才有可能具有内在价值,而具有道德地位的事物不外是有其自身的好的个体事物[1]。
阿特弗尔德认为,生物个体作为有机体是生态进化的实体。生态系统由个体生物组成。保护自然和尊重自然的实质也是保护和尊重个体的生命。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或者是对稀有物种的拯救,最终都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生物个体上[2]。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很多生态中心主义者持整体主义观点,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针对生物道德关怀的扩充提到 :“不仅从人扩展到其他生态系统成员,而且从任何一种个体扩展到整个系统……(一种)拥有价值的共同体。”[3]。也就是说,不仅所有的生物个体都具有价值,而且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都具有价值。奥尔多·利奥波德所倡导的大地伦理也是一种坚持整体主义立场的生态中心论。他的大地伦理学认为,生物个体,包括个人,在重要性上低于作为整体的大自然。他所看重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或者说大地共同体。在利奥波德看来,生物个体的快乐或痛苦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必然现象,与善恶无关;如果作为整体的大地共同体是好的,那么痛苦和死亡也是好的[4]。
基于这种整体主义,许多环保主义者优先考虑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虽然能够认识到物种和系统的生存对于个体的生存和福祉是有功能的,但认为最终应该重视的是物种和生态系统。个体的重要性取决于他们对物种或生态系统的贡献,或者对生物圈的贡献。在理论层面,这是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理论,它定位了整体的独立价值(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类似于社会和伦理理论,它们将社会的价值定位于整体,而不是其个体成员[5]。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而内部的个体价值是通过它们对生物圈的丰富、对系统的更好发展所体现出的贡献和作用来评价的,这是整体主义的思想。整体主义更关心的是个体能够支持生物圈的系统和生物的多样性,而不是最大化其中个体成员的内在价值和关注个体的存在。利奥波德在其大地伦理学中指出 :“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6]这是将保护一个完整的生物圈作为评判正确行为的标准,并且关注点在于生物共同体的系统性和多样性。
但阿特弗尔德认为,系统重要,是因为个体的生命依赖于它们,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生物圈系统对于保护所有有价值的生物是必需的,但这并不能说明生物圈及其系统就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显示它们具有工具价值,因为其本身具有价值的个体依赖于它们的支持和维护。无论生物共同体还是系统的多样性,都没有内在价值[7]。我们强调要保护生态系统,但我们不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去保护它们,而是为了依赖于它们的个体的目的去保护它们;并且,如果整个生物圈被看作具有道德地位,那么在最大化它的内在价值和最大化它的成员的内在价值之间就会存在冲突。同样,多样性也不具有内在价值。虽然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价值依赖于那些从生态稳定中获益的生物的价值,本身并没有价值。
阿特弗尔德赞同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应该获得道德关怀,但反对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他持一种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反对整体主义的价值观。
物种的利益,不仅是指当前个体生物的利益,也包括未来物种的个体生物的利益。保护稀有濒危物种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稀有物种被破坏,甚至是最后一个能繁衍后代的生物被灭绝,也就意味着这种生物将不再有后代的个体,这比杀害物种丰富的个体要严重得多;毁灭一个物种并不符合个体论的思想主张,但是,由于物种和生态系统不是活着的有机体,它们也就缺少自己的利益;而构成物种及种群的无数个体才具有真实的利益。
古德帕斯特建议,每个物种的成员拥有平等的道德意义,而不考虑它们不同的能力[8]。与之相反的,著名动物解放论者彼得·辛格认为,平等的利益应给予平等的关怀,这是合理的,但正是不同个体的能力差异会导致对它们不同的道德关怀。阿特弗尔德赞同辛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人类在有自主能力和愿望的生物与缺少这种自主能力和愿望的生物之间进行选择,第一类生物的生存优先于第二类生物的生存。这一优先原则普遍适用于伦理的准则[9]。没有生态系统,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生物生命也将不复存在,但是,这种道德关怀仍将被赋予那些由生态系统支撑而生存的个体生物,而不是生态系统本身。我们的主要责任是关注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考虑生态系统的任何退化或缩小问题。
二、生物利益选择的实践可操作性
当不同生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阿特弗尔德指出,可以通过区分不同生物的道德地位与道德重要性来解决。这就使得他的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具有更强的实践操作性。
(一)利益选择的总原则
针对生物的利益选择,阿特弗尔德提出了一个总原则——当生物拥有相同的利益时,就应给予相同的考虑,具有复杂高级能力的生物的利益大于普通生物的利益。他认同生物中心主义将所有生命的物体都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但他反对生物中心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思想。
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思想认为,所有生物的好的实现都有着同等的内在价值。但是,阿特弗尔德认为,所有生物具有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而且,泰勒理想化的生物平等主义思想并不能在现实利益选择上具有操作性。阿特弗尔德认为,只有通过区分道德地位和道德重要性才具有实践可操作性。树木不能像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感受能力,感受不到快乐和痛苦,没有欲望和目的,这样看来它们的利益的价值要少于拥有这些感受能力的生物,但这并不能说明树木就不具有内在价值的利益,而只是说明树木的道德重要性相较于有感觉能力的生物是极小的[10]。在实践中,有很多理由忽视树木的利益,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和动物的利益几乎总是更重要。再者,没有感受能力的生物具有内在价值,这是由它们的某种能力和状态所赋予。当一些个体缺乏繁荣的能力或者是先天或偶然的阻力阻碍了其生长,或是已经进入自然衰败的阶段时,这些生命便不再具有内在价值。由此,阿特弗尔德有了生物道德关怀的等级层次,人类的道德关怀与动物相同,属于第一等级,植物属于第二等级。特殊情况下也有明确的利益选择 :濒危物种的优先保护。利益选择的总原则即相同的利益应给予相同的考虑,当具有较大能力的生物的利益实现被危及时,具有较大能力的生物应该得到优先考虑。
(二)利益选择的优先性——濒危物种的优先保护
阿特弗尔德在生物利益选择中除了总原则——人类与动物的道德第一关怀,植物第二关怀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濒危物种的优先保护。
在《全球2000年报告》中有过预计,物种正在大量灭绝,在未来的几十年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物种将有可能灭绝。1966年国会通过的《濒危物种法》中提到,目前人类对物种的关心和保护远远不够[11]。基于对各种生命形式的责任,阿特弗尔德在论述生物利益选择优先性时又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濒危物种的优先保护。考虑到种群的数量、稀缺性和受破坏程度,如果一种物种种群的数量锐减,或处于稀缺状态,或严重受损,应对这些结果应当在价值和利益上进行加权,并给予优先考虑。
物种的灭绝有时候不仅仅是关乎某类物种的生死存亡,生态圈是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平均来说,每一种植物的灭绝,连带着会有十多种依赖于这种植物的昆虫、动物或其他植物遭到灭绝。这是一种连锁型的灾难性灭绝,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多种其他生命形式。阿特弗尔德在道德关怀的提升上肯定了所有生物的道德地位,尊重个体的内在价值,强调要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认为濒危物种的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一方面,濒危物种的优先选择是在给普通生物和濒危物种利益选择作出了一种利益考量。对于动物和植物道德关怀给出的利益选择的一般原则——动物大于植物,但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原则已经远远不够解决动物与动物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具体又如何进行利益选择的问题。由此,阿特弗尔德就给出了一个濒危物种的优先选择原则。另一方面,濒危物种的优先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现代人类及未来人类对医学和农业研究的兴趣、对科学调查的兴趣、对娱乐的兴趣,以及对自然的审美鉴赏兴趣也极力要求保护大多数物种及其相关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不能忽视荒野自然对人类的象征意义。濒危物种同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地位,而且它们有自己的利益。它们本可以实现其自身的能力,如果因为人类的阻挠而受到损害或死亡甚至是物种灭绝,考虑到未来人以及非人类生物的利益的关联,人类是有优先保护的道德义务的。
三、动物道德关怀的扩展
阿特弗尔德在动物道德关怀的扩展上,一方面是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进入生物中心主义的领域,提出人类与动物道德关怀等级相同的理论;另一方面,与泰勒等生物中心主义论者不同的是,特殊情况下,动物的道德关怀以及利益有可能高于人类。
(一)动物与人类的同等道德关怀
在阿特弗尔德的生物中心理论中,每个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都被包含在道德关怀范围内,并明确划分了道德关怀的等级,人类与动物属于第一等级,植物则属于第二等级。
针对非人类物种的道德地位,阿伦·奈斯认为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切物种皆平等[12],以及菲利普·迪瓦恩认为人类优于非人类物种[13],阿特弗尔德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考察非人类物种,尤其是动物的道德关怀,应该从利益平等原则和自我意识及能力两方面来看。
利益平等原则指的是一个行为所涉及的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都应该受到关怀,并且相同的利益应给予同等的关怀[14]。以彼特·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者认为 :“快乐是唯一的善,痛苦是唯一的恶,如果一个生物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满意和沮丧的能力,那么它们都应该被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之中。”[15]阿特弗尔德认为,辛格的这种观点虽然肯定了非人类物种的道德地位,但是并不赞同没有感觉快乐和痛苦能力或潜能的那些存在物就没有利益。
人类能够在自主选择、交友、维护自尊和免受痛苦方面拥有利益;而非人类的生物,无论有无感觉能力,通过发展自身特有的能力,在以自身方式繁衍生息方面也同样拥有利益[16]。有利益的存在物就有道德地位。
任何道德考虑的关键因素要么是看其承受能力,要么是它有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自我意识。大多数非人类的动物都有这种能力,尽管程度不同;而且,只要他们是有意识的,有自己的观点,从这些观点出发,事情可以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糟[17]。非人类的动物应该被考虑到与人类具有同等的能力,动物有自己的意识,有自主选择性和其他的一些与人类相同的能力,理应与人类具有同等的道德关怀。
一方面,阿特弗尔德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的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和利益、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人类赋予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意味着,当人类以一种意识附加于一件事物时,那些尚未被人类评价的事物就会突然从无价值变为有价值。但在很多物种还没有被评价的情况下,就断定它们是无价值的,这是没有合理根据的,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阿特弗尔德吸取了边沁、雷根等人的思想,认为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和绝大多数无感觉的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都应该受到道德关怀。动物与人类同样拥有这种能力,应将动物的道德地位提升到与人类同等的地位[18]。
(二)动物高于植物的道德权衡层次
阿特弗尔德已经论证了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是这些生物的道德地位是有所区别的,即动物高于植物的道德权衡层次。
阿特弗尔德首先论证了植物也有道德地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应该获得道德关怀,是因为其本身的性质或者具有某种感受能力,比如能够感知快乐和痛苦,而动物也是如此。但运用到植物身上,这种理论便无法支持了。阿特弗尔德在《21世纪环境伦理学》一文中提到 :“在任何情况下,拥有过适合其物种的生活的能力是具有自身利益和好的充分条件。”[19]这是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所共有的东西和特质。这就支持所有生物,包括无感觉的生物,如植物,都有自己的道德地位。所有的生物都有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发展和实现的可能性显示出生物具有自身的好。植物能够汲取水分、阳光,利用光合作用维持自己的生命并繁荣生长,这说明了它们有自己的需要、利益和好。
植物有了自己的道德地位,另一问题便是同其他生物相比,植物的道德重要性低于人类和动物。阿特弗尔德将植物的道德地位划分在人类和动物之下,并给出了充分的依据。首先,道德重要性与生物的能力差异相关。植物缺乏感受能力,无法感受快乐和痛苦,也不像人类与动物有目的和欲望,这使得它们的利益的价值低于具有这些能力的生物,这说明了植物的道德重要性相比人类与动物具有感受能力的生物要小得多。其次,阿特弗尔德反对生物平等主义中将所有生物的道德地位平等看待。所有生物都有其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所有生物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
四、阿特弗尔德生物中心主义思想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启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紧密互利、不可分割的关系。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一种自然链,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实现循环。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健康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阿特弗尔德对生物道德关怀的扩展,肯定了生物的内在价值,给出了生物利益的选择顺序,跳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绝非对立也非人类凌驾于自然,也不是简单统一,而是生命共同体等思想内容,正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哲学理念。这对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发。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实现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破坏、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等,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将会制约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影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阿特弗尔德对生物道德地位的扩张和生物利益的选择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其个体论思想突出生物的内在价值和道德重要性,对于促进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有重要参考价值。对生物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对所有生物的道德关怀,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从而可以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
五、结语
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吸收借鉴包括阿特弗尔德在内的一切环境伦理思想,树立生态价值观,形成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