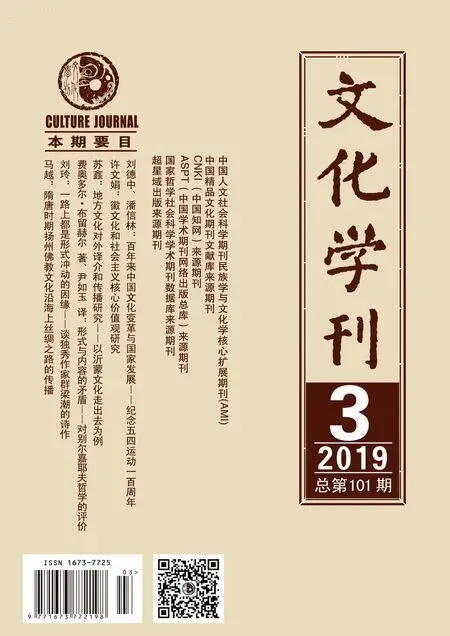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的接受美学思想探微
牛梦珍
距今一千五百年之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专篇中就强调了鉴赏文艺作品时,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 :只有经过“观文者”的阅读鉴赏,“缀文者”创作的文本才能变成审美对象,作品的价值方能得以实现。以往学界多从批评论、鉴赏论、批评鉴赏论的角度界定该篇,却往往无法准确掌握其理论底蕴[1]。原因之一在于《知音》篇不单是为了阐述批评或鉴赏问题,其中还时刻流露出一种读者意识。无独有偶,于联邦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对读者接受过程及规律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接受美学将研究的角度集中在接受者及接受活动中,认为在接受阶段读者才是文学活动的主体。
一、《知音》篇中的读者意识
中国古人倡导礼乐制度,“礼乐刑政”并举。成书于西汉的《乐记》,是中国儒家音乐理论的专著,这里的“知音”用了本义,即通晓音律之义。而在《吕氏春秋·本味》中则以“知音”喻知己。发轫于汉末的知音论,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业已成熟[2]。就文艺鉴赏而言,知音便指对作品能进行深入理解并给予正确评价的人。
先秦轻文学理论阐发,重文学创作实践,是以到了魏晋,仍有不少文人讥笑文学理论是雕虫小技。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后,曾请师傅僧祐、太学博士何思澄指点,且多次求见南朝齐梁大家沈约品评,虽终受赏识,但经历甚是坎坷。有感于贤能之士多被埋没,刘勰思之怆然,写就《知音》。而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知音”,寻的便是对作者文心的体察,对作品的认同。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作者的本义视为唯一金科玉律显然不可行。在文本创作完成的境况下,接受者的能动感知既包括接受者对文本的直觉感受能力,也涵盖对作者所思所想的理性分析。千古悠悠,许多作者的生平已不可考,其为文时的心路历程更是无从追索。自知尚属不易,勿论他知,且文学用语多忌讳直白,读者在文本的深层蕴藉中,想要心领神会作者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不妨换种角度,在关注作者、文本之余,依靠接受主体阐释文本,也不失为一种妥帖的诠释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也讲“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这就是在肯定读者阅读的再创造性质。可见,“接受美学”这个概念虽源自西方,但文学接受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
《知音》篇便从始至终都有着鲜明强烈的读者意识。首先,审美接受主体受限,会导致知音之难。其次,从外在层次看,种种成见会混淆蒙蔽自我审美感受;从内在层次看,客观上“文情难鉴”,主观上接受主体存在“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的审美趣味差异。在此基础上,刘勰以“博观”指导接受主体提高自身的审美鉴赏能力,用“六观”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鉴赏方法。至于《知音》篇的最后一部分,涉及的则是文学接受的途径问题。
二、反观《知音》篇中的接受美学思想
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构成了对传统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的挑战,认为读者是未参与创作的作者,读者的接受才使文学活动顺利完成。这里读者的鉴赏不再被看成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3]。姚斯把对文本的理解过程视为文本完成与读者阅读相合璧,即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当文本与读者的既定心理图示一致时,读者能很快完成阅读,对文本的理解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障碍;但若读者的既定心理图示与文本不一致乃至相对时,就需要读者打破原有的阅读经验,重新解读文本。
首先,接受主体的审美趣味、性格气质等,会导致其对文本产生不同的情感倾向。在《知音》篇中,刘勰也清晰地指出了接受主体会根据自己的期待选择阅读对象,人们总是对符合自己口味的作品称赏,对不符合的就不加理睬或束之高阁。此外,刘勰为了考察文本中的思想感情所提出的“先标六观”法,对文本体裁、词汇、表现手法、结构等方面的关注,体现了当时士人对于为文优劣的评判标准。这种集体性期待视野,亦展现了刘勰所处时代对于文学作品鉴赏或批评时的某种广泛社会共通性。
其次,接受主体对文学的艺术鉴赏,与自身在漫长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审美能力密不可分,这就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审美素养,并不断拓宽自己的期待视野。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提出了“空白”结构概念,即是说作者本人在创作文本时,留下了“空白”,而这些“空白”召唤着能将文本具体化的读者前来交流[4]。接受美学用“隐含的读者”表示作者设定的特定类型的读者。中国古代文论也看到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对作品作出正确解析,刘勰所说的“见异,唯知音耳”中的“知音”也合此义。知音之难,不仅难在接受客体纷繁复杂,“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更难在读者对文本的领悟程度上。这就需要读者努力提升自己的学识与修养,培养高超的赏识力,达到晓声识器的高标准。正因多读多品,接受主体的审美心胸方能随之扩大,在阅读过程中就能不以个人喜好评定文本,从而对文本价值作出公正客观的评论。
最后,文学接受也注重对读者接受效果的研究,其目的是使接受主体通过文本的引导,获得审美愉悦和情感体验。而要做到见解深刻,洞悉作品深意,读者就要和文本发生深层次的情感联系,能被文本打动,从而与之达成情感的共鸣,净化乃至超越自我。
艺术鉴赏并非一次性的直线运动,读者和文本之间会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交流。艺术水平越是优异的作品,越会暗藏“未定性”和“空白度”,这样纵使斗转星移,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也不会因为时空差异而损减分毫。按照伊瑟尔的看法,在具体的文学阅读活动中,其内部会存在一个不断运动的游移视点[5]。“游移视点”是接受主体得以在文本中存在的一种手段,是读者领会接受对象的独特方式。游移视点的主要性质和功能是联结、转换、修改、综合。中国古典诗文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境。无论是对炼字炼句的精雕细琢,对叠字叠词的匠心独运,抑或以典入诗时的别出心裁,在增强诗文艺术性的同时,也给读者设置了阅读障碍。受众对其爱不释手、一咏三叹,原因在于读者于阅读活动中,会不断自我分离和重塑,从一个视点转向另一个视点。这种对作品空白和未定点的填补,时刻受到作品本身的限制,这也就很好地防止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出现太大偏差。是以欣赏者倘能做到“披文入情,沿波讨源”,自然可以在字里行间俯仰天地。
三、中西文论对话下的审美启示
不同理论的碰撞磨合,有助于人们广开思路,从多种角度看待文学领域出现的普遍现象。比如 :刘勰谈到曲高和寡的文学现象时,痛惜世人多抛弃深刻作品而欣赏浅薄之流,知音难求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各类文学作品在市场上也是良莠不齐。但真正高品质的作品,无须迎合大众,自有从容玩味者。接受美学虽不认可艺术作品有永恒性,但因其丰富了“读者”的内涵,使得更多的受众能够参与文学活动中。既然读者在文学活动中占据着决定地位,那么自不惧文情难鉴、知音难遇,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意。
四、结语
将对读者的重视,视为中西文论对话的契合点,就能借助异质文明中产生的接受美学理论,挖掘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审美意蕴,这样也有利于建立我们民族的理论自信,在求同存异的互证过程中彰显自身特色。因此,我们不能囿于外来理论本身,而要结合中国文论自身特点进行辨析,由此构建中西文论、中西文化思想的对话、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