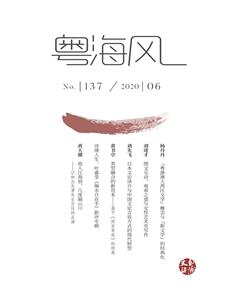光影流转中的“诗”与“禅”
刘海玲
摘要: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讲述了叶嘉莹先生在诗作、诗学、诗教中的人生经历和诗学理念,以及导演在空间、雅乐、物象等镜语中包蕴的人物理解和美学观念,在“声画”“虚实”“情景”“有无”等交融和谐中显现着中国传统的“诗”与“禅”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叶嘉莹 电影 诗词 禅意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片名出自【唐人于良史的《春山夜月》诗】:“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诗人沉浸在春山、皓月、清泉、芳菲、远钟、楼台交融的意境里,沉醉忘归。本片传主叶嘉莹先生一生研赏唐诗宋词无数,导演陈传兴却独取世人不甚熟知此诗此句为片名,可谓独具慧眼,别出心裁,最能切合并传达本片特有的美学意蕴:以手掬水,月在水中,亦在手中,亦在心中,我亦化入其中。恰如叶嘉莹先生笑言:影片中的我不是我,是镜中人。
陈传兴导演说,我们太习惯西方的电影美学,比如绘画,会用西方的透视观看西方的绘画,“所以,我一直在摸索,是不是有可能有一种很特殊的电影叙事方式,是用中国古诗词的方式。在《掬水月在手》里,我想要去尝试,有没有可能,去找到一种真正中国的叙事美学”[1]。陈传兴导演早年留学法国,师从符号学家麦茨,专注于视觉与影像的美学研究,融合中国传统美学,主持策划了《他们在岛屿写作》等6部纪录片,并担纲其中《化城再来人:周梦蝶》《如雾起时:郑愁予》两部的编导。《掬水月在手》是其“诗的三部曲”的终章,在本片中,陈传兴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哲思和美学旨趣,与传主叶嘉莹先生的精神气质适相契合,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中“诗”与“禅”水乳交融的镜像风格。
一
陈传兴导演在《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序中写道:“这系列影片的每位作家,都是台湾当代文学的群峰”,“社会事件式的纪录片手法,即兴与等待事件发生的拍摄方式,显然地不适用”[2]。《掬水月在手》也是如此。96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出生于国民革命开始的1924年,经历了整个中华民族上半叶的战乱,国民党退守台湾的白色恐怖,执教并迁居美国、加拿大的动荡生活,往来祖国经历改革开放40年直至定居南开大学的诗教生涯……叶嘉莹先生的个人命运与动荡的20世纪中国紧密相连。
但影片并未从某个客观视点扫描这个大时代,大社会,而是首先把传主定位为一位诗人。“回首从前,很多详细的情况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幸好我有作诗填词的习惯,很多经历感悟都通过诗词记录了下来。”因此,本片的一条重要叙事线是以时间为序,以叶先生创作的诗词为纲,从1939年第一首诗《秋蝶》开始,到2007年创作的《绝句二首》,叶先生一生中每一个重要的生命感悟、悲喜经历、时空节点,都由诗歌作导引进行追述。如第一次诗歌处女作、少年时陪女同学经历的约会、母亲突然病逝的痛悔、与老师顾随先生的诗词应和、接到久无音讯的父亲来信的感慨、经历台湾白色恐怖寄人篱下的日子、哈佛讲学后的留别、温哥华备课时的情景、初回祖国大陆的激动、痛失女儿女婿的悲伤、在南开诗教生涯的感悟,等等。从诗歌写作的缘由、情感到剖析每首诗歌重要词句对生活经历的概括和隐喻,诗歌创作与人生经历相融合。“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叶先生这句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价也是她本人的写照。
诗人与父母、女儿等至亲的真挚情感在诗中倾泻而出。“噩耗传来心乍惊,泪哭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哭母诗》八首之一)”“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母亡后接父书》)”“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转蓬》)“”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哭女诗》十首之一)”
诗人对故乡和祖国的思恋,以及回国的喜悦寄予诗中。“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转蓬》),“昨夜明月动乡思”(《浣溪沙》),“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再吟二绝》),“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祖国行长歌》)”
有對诗教生涯的执着、困境与希望,“变海为田夙愿休”(《梦中得句杂用义山诗足成绝句三首》),“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鹏飞》)”“白昼谈诗夜耕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遥天谁遣羲和月,来送黄昏一抹红。(《七绝一首》)”“柔桑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鹧鸪天》)”
有贯穿诗人一生的人生哲思与禅道之意。“三生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秋蝶》)”,“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学禅未必堪投老,为赋何能抵送穷。二十年间惆怅事,半随秋思入寒空。(《晚秋杂诗》)”“便觉禅机来树底,任它拂面雪霜飘(《庭前烟树为雪所压》)”。叶嘉莹先生19岁写就的诗句“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用在她90岁时建成的迦陵学舍的门楹,“这两句我很喜欢,因为这代表我做人做事的态度”,“立身处世的理念”。叶先生用自己的原创诗词,连缀起时间的经线和北平到台湾,以及纽约、温哥华,天津的空间纬线,织进了对至爱亲朋、师长后学的情感温度,关于择辞用典、附声采韵的诗学趣味。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庆明在片中说,“文学是一定要有生命主体的介入才会真正精彩。我一直认为,叶老师的诗词,是了解她的最好途径。”
二
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诗人和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教学。穿越千年光阴,叶嘉莹先生解读杜甫、李白、李商隐等伟大诗人的诗歌精神,并阐释了“兴发感动”说,“弱德之美”说,“词体缘起”说等诗学理论。但作为纪录片,既不可能全面介绍叶先生深厚系统的诗学理论,也无法通过片段实录展现叶先生授课的诗教至境。剧组历时三年远赴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地区)的几十个城市,采访了四十多位与叶嘉莹先生有交集的朋友、同事、学生、邻居,并对叶嘉莹本人做了十七次深度访谈和实录。关于叶先生的诗学和诗教,采用了“主辅和音,和而不同”的呈现方式。
由叶嘉莹先生陈述、解说或吟诵为主调。从最早的诗教启蒙“朝闻道,夕死可矣”,求学生涯对诗歌的领悟,到经受苦难后“开始欣赏杜甫诗的好处”,一字一字誊抄整理关于《秋兴八首》评注的研究过程;从诗歌用词用韵的鉴赏评点到融入自我情感美感的古音吟唱,用具有代表性的诗句和诗人带出“兴发感动”“弱德之美”等诗学概念。叶先生与古典诗歌、诗人的精神遇合串联起庞杂散乱的材料,勾连起叶先生的诗学脉络。
众人言说作为和音。依据叶先生的生活履历,依次穿插台湾时期的白先勇、痖弦、席慕蓉等,哈佛时期的郑培凯、田晓菲、张凤等,温哥华时期的刘秉松、陈山木、谢琰等,南开时期的陈洪、徐晓莉、张静等几十位同事、友人、学生,邻居。这些学养深厚、身份独特的受访者,讲述他们亲历的叶先生的诗教学问和人格魅力。痖弦说叶先生是“穿裙子的士”;席慕蓉说叶先生“讲辛弃疾的时候,你会觉得辛弃疾本人来了”;施淑说,“从没有见过一个人把文学作品用口头语言诠释的那么好”;刘元珠说,“她是真的很爱国”;白先勇说,“唯有具备佛家的心胸才能如此悲悯,而叶先生就是具备佛家心胸的”。在讲述者的讲述中,还有言说不清、言说不尽的悠长空白。比如好友刘秉松女士讲述爱女离世后的叶先生:“参加完葬礼,回来还照常去工作,见到同事朋友,最多眼圈一红,就过去了”。影片结尾处,刘秉松女士简练并略有停顿的语气:“这一生很难遇到像叶嘉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少有。”云淡风轻中却饱含了令人遐思的无限余味。
“腹有诗书气自华”。由众多诗人、诗歌爱好者和诗歌研究者进行言说的叙述方式,个性化的声音、言辞、表情,叙述者的性格、经验、修养,以及讲述者特有的交往情景和个人感受,还有叙述者在丰厚的人生记忆中寻找、梳理有关经验的思维质感,再经影片的精选剪辑,一部纪录片的本事就呈现出声情并茂、意义外溢、余味悠长的诗学效果,蕴含着情、景、理的艺术之境得以呈现。
三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从个人的幽微记忆开始:一片清雾弥漫的水面上静泊着一叶小舟,画外音响起,“您第一次记事,是什么时候?”叶先生略带北京口音的画外音,“是在4岁的时候儿”,蕴含中气却依然苍老的声音像是划着桨橹的一叶扁舟,把观众,也把传主自己渡到迷离久远的时间彼岸。
文字为载体的诗作、影像构成的照片作为叶先生人生实历的证物,传主及众人的讲述作为叶先生诗学诗教影响力的证词。但是,“叙述的对象并不是原生事件,而是意识事件。叙述者面对的并不是作为客观发生的事实事件而是经过意识和记忆反应之后的往往不在场的事件”[3]。叶先生一生所历,依然是向记忆深处唤回的模糊影像。“自我记忆的邀约,很少人能抗拒”,“记忆有如影随形,从生至死不离不分的伴随者、守夜人”。但记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神场域,“分享记忆的不可能就像集体记忆的神话一样,都是拟真的假设。第三人称的传记书写,构建他者的记忆,迂回进出邀约与拒斥”。[4] 对客观实存的信息在记忆中的保存、变异和丢失,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命题。除了文字图像之类的物证固化,根据记忆的空间特性建立并强化内在记忆的方法被称作“记忆术”。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记忆术”都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这种依空間顺序安放记忆的方法叫作“记忆宫殿”并传授给中国人[5]。法国哲学家斯东·巴什拉认为记忆“是静止的,它们越是牢固地被固定在空间里,就越是稳妥”[6]。“如何面对他者的记忆,创造适度伦理场域转化记忆独白的邀约,成为分享的责任”。[7]
陈传兴导演是否受到西方记忆术的影响不得而知。关于记忆的表征方式却是一致的,“记忆其实就像一种空间,一种集结”[8]。无论是为了记忆建造空间,还是利用空间印证记忆,关于时间的记忆和空间的表征融合为一体,和谐地呈现在影片结构中。镜头对准叶嘉莹先生的祖居察院胡同23号四合院,建筑的空间结构成为追溯生命历程的时间标识,“大门”安放着宗族家谱,“脉房”为伯父对她的诗歌熏陶,“内院”是求学时与老师顾随诗歌的唱和与诗艺的成长,“庭院”和“西厢房”是辗转美国、加拿大的诗教西传,到了第六章,建筑的空间标识成为“无”的省略。
空间的从有到无,从现实层面也许影射叶先生的祖宅故居在2003年被拆除,或隐喻叶先生从自己的故居出发游历世界后再回到祖国到草原上的一次寻根之旅,“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从哲学层面,则隐喻从传主的生活实存进入到悠深亘远的精神世界,以及由外而内、由远及近、由实入虚,进入到本片的核心概念——中国诗歌“中有千壑”的“诗境”之中。陈传兴导演以西方现代哲学框架下的记忆为起点,通过记忆、回忆的长廊,过滤生命中的大悲大喜,沉淀了生命的至纯,最终通向了彻悟生命的东方美学之境。那么这个“无”,是不是也隐喻着由外而内,从有到无,最终融入到传主自然超脱广阔无边的生命世界?
四
叶嘉莹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蓝鲸的声音能穿越苍茫大海,最终找到彼此,“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叶先生对古诗词的吟唱独具特色,几无人及。她主张吟诵者不仅是还原“平仄上去”的古音和原有古韵,也是自己对诗歌的深切理解与“诗魂”的一次相遇,“诗人的意境情感在你的声音里复活,这就是吟诵”。陈传兴导演则说“叶先生的吟诵,就像萨满一样在祈求天地的神灵”。吟诵之声,与《掬水月在手》悠长深沉的音乐一起,如空谷足音,叩响了心灵之门。影片的音乐主调是依杜甫的《秋兴八首》由日本著名作曲家佐藤先生创作的雅乐《秋兴八首》。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先生重要的诗学成果。叶先生对杜甫的诗歌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谈到我国旧诗演进发展的历史,无疑唐代是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9]“不仅使杜甫在诗歌的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达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贯汇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养与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种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的合一。”[10] 而杜甫的《秋兴八首》,“无论是内容还是技巧,都显示出杜甫的七律已经进入到一种极为精醇的艺术境界”[11]。因此为《秋兴八首》谱曲并作为主旋律,彰显的是杜甫的诗歌与人格,以及叶先生的诗学与品格。
雅,正也。雅乐,即典雅纯正的音乐。曲风庄重、浑厚,是一种宫廷和祭祀的音乐,在西周时期即已形成。唐时传至日本并保留至今。陈传兴导演远赴日本唯求为影片配乐,可见他对音乐的独特旨趣。《秋兴八首》选用琴、筝、筚篥等,辅以西洋弦乐,加一女高音和一男中音的歌咏。筚篥是在汉代由胡人传至中原,并于唐代盛行。唐代杜佑撰《通典》中说:“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音色深沉、浑厚的筚篥可以表现圆润不断,委婉起伏的持续长音,常用于民间、寺庙之中,具有表达情感的独特冲击力,尤其擅长表现凄怆、悲愤、激昂的情绪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自周以来就极为重视乐声,在《礼记·乐记》中音乐发展成为“审乐知政”的传统,由音乐曲风即可知一城一邦的民风与政治。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编撰的《诗三百》,亲自为“大雅”“小雅”“颂”等辞章“弦歌之”,并肯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12]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13]。“和”,即和谐统一,是艺术最基本的品格。音乐的美感与“心平德和”联系起来,成为君子的操行,体现了“善”的伦理价值。陈传兴导演说:我花了很大精力投入到声音设计。让吟诵与讲述形成和谐音场。诗词产生的盛唐时期,我让雅乐回来,形成声音的层次,丰饶的肌理,形成了“副歌”的多声部和鸣(《掬水月在手》广州方所见面会,2020年10月11日)。叶先生的讲述、吟诵,是向自我的生命的深处汲取清流,与古诗人的诗心诗情形成荡涤千年岁月的回响与交融;他者的讲述是在记忆中萃取最深刻的印痕,外化为可感可敬可亲的传主形象,并彼此形成声部的互补和回响;雅乐《秋兴八首》的声音则是杜甫为代表的古典诗人与今人的灵魂尝试一次遇合,实现了“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善”的最高境界。
五
无论是叶先生作诗解诗经常说到的“禅”字,还是众人对叶嘉莹先生慈悲胸怀、淡泊宁定的感叹,还都不足以表征影片中必然的“禅意”。当雅乐《秋兴八首》的乐音“神圣性、宗教性的吟唱”响起,自然物象的枯荷、幽竹、雪丛,建筑物象的门廊、屋檐、庭院,生活物象的石砚、织物、锦缎,古迹物象的壁画、碑刻、铜镜、石雕等,以静态影像反复、舒缓地浮现时,“禅定”二字自然生出。
陈传兴导演说,命运里不可抗拒的偶然,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淡淡的“侘寂”的方式呈现。但是我们怎么用具体的美学实践,应有新的可能性。陈导在访谈中多次说到的“侘寂”一词,起源于中国宋代的道教,后传入佛教禅宗,再傳入日本,成为日本美学中的专有概念。“侘寂”美学在视觉艺术的表达中,常常以一种静定简约的线条、光影造型,呈现为一种“空”“静”“古”的审美心境,代表一种用宁静超脱的心态看待不恒久、不圆满和不完美。
“侘寂”的美学表达,核心是“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陈传兴导演所说的“新的可能性”,即是与“侘寂”美学暗合的大量空镜的运用。空镜之象,是节奏、是韵脚,起承转合着叶先生讲述中的一生。空镜之意,与叶先生所创造的“弱德之美”、与陈传兴导演所说的“这也是一部女性版的‘百年孤独”相关。空镜之味,则如影片无名字的第六章,“整个回到了‘无和‘空的状态,寓意叶先生度过了近百年人生,回到一种更为纯粹的状态”。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影片结尾的空镜,即是这样一幅图景:在洁白的雪地上一串孔雀的淡淡的爪印蜿蜒而去……此种“空”“无”之境,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精思,可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叶先生身处尘世之中,内心却要永远保持一片清明。而艺术的理想境界亦是“澄怀观道”,在语词声乐光影意象中抵达微妙至深的禅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注释:
[1] [8] 行人文化,活字文化 编著:《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297页。
[2] [4] [7] 王耿瑜 著,目宿文化 编:《他们在岛屿写作》,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9、20页。
[3] 尤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17页。
[5] 史景迁 著,陈恒、梅义征 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6] 戴维·哈维 著,阎嘉 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由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3页。
[9]《迦陵谈诗》,叶嘉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7页。
[10]《迦陵谈诗》,叶嘉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1页。
[11]《迦陵谈诗》,叶嘉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1页。
[12] 王忠林 编:《荀子读本》,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307页。
[13] 蔡锺翔,邓光东 主编,陶礼天 著:《艺味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