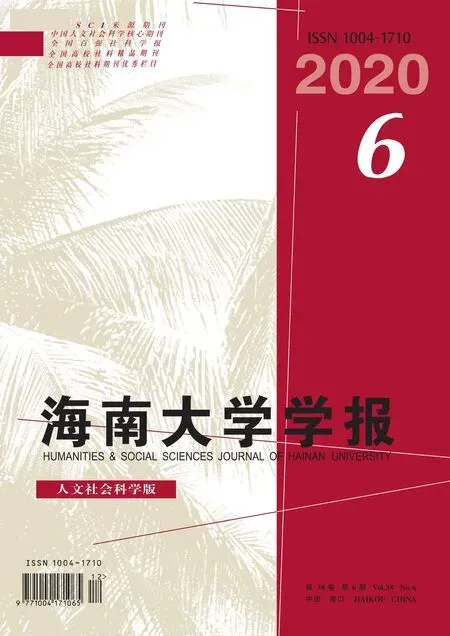阳明学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刍议
彭丹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010)
理学兴起后,孔子在以尧舜为起始的道统传承统绪中之地位成为一个关键的诠释问题。此问题蕴含了一个内在两难:一方面,孔子在历史的先后序列中处于尧、舜之后,如果道的传承是线性的、内容一致性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后来者比开创者具有价值的优先;另一方面,理学道统本身所蕴藏的师道又有着超脱于政治现实的价值优越,使其必须要将孔子这一无位者放在比尧舜更高的地位上,以树立超越现实权力的典范。
在中晚明,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也是阳明学在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早岁学于王门,后来自立门户的李材即“每挈以发友朋,谓是儒门中一个大公案……以为此真学脉所由分”(1)李材:《见罗先生书》(卷十一),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9页。。当代学者邓志峰指出:“争论尧舜与孔子高下,是晚明师道复兴思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邓志峰所说的“师道复兴”,主要是指王艮和泰州学派“处则为万世师”的观点。不过,总体来看,相对于朱子学道统思想研究的兴盛,学界对阳明学此方面的关注明显不够。本文拟对阳明学的有关论述加以考察,以期揭示其对于阳明学和整个道统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问题起源与程朱的“事功说”
在探讨阳明学的相关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思想史上的问题缘起和相关诠释史,为后文论述提供背景。《孟子·公孙丑上》最早提及尧舜与孔子的高下问题。先是设问:“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孟子说:“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又说: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5842 页。
这里记载了孔子弟子们对于孔子的种种赞美,其中宰我更明确地说“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但所谓的出类拔萃,《,《孟子》中并没有说明原因,这就给后世提供了各种诠释空间。汉赵岐注指出孔子在政治上虽无王位,但已能制作和尧舜相提并论的“素王之道”,“如使当尧舜之处,贤之远矣”(4)焦循:《孟子正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17 页。。同时,赵岐又认为,说孔子乃“生民以来无有”的原因是“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也”(5)焦循:《孟子正义》(卷六),第218-219 页。。赵注兼“素王”和“赞美”二意,成为后世种种解释的鼻祖和滥觞。
道统角度的解释发轫于理学兴起以后,程子解释《孟子》此段道:“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6)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76 页。此语未标明是二程中谁之语,不过很可能为明道语。程子未明言其事功究竟何指,朱子则推演程子语说“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34 页。程朱的“事功说”影响很大,成为其后学者评论“夫子贤于尧舜”一语的根据。如朱子弟子辅广就从事功久远和事功始终成就两个方面诠解程朱之言:
“语圣则不异”,以其德言也;“事功则有异”,就其所为事与成功而言也。“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此言事功久远之不同也;“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此言事功始终成就之不同也。(8)周群,王玉琴:《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823 页。
所谓“事功久远”,是指尧舜乃一世之功,孔子乃万世之功;所谓“事功始终成就”,是指尧舜不过起始,而孔子则为后世确立了终极标准,辅广另有言“当时若无孔子,今人连尧舜也不识”,即是此意。程朱一系相关诠释的内在精神都是着眼于孔子拥有尧舜未有之事功之上。此所云事功,非是尧舜治理天下的实绩,而是垂教万世、继往开来的功业。孔子对于道的发扬光大使得后世继道者有了凭藉依靠,因此其地位在尧舜之上。这种解释的实质在于指出道统中的后来者孔子,对初始者尧舜的治道进行了推演扩展,使道摆脱了难以认知传承的限制,获得了万世相传的可能;而推扩的具体形式可以理解为儒家垂教万世之经典文本的生成。《宋史·道学传》指出:“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9)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2709-12710 页。这样,程朱所谓的事功乃至于道实际上就更可能理解为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圣学传承。朱子后学元儒陈栎就在这个意义上用横渠“四句教”称颂孔子:“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业岂不贤于尧舜远哉!”(10)周群,王玉琴:《四书大全校注》,第823 页。
不过,朱子对于此问题的理解还蕴含着另外的深意。朱子有时也区分道统和道学,认为道统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到周初之圣贤所传之道,其特征是传道者皆是有位之人,可以治天下。周公之后,内圣外王分裂,孔子“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15 页。朱子有没有严格区分道统和道学,学术界有很多争论。笔者认为朱子虽然在用词上有时混淆,但其实有此用心。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18-24 页。。显然,通过对孔子无位却继往开来的定位和强调,朱子凸显了其中所蕴含的无位而有道者对于有位者的价值优越和规范批判权力。这种“士大夫主体精神的理论建构”(12)朱汉民:《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哲学动态》2020 年第7 期,第37 页。的师道思想,成为后来理学衡定孔子道统地位的基本格调之一。
二、王阳明的“精金喻圣”说
相对于朱子,王阳明对尧舜与孔子地位高低的看法是颠倒性的,这典型地表现在阳明自出机杼的“精金喻圣”命题中。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就好比“足色”的精金之所以为“精”,是因为“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的缘故。不过,圣人才力如金之分两,也各有不同:
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1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34 页。
阳明以精金的判断标准“在足角而不在分两”来譬喻“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所以即使是凡人,只要一心向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1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34-35 页。。
阳明“精金喻圣”的比喻在当时门下就有疑义。有弟子质疑阳明为什么把尧舜说成“万镒”而把孔子说成是“九千镒”。阳明答道此只是从“躯壳上起念”,而为“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在阳明看来,圣人“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如何使得自己的“足色之金”能够永远保持不变,这才是人们应该关注的(15)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38-39 页。。
不难看出,“精金喻圣”说主要关注此心是否精纯,“分量轻重”只是各人才力之差别。然而,虽然此说本来的用心并不在于评骘尧舜与孔子的高下,却泄露了在阳明心目之中,尧舜地位高于孔子的消息。因为既然两者纯乎天理之点并无二致,那么就很难不让人生发出尧舜高于孔子之感。阳明让人只论精一,不论多寡恐怕难以如愿。因此有弟子又对“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不能释然,并且一再请问。阳明乃以《易》作答,认为:
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二圣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间矣。孔子则又不同。其壮年之志,只是东周……自许自志,亦只二圣人而已。况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精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尧、舜,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97-1298 页。
阳明此答和前两次谈及“精金喻圣”不同,正面陈述了何以尧舜分量重于夫子。他指出,孔子只是玩《易》学《易》的“好古者”,尚且比不上演卦演爻者如文王周公,若比之于用《易》的尧舜,则“孔子亦不自安也”。依阳明此处的语义,恐怕在其心中,孔子与尧舜不是只有千镒之差,孔子不如尧舜可谓远矣。而此点可能是阳明一贯的看法。阳明曾经明言“中国圣人,以尧舜为最”(1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第358 页。,“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1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16 页。;对孔子则持保留看法,“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1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第94 页。。阳明对孔子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关联于对六经繁文文教价值的质疑:“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2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10 页。这反映出心学对经典文本的忽视,阳明的着重点始终放在“敦本尚实”的实际作为之上。
同时阳明又以为圣人“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2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12 页。而之所以各个圣人作为不同,乃是因时而作,“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2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第15 页。。在道一的观照之下,将各个圣人事业归结为“时事”的性质,必然导致用现实事业本身的多少众寡来衡断圣人高下的结果。邓艾民就认为“精金喻圣”反映了阳明和朱子不同的思想体系特点:“朱熹重立言垂训,故以孔子贤于尧舜……王守仁重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以用《易》高于学《易》,故以尧、舜贤于孔子……这与二人的思想体系是相应的。”(23)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65 页。
邓艾民独具慧眼,敏锐地体察到了阳明在尧舜贤于孔子命题中体现出的对现实伦理秩序治理安顿的强烈关切。这种关切以期盼唐虞之治为中心,在以《拔本塞原论》为代表的晚年阳明思想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同于朱子以孔子垂教后世的理解,阳明将视角转移到外在平章治理一面,这也为阳明后学在判分尧舜与孔子高下时所承继。
三、对朱子“事功说”的批评
阳明的“精金喻圣”说提出后,其学生颇有疑虑,反对者们也大肆抨击,以为离经叛道。如陈建《学蔀通辨》批评阳明此论道:“信斯言,则文王、孔子均未得为至圣矣。阳明之猖狂无忌惮甚矣。”(24)陈建:《学蔀通辨续编》(卷下),见黎业明编校:《陈建著作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31 页。而冯柯《求是编》更认为阳明的前后两次回答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自以为不从躯壳起念,不替圣人争分两,何不以孔子为万镒,尧舜为九千乎?”(25)冯柯:《求是编》(卷三),见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88 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742 页。陈建所言是一种意气之争,不足为论;冯柯对于阳明的批评有其理致,但其明显没有理解阳明所论背后蕴含的深厚意义。继续如阳明对尧舜加以肯定的是他的大弟子王畿。
有弟子问王畿:“夫子贤于尧舜,释之者则以为圣不异,而异于事功。窃意门人称颂当时,非事功已也。”问者批评程朱的“事功说”,认为尧舜与孔子的区别在于“尧舜执中,夫子时中,执之与时,犹守之于化也”。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夫子之所以为时中,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是以尧舜之德大哉至矣”!孔子的“绝四”,“未之前闻,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王畿同样也批评了“事功说”,其答云:“尧舜未易贤也,释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亲炙者,其情密而属意深,得于传闻者,其情疏而用意渺。”王畿认为孔子弟子称赞孔子,“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别议”。他特别从事功的角度比较了尧舜和孔子:“若论事功,唐虞之际,荡荡巍巍,精一执中,开万世心学之源,区区欲以删述宪章盖之,浅之乎其言之也!”(26)王畿:《王畿集》(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67-68 页。
在此段问答中,王畿并未言及阳明所持的尧舜优先观点,但其思想意涵无疑倾向于认为尧舜优于孔子。问者所持尧舜执中、夫子时中,尧舜守之、夫子化之,所以夫子贤于尧舜的解释思路,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王畿本人以“无执不滞”诠解良知的一种体现。这本是王畿良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含义是工夫不执着造作,顺应自然而发。但王畿却不认可这种判断,而认为《孟子》中所言只是弟子称赞孔子的人之常情。这种解释和上文所引赵歧注有所类似。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从事功而言,孔子是不能盖过尧舜的。王畿此处所言的事功,是“荡荡巍巍”和“精一执中”两面。后者显然是指朱子所确立的理学道统论中,圣圣相传的所谓“十六字心传”;前者其又解释云:“尧舜事业荡荡巍巍,莫非道心发用之实学。”(27)王畿:《王畿集》(卷十),第260 页。可见王畿所理解的尧舜之事功是精一之心学以及由道心而发用之实学。尧舜既然开此万世心学之源,当然比仅仅删述宪章的孔子为高。和阳明相同,王畿对孔子删述使得经典流传的功绩十分看轻。他既否定了朱子“事功说”所蕴含的孔子在心传即精神之道的承续上高于尧舜的观点,又重申了王阳明从外在事功角度推崇尧舜为圣人之最的思想。
阳明另一弟子季本也对朱子的“事功说”有所批评。他认为程朱所持的夫子贤于尧舜的根据即夫子“推尧舜之道,以垂教万世”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无论从内在心学还是从外在平成来看,尧舜在事功上都是高于孔子的。而如果将贤理解为德,所谓“圣以德言”,则“尧舜之德万世莫加焉,而孔子之德何以过之”?因此季本只能提出孔子“鄙事无所不能,练事又益精”“使当尧舜时,则其智虑必有济二圣之不及者”,颇为勉强地为“夫子贤于尧舜”说寻找理由(28)季本:《说理会编》(卷十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2-223 页。。季本所论虽然看似维持传统的观点,但却明显偏离了程朱的解释路径,解释效力不高。
从王畿和季本所论可以看出,持较纯粹心学立场的学者,一般都忽略孔子删述经典对后世文教的垂示启发意义。总之,在尧舜开心学之源、成唐虞之治的前提下,学者只易于秉持尧舜高于孔子的立场,想要说明孔子贤于尧舜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理论困难。
四、王艮和泰州学派的“孔子无位而行仁”说
于是,王门系统中的泰州一脉,通过强调孔子无位而做了有位者尧舜的事业,来凸显孔子的优先。王艮即从有位无位角度比较,认为孔子过于尧、舜、禹:
尧舜禹相传授受曰:“允执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统。仲尼祖述者,此也。……盖尧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于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便做了尧舜事业,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处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先师尝有精金之喻,予以为孔子是灵丹,可以点石成金,无尽藏者。(29)王艮:《王心斋全集》(卷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 页。
所谓孔子可以“点石成金”,表明王艮反对其师的“精金喻圣”说,而认为孔子无位却做了尧舜事业,“为独盛也”,实有过于尧舜。他用标志性的“淮南格物”说诠释道:“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30)王艮:《王心斋全集》(卷一),第33 页。孔子因为独发作为天下国家大本的安身之义,亦即是可以“随时随处无歇手地”“点石成金”,故而独盛。王艮的最终关怀指向外在的安顿位育,“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31)王艮:《王心斋全集》(卷一),第6 页。。
于是,以无位而能位育天下的孔子为典型,王艮极力表彰“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出处意识,认为学术宗源全在“出处大节”(32)王艮:《王心斋全集》(卷一),第15 页。。对出处师道的张扬无疑伴随着对于现实权威的否定,其隐含之论是认为无位者相较于有位者在先天上就具有了有道这一道德优越地位的可能,这无疑延续了朱子学以道抗势的理想情怀。不过,虽然王艮与朱子一样都坚持道统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都突出孔子的“无位”性格,但二者推重孔子的实质内容是不同的。在以位育天下为旨归这一点上,王艮毋宁说是继承了阳明的用心。
孔子即使无位而亦可行仁、位育天下是泰州学派学者相当普遍的看法。比如耿定向弟子刘元卿最能发明有位无位皆能行仁之意(33)刘元卿:《刘元卿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86 页。,其称赞孔子道:“孔子未尝有广土众民,未尝中天下而立,而明此仁与天下共由之,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34)刘元卿:《刘元卿集》(卷十二),第502 页。刘元卿认为无位者的“为仁之器”就在于师友(35)刘元卿:《刘元卿集》(卷四),第109 页。,在师友所体现的教、学亲民实践意义上,“即教以学,即学以教,用以此行,舍以此藏,不假权势,其仁常流。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这也是孔孟一生精神(36)刘元卿:《刘元卿集》(卷三),第66 页。。
同样以师友之道诠释无位者可以行仁的还有何心隐。其在《原学原讲》中以仁为核心反复申论孔子之“生民以来未有之盛”,具体解释“仲尼贤于尧舜”究竟贤于何处则云尧舜“局局于君臣以统天下……此友朋之道,天启仲尼,以止至善者也。古谓仲尼贤于尧舜,谓非贤于此乎”!何心隐所说可以使天下自归仁的“友朋之道”自然也是一种不在位的在下之道,道统也因此归于孔子:“惟友朋可以聚天下之英才,以仁设教,而天下自归仁矣。天下非统于友朋而何?故春秋以道统统于仲尼。”(37)何心隐:《何心隐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66 页。
说明孔子无位而可行仁的学者一方面肯定孔子贤于尧舜,一方面又注目于现实伦理秩序,有着内在的合理性。肯定孔子可以坚持道统所有的正统性批评地位,而注目道德实践又可以致力于随时随处的现实伦理秩序之位育(38)这也就是余英时所谓“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跨时代的转变”的“觉民行道”。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90 页。。只是他们不持尧舜价值优先立场,所以没有发现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那就是无位者所行之仁,是局部的和受限制的;在传统儒家思想范围中,整体和全局的现实政教秩序的极致实现,终究要依赖于掌握现实秩序之位,而这又必将侵吞道之理想性一面所具有的批判功能(39)彭国翔分析了“觉民行道”和“得君行道”在阳明学中作为两种不同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指出“觉民行道”所隐含的“民众政治主体”这一观念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所面临的困难,和本文此处所论相通。彭国翔:《阳明学的政治取向、困境和分析》,《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3 期,第22-31 页。。
五、管志道对孔子贤于一切圣人的批判
将理想性之道与现实一面之位相结合的观点从逻辑上讲可以化解上述矛盾。泰州后学罗汝芳已有此倾向,而管志道则更为此种观点的代表。管志道也是耿定向弟子,在学脉上属于泰州学派,但其思想倾向却又是反泰州学的。管志道对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的系统阐释就针对王艮所论而发。他认为王艮以程朱说为本,当他的弟子引用程子、朱子的解释问道:“果当孟子之意否?”他说:“近之矣。然但可为泰州王氏之尊见龙而卑飞龙张本耳。”这显然是对程朱、王艮说无位而有道之意涵的批评。管志道将问题重心由孔子与尧舜的高下转移到为孔子是否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若宰我贤夫子于尧舜之评,则近于生民未有之评。然谓孔子贤于尧舜犹可,谓孔子贤于生民以来一切大圣人,则不可。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见。宋儒高其标而局其学,大似子路使门人为臣。(40)管志道:《孟义订测》(卷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7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524-525 页。
“子路使门人为臣”的典故出自《论语·子罕》,主旨是孔子对子路僭越而违反礼制的批评。管志道以这个典故类比宋儒对于“夫子贤于尧舜”的道统论解释,批评程朱和泰州学派高标孔子道统地位的做法,从而解构了程朱道统论中孔子之道对于政治势力的道德优越性。他所说“子思之祖述章”是指《中庸》中形容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一段。管志道认为:
千古尚无见诸日用之圣人,而于仲尼见之也,故以为生民未有。独未炤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根源处,故从川流之功用处见群龙之有首,而不透敦化之全体处见群龙之无首也。子夏言及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方是合体用而兼状其实。(41)管志道:《孟义订测》(卷二),第525 页。
管志道部分肯定孟子参到孔子“万物并育”“见诸日用”,认为此可见群龙有首;但批评孟子未见根源处之群龙无首,并以子夏言“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作为比较。群龙无首出自《周易》乾卦用九爻辞,管志道惯用此语形容学说、思想和人物的平齐。子夏语则见于《论语·子张》。所谓宗庙之美,在管志道看来即是体,是全体根源处;百官之富,即是用,是川流功用处。孟子不如子夏“合体用而兼状其实”就在于只片面表彰了孔子用之一面的群龙有首,而忽视了其在全体之一面的群龙无首。
管志道用群龙无首贬低孔子独尊地位的深层原因在于,他认为孔子并非制礼作乐的制作者:“悟到群龙无首去处,因复想子贡此评,原推开太上未作礼乐之世说,而从删述百王之世说也;有若从超凡入圣之类萃中表孔子,意亦然。”他赞扬子贡和有若都不凿定“圣人必无如夫子”者,“故圆”;而“孟子尊孔子为生民未有……凿定孔子为开辟后之一人,便乖大易群龙无首之旨”,自然语滞(42)管志道:《孟义订测》(卷二),第524-525 页。。从非作者角度对于孔子“群龙无首”的诠释,显然蕴含着管志道对作者任道意义上的推崇,“凡议礼、制度、考文,皆任道者之事也”,也就是君主天子之事,“道非居下位者之所敢任”。所以君师应该道合,“天子为天下君,即为天下师”,如果“创起一宗”“以师匹君”,就是“以师道蔽君道”,是圣人所不应为者(43)管志道:《师门求正牍》(卷上),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由此,管志道认为孔子无资格予言道统,“道实统于帝王”(44)管志道:《孟义订测》(卷二),第704 页。,而明太祖是有位之天子而又以纲常伦理实际治理天下,故能“与于道统”。事实上,管志道常笼统地说“祖述孔子,宪章高皇”,对孔子贤于尧舜的单独表述并不过于计较;但孔子是否贤于“生民以来一切大圣人”实关系到对道之本质的根本理解,故而其必云不可而力驳之。管志道对孔子“非作者”的评价,与阳明以孔子只是玩《易》学《易》者无疑有某种暗合。他最注重的始终还是明太祖式道治合一所代表的现实政教秩序。
六、结 语
从王阳明到王艮再到管志道,三者关于尧舜与孔子高下的看法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线索,阳明以尧舜为圣人之最,王艮以孔子为独盛,而管志道又批判了王艮的观点。但三人思想背后的本质是一致的:阳明对唐虞之治的憧憬、王艮对位育天下的追求、管志道对礼治纲常的强调都指向现实伦理秩序安顿的外王之维。
进一步而论,阳明推重唐虞之治,是基于当时社会伦理沦丧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期待,但其并未明确将此与有位无位关联;王艮转到从出处大节上高扬孔子,已经有着非常鲜明的以无位者行仁的要求,但由于无位,始终还是容易被限缩在理想层面,或只是一种局部的实践;管志道则彻底把这种外王理想与有位者结合,并以之来定义道统。三者对外王之维的重视,又呈现出一种与“位”之联结逐步加深的面貌。
总之,从本文所论阳明学对于夫子和尧舜高下问题的理解来看,阳明学者对于道的传承之中外王一维的强调,不同于朱子学所论的重心,敞开了儒者对于内外一体秩序的追逐。这种追逐在广义阳明学中所表现的最后形态,就是管志道式的道治合一。管志道其实并不像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所说的那样是帝王绝对权威的拥护者(45)荒木见悟:《阳明学の位相》,东京:东京研文社1992 年版,第357 页。,因为明太祖即使是有位者,也仍然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但顺着管志道思想而下,在清初却的确出现了道统被实际政治融合的现实,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内圣外王之整体理想在实际历史中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深刻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