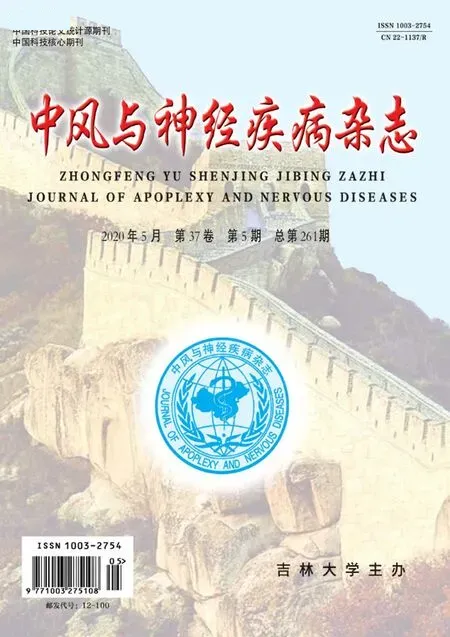缺血性卒中相关性癫痫与他汀类药物的研究进展
刘 燕,陈永敏,刘会娟,马 琳,陈 蓉综述,李其富审校
狭义上的卒中相关癫痫(Stroke-related epilepsy,STRE)特指的是卒中后早期痫性发作(Early-onset Seizures,ES)与晚期癫痫发作(Late-onset Seizures,LS)[1]。目前,国际抗癫痫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更倾向于以时限为1 w,将卒中后癫痫发作分为ES和LS[2]。ILAE认为ES可能为脑卒中诱发且一过性损害,而卒中后晚发性癫痫发作为结构性改变以及不可逆的损害,并且其在未来10 y内其再发风险高(至少60%)[3]。因而卒中后癫痫(Post-stroke Epilepsy,PSE)指的是LS。针对ES与PSE发病机制不同,显然两者治疗方案也截然不同。ES一般无需或3~6 m的短期抗癫痫治疗,LS却需要长期规范、个体化的抗癫痫治疗[4]。近年来,他汀类药物已被证实可保护皮质神经细胞免受兴奋性毒性,以防止癫痫的发生。另一方面,相比下,他汀类药物较传统抗癫痫药物副作用少、药物间相互作用少、对老年患者更易耐受[5]。新研究发现早期使用他汀类药可以降低脑卒中后ES的发病风险,因此,可考虑将他汀类药物是否用于预防STRE。
1 STRE的发病机制
关于STRE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迄今为止尚未完全阐明。既往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临床观察寻找其相关危险因素,常见如性别、年龄及脑卒中类型、部位、梗死面积、癫痫发作类型、卒中严重程度等均可增加PSE的风险[6]。此外,英国一项大规模研究报告显示,血管相关危险因素可能与LS有关,如心肌梗死病史、外周血管疾病、高血压、总血清胆固醇和左心室肥厚等[7]。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基础实验得出其重要的发病机制为:(1)ES:电生理稳定性和神经递质平衡的改变;(2)LS:遗传学因素、破坏神经血管单位的完整性、改变神经元之间联系以及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引起结构性改变。最初IS引起急性脑损伤破坏神经元细胞膜稳定性,缺血缺氧状态下可导致钠泵功能衰竭,Na+内流增多使细胞去极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钙离子通道被激活后Ca2+内流。同时Ca2+的内流可能导致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且参与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与NO产生途径,导致神经元兴奋性增加促痫性发作;海马对缺血缺氧耐受性较其他脑组织差,容易成为致痫灶;急性脑梗死血管再通引起再灌注损伤,导致反应性脑血管痉挛也可能促使早发性痫性发作[8~10]。在遗传学方面,有研究者发现醛脱氢酶2(ALDH2)rs671、CD40-1C/T多态性等与PSE有关[11,12];通过对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BBB)的破坏、血流动力学改变与脑组织的炎症反应导致神经元异常放电;PSE位于大脑皮质和海马反应性胶质细胞异常增生,其离子通道摄取K+减少,同时氨基酸合成酶表达发生变化,造成细胞外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过多,导致自发性癫痫发作,最终形成致痫灶[8,13]。最新研究发现,在IS后BBB破坏的基础上,凝血酶及其蛋白酶激活受体1(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 1,PAR1)在PSE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可能是通过诱导缺血事件后发生永久性结构改变,进而发展为癫痫病灶[14]。
2 他汀类药物对STRE的可能作用机制
他汀类药物作为临床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线药物,其作用除了常见的降脂和稳定斑块,近年来研究还发现抗氧化、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等多效性作用。其中重要作用是具有脑神经的保护作用,此作用可以不依赖降脂效应,改变致痫的发生过程,达到抗癫痫效能[15]。
2.1 他汀类药物能降低ES风险的机制研究 首先,急性脑缺血导致谷氨酸水平显著升高,进而导致癫痫样放电。他汀类药物被发现通过降低谷氨酸的摄取,调节NMDA受体(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receptor,NMDA)活性和降低细胞内钙离子水平,减少谷氨酸的神经毒性。其次,由于炎症可以增强神经元的兴奋性,增加BBB的通透性,导致神经元异常放电,进一步加重脑缺氧,形成恶性循环。他汀类药物被推测通过其抗炎作用,降低BBB的通透性,抑制内皮细胞中NO的合成以及下调促炎基因的表达;减弱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增加IL-10的合成;抑制自由基的形成与脂质过氧化,以进一步发挥其抗惊厥作用。第三,以往的一项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中风的兴奋毒性的细胞凋亡可能与癫痫具有共同的发病机制。他汀类药物通过调节Bax和Bcl参与的细胞凋亡途径,协助促凋亡和抗凋亡蛋白的表达,促Akt(即蛋白激酶B)磷酸化,促使神经元存活[16]。
2.2 他汀类药物能降低LS风险的作用机制 与ES不同的是,LS是由急性脑梗死后对大脑不可逆性结构与功能的重建所导致永久性神经元兴奋,这种过度兴奋状态会提高癫痫活动的风险。海马苔藓纤维出芽是继发性癫痫发生常见的病理改变[17]。他汀类药物在动物实验中被发现其能抑制诱导损伤的细胞因子表达(IL-1和TNF-α)和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增多,降低了癫痫脑放电的频率,这可能与抑制了海马异常苔藓纤维出芽(mossy fiber sprouting,MFS)有关[18]。异常MFS是由于CA3区椎体神经元和齿状回(DG)区域内的中间神经元的变性,颗粒细胞的轴突失去正常的连接靶点而异常发芽[19]。然而,出现这一现象的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确。除此之外,从多项临床研究中发现IS的病灶范围越大,越容易引起缺血缺氧的情况,易诱发癫痫发作[20]。经过既往的体内实验表明他汀类药物在脑缺血后短期内使用可缩小梗死病灶面积和降低卒中的严重程度,从而间接降低癫痫发生的风险[21,22]。
3 STRE应用他汀类药物的临床研究
现今,大量证据表明他汀类药物因具有降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改善IS患者的神经功能预后,成为IS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基础治疗方案之一[23]。基于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使用者患有癫痫风险较低,这一发现也得到动物和体外实验的证实[24]。该类药物不仅仅独立对IS与癫痫发作的神经保护作用,同样在STRE有类似的积极作用。
近期文献报道,AIS患者中出现急性症状性发作即ES为PSE的危险因素,而且PSE的SeLECT预测评分,其中ES是最为显著的危险因素[25]。Luigi等通过运用MRI-T2加权像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模型的脑梗死24 h后高信号区域面积的测量,进行安慰剂组与脑梗死后使用辛伐他汀(20mg/kg)及阿托伐他汀(10mg/kg)治疗组进行比较梗死面积,治疗组的梗死面积皆较安慰剂组明显减少,表明在他汀类药物治疗后24 h内会发生神经保护的病理和生化变化[21]。Soichiro等[26]对2969例AIS患者进行研究,发现54.6%例患者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其中只有2.2%例患者发生ES,提出他汀类药物对ES的神经细胞产生保护作用,此作用不受卒中类型和体内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在此方面做了相关研究。赵岚青等[27]研究学者对卒中后ES组与非ES组患者进行比较急性期是否使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他汀类药物、降压药物等基础治疗药物,经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脑梗死急性期应用他汀类药物、抗血小板药物及降压药物均可能降低卒中后ES的发病率。Guo等[28]学者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中提出使用他汀类药物,尤其在脑梗死急性期,可以降低卒中后ES,也降低ES患者发展为PSE的风险(OR=0.36,95%CI0.20~0.62,P<0.001),同时可预防PSE引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可发展为难治性癫痫。
实际上,既往研究中癫痫发作事件的数量少、应用他汀类药物种类有限以及较少ES患者仅在脑卒中前使用他汀类药物,则无法评估脑梗死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对ES的影响。前面提及的研究已证明,他汀类药物治疗ES发挥其保护作用,他汀类药物剂量和延迟治疗时间对PSE风险降低有一定的影响,改善患者长期预后。此外,胶质细胞增生是导致PSE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可能抑制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增生,甚至减少神经元丢失[29]。因此,从理论上考虑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PSE发病风险。Guo 等[28]还发现他汀类药物用于部分ES患者,可降低发展为PSE的概率(OR=0.34,95%CI0.13~0.88,P=0.026)。相反,Motika 等[30]针对Guo等的研究提出该项研究结果的质疑:只有少数卒中患者会发生PSE,他汀类药物的类型和剂量在所有患者中并不一致,难以明确他汀类药物对PSE直接关系,也无法排除其他因素起到保护作用。在Ju等[5]通过对大量台湾人群的健康声明以及对该人群长期随访的研究,对卒中前1 m(aHR 1.11;95%CI0.84~1.47;P= 0.464)和卒中前1 m至1 y前(aHR 1.20;95%CI0.93~1.53;P=0.157)使用他汀类药物,与卒中前未使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比较,前者的发生PSE风险明显降低。之前发现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PSE风险的降低以他汀类药物累积限定日剂量(cumulative defined daily dose,cDDD)呈依赖关系,但其中更强调的是,卒中后使用他汀类药物与PSE风险降低有显著相关性。Etminan等[31]的一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中,也报道了阿托伐他汀钙片使用和降低癫痫风险之间呈药物剂量依赖性效应,每增加1克阿托伐他汀钙片,因癫痫住院风险降低5%。另外,国内Li等[16]的前瞻性研究对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2015年1月~2017年6月期间住院治疗的1051例新发脑梗死患者,经过临床诊断以及头部CT或核磁共振证实,既往无癫痫病史者,平均随访2 y,将2次及2次以上LS定义为PSE。他汀类药物治疗降低ES(P=0.009)、LS(P=0.007)及PSE(P=0.009)的风险,而在使用他汀类药物强化剂量时降低ES(P=0.003)、LS(P=0.004)及PSE(P=0.006)的风险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对他汀类药物开始使用时间、种类、剂量以及疗程对PSE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仅发现强化降脂与延迟他汀类药物的治疗时间可明显降低的发生PSE的风险。但他汀类药物对PSE具体的影响机制仍是值得挑战的难题。
4 他汀类药物与其他药物联用对PSE的影响
目前,卒中后癫痫的诊断与治疗仍有争议,对卒中的预防和治疗才是PSE治疗的关键。在临床工作中除了溶栓治疗,他汀类联合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较为广泛应用于防治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能帮助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改善疾病预后,最终提高患者生存率。另外,近年来多项大型研究表明积极的他汀类药物治疗并不会增加脑出血风险[32]。丁苯酞是我国自主研发新型的I类用药,多用于治疗脑梗死,具有改善缺血组织微循环、改善神经缺损、改善脑梗死患者认知等作用。他汀类药物联合丁苯酞能降低纤维蛋白,抑制体内血液高凝状态的形成,同时减轻Hcy诱导的血管内皮损伤及控制Hcy相关炎症反应,进一步阻止血栓形成和病程进展[33]。
根据2018年AHA的指南仍不推荐对脑卒中患者应用抗癫痫药物进行预防性用药[34]。但LS患者因脑内癫痫病灶形成,则需要长期且规范的AEDs个体化治疗。对于仅少数LS患者疗效欠佳时,需联合用药或手术治疗。抗癫痫药物与他汀类药物联用出现协同作用与拮抗作用。Stepien等[35]研究显示氟伐他汀在卒中急性期给药,可增强卡马西平和丙戊酸的抗惊厥作用。Russo等[36]认为因为他汀类药物改变部分AEDs大脑的药物浓度,间接影响AEDs能否与血浆蛋白结合和作用的强弱。亲脂类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透过血脑屏障增强部分AEDs的抗惊厥活性;脑内的卡马西平、地西泮药物浓度增加与他汀类药物同时使用可明显降低癫痫易感性。与之对比,加巴喷丁、左乙拉西坦、奥卡西平、苯妥英钠和苯巴比妥的药效不受他汀类药物的影响。经过动物实验推测出癫痫小鼠模型的大脑内兴奋性神经递质的减少,可能是他汀类药物与部分AEDs合用时能使抗惊厥作用增强的原因[37]。据报道,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均属于P-蛋白的抑制剂,但普伐他汀和氟伐他汀并没有明显抑制P-糖蛋白的作用。因此,抑制P-糖蛋白可能为与AEDs合用时增强抗癫痫效应的理由之一[36]。与之相反,Stepien等还发现阿托伐他汀卒中慢性期给药,可能降低卡马西平的抗惊厥作用。在癫痫早期阶段,左乙拉西坦通过改变钙蛋白酶-1(calpain-1)的表达起到神经保护作用,而辛伐他汀还未具备相同的作用,但两者联合治疗并不比单一使用的抗癫痫效果更为优势[38]。另外,血脂异常是酶诱导型抗癫痫药(enzyme-inducing antiepileptic,EIAEDs)潜在的副作用。他汀类药物与EIAEDs合用可能削弱他汀类药物的降脂疗效,癫痫患者在使用他汀类药物降脂时需监测血清总胆固醇水平[39,40]。最近研究表明新型的抗癫痫药物艾司利卡西平在临床使用中对血脂没有明显影响,而且与各种他汀类药物之间的药代动力学和药间相互作用在临床上无显著的药物学效应[41]。
5 展 望
临床上对STRE高危人群进行脑电图检查为早发现、早治疗提供有利条件。相当多的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的使用有助于降低罹患STRE的风险。如果他汀类药物能被广泛用于STRE的防治且作为卒中的常规二级预防,故可以实现更好管理脑卒中患者,减轻社会和医疗负担。可是,目前的机制研究多局限动物实验,需要更多关于信号通路和病理学方面的研究,以更深入探索他汀类药物抗癫痫机制以及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临床研究样本量不足,多为观察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卒中前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较少,乃至无法评估卒中后使用他汀类药物的抗惊厥效果。因此,期待未来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或临床随机试验来进一步验证他汀类药物对STRE的疗效和安全性,并确定其对防治STRE最有效且合理的剂量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