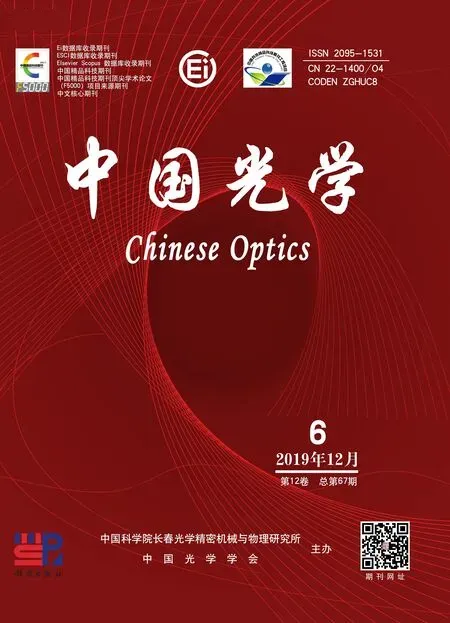泡沫覆盖不规则海面的非均匀空-水信道量子密钥分发
王 潋,周媛媛*,周学军,陈 霄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 战争研究院 北京 100091)
1 引 言
针对传统对潜通信方式在传输和安全方面存在局限性的问题[1],2011年,Marco Lanzagorta[2]提出在空-水间建立经典和量子两条光信道的设想,经典信道用来传输信息,量子信道用来实现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 Key Distribution,QKD),以保证经典信道通信的无条件安全[3]。至此,基于空-水信道的QKD才逐渐登上舞台。空-水信道是由大气、空-水界面(海面)和海水组成的混合信道。由于空-水QKD常以光量子的偏振态承载信息,因此信道介质(水、大气及界面)会对偏振态产生吸收和散射等消光效应,从而导致能量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QKD的传输性能,其中粒子散射更可能会改变偏振态传播路径,或是造成偏振态的偏振劣化,引起误码。
纵观QKD的发展历程可见,其理论和实验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基本都是基于光纤信道[4-7]和自由空间(大气)[8-11]进行研究的,即均匀或类似均匀的介质,而基于空-水信道的QKD研究却鲜有报道。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空-水经典激光通信为研究对象,关注于光束的时间扩展、空间和角度分布、能量变化、光斑形状等[12-14],未深入到光量子范畴。而涉及空-水QKD的研究还只是基于理想条件或单一信道因素展开。周飞等仅考虑理想平静的空-水界面来分析不同介质间的QKD性能[15],但实际海面总处于随机波动状态。Marco Lanzagorta 2012年验证了均匀海水中实现QKD的理论可行性[2,16]。之后,顾永建团队分析了均匀海水信道中的单光子传输特性和QKD误码率[17-18]。2017年,金贤敏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个海水量子实验,验证了光子偏振态在海水中仍可维持其量子特性[19],为空-水QKD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空-水信道结构组成复杂,光学特性多变,应用于水下QKD研究的均匀单层介质模型已不适用[2,16-18]。此外,上述QKD研究都只是单独针对空-水信道中的某一部分展开的,未涉及完整的空-水信道建模及整体空-水QKD性能分析,因此建立更符合真实环境的空-水信道整体模型,对光量子的吸收、散射及空-水QKD传输性能进行系统分析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综合考虑覆盖泡沫的不规则海面、空-水信道的复杂多变性和量子偏振态连续经受多重散射过程,将离散泡沫粒子体散射与不规则海面折射作用相结合,并对实际环境下的空-水信道作垂直分层处理,建立非均匀空-水信道整体复合模型。据此进一步完善空-水QKD系统量子误码率理论模型,并采用偏振矢量蒙特卡罗算法模拟,对非均匀空-水信道光量子传输性能、非均匀空-水信道QKD的整体传输性能进行数值仿真与系统分析,以验证复杂空-水信道实施QKD的可行性,为未来实现空-水一体的量子通信链路提供参考。
2 非均匀空-水信道模型构建与分析
对空-水QKD而言,光信号传输要穿过大气、空-水界面(海面)及海水共同构成的混合信道。而实际大气和海水信道为非均匀介质,其结构组成复杂多变,空-水界面受风、潮汐等因素影响会出现高低不等、长短不齐的波动,造成界面斜率不规则变化,并会不同程度地被泡沫覆盖,这些都将对空-水QKD信号的传输产生影响。因此为分析空-水QKD下行链路的传输性能,首先要构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非均匀信道复合模型。
2.1 “泡沫-不规则海面”空-水界面模型
空-水界面是空-水信道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实际海面在潮汐、风暴潮、海啸及海浪的作用下呈现出不规则波动状态。由于潮汐、风暴潮和海啸产生的波长远大于QKD光信号的波长,故忽略它们的影响。海浪主要由海风引起,在风速影响下破碎波会产生泡沫覆盖上层海面,风速是影响空-水QKD光量子传输的一个主要因素[20]。由此,将离散泡沫粒子的体散射与实际不规则海面相结合,建立风驱随机波动海面覆盖水气泡层的“泡沫-不规则海面”的“体-面”复合模型,如图1所示,假设初始光束以α0角度入射,先与泡沫层(厚度为d)的泡沫粒子进行一次或多次碰撞,发生散射、吸收、移动后,存活的光子经过不规则海面,在此处发生反射和折射后再射入海水信道,并由QKD的水下探测器接收。

图1 “泡沫-不规则海面”模型 Fig.1 Model of “foam-irregular sea surface”
由于海面泡沫主要由水气泡组成,以往的球形粒子模型已不适用,因此将泡沫等效为外层水膜、内层空气核的球形分层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a为内半径,b为外半径,粒径分布满足伽玛分布[21]。根据已有实验数据可知,海面泡沫的数量分布与风速相关,单位体积内泡沫粒子数n0可表示为[22-23]

(1)
式中,fs为体积占空比,可表示为

(2)
式中,V19.5为距离海面19.5 m处的风速。粒子数与粒径分布共同决定泡沫粒子的散射和衰减系数。

图2 泡沫粒子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foam particle
光束在穿过泡沫层后将到达海面,发生反射和折射作用。事实上,光滑平静的海面并不存在,实际海面受海风影响总处于不规则变化状态,这必定会引起界面法线的偏离,从而改变入射光线的传播方向。如图3所示,α0为入射光相对于平静海面的入射角,α1、α2为不规则海面的实际入射角和折射角,β为实际不规则海面引起的法线偏离角,即法线方向与z轴的夹角,称为俯仰角,且有α0,α1,α2,β∈[0,π/2]。反射光束不在水下探测器的探测范围,故将其忽略。
在海风作用下,不规则海面虽具有随机性,但也遵循一定规律。Cox和Munk基于大量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给出了一定风速下海面法线俯仰角的经验归一化概率密度公式[24],为

(3)

图3 不规则海面的光束传输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beam propagation for irregular sea surface
式中,κ2=0.003+0.005 12v,v为风速(m/s)。对概率密度进行采样,可得相应的俯仰角为

(4)
式中随机数ζ∈(0,1]。
由此可知,不规则海面的实际入射角为α1=|α0±β|,再结合Snell定理求得折射角α2[25]。根据Fresnel公式可得,不规则海面的透射率为[26]:

(5)
同时,泡沫粒子也会对实际海面的透射率造成影响,且与海洋风速v有关,有

(6)
因此,“泡沫-不规则海面”的总透射率为
T=T1T2.
(7)
此外,入射光穿越“泡沫-不规则海面”后,其偏振态会发生改变,使空-水QKD性能受到影响。光束经过大气先到达海面泡沫层,与泡沫粒子相互作用发生散射,从而导致承载信息的光子基矢偏振态发生φm角度的偏转。随后再射入不规则海面,由于此界面折射光路没有位相变化,故光子偏振态c1|p〉+c2|s〉(c1、c2为复数)在穿过不规则海面后转变为c1tp|p〉+c2ts|s〉。因此,光子穿越“泡沫-不规则海面”的整个过程中,其偏振态的最终偏转角可表示为:

(8)
式中,tp和ts为光束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振幅透射率。
可见,“泡沫-不规则海面”对光量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能量衰减和光量子偏振态的劣化,进而影响空-水QKD的性能。
2.2 大气/海水信道分层模型
大气由气体分子、水汽、漂浮的固液态气溶胶等杂质粒子混合组成。海水则由水分子、溶解物、悬浮颗粒和种类繁多的有机物等构成,其对光量子传输的影响要远大于大气信道。实际上,大气和海水信道中的各类颗粒物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导致信道中不同位置的固有光学特性各不相同,从而对光量子的传输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因此需构建符合实际环境的大气/海水信道分层模型。
考虑到除蓝绿波段(450~550 nm)外,其他波段的光束在水下的衰减太大[27],空-水QKD选用处于蓝绿波段的光束来传输信息。根据大气和海水信道在蓝绿窗口内的光学特性[28-29],对大气/海水信道在垂直方向上作分层处理,以较小尺度范围为一层均匀介质,且此单层介质(子层)内的粒子等效为大小、性质均相同的球形实心粒子,即基于高度分层的大气信道模型,每1 km为一层且在50 km高度以上视作真空环境,不影响光子传输[28];基于叶绿素浓度的深度分层海水信道模型,每1 m深度为一层,每层都是密度均匀、稳定的信道[30]。如图4所示,光子在多层大气/海水信道中传输会与其中的一个粒子碰撞,产生散射,从而改变光子的传输方向和偏振状态,而后又碰到下一个散射粒子。

图4 多层大气/海水信道模型的光传输图示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beam propagation in the multilayer atmospheric/seawater channel model
假设光子先在第i层的p0处发生散射,经过j个子层边界后碰撞下一个粒子,在第(i+j)层内的p1处被散射。光子在第i层和第(i+j)层的传输距离分别为t和s,而在穿过(j-1)个子层内有相同的传输距离r。同时由于光子穿越了不同子层边界,各子层的各项物理参数不同,如第k层的消光系数记为αk,使得光子散射步长发生变化,因此简单的随机取样法已不再适用于多层信道模型。
为解决这一问题,下面对该多层信道的光子传输进行详细分析。由Lambert-Beer定理可知,光子透射率为

(9)
式中,I和I0分别表示光子散射前后的光强;l为光子散射步长;α为信道消光系数。
光子在p0处散射后的透射率可表示为:
τ=τiτi+1…τi+j-1τi+j,
(10)
式中,τi为第i层的透射率。
由此可得,

(11)
而后,结合迭代法计算光子单次散射后的总步长l。假定p0处的坐标为(x,y,z),光子散射后的传输方向为u=(ux,uy,uz),可分3种情况讨论其散射步长:
(1)当uz>0时,光子发生前向散射,可求出:

(12)
若s>r,令i=i+1,再进行下一轮迭代运算。反之,若s≤r,则可知此次光子散射步长为
l=t+(i-1)r+s,
(13)
(2)当uz=0时,散射后光子的运动方向与z轴垂直,故光子一直位于第i层信道内,其步长为:

(14)
(3)当uz<0时,发生后向散射,式(11)和(12)应改写为:

(15)

(16)
此外,如果下一次散射仍发生在第i层信道中,即p1仍位于第i层,那么利用单层大气/海水信道模型处理,即运用式(13)即可求出步长。
3 非均匀空-水信道传输性能分析
3.1 非均匀空-水信道的光子散射
空-水QKD利用光子的偏振态实现信息传输,因此可用Stokes矢量来表示光量子所有偏振信息。而光子在空-水混合信道中传输时,存在的吸收、散射和折射等作用会改变其偏振状态、传输方向和振幅等,进而影响QKD信号的接收。为研究空-水QKD的传输性能,在建立的非均匀空-水信道复合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Mie散射和Rayleigh散射的影响,采用偏振矢量蒙特卡罗模拟,以推导出光子穿过空-水信道的Stokes矢量。
假设入射光子的初始偏振态为S0=(I0,Q0,U0,V0)T,经单次散射后,偏振态转变为S1=MS0,M为穆勒(Mueller)矩阵,是关于散射角θ的函数,表示与信道粒子碰撞发生散射。在空-水信道中,光子散射主要考虑Mie散射和Rayleigh散射。由于大气和海水中所含各类颗粒物以及海面泡沫粒子的尺寸分布大于光波长,因此根据Mie散射理论,M可简化为

(17)
式中,矩阵各元素m11(θ)、m12(θ)、m33(θ)、m34(θ)可由散射振幅函数S1和S2求出。将颗粒物等效为各向同性的球形实心粒子,其Mie散射系数可表示为:

(18)

(19)
式中,r表示半径,jn和hn分别表示第一类Bessel球函数和半整数阶第二类Hankel函数。泡沫粒子看作空心分层球形粒子,其Mie散射系数为:

(20)

(21)
式中An(ζ,χ),Bn(ζ,χ)已由文献[31-32]给出,参量σ=kb,ζ=kbb,χ=kaa,kb和ka分别为壳、核波数,yn(ζ)为Neumann函数。
而对于大气和海水分子,其尺寸分布远小于光波长,故光子与之发生Rayleigh散射,M改写为:

(22)
为了得到散射后的Stokes矢量,必须先获得光子的散射角和方位角。以往通常由Henyey-Greenstein(HG)函数确定散射角,由[0,2π]内均匀抽样法获得方位角[33]。与之相比,本文采用偏振矢量蒙特卡罗算法,可同时获得散射角和方位角,其本质优势在于这两个角度是由基于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的“舍选抽样法”来确定的,散射相位函数表示为:
ρ(θ,φ)=m11(θ)I+m12(θ)·
[Qcos(2φ)+Usin(2φ)] .
(23)
同时,由于空-水混合信道的组成成分较为复杂,悬浮粒子大小不一,故需采用随机取样法来判断大气/海水中各次的散射类型。在每一个子层内发生Mie散射的概率为

(24)

ρ(θ,φ)=(1+cos2θ)I-sin2θ×
[Qcos(2φ)+Usin(2φ)] .
(25)
3.2 非均匀空-水信道的光子传输
在空-水QKD信号下行传输中,光子依次经过大气、空-水界面和海水介质,与介质中的各类分子、悬浮粒子及海面泡沫等发生一次或多次碰撞,产生吸收、散射、移动,在不规则海面处发生折射作用后射入海水中,最后由QKD系统的水下探测器接收,如图5所示。

图5 空-水信道光传输示意图 Fig.5 Diagram of beam propagation in the air-water channel
由于大气信道QKD研究较为成熟,且为了简化分析,重点突出实际海面和海水介质对QKD的影响,设定发送端位于干洁大气条件下的低空机载平台(此范围内基于高度分层的大气信道模型的光学特性参数为固定值),因此光子经过此段大气信道后,仅发生衰减,传输方向仍保持不变。假设光束初始入射角为θ0,方向角为φ0,光束穿过大气到达“泡沫-不规则海面”,经与泡沫粒子的m次散射后,射入不规则海面,此时的Stokes矢量为
Sm=R(γm)M(θm)R(φm)…
R(γ1)M(θ1)R(φ1)R(φ0)S,
(26)
式中,R(γi)和R(φi)为关于角度γi或φi的旋转矩阵,γi为第i次散射后Stokes矢量由散射面转到参考面的夹角,φi和θi为第i次散射的方向角和散射角。
经过整个泡沫层m次散射后,最终光子偏振变化的偏转角为

(27)
式中,S0=R(φ0)S。光子在最后一次散射后的传输方向为Dm=(uxm,uym,uzm)T,其中

(28)

(29)
式中,Dm-1=(uxm-1,uym-1,uzm-1)T为此次散射前光子的传输方向。
因此,光子穿过泡沫层后,射入不规则海面的入射角为:

(30)
式中,Z=(0,0,1)T。
同时,由于实际不规则海面引起界面法线偏离,因此光子穿过不规则海面后,其传输方向和偏振状态都会发生改变,Stokes矢量转变为:

(31)
式中,T为一个变换矩阵,表示光子穿越空-水界面引起的偏振态变化可表示为:

(32)

在经过整个空-水信道后,光子偏振变化的最终偏转角为:

(33)
此外,光子到达接收端由水下探测器测量时,其偏振态的改变会导致误码的出现,从而引入偏振误码率,可表示为:

(34)
4 非均匀空-水信道的量子密钥分发
量子误码率(Quantum Bit Error Rate,QBER)作为评估QKD系统的一个重要指标,对空-水QKD系统来说,其误码的产生与环境背景光噪声、散射噪声、探测器暗计数及探测效率等有关。基于上节建立的非均匀空-水信道模型,进一步完善文献[2]中QBER公式,可推出该空-水QKD系统QBER表达式为:

(35)



(36)

由文献[34]可知,该系统Y1下界的通用计算公式为

(37)


(38)
且

(39)
其中,

(40)

(41)

(42)
5 仿真结果与分析
由于空-水信道的结构组成复杂、多变,且存在随机分布的各类颗粒物质,导致光子在其中传输时产生的散射、吸收和移动是不确定的,因此本文利用偏振矢量蒙特卡罗算法对非均匀空-水信道模型下行链路的量子密钥分发进行仿真分析。为便于分析,本文数值仿真中假设发送端位于100 m高度的低空机载平台,对应的衰减系数为1.699×10-4m-1,以便于对不同海洋环境下的空-水QKD系统进行性能分析。仿真中泡沫粒子平均外半径取250 μm,水膜平均厚度为20 μm,泡沫层厚度取2 cm,采用Jerlov 5种水体类型中的JWT I(清澈)、JWT IB(中等浑浊)和JWT II(浑浊)型海水进行仿真分析,其他主要仿真参数如表1所示[2,34]。

表1 主要仿真参数设置
图6表示基于本文建立的非均匀空-水信道复合模型,在发射光子数为106时,不同海水类型条件下,水下探测器接收到的光子数与水下传输距离的关系。可以看出,无论处于哪种海水类型,随着水下传输距离的增加,接收到的光子数量都在不断减少。对于不同类型的海水,其有效传输距离也不同,在JWT IB和II型海水中,光衰减(吸收和散射)较为严重,有效传输距离仅约为31 m和19 m,若超过这一范围,探测器几乎不能再探测到信号光子,因此为确保QKD的有效传输距离,后续研究中主要考虑JWT I型海水中QKD光信号的传输,且潜艇主要航行于此类海域[2]。同时由于衰减(吸收和散射)的存在,JWT I型海水中的QKD水下传输距离也限制在了百米量级,但这仍可满足潜艇和水下航行器100 m安全潜深的要求。

图6 不同海水中,光衰减随传输距离的变化 Fig.6 Light attenuation varies with transmission distance in different sea waters
图7表示考虑JWT I型海水,光子经过非均匀空-水信道到达水下探测器时,其基矢偏振态的退偏比和保真度与水下传输距离的关系。由于光子受信道折射和散射作用影响,其偏振态会发生改变,从而造成误码率增加,因此利用退偏比和保真度从量子角度衡量偏振变化前后的相似度。可以看出,风速增大会导致光子退偏比的增大和保真度的减小。当风速由0 m/s增至40 m/s时,光子射入海水的退偏比由0.067增加到0.156,保真度则由0.983减小到0.96。这主要是因为风速的增大使得“泡沫-不规则海面”所含泡沫粒子增多,散射系数和随机起伏程度增大,导致散射次数和实际法线的偏离程度增大,进而影响光子的偏振态。此外,随着水下传输距离的增加,光子的退偏比和保真度分别呈逐渐增大和减小趋势,因为在JWT I型清澈海水中同样存在光子的吸收和散射作用,只是此类海水的散射系数较小,故对光子偏振态的影响较小,但在100~130 m范围内该趋势显著增大,这是由于此范围内海水散射系数骤然增加所致。

图7 不同风速下的光子退偏比和保真度 Fig.7 Depolarization ratio and fidelity of the photon at different wind speeds

图8 不同风速下的偏振误码率 Fig.8 Polarization error rate at different wind speeds
图8表示考虑JWT I型海水,经过非均匀空-水信道后,到达水下探测器的光子偏振误码率与水下传输距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偏振误码率随水下传输距离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水下传输距离的增加使光子与海水中各类颗粒物质的碰撞几率增加,导致光子的散射次数增加,从而加剧光子偏振态的变化程度,使光子击中错误检测器的概率增大;其次,偏振误码率的上升总体较为缓慢,但在100~130 m深度范围内会骤然增大,这主要是由实际海水介质的非均匀性导致的,其散射系数在此范围内急剧增大到一个峰值再下降,而散射系数的增大必定会加大光子的退偏程度,使偏振误码率上升;再者,海面风速的增大也会引入更大的偏振误码率。由图8可见,在水下传输距离为0 m时就已产生偏振误码率,这是因为光子在射入海水前穿过“泡沫-不规则海面”会发生散射。可见,海面泡沫、风速及海水中的杂质粒子都会给系统带来偏振误码,但清澈海水引入的偏振误码率较小,尤其在100 m深度以下,明显小于“泡沫-不规则海面”引入的偏振误码率。

图9 不同风速下的QBER Fig.9 QBERs at different wind speeds
图9(彩图见期刊电子版)表示考虑JWT I型海水且平均光子数取0.1,不同海面风速(0 m/s无风,5 m/s微风,10 m/s劲风,20 m/s大风,40 m/s暴风)条件下,非均匀空-水信道QKD系统量子误码率QBER与水下传输距离的关系。可以看出,随着传输距离增加,QBER会逐渐上升。同时,海面风速会对该系统的QBER和安全传输距离造成影响,风速越大,QBER越大,安全传输距离越短。当QBER=10%(最高安全界限)时,该系统可抵御任意类型的量子攻击,在泡沫层厚度为2 cm时,风速若从0增大到40 m/s,水下安全传输距离则由57 m减小至43.5 m;当QBER=25%(最低安全界限)时,该系统只能抵御简单的截获-重发量子攻击,此时随风速的增大,水下安全传输距离由106.5 m缩短到102 m。在实际海洋环境中,最佳的QBER目标值应在10%~25%之间[2],当最大安全传输距离不满足潜艇和水下航行器的工作需求时,可采用拖拽浮标等方式来完成QKD,以确保通信的安全。

图10 不同泡沫层厚度下,密钥生成率随传输距离的变化情况 Fig.10 Key generation rate varies with transmission distance at different foam thicknesses
图10(彩图见期刊电子版)表示考虑JWT I型海水并最优化信号态强度,在40 m/s暴风(或无风),不同泡沫层厚度条件下,基于非均匀空-水信道的4强度诱骗态BB84 QKD系统的密钥生成率与水下传输距离的关系。可以看出,海面泡沫层厚度和风速增大会使QKD密钥生成率和安全传输距离减小。因为泡沫层厚度增加,会使信号光子经过泡沫层的移动距离增加,从而增加了光子与泡沫粒子的碰撞次数,也就增加了光子的散射次数,而球形粒子的多重散射易产生退偏现象,且风速的增大会加大界面法线的偏离,两者都会加剧光子的退偏程度,引入更多误码,同时风速和泡沫层厚度的增加也会降低空-水界面透射率。此外,多层大气/海水信道中的光衰减(散射和吸收)也会降低系统传输性能。当海面无风无泡沫(d=0 cm,v=0 m/s)时,QKD系统的水下安全距离约为120.8 m;当海面无泡沫但出现暴风(d=0 cm)时,水下安全距离约为108.8 m;而处于最糟糕“泡沫-不规则海面”的海洋环境(d=6 cm)时,其仍可传至85 m,基本能保障水下航行器近百米量级的安全潜深,采用拖曳浮标等措施,可进一步延长空-水QKD的安全通信距离。由此验证了泡沫覆盖不规则海面的非均匀空-水信道实施QKD的可行性。

图11 不同波长下,密钥生成率随传输距离的变化 Fig.11 Key generation rate varies with transmission distance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图11(彩图见期刊电子版)表示考虑JWT I型海水并最优化信号态强度,在40 m/s暴风和6 cm泡沫层厚度,及发射光源波长不同条件下,非均匀空-水信道的4强度诱骗态BB84 QKD系统的密钥生成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蓝绿窗口范围内,随着QKD光波长的增大,密钥生成率和安全传输距离得到提升,在糟糕的海洋环境下,当光波长由470 nm增至532 nm时,最大安全距离由77 m延长至85 m。这主要因为一方面光波长的变化会影响“泡沫-不规则海面”的透射率;另一方面,光波长的增加虽会使泡沫粒子的尺度参数减小,导致泡沫散射系数增大,偏振误码率上升,但在蓝绿窗口内海水的衰减系数(尤其是散射系数)会随波长的增大而减小,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光子在海水中的能量衰减。此外,532 nm光源发展较成熟且应用较广泛,因此空-水QKD可选用532 nm作为目标波长,以尽可能延长其安全传输距离。
6 结 论
本文针对实际泡沫覆盖不规则海面下的非均匀空-水信道,综合考虑海面泡沫和海风作用、空-水信道的复杂多变性及量子偏振态连续经受多重散射过程,基于Mie和Rayleigh散射理论,构建了完整的非均匀空-水信道复合模型,包括基于高度分层的大气信道模型、基于叶绿素浓度的深度分层海水信道模型和“泡沫-不规则海面”界面模型。在此复合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QKD系统量子误码率理论模型,并采用偏振矢量蒙特卡罗算法模拟,讨论了非均匀空-水信道的光量子传输性能。且以4强度诱骗态BB84为对象,详细分析了不同海洋环境下空-水QKD系统的误码率、密钥生成率和安全传输距离及光波长对空-水QKD的影响。结果表明:清澈海水(JWT I型)能保障水下百米量级的QKD;经非均匀空-水信道,QKD信号光子因受信道折射和散射作用影响,当风速和传输距离增加时,会加剧光子退偏效应,使其退偏比增大,保真度减小,导致偏振误码率上升。由于风速会影响空-水信道的界面波动程度,海面泡沫会引发光子散射,且两者均会影响界面透射率,因此风速和泡沫层厚度的增大都会造成量子误码率的上升,密钥生成率和安全传输距离下降。当信道无风无泡沫变至暴风40 m/s且泡沫层为6 cm时,水下传输距离由120.8 m缩短到85 m,基本能保障水下航行器百米级的安全潜深,加上拖拽浮标等措施可进一步确保空-水QKD的安全距离。此外, QKD的密钥率和传输距离随蓝绿窗口内的光波长的增大而增大。综上所述,实际非均匀空-水信道下的诱骗态QKD即使在海风和泡沫的剧烈影响下仍可在清澈海水中实现百米量级的密钥分发,这对未来构建空-水一体的量子通信链路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