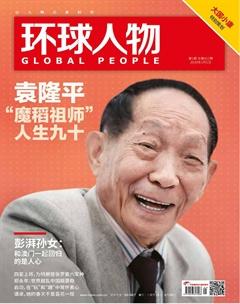克格勃杀加缪?有点荒谬
陶短房

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生于阿尔及利亚,早年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二战期间参加反对纳粹的反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担任《战斗报》主编。上世纪3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是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7年,44岁的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后的1960年1月4日,加缪在度假途中死于车祸。
60年后,一位意大利作家声称,加缪之死并非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是一场意外——他是被苏联克格勃谋杀的,而当时的法国政府“或许也脱不了干系”。
“旧货翻新”的“阴谋论”
提出这一论调的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卡特里,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诗人、翻译家扎布拉纳1980年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得出了这一令人惊讶的结论。
扎布拉纳在日记中称,1957年3月,加缪在法国《自由射手报》上刊登一篇文章,称颂苏联反体制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并激烈抨击了1956年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現,由此引来杀身之祸。扎布拉纳援引“可靠的消息来源”称,克格勃高官谢皮洛夫1957年下令“制裁”加缪,具体执行者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找到合适的机会,他们设法将一种特殊装置装进了加缪所乘汽车的轮胎,当汽车达到一定速度后,这种工具会不知不觉地刺穿车胎,导致汽车失控。
早在2011年,卡特里就毫不怀疑地采信了当时已经去世的扎布拉纳所写的一切,并在《米兰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以此为基调的文章。不过,此说在当时就引发激烈争议。《加缪传》作者奥利佛·托德直言不讳地指责卡特里的论点“纯属基于阴谋论的捕风捉影”。托德和加缪本人以及公认最熟悉加缪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朋友圈”过从甚密,《加缪传》对传主生平记载详细且持论公允,对其死因描写更是细致入微,他的论断可谓一言九鼎,“卡特里假说”就此波澜不兴,一度被人遗忘。
不甘心的卡特里,此后又花了数年时间为自己的说法寻找论据:他采访了扎布拉纳的遗孀玛丽,翻阅了克格勃在冷战期间渗透法国的各种档案材料,包括被认为“说话不靠谱”的法国律师维尔热的一些相关证词。他将这些都写入自己的新书《加缪之死》,重申加缪之死不是意外而是阴谋,罪魁祸首正是克格勃,并暗示当年“不作为”的法国当局也是间接帮凶,因为后者急于同苏联搞好关系。
卡特里还为自己的“新书老观点”拉来一位“吹鼓手”——意大利大律师斯帕扎里,这位大律师在《加缪之死》一书的意大利版上市后发表书评,称自己“的确曾经听已故的维尔热律师说过这些”,但“细节他没透露,大概不敢透露吧”。
《加缪之死》已在法国、阿根廷和意大利3国出版,卡特里正摩拳擦掌,要在英国出版英译本,并斥资在《卫报》等媒体上大打广告,连篇累牍地渲染这一“旧货翻新”的“阴谋论”。
孤独的加缪
加缪1913年11月7日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今为阿尔及利亚德莱昂),父母都是法国移民后裔。年轻时他曾渴望成为一名足球守门员,但17岁时患上结核病让他梦想破灭。这一疾病还让他在二战时期入伍抗击纳粹的理想落空。
年轻时的加缪是个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曾先后在1935年和1936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并在二战期间撰文激烈抨击纳粹,号召法国人抵抗法西斯主义。战后,他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开始“既反美又反苏”,并因此与当时普遍左倾的法国社科界、包括自己的多年挚友萨特关系破裂。
加缪开始抨击一切政府和一切权威,激烈地反对死刑(尽管二战期间他曾积极主张处决法西斯分子),热情讴歌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他猛烈批评苏联,但也并不支持苏联的对手。1952年,联合国接纳独裁者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成为会员国,加缪愤而辞去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以示“不与法西斯主义者同流合污”。

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卡特里(上)引发争议的新书《加缪之死》(下)。

1960年1月导致加缪死亡的车祸现场。
在故乡阿尔及利亚,加缪和他的父辈是尴尬的存在:在法国移民后裔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穷人,没有金钱,没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当地阿拉伯人和卡皮里人眼里,他们又是如假包换的“殖民者”,享受着远远高于当地土著的特权。这些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后裔被统称为“黑脚”,夹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间左右为难,本土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乡巴佬”,而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人又视他们为“侵略者”和“异己”。
加缪就是一个典型的“黑脚”,面对两难,他用经典的“黑脚思维”来应对:既毫不留情地斥责法国当局、军方、地方警察和“黑脚”中强硬分子的残暴行径,又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殖民起义。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他一方面认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的殖民统治也是正当的,并天真地恳请厮杀中的双方停火,“和和气气地商谈如何共存”,结果自然让双方都远离他。他绞尽脑汁试图说服两边,结果却是两头不讨好。
正如《加缪传》所言,加缪自幼父亲亡故,家境贫寒,后来又饱受疾病伤害和妻子背叛之苦,这给他的人生和心理带来巨大创伤,令他对家庭、忠诚、正义等许多理念产生质疑。但他又说:“世界并未与我为敌,我的童年也是幸福的。”他曾激烈地质疑哲学、质疑文学,最终却成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法兰西人。他公开说自己“绝不是个存在主义者”,却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铭刻于史册。他支持一切反抗,并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却又质疑反抗的目的性,认为反抗的意义不在于拯救世界或人类,而在于拯救反抗者自身的灵魂,也就是说,反抗的意义仅仅在于人必须反抗而已。正因如此,尽管化名“伯夏尔”的他在二战期间的反抗宣传曾激励过千万人,但作为加缪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表现却让无数人感到困惑。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界,加缪曲高和寡,只和著名出版社加利玛尔及其负责人米歇尔·加利玛尔关系很好。1960年1月4日,加缪应邀搭乘加利玛尔驾驶的私人汽车去勃艮第地区度假。汽车行驶至里昂附近,在一处10米寬的直道上突然失控,撞在一棵大树上,加缪当场死亡,加利玛尔几天后也在医院去世。
里昂附近小镇维勒布勒万的大富萨尔广场,有法兰西领土上仅有的一处“准官方”加缪纪念地:一座乍一看无法分辨的纪念碑,一边镌刻着加缪的浮雕头像,另一边是市议会的致敬铜牌——这里正是加缪因车祸丧命的所在。耐人寻味的是,加缪本人最厌恶的死法恰是车祸,他曾说“没有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事”。
加缪最好的朋友和“敌人”萨特有着无可比拟的大众魅力,他的墓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蒙帕纳斯公墓,墓地前总是摆满鲜花,永不寂寞。而与之齐名的加缪却只能孤独地长眠于他晚年曾经居住的卢马林农场的墓地,在一块朴素的墓碑后与一群普通人为邻。但这种孤独、寂寞也许恰是加缪所期待、所欣赏的。出身贫寒、习惯于孤独和独立思考的他,总是有意与各种奖项、荣耀和社会名流保持距离。对他而言,这里恐怕是比贝尔·拉雪兹公墓、蒙帕纳斯公墓甚至巴黎荣军院更幸福的所在。“但愿人们真的能了解我”,加缪去世前不久曾如此说。在他的《西西弗斯神话》中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

加缪长眠于卢马林农场墓地,墓碑十分简陋。
“阴谋论”可信吗?
特立独行的加缪,完全想不到在离世60年后,还会有这么多奇怪的猜测依然追随着他。
和2011年时一样,卡特里执拗地捍卫自己的“阴谋论”,他的支持者包括前面提到的律师斯帕扎里,以及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等。早在2011年,奥斯特就反复发表论调相同的文章,称卡特里“论点可信”。
但不以为然者则更多。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和加利玛尔家族后人均对卡特里的论调表示强烈不满,联手回绝了卡特里想让《加缪之死》法文版在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的要求,称之为“纯属痴人说梦”。
剑桥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埃里森·芬奇等学者从逻辑上论证“阴谋论”的破绽百出。他们指出,不论诗人扎布拉纳还是律师维尔热,都不是所谓“阴谋”的直接目击者,又都对苏联抱有毫不掩饰的仇恨,这些都足以让他们相信对苏联不利的一切,不会深究那些是否都是事实。更有评论家指出,扎布拉纳和维尔热几乎是《加缪之死》的唯一论据来源,而这两人都不是一手信源提供者,作者卡特里甚至未能在这两人生前采访他们。一个间接采访者,归纳两位“传闻听到者”所遗留文字的“二手回锅肉”式文章,能有多少说服力?
一些冷战史专家认为,二战后克格勃确实搞了一些境外秘密行动,但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同行”、反苏分子,尤其是有苏联血统的“叛徒”。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几乎站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对立面的加缪,既不是“苏联叛徒”,也远谈不上苏联的敌人——虽然他显然不是苏联的朋友。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冷战中“贵人事忙”的克格勃,会对这样一个非敌非友,且貌似并无太大影响力的外国人如此大费周章。
当然,如果卡特里真如一些读者的恶意揣测,不过是借炒冷饭兜售新书,那么他可谓大获成功:此书的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版都登上了所在国的畅销书榜,而英文版的推出,恐怕也仅是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