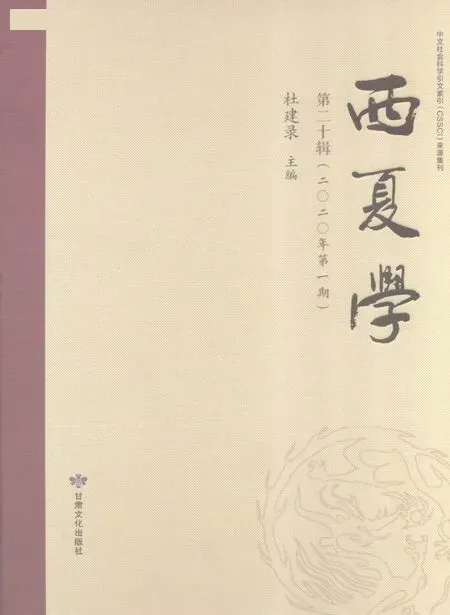灵武窑出土西夏褐釉刻花大瓶装饰图像考释
陈彦平
一、学者对褐釉剔刻花大瓶装饰图像的考证
宁夏灵武窑出土褐釉剔刻花大瓶(以下简称大瓶,图1)①马文宽:《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25页。,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口径9厘米、腹径37.2厘米、足径13.5厘米、高49.8厘米,短束颈,溜肩,深曲腹,暗圈足,通体施褐釉,腹部中间刻画有丰富的装饰图像。对于这些装饰图像,许多学者都做过考证。马文宽先生在《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一书中指出:褐釉刻花大瓶腹部“中间一马奋蹄,鞍上立有幡旗,马前一狗似为前导,狗左前侧有鹅一只,鹅右前方为一猛鹰在追捕一兔,惜因瓷片残缺而未能看到连续画面。此图刻画技巧虽欠熟练,但在瓷器上用刻釉技法表现出行猎的场景,尚属罕见。”②马文宽:《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2—3页。李知宴先生指出,“灵武窑出土的褐釉刻花大瓶,厚厚的釉层上刻画一组幡旗画面。瓶肩部一圈无釉,腹中央一马驮着一朵盛开的莲花,上立幡旗,马前是耷耳奔跑的犬,犬的左前侧是一只肥鹅,鹅前方是猛鹰在追逐一兔,画得纯真稚拙,生动异常”③李知宴:《西夏陶瓷的初步研究》,《河北陶瓷》1990第9期,第43页。。这两位专家学者对大瓶装饰内容的考证基本是一致的,唯一的分歧是马文宽先生认为马背上刻画的是马鞍,而李知宴先生认为是一朵盛开的莲花,马文宽先生还指出此图表现出行猎的场景。另有学者赵龙认为大瓶腹部装饰图像与送葬有关,他指出,“马的后方刻有靴子挑着灯,从整个构图的走势来看,靴子后面尚有其他的物品,……从这里也能窥视出西夏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都是希望已故的人在阴间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①赵龙:《西夏瓷器民族风格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80—81页。。对于大瓶装饰图像所反映的主题,学者尤桦、于慧黎认为与西夏贵族驯鹰狩猎有关②尤桦、于慧黎:《西夏猎鹰与民族文化探析》,《西夏学》第十六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图1 褐釉剔刻花大瓶
从以上简要梳理来看,学界对大瓶装饰图像的内容及主题并未形成统一见解。由于分歧见解的存在,使得我们对大瓶装饰图像还需做进一步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二、大瓶装饰图像考释
(一)马
大瓶腹部中间装饰的主体图像,应该就是一匹马。马四肢迈开,尾巴长拖,颈部细长略微弯曲,虽刻画粗略,但马的特征表现的还是很到位。唯一让人疑惑的是马的颈部过于细长,整体比例显得不协调,跟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马的体型特征相差甚远。然而,这种颈部细长的马在西夏以及宋辽时期的美术考古中确有发现。 如西夏岩画中就刻画有一种颈部细长的马③崔星:《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5期,第93页。;另外,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子辽墓一号墓墓道两壁所绘备马图中各有一匹马,一站一走,右侧壁的马头小而颈细④邵国田:《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第1005页。,学者冯恩学考证,这种头小而颈细的马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以及库伦旗前勿力不格墓地等的壁画中均有发现。他通过对唐墓、辽墓壁画中所见部分马匹的体长与头长比值的实测和比值对比,认为辽马的体长与头长比值要高于唐马。他还通过对宋代李公麟《五马图》等绘画作品中马的体长与头长两项数值的对比,认为绘画作品中这种马的体长与头长比例之间的差别“似乎不会仅是因为各代画风差别所致,而应与马的品种相关”⑤冯恩学:《辽墓壁画所见马的类型》,《考古》1999年第6期,第88页。。依据冯恩学的考证,这种头小而颈细长的马的确存在。另外,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五代时契丹画家胡瓌的《番马图》上,有北宋人郭雍的跋文,“……衣裘鞍马皆北狄也,马之颈细而后大者,胡人谓之‘改马’”,从中我们可得知这种颈部细长的马在当时被称为“改马”①曹星原:《传胡瓌〈番马图〉作者考略》,《文物》1995年第12期,第80—90页。。
(二)猎狗、鹅与幡旗
大瓶马前刻画的应该就是一猎狗,猎狗大耳朵耷拉,尾巴略带旋转状卷起,特征很明显。猎狗的前方,马文宽先生等一致认为刻有一鹅,鹅的前方,刻有一猛鹰追捕一野兔,由于本文依据的图片资料并没有显示出鹅前方的图像,所以笔者也认为鹅前方是猛鹰在追逐一兔。但对于猎狗前方的鹅,笔者通过对大瓶图像的仔细观察发现,大瓶上刻画的应该是一天鹅,而不是鹅。鹅与天鹅的外形特征很相似,如脖子长、身体宽壮、尾短等,但两者在体型上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天鹅的颈要比鹅的颈长,天鹅的颈一般超过体长或与身躯等长;其次,天鹅属鸟类,鹅属家禽,所以,天鹅的翅膀和尾羽要比鹅发达。大瓶所刻画物象的外部特征是颈超过体长且尾羽很突出,所以,应该是天鹅更为准确一些。另外,综合整个大瓶腹部画面来看,画面再现的是野外活动,而鹅是已经被驯化了的家禽,再去捕捉它或者让它像猎狗一样去捕捉其他猎物显然都不太合理。再次,从目前发掘的文献资料来看,确有辽夏时期游牧民族利用海东青捕捉天鹅的记载,如据《辽史·营卫志二》载:
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②[元]脱脱等:《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374页。
这则文献记载的是辽国皇室擎海东青捕捉天鹅的情景,处在同一时期的游牧民族驯鹰狩
猎过程应该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它也可以作为我们探讨西夏党项族狩猎习俗的参考资料。从文献“鹘擒鹅坠”一词可以看出,擎鹰狩猎过程中的鹅指的就是天鹅。很显然,鹘与鹅经过一场搏斗之后,是从高空中坠落的,那么,这里的鹅肯定就是天鹅了。综合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大瓶腹部狗的前方刻画的是一只天鹅。至于学者们为什么认为是鹅,或许他们所说的鹅就指的是天鹅,或许是与天鹅处在陆地上,而没有在天空中飞翔,因其特征很接近而误认为是鹅。那么,大瓶上天鹅为什么没有在天空中,而是在陆地上呢?从文献记载的辽国皇帝用海东青捕捉天鹅的过程来看,有“鹘擒鹅坠”“举锥刺鹅”的环节,也就是说,当天鹅被海东青从天空中击落至地面之后,天鹅并不会立刻死去,还需要狩猎者继续捕捉直到最后刺杀,而大瓶画面中再现的应该就是天鹅坠地之后被猎狗捕捉的情景,这也许就是大瓶上的天鹅处在陆地上的原因吧。在这里,不论学者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认为大瓶上刻有一鹅,但鹅与天鹅之间确实存有区别,为了使画面图像更为明确,笔者在这里对天鹅做了详细的考证和明确的界定。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大瓶画面狗前方刻画有一天鹅,表现的应该是猎鹰击落天鹅至地面之后被猎狗追捕的情景。既然大瓶上刻画的是天鹅,那么,依据有关海东青捕捉天鹅的文献记载,大瓶上的猛鹰可能就是海东青了,因为只有海东青才最擅长捕捉天鹅。
马背上的图像,学者们考证刻画有一幡旗,从画面来看,幡旗刻画的比较模糊,特征不是很明确。在辽皇帝捕猎的文字记载中也多处出现幡旗,“有鹅之处举旗”“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另外“探骑驰报”中探骑背部也可能有一面旗,可见幡旗在整个捕猎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西夏岩画中,画面中有一人骑马,身后有类似于猎犬、野鹿等动物,应该与党项族的狩猎有关①崔星:《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5期,第93页中认为是出征图。因为马后有类似于羚羊的画像,所以笔者认为是与出猎有关。,而画面中的人物也举一旗。由此可见,大瓶的马背上刻画一幡旗是与整个画面内容有关联的。
(三)马鞍与莲花
马背上除了幡旗,还刻有一个物象,马文宽先生认为是马鞍,而李知宴先生认为是一朵盛开的莲花。从大瓶图像来看,马的躯干部位刻有一马垫子,垫子上刻有一马镫,马镫直接连着马背上的物象。既然有马镫,那么与马镫相连的应该就是马鞍,另外,马背上驮一朵盛开的莲花,似乎很难去解释其用意,更何况是一朵体型无比硕大的莲花。因此,马文宽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合理一些。然而,从图像特征来看,马鞍的形状却似一朵盛开的莲花,但从马鞍的发展演化过程来看,如此造型的马鞍是不存在的。
依据学者李天宇的考证,中国境内的马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这一时期马鞍的造型极为简陋,形似于一个鞍垫。西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马鞍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高桥鞍”,其造型特征为,鞍的两头直立、鞍桥较低平。隋唐时期,“高桥鞍”的造型略微发生了变化,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向下倾斜,宋辽时期,马鞍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是“契丹鞍”的制作工艺在鲜卑、突厥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不过整体造型还是“高桥鞍”的特征,仅是马鞍整体加宽,前鞍桥加高,后鞍桥略低于前鞍桥,辽代北三家子 M1《契丹人引马图》中马鞍,在造型上就是“高桥鞍”的特征②李天宇:《马鞍的由来及演化》,《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93—96页。。西夏时期的马鞍,在西夏美术考古中也有发现,如武威西夏遗址花大门石刻塔群的崖面正中,有一较大石龛,石龛右壁阴刻两匹马,其中后面大马的马背上刻有一马鞍①于光建、黎大祥:《简述武威西夏文物中的马》,《陇右文博》2014年第2期,第35页。。从马鞍造型来看,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这跟中国古代一直流传的“高桥鞍”的造型一致。另外,在原甘肃省武威县城西北隅的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木板画,其中有一幅牵马木板画,表面彩绘一牵马人物图,马背负黄色马鞍。此图中的马鞍造型比较简陋,跟战国西汉初年的马鞍造型一样,形似于一个鞍垫(图2)②汤晓芳:《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图2 武威西郊林场牵马人物图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马鞍造型发展的梳理以及西夏时期马鞍考古资料的发掘来看,无论是比较简陋形似鞍垫的马鞍,还是“高桥鞍”,马鞍造型的设计是以适合骑者骑坐为出发点的,西夏马鞍的造型也不例外,从永昌花大门石刻中的线刻马鞍以及武威西郊林场马鞍木板画彩绘马鞍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然而,大瓶马背上的马鞍却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显然,这种造型的马鞍并适合骑者骑坐。既然马背上刻画的图像是马鞍的说法也说不通,那么马背上刻画的图像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发现,虽然马背上的物象既不是莲花花瓣状马鞍也不是盛开的莲花,但都与莲花有关。莲花,象征纯洁,寓意“吉祥”,是佛教艺术常见的装饰题材。莲花装饰在西夏也很盛行,西夏瓷器中就有大量的莲花装饰,有学者通过考证指出,这种莲花装饰是与西夏崇尚佛教有关③刘文静:《西夏瓷的纹饰图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19页。。另外,前文提到的武威西夏遗址花大门石刻塔群,在北部山崖离地面一至十米的崖面上雕刻有50余座藏传佛教浮雕塔。在崖面正中洞窟内,正壁阴刻一西夏文“佛”,洞窟右壁除了阴刻两匹马以外,在后面大马的旁边还阴刻一朵莲花。武威杂木寺石刻遗址残存塔基之下有一处石刻佛像遗存。上组存五佛,下组存四佛,上下组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上排五佛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花座置于法台之上,法台左右浮雕一对背立的马。宿白先生认为此处石刻造像较为特别,特别是双马驮佛坐具还属在国内仅见,而造像风格极有可能是属于西夏时期①于光建、黎大祥:《简述武威西夏文物中的马》,《陇右文博》2014年第2期,第34—35页。。在这两座西夏时期的佛教遗存中,都有莲花装饰,而且,莲花装饰与马同时出现,特别是武威杂木寺石刻遗址塔基上,双马法台之上置一莲花座,宿白先生称之为在“双马驮佛坐具”,佛坐具就是莲花座。“双马驮佛坐具或莲花座”这种形式将马和莲花座紧密关联在了一起。如此看来,既然大瓶马背上刻画的图像是马鞍与莲花的说法都说不通,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大瓶马背上的图像理解为一种雕刻成莲花花瓣形的坐具呢?“双马驮莲花座”这一图像与大瓶“单马上一莲花形坐具”两者之间是非常的相似,由此笔者大胆的推测,大瓶装饰中马背上的图像就是一莲花座。
另外,大瓶腹部刻画的狩猎图像与《辽史·营卫志二》记载的狩猎场景以及西夏岩画中的出猎图最大的出入是,大瓶马背上只刻画有幡旗,而没有刻画人物。依据文献记载,射猎过程中,有“有鹅之处举旗”的士兵,还有“举帜”的“左右围骑”。西夏岩画出猎图中马背上有一人举一幡旗。那么,大瓶的马背上为什么只刻画有幡旗,而没刻画人呢?这也许就跟马背上的物象有关,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发现,在西夏佛教装饰中,马与莲花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大瓶马背上极有可能驮的是一莲花座。如果马背上的物象是莲花座的话,那么,莲花座上刻画的物象就不是普通的人了,而应该与佛教有关,这也许就是大瓶马背上只刻画有幡旗,而没刻画人的原因吧。由此可见,大瓶装饰图像所再现的是一场充满了浓厚佛教色彩的西夏党项族擎鹰狩猎活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西夏狩猎题材的装饰图像中为什么会有佛教因素呢?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也许跟现实生活中的西夏狩猎活动有关,也就是说,西夏狩猎的过程中会有佛教礼仪活动;另一方面或许就是工匠在绘制、刻画狩猎场景时出于某种考虑而加上去的。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在此不敢妄加深入。但是,在黑水城出土的一幅《西夏皇帝和众侍从》图画中②尤桦、于慧黎:《西夏猎鹰与民族文化探析》,《西夏学》第十六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33页。,人物的头顶绘有一组飞天画像,两飞天衣带随风飘逸、凌云飞翔。飞天是佛教中非常典型的装饰题材,很显然,这幅与西夏狩猎有关联的图画也充满了非常浓郁的佛教色彩。而现实生活中是没有飞天的,所以,黑水城出土的这幅狩猎图画中的佛教元素应该就是工匠在绘制、刻画的过程中加上去。由此可以推测,大瓶装饰图像中的佛教因素也与现实生活中的西夏狩猎活动无关,而是西夏佛教信仰在装饰艺术中的体现。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笔者认为,西夏褐釉刻花大瓶腹部中间的装饰图像表现的是西夏党项族的一次集体驱鹰狩猎活动。整个装饰以马为主体,马头小而颈部细长,马背上刻画有一莲花花瓣状坐具,坐具上立一幡旗。马的前方刻有一只猎犬追捕一只坠地的天鹅,天鹅前方是一海东青追捕一野兔。马背上的莲花状坐具形似佛教中的莲花座,整个狩猎画面由此充满了浓郁的佛教色彩。工匠巧妙地将佛教中的莲花装饰和马背上的坐具相结合,既含蓄地传达出了西夏人的佛教信仰,又使整个画面的狩猎气氛非常和谐。大瓶上的装饰图像,不仅是西夏社会狩猎场景的再现,更是西夏人佛教信仰在装饰艺术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