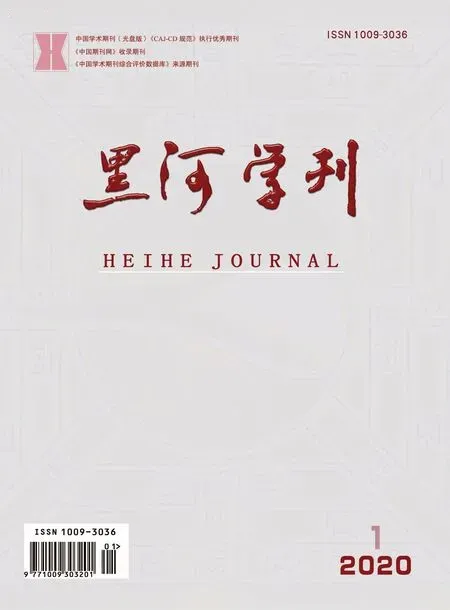论陆焉识的俄狄浦斯情结
王 鑫,时曙晖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 伊宁 835000)
严歌苓身为美籍华人作家,其作品每次出版都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于2011年出版的小说《陆犯焉识》也不例外。《陆犯焉识》主要讲述了男主角陆焉识波澜起伏的一生,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陆焉识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陆焉识与很多女性都有过情感上的瓜葛,但实际上这些爱情背后都有着其继母冯仪芳的影子,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恋母情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陆焉识在面对母亲冯仪芳的时候会时常陷入幻想这一现象,以及之后对自己妻子冯婉喻前后期情感上的转变,都表现出了其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而陆焉识身上之所以展现出了这些特点,一方面是因为陆焉识的懦弱的性格催生出了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也与其特殊的家庭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俄狄浦斯情结,又被称为恋母情结。具体来说就是指在来自异性父母的刺激下,孩子自身表现出对异性父母产生爱恋,同时也会表现出对同性父母产生妒忌与憎恨。在陆焉识身上具体表现为会在幻想之中对母亲冯仪芳产生出类似与对“妻子”的感情,以及之后对社会秩序的仇恨,同时对自己的妻子前后的情感上的转变,也体现出了其身上的恋母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孩子会对母亲表现出一种具有乱伦性质的欲望,但孩子的这种欲望并不会直接化为一种行动,而是通过一种幻想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孩子现实化这个不能实现的乱伦欲望的企图。但是这个乱伦欲望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虚拟的欲望,从来不曾满足,它是客体,是父母中的一个且它的目标并非是要获得生理快乐,而是获得享乐”。面对孩子不断的索求,母亲不可能一一有所回应,这使得孩子的欲望得不到最为理想化的满足,而这些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迫使孩子建构起一个幻想,在这个幻想中母亲的所有都属于自己,自然自己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得到回应,由此看来在孩子的幻想之中,母亲充当了一个类似于“妻子”的角色。
对于陆焉识来说,母亲冯仪芳充当的就是这样存在于幻想之中的“妻子”的角色。在小说中恩娘冯仪芳经常会对陆焉识做出一些过分的举动,但陆焉识并没有抵触恩娘的恣意妄为,“他不在乎恩娘那一眼是多么媚,多么抹杀辈分甚至体统。恩娘暗中想在他身上索取什么就索取什么吧”。从表面上看,陆焉识是在忍受着恩娘种种出格的举动,但通过文本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陆焉识至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一丝忍受的痛苦,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悲悯。这种悲悯是高高在上的悲悯,“焉识一阵悲冷:一个男人要折磨女人,摆布女人多容易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陆焉识之所以会这么想,都是因为陆焉识为自己建构起了一个幻想,在这个幻想中,恩娘的命运是惨痛的,而这种惨痛的命运的原因是在于其自身身份的卑微。在自己幻想世界的恩娘是卑微的,自然也有义务与职责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她的可怜,她的卑微,她做出的那些动作与行为,无不是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觉得她(恩娘)可怜得动人极了,他看入迷了”。总之,陆焉识其实是在享受恩娘,享受着冯芳仪的卑微与楚楚可怜,而正是这样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陆焉识的恋母情结。
陆焉识的恋母情结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冯婉喻“无爱”的婚姻上。在恩娘的胁迫下,陆焉识不得不与冯婉喻结婚。但这段婚姻对于陆焉识是痛苦的,他一直在内心世界宣称着自己对冯婉喻的“无爱”,甚至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心中也无不盛满了痛苦:“坐在座位看戏的时候,他心里的牢骚往上涨,连胳膊都不愿意碰到婉喻”。沉溺在恋母情结下的陆焉识清楚的感受到他的爱是属于恩娘,能够充当他的“妻子”的自然也只能是恩娘,相较而言,婉喻成了一位可有可无的“妾”,而他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妻和妾之间周旋的男人”。
但随着母亲这一角色的离席,陆焉识对冯婉喻的情感发生了转变,而这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恩娘去世之后,陆焉识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着的是冯婉喻。陆焉识在劳改岁月中回忆着婉喻的好,并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忏悔着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以此来突出自己有多么地爱着婉喻。可事实上,这种看似正常的情感转变其实是陆焉识恋母情结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妨先看看陆焉识对冯婉喻的第一印象:“所以十八岁的陆焉识在1925年6月初的下午跨进客厅时,看到的不止一个恩娘,还有一个小恩娘——长着恩娘的细长鼻子,细白面皮,裙子下露出跟恩娘一模一样的解放脚,穿着跟恩娘一模一样的黑色仕女鞋”。可以看到陆焉识在第一次见到冯婉喻的时候就显露出将其与恩娘混淆的倾向,模样的相似使得冯婉喻在陆焉识眼中成为了恩娘的代替品。随着恩娘的去世,冯婉喻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在恩娘去世后,陆焉识经常会在心里用“小恩娘”这个称呼来称呼冯婉喻,也就是说在陆焉识心中,此刻的冯婉喻就是恩娘,就是自己恋母欲望的承受者。所以如果说恩娘冯仪芳所做的是将陆焉识的恋母情结激发出来,那冯婉喻存在的意义就是为陆焉识的恋母情结提供了一种延续下去的可能。
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还会使孩子对父亲产生仇恨这一情绪。精神分析认为,在孩子不断坚持自己恋母情结的过程中,他发现由于父亲的存在,母亲并不能完完全全地属于自己。因此他憎恨着占有着母亲的父亲,同时也因为自己与父亲力量悬殊,又不得不强忍着自己对母亲的性欲。于此,孩子便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孩子知道由于父亲的存在自己永远无法得到母亲,另一方面孩子又不愿割舍自己对母亲的爱以直面现实,所以为了缓解现实给予他的痛苦,“虽然他会对于阻断自己和母亲的父亲心生恐惧与反感,然而最终还是会服从于父亲的规则,接受自己长大后变得像父亲那样,同时找到一个女人充当母亲的替代”。孩子就这样一边与现实妥协,一边长大。
但是在小说中,陆焉识父亲这一角色一直都是缺席的,所以替父亲承担起陆焉识的嫉恨与仇视的是社会的秩序与伦理。在小说中,陆焉识一直都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遵守着学术圈的潜规则,站好队伍,而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一直对自己标榜着“不属于”。陆焉识就是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抗着充当自己“父亲”的社会秩序与伦理,但事实上,他以一己之力又怎么可能撼动社会秩序与伦理,从这个角度上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小说中的陆焉识一直都怀着一种迷茫感与无力感,正如恩娘在去世前评价他那样:他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随着恩娘的去世,俄狄浦斯情结迫使陆焉识将自己的情感转向自己的妻子,而这种被动的欲望移置却矫正了陆焉识秩序与伦理的缺失。虽然陆焉识对妻子的深情还是建立在自己恋母的欲望之上,但是此刻欲望的驱动却又使得陆焉识回归到正常的伦理结构当中,他的恋母情结使得他爱上了自己的妻子,爱上了秩序规则允许他爱的女人。以此为起点,陆焉识开始感受到了社会秩序与规则的存在,并且开始认同这种伦理与秩序,他不再像恩娘活着的时候那样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而是尝试学会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规则,并且加以灵活运用。可以说,社会的规则充当了那个让他痛苦的“父亲”。陆焉识在生活上的碰壁使他发现自己一直都陷入一种骗局当中———自己没有自己想像那样伟大,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撑起整个陆家的,他需要社会的帮助,而获得帮助代价就是遵守社会的规则,所以他可以在劳改的时候装聋作哑,必要的时候也会奉承与贿赂,他尽自己一切可能学会这个社会的秩序与规则,并且遵守它,利用它,进而求得对自己的保护。
二
陆焉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有着其独特的原因:一方面从客观上讲,自己亲生父母早逝的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陆焉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由于亲生母亲的缺失,使得年幼的陆焉识心底潜藏着失去母亲的痛苦,而继母冯仪芳的出现,无疑填补了陆焉识心中对母爱的缺失,正是如此,陆焉识格外地珍视自己的继母,同时为了防止失去母亲这一悲剧的重演,陆焉识对冯仪芳充满了保护欲,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陆焉识的恋母情结。而父亲的早逝导致陆焉识的母亲冯仪芳缺少了合法的伴侣,无处释放的欲望自然移置到了家中的另一个男人陆焉识身上,继母冯仪芳种种具有勾引意味的行为无疑刺激着陆焉识恋母情结的形成,而由于缺少来自父权的压迫,陆焉识面对继母的勾引,无疑可以做到坦然接受。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陆焉识性格中的懦弱与妥协使他失去了选择恋爱对象的自由,陷入了“无爱”婚姻之中,而为了报复使自己痛苦的婚姻,他选择将自己的爱倾注到继母冯仪芳身上,以此来抗拒着自己真正的妻子冯婉喻,而这种抗争的方式,恰恰又使得陆焉识陷入了恋母情欲之中。
年幼时缺少母爱的经历,使得陆焉识对母爱格外地渴望,而这种渴望感无疑影响着其恋母情结的形成。小说中并没有提及陆焉识的亲生母亲,但通过继母冯仪芳“填房”的身份可以判断出陆焉识的亲生母亲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过早地失去母亲无疑在陆焉识心中留下了情感的伤痕,年幼的他深刻地体会到失去母亲的痛苦,并随着之后的成长,这种痛苦一直潜藏在陆焉识的无意识当中。直到继母冯仪芳要被自己祖母赶出家门的时候,陆焉识心底的失去母亲的痛苦再度被唤起,他无法忍受自己再度失去母亲的痛苦,所以他在冯仪芳即将离开陆家的时候站了出来,“十四岁的焉识说,他绝不会让人把恩娘退回娘家;他已经大了,不久就是陆家当家的男人,该他来赚钞票养活恩娘了”。陆焉识对继母挽回实质上就是在促成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童年时期母爱被剥夺的痛苦不会轻易从心理中消失,母爱的缺失使陆焉识对母亲这一角色的渴求不断生长,而挽回继母实际上就是在缓释着自己心中失去母亲的痛苦;同时,在挽回继母的过程中,陆焉识感受到了自己在这个家庭结构中的强大力量,使他产生了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母亲,甚至是占有母亲的认识,而这样的想法无疑激化了陆焉识的恋母情结。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陆焉识的父亲在其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也就意味着冯仪芳在嫁到陆家没有多久就失去了丈夫,换句话说冯仪芳合法的欲望对象是缺席的,她过剩的欲望迫使她去找一个对象来宣泄,而人选自然就落到了陆家最年长的少爷陆焉识身上。正如弗洛伊德所宣称的那样:“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也与父母的刺激相关,父母的爱常表现出选择性,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如果婚姻降温,子女很可能成为他们爱的替代物”。事实上,这样感受母亲偏爱的机会对于陆焉识来说成为了一个刺激,使得他开始感受到来自异性的快感,这种快感具体在文中体现为恩娘为陆焉识单独做一些好吃的,或者在坐车的时候恩娘贴着陆焉识坐,这些行为看上去像是一种母亲的偏爱,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其中具有着挑逗的成分。这些行为更像是打着母爱的幌子,实际上是对自己儿子的引诱。而正是这种引诱,促使陆焉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同时不可忽略的是,陆焉识父亲缺席也对陆焉识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父亲这一角色的缺席,陆焉识这种乱伦式的欲望便无法得到控制,没有人能阻碍陆焉识向恩娘的索取,这无疑就形成了一种最为完美状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构———没有父亲的约束与管制,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的俄狄浦斯式欲望。
俄狄浦斯情结本质上是我们沉淀在我们无意识层面中的乱伦情欲,这种情欲体现为孩子渴望占有母亲,而其产生是有着其主观原因的。精神分析派认为:“哺乳经验的挫折激起了俄狄浦斯情境……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是在‘恨’的驱使下产生的”。换句话说,婴儿因为无法获得及时的哺乳,产生了对母乳渴望而不得的焦虑,而正是这种无法满足的痛苦转化为一种憎恨,使孩子开始痛恨那位不理睬自己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无法离开母乳的养育,于是孩子的渴求与憎恨都投射到母亲身上,促使孩子产生一种想要占有母亲的欲望。
在小说中,陆焉识一直都是懦弱的,但正是这份懦弱恰恰成了他爱上母亲的动机。陆焉识一生都在“忍受”中度过的,在被陌生人敲竹杠的时候,他选择隐忍;在被同事排挤的时候,他选择接受;在被好友对自己提出无礼要求的时候;他选择默许。他对于任何人都缺乏拒绝的能力,以至于在面对恩娘一次又一次剥夺自己珍贵的爱情自由的时候,陆焉识依然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任由这个女人恣意下去:“女人的可怜让他这样的男子没有出息,为她们常年神伤,只要她们需要,他就把他的前程、幸福、自由拱手相让,供她们去消耗、糟蹋”。可陆焉识又不甘心就这么失去爱别人的机会,他清醒地认识因为冯婉喻的存在锁死了他爱情的自由:“这个冯婉喻不光是一个十七八的花季少女,也是恩娘的一根丝,她打算用她在焉识身上打个如意死结”。他恨着这个家庭,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家的存在才使得他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但他心中的懦弱又不允许他彻底地割舍掉这个让他痛苦的家,所以他为了报复,只能选择一个妻子以外的人去爱,以这样的形式来反抗这个剥夺了他自由的婚姻,而这个角色自然就落到了母亲冯仪芳身上。就此,出于报复,陆焉识将自己的爱投射到了冯仪芳身上。例如在婚后的生活中,冯仪芳与冯婉喻之间矛盾不断,而陆焉识每次都会站到冯仪芳的身边支持自己的恩娘,这恰恰表现出了陆焉识的报复以及这种报复衍生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说,正是在这样扭曲的报复之中,陆焉识的懦弱催生了自身的恋母情结。
总之,无论是在面对关于恩娘的幻想,还是在面对冯婉喻的深情,甚至在面对社会秩序的方式上,俄狄浦斯情结都对陆焉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小说是如此的矛盾,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无法拒绝心底的欲望的诱惑,无法抗拒自己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是自己心底最深层次欲望的反映。而这种欲望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恩娘的种种诱惑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因为陆焉识的父亲的缺席。在二者相互作用下,陆焉识凸显出极其鲜明的恋母倾向。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