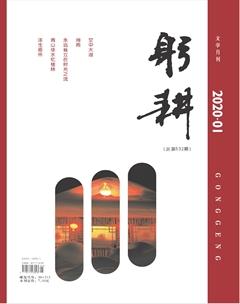空中大湖
夏江
那一夜,他又梦见自己抓住了一条很奇怪的大鱼。它有蛇一样狰狞可怕的头,黑鱼一样浑圆鼓胀的身体,鳐鱼一样又细又长的尾巴。他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却在梦中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怪亚。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叫它这个名字。怪亚刚露出水面时,着实吓了他一大跳。不过,停了一会儿,他就镇定下来。它虽然看着奇怪,但终究只是一条鱼,而且还是一条落入他网中的鱼,它能怎么着?可是……可是……接下来,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怪鱼竟然不可思议地张嘴说话了。
“大哥!大哥!你为什么要捉我呢?”鱼说。
他吓坏了,只有僵硬的嘴巴勉强咕哝了一下,“啥?”声音虚弱得像是濒死之人发出的。鱼继续说道:“大哥!我是你前世的兄弟啊!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吗?你可不能杀害自己的兄弟啊!”
“什么?兄弟!”他惊悚万分。
鱼又说:“我是你的兄弟海良啊!”
当听到“海良”这两个字时,他吓得灵魂都出窍了。
他的确有一个好兄弟叫海良,可他已经死去多年了。鱼怎么会知道?莫非它真的是……
吓死了!吓死了——
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然后,满身大汗地起床,小跑着打开门,冲到院子里去看昨天捕到的那条大鱼。大盆子还在,可里面那条奇形怪状的大鱼却不见了踪影。
这究竟是怎么了?怪事一件接着一件。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就蹲在地上,抱着大盆子扯开喉咙大哭起来。
泪眼朦胧中,眼前的大盆子开始变形,拉扯得盆中的水无限宽阔起来,像一片诡异莫测的湖泊,里面映照着神秘的天空,还有各种高大树木的影子,它们和近岸处低矮的水草交横在一起,被微微荡漾的水波扯成模糊的碎片。“大湖”里的景象充满了诱惑。他很想变成一条小鱼,自由自在地在湖底探秘……
這时候,不知是谁冲他又是吼又是叫的,还用尖利的指甲狠命地掐他的胳膊。他彻底醒了。老婆正坐在他身边。原来是一场惊梦。他坐了起来,呆呆地看着老婆。她吃惊而疑惑地瞪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嘴里开始不住地咕哝:“怪亚!海良!怪亚!海良!”
“发什么神经啊!”老婆使劲摇他,“你这会儿还在捕鱼啊?”
他随口说道:“还捕啥鱼呢?我的好兄弟都死了,我还捕啥鱼呢?”
老婆被他弄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得像大黑鱼,想要满口利牙地咬他一口。后来,她恶狠狠地对他说:“不捕鱼饿死你个鳖孙子!”
她说得对,不捕鱼他会饿死的。他就是以捕鱼为生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经常会做这样奇怪的梦。当然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梦,现在都忘掉了。只留下一个感觉:那些怪梦恐怕就是自己狼狈中年开始的预兆。只是,那时的他却不自知。现在,他是真的老了。不过,令自己分外欣慰的是,老是老了,但终究还是归来了。
虽然未必会长久待下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回来了。虽然从遥远的城市还时不时会传来一些“小干扰”,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太太已经如愿住在自己的老宅子里了。
说起老宅子,现在的他可是满心欣喜。当初,他是有一个宏伟的重建梦的,是太太轻轻点醒了他。她说:“何不雅致些呢?”“雅致”这个词甚合他的心意。就这一点来讲,太太真是个好太太。也亏得她,老宅子才能收拾得如此合乎心意。
这天清晨,他们照例起得早。山村里一片安静。他们院子里的杏树上挂着一个鸟笼,里面养了一只玲珑的小画眉,眼似黑珍珠,歌声婉转悠扬。太太很喜欢它,每天或注目,或喂食。她还喜欢养些毛茸茸的小鸭、小鸡。不过,她会在它们快要长大时,把它们送给乡邻养。靠北的墙边,是一片菜地,大概有五六畦吧!地里呢,都是些时令青菜。
在院子里待了一会儿后,他们出了大门。出了门,阳光正好笼住了他们。他们停住脚步,身后的影子便呆住了。这时,恰好有一个同样早起的老汉打门前过,看见他们时,脸上满是敬意。不巧,老汉咳嗽的老毛病这时候抑制不住地犯了,吭吭咔咔咳个不停。这样一来,老汉脸上的敬意变为羞愧,原来酱紫色的脸上泛了一层红,叫他们看了也替他难为情。
“哦!哦!恁俩老早哇!”老汉捋了捋喉咙,强忍着咳嗽说道。
“早!早!老缪早啊!”他应道。太太在身旁冲老缪礼貌地微笑。
老汉又咳嗽了。他又是嗯嗯又是咔咔的。两种声音交替着将他的身影往远处拉扯。过了拐角处,那个身影没入墙后。人影没了,激昂的声音却忽起,“恁俩的房子好哇!”
“是啊!是啊!”他不由得应着。但这样的回答似乎不合时宜了,因为老汉再也听不见——他早已走远了。
但他还在猜测老缪的心思。他觉得,老缪的心思自己应该判断得了。夸赞房子好是真的。想必老缪心里会进一步想:啥时候自己也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也许是瞎猜。老缪会羡慕他们的日子吗?恐怕还是自己乱想。日子好不好全在自己怎么想,兴许人家老缪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艰难或者平顺,知足了就好!
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笑了笑。太太注意到了他的笑,轻声对他说:“凯堂!四处转转吧!”
“好!好!”他应着。
于是他们随意而行。结果却是围着老宅转了一圈。又到门前时,他们相互看着对方笑起来。
在他眼里,老宅子就是一个梦。它四四方方,白墙黛瓦,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仿佛从江南水乡移植入北方的小山村中,难道不是梦?其实,老宅子应该是真切的梦,它和村子里的房屋相连,和高大的树木、宽阔的田野、蜿蜒的河流、连绵的群山相连,也和他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脉相连。
他想,在这一点上,太太应该是懂他的。
到了傍晚,他们一起来到村外河边的堤坝上。对岸沿河边是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它把这个秀美的小山村和南面的大城市连接了起来。晚风轻拂,脸上便有些夏日难得的清凉感觉。抬头向河流方向远望,河水蜿蜒地沿着山脚向远方流去,水面闪烁着夕阳的余光,如碎银般在水面上跃动,叫人禁不住想象水中那些白色的鱼,似乎就是它们的鳞片和落日的余晖交错在了一起。岸边是密密麻麻的野草,平铺开来,绿毯一般装扮了河边这片开阔地带。离堤坝很近的一片区域,绿草停止了自己的铺陈,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杨树。
四周环抱着连绵起伏的小山,凡是稍稍突起的山头上,也都矗立着巨大的白色风车,总得有二三十个之多吧。它们不仅充分利用了这里作为著名“风口”的自然资源,更是一下子把他的家乡装扮成了“风车之国”。这让他感到特别欣慰。
这时,他的脸上一定绽开了笑容。当然,他抑制着没有出声。因为,此次回乡,他必须控制自己,不能让太太觉出什么异样。可是,看着眼前的风景,他还是想和太太说说那个梦。
于是,他转过身来。太太正随意看着四周的山村风光。他先是看了她一眼,然后朝着与剛才相反的方向望去。远处是太子山。山脚下逐渐低缓下来的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他的家乡夏村。到了堤坝这里,就属于河流的范围了。想当年,这里也曾经有过水面浩荡,浊浪拍岸的景象。时至今日,河流已经瘦弱,再无往日的气势,但当年的印象却依然顽固。
他又看了一眼太太,他真的很想和她说说那个梦。办公室里的那幅画又在脑海里闪动了。画的名称是《海滨小镇》,是他请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油画大师创作的,有电影《云上的日子》中那个小镇的影子。虽然现在已经被儿子换成了《红日苍鹰图》,但他对原来那幅画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你看!太太,你看我们这里是不是有点儿海滨小镇的样子呢!”他的声音里带着激动。
太太看着他,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在捕捉他的内心。她是懂他的。趁着这短暂的默契,他怔怔地回味油画中的“海滨小镇”: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水汽,到处都是令人着迷的雾,空气中的味道混合了腥味儿、甜味儿和香味儿……
停了一会儿,太太轻声说:“不说这吧!”说罢,抬起右手食指晃了晃,好像是在抚摸什么东西。他也是懂的。她是在指点远处掩映在村庄中的老宅子。
“好吧!不说这了。”他回应道。
不说海滨小镇了。可鬼使神差的,他的目光又兀自窜到了那个地方——一个像钉子一样扎在心脏上的地方。它就在眼前。可真看过去时,似乎踪影难觅。有时候,越是真切的东西反而越觉得虚幻。这是他步入老年后产生的奇怪感受。
太太小心提醒过他的,莫提!他也努力这样做过。可是,又怎能莫提?忘不掉的。因为,那个地方记载了他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
“太太!你还记得月湾潭吧!”他忍不住说道,“那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捕鱼,那时候你还是个叫丁兰的农村女人。”他的语气有点儿像开玩笑。
太太用异样的眼神看了他一下。然后平静地说:“记得,当然记得。”
“还有海良。”他说。
“海……海良吗?”太太楞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哦!海良,记得。”
“你是不是又梦到他了?还有那个怪鱼?”太太突然又问他。
他点点头。然后深情地看着远处的月湾潭,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那时候啊!正是最苦的日子。他二十多岁了,家里穷得叮当响。除了种地,只能靠在河里偷偷捕鱼换些零钱。和他搭伙的是海良,他们通常是晚上捕鱼。冬天的时候,冻得要死。夏天时又经常发洪水,好几次都险些丧命。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间悄然流逝,河里面也不再平静。一开始很少有人捕鱼,渐渐人就多了起来。一开始是拉网、下滚钩、摆迷魂阵,后来就不择手段了,用药毒鱼、拉电线电鱼,甚至用炸药炸鱼……
除此之外,村民想尽各种办法在河里面“捞钱”。还有人打起了河沙的主意,他们疯狂地挖沙,把这条河弄得千疮百孔。
他们两个捕鱼越来越难,就连月湾潭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忙得要死要活也捉不到多少鱼。他和海良急得要死,整天都在想怎么发财,到后来,竟然相信了老一辈子人的传说。他们这里一直传说月湾潭里有金子。最近的证明就是几十年以前,一些外地人在潭里找到了金鸭子、金鲤鱼、狗头金……
尤其是海良,简直对此入了迷。常常念叨“金山银山比不上太子山”“月湾潭底下有个洞,洞里有个金宝藏”之类的话。
有一天晚上,他俩喝酒时,他对海良说自己曾经见到一个神秘的外地人,那人说在月湾潭里淘到一根金条。还说潭底下有一个神秘的洞穴,跟太子山相通,足有十几里长……
海良满嘴酒气冲他吼道:“你放屁吧!鬼才相信你的话哩!”
“你才放屁哩!那个外地人说的,能有假?”他不甘示弱。
“他咋能钻到潭底儿?他咋能钻进水底的洞里?他咋能钻到十几里深的山洞里?你是傻子吧你!”
他被海良激怒了,说道:“你才傻子哩!弄个潜水衣不就行了吗?老子正打算进去呢,到时候你可别羡慕老子的金子!”
当时的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想想,多半是发酒疯说胡话。
谁知,海良竟然把他的话当真了。一天夜里,他一个人偷偷跑到月湾潭里找金子,突遇山洪,整个人消失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海良的死让他很难受。一直到现在还难受。他觉得,海良是被他害死的。
从此以后,他就常常做那个怪梦:自己抓住了一条奇怪的鱼,蛇头、黑鱼身、鳐鱼尾巴。要命的是它会说话——大哥,我是海良呀!我是你前世的兄弟海良呀!
这个怪梦让他难以心安。
“海良真的是死在那里的吗?就是这个月湾潭?”他突然问太太。
“什么?什么……”太太正在想着别的事儿。
“我说的是海良。”
太太缓过神来,先是肯定地说:“是……是……”接着话锋一转,“不提以前的伤心事了!后来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不是去山西了吗?”
“嗯!”他应道。
“还是听我的对,出去对,你看现在……”她的眼光突地亮了一下,马上又恢复平静。太太接着又说,“你那时候不是一直嚷嚷着不出去吗?也说不捕鱼了……”
“还说‘咱这里五谷丰登、鱼米之乡之类的痴话。”她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事了。”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不说了,不说好!”太太语气庄重地说,“过好现在吧!现在,你……”她欲言又止。
“不说了,回去吧!”他说。
晚上睡前,他在卧室里燃了两根檀香。烟气袅袅,沁人心脾。他的心情逐渐平静,睡着时分外安然。
梦也与平日不同——成群结队的银色小鱼围绕着他,时而亲吻他的眼睑,时而亲吻他的嘴唇……忽地,怪亚张着血红的嘴朝银色的小鱼撕咬过来。吃掉了银色小鱼,又朝他咬过来……
他顿时惊醒,身上一层冷汗。还好,太太没醒。黑暗中的他深感不安。过了一会儿,心里稍稍静了些。
但还是有一些慌乱。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站在门口看院子里的风景。这时,太太左手端着一杯牛奶,右手掌心托着一枚剥了壳的鸡蛋走过来。他转身说:“放屋里吧,待会吃。”
太太没有动,两只手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似乎已经忘记了手中的牛奶和鸡蛋。她的下巴微微向上抬了抬,而后又轻轻点了一下头,诗句便从口中吐出:“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说完,眼光从院墙上擦过去,一直到达远处连绵不断的小山上。他也随着向那里望去。群山起伏,山林葱郁,被清晨的雾霭染得一片朦胧。
停了一会儿,太太悄悄转身回屋,轻轻把牛奶和鸡蛋放在桌上的盘子内,而后坐下来翻看《唐诗宋词精粹》。又过了一会儿,太太从屋里出来,手里捧的是一本书法帖页。她的脸上满是欣喜,兴奋地指着上面的“悟”说:“凯堂,你看这个悟字,多么周正端庄。”他盯着字看,感受到了这个字的方方正正和宽阔厚重。
吃过早饭,太太收拾停当后,给他沏一杯上好的绿茶。她自己呢,自然是咖啡。端过来放在桌子上,一杯是清水中竖起根根茶尖,一杯是贮在洁白瓷杯中的浓稠褐色。性质不同,感受亦不同。咖啡给人富贵和华丽之感,绿茶则代表简单直白。但在他眼里,这茶尖分明就是那悟字的“一竖”。只不过,这“一竖”究竟是颜体之敦厚,还是柳体之尖利?一时叫人迷惑。
喝到第三杯时,太太用眼神示意他有话要说。他看了看她,预感到要说的是什么事情,但还是很平静地等着太太开口。
“儿子想通了,他答应回来呢!”太太安慰他似的说。
“哦!哦!”他应着。到底还是这个事情。
“凯堂呀!儿子真的想通了!”太太郑重地说,“我也给他交代了,他答应了,他会向你汇报的!”太太竟然用了“汇报”这个词,久违了。
“真的吗?”他瞪大眼睛看着太太,“他不是对我的想法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吗?”
“以前是,这段时间我和他沟通了,他想通了!儿子呢,说到底,心里有你!”
话说到这里,他心里舒畅了许多。他还想问问孙子、孙女回不回来,但到底又不好意思问了。说起来,目前自己儿孙绕膝的想法的确是不合时宜的。城里学校的条件好,孩子上学最要紧,还要上这班那班的……
可老家也不能一次也不回来吧!总得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可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说这事儿……
午休后,太太到画室去了。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便想去外面转转。他没有打扰太太。现在,她肯定正在作画呢。
此时,他已经走在了村外的小路上。想到从外面回来后,太太必定又要拉着他对她的画品味一番时,他不自觉地笑了起来。这样的情景可真是不少呢!太太可真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啊!想到这儿,他停住了笑。太太的脸开始在眼前浮现。她的脸虽然已被岁月的风刀霜剑雕刻,但笑容仍然像开在他眼中的花。
正在品味太太的笑容时,眼前竟然真地出现了一张老妇人的笑脸。当然不是太太的,是迎面走来的一个农村老婆婆的——他竟然在这个老婆婆脸上看见了惊人心魄的东西。
他走神了。
他盯着她看……她脸色偏黑,满是皱纹……她的眼睛……
他失态了。
他们快要错身走过去时,老婆婆对着他说了一声:“出去转啊!”
他慌慌张张地应着:“嗯!嗯!”
之后,两个人就各走各的了。距离越来越远。他仍旧沉浸在刚碰面瞬间的“惊心动魄”感觉之中。
恍惚间,竟然又有一张脸从无限寂寥的时空中翩然而至,像幻影,似魂魄,像风中的柳叶,似迷雾中的照片。不只一张,是两张、三张、四张……无数个笑靥如烟似雾妖娆而来,不偏不倚正好印在老婆婆的脸上。他闭上了眼睛,他不忍心看见现实中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眼前的现实离自己的幻梦相差萬里。他别无选择,只能任由自己在恍惚中想象那个笑魇如花一样盛开。
那盛开的笑魇是太太的吗?
它是美人的剪影,是缭绕的暗香,是爱情的幻觉。分明不是太太丁兰的。
记忆中丁兰的笑脸虽然也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可它绝不是这模样,那是虚假地挂在脸上的笑。它们一旦在公共场合示人,必定包含着表面的平和大气和内里的进攻搏斗……
不!不!一定不是丁兰的。
那,那又是谁的呢?十分肯定的是,也不是那个老婆婆的。他并不认识她。
可,可……她分明给了他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在寻找。他既不想让眼前的幻觉太多太久地呈现,也不想让它过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他从老婆婆的眼神中寻找到了,那里面闪烁着一股清凉惬意而又摄人心魄的光彩——是良媛,是她的笑魇,是她的光彩。啊!美人的剪影,缭绕的暗香,爱情的幻觉,这一切的答案竟然真的是良媛。他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他甚至十分荒唐地在丁兰锐利的眼神中也发现了那种“光彩”,只不过,良媛的“光彩”迅速被丁兰的锐利和仇恨一扫而光……
幻觉还是不可避免地迅速消失了。他睁开眼。眼前空无一人,前面是惶惶然似在颤抖的小路、田野、群山、天空……
这一阵摄人心魄的幻觉和躁动让他心绪难平。但他又必须尽快平复,于是就找了一块儿平坦的草地坐了下来。
他不觉陷入回忆之中,那些遥远的往事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
四十多年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时候,他还是个穷小子。当然,不只是他,村里人都穷得叮当响。年轻人到了该娶媳妇的时候,好多都因为穷找不到媳妇。他和海良也是如此。
有一天,海良突然对他说:“丁兰这妮儿看上你了。”
他不相信,就说:“她咋能看上我?”
海良没有回答,而是咬着牙骂道:“呸,贱货!”
他不明就里,不知道海良为啥这样生气。
后才他才知道,原来,海良暗暗追了丁兰很长时间,可她不同意。有一次,被海良逼急了,丁兰就对海良说:“我喜欢的人是张福祥,我老早就喜欢他了。“
张福祥是他那时候的名字。
为这事儿,有一次他俩喝酒时,海良愤愤不平地把他狠揍了一顿。他当时没有反抗。好歹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不能自己一个人得了便宜,还不让海良发泄一下。他很同情这个哥们儿。
在这一点儿上,他比海良舒服,他和丁兰早早把男女之事办了。完事后,他问丁兰为啥看上自己?丁兰说:“海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想吃,我偏不给,你不想吃,我偏要给!”
他听了心里很不快。这算啥!人家要,你不给,不要,你偏给!
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说。俩人就这样好上了。
因为丁兰,他和海良的关系多少受了些影响。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兄弟,毕竟还得在一块儿捕鱼。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和好如初了。
偶尔还会有些小别扭。海良喝醉时还会愤愤不平。他就是这样的牛脾气,你不能跟他解释,越解释越急。再说,男女之间的事儿能说得清吗?说不清的。
良媛就是这个时候从城里来这里的。
她一来,立马就把村里男人的眼光吸住了。也难怪,城里的女人就是漂亮,看着就是得劲,看着就是叫人心里乱。
良媛不仅脸蛋儿漂亮,眼睛更是流光溢彩,就像黑夜里的一轮弯月一样叫人沉醉,叫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她温柔娇小,仿佛一头可爱的小鹿误入满是野兽的森林。可村庄毕竟不是森林,男人也不是野兽,可不能由着性子乱来。但男人们心里的“兽性”还是抑制不住地在发酵。
他也喜欢上了良媛,但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是真心喜欢她,他时时念着她,他处处护着她。他真的非常担心她受到伤害。良媛多么聪明,她懂他的心。渐渐地,他们在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中产生了极其纯粹的感情。
对于他们的关系,就像海良说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海良还说:“你小子该挨刀子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小心丁兰打了你。“
他没有挨刀子,也没有被丁兰打。丁兰只是结结实实把他臭骂一通,并撂下狠话:“张福祥你走着瞧,得罪了老娘,有你好看的!”
他没当回事儿。后来的确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只是有一次,海良喝醉时又把他摁在地上揍了一顿。他问为啥,海良说不为啥,就是气不过。这事儿有点奇怪。
后来,村里就流传起良媛的风流韵事来。说她和男人们乱搞。这些男人里最多的是海良,却没有他。
他很纳闷。有时候就怀疑是丁兰在搞鬼,但看她风平浪静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
终于,还是出了大事儿。有一天夜里,良媛竟然淹死在了月灣潭里。
他那时痛得发疯,而后又晕晕乎乎了很长时间……
他竟然没有跑过去看一眼良媛……
丁兰黑着脸追在他身后,发狠说他敢去看一眼,她就一头扎进潭里……
他竟然还好意思问海良她是怎么死的?
海良真不像个爷们,完全像个干尽坏事的土匪。他一脸坏笑地说:“她想死,谁能拦得住!”
往事不堪回首。想起良媛他的心就痛得要命。坐在草地上,两行热泪禁不住滴落下来。
后来,海良也死在了月湾潭里。
再后来,眼看在家里待不下去了,他就和丁兰一起跑到山西讨活路。
时光真是匆匆,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
现在回想那些往事,它们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礼,竟然消逝了原来的凌厉和刺痛,变成恍恍然、虚飘飘的了。
时间真是个无限鬼魅的东西,让原本清晰可见的万事都在它的河流中飘荡、褪色、变形、消散……
难道不是吗?
难道是真的吗?
就像他和丁兰,仿佛已经被时光悄然洗白,哪里还有半点当初的样子。可是,一切真的都可以洗白吗?
就像海良的死,时间又带给他新的怀疑,他真的是为了捞金子而淹死的吗?他的水性那么好。不仅仅是他在怀疑。村里人也有种种说法。在他们远走山西后,不是还有人传着说是他为了独吞金鸭子、金鲤鱼、金疙瘩而害死了海良吗?
真是荒唐可笑,造谣者真可恶。
就像良媛,当时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吗?有说是丁兰害了她,也有说是海良奸杀了她,甚至有人说是他……
这些东西若隐若现,穿过四十多年的时光迷雾,经过了时间如此鬼魅的洗礼,究竟还是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呢?
又有许多往事纷至沓来。又想起了逃亡山西的事了。
怎么会是逃亡呢?可不就是逃亡呢。丁兰悄悄地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说是要做收粮食的生意。然后就拉着他跑到了山西,这不就是畏罪逃亡吗?
……后来,他们隐姓埋名,在一个叫陈远的煤老板手下混日子。他渐渐成了老板的得力助手。也是在老板的帮助下,他和丁兰成功地“改头换面”。不仅改了姓名,而且换了身份证。
太太现在不叫丁兰了,叫马楠,而他则叫张凯堂。原来叫什么呢?噢!对了,叫张福祥。他现在几乎快要忘掉这个名字了。
再后来,老婆丁兰,不,是马楠。她组建了一个保安公司,偷偷从老家物色年轻人,明里是给煤矿老板们看家护院,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暗地里却干些不正当的事儿。不过,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虽然各种麻烦和争端不时出现,但是却挡不住钱源源不断地往腰包里钻。
渐渐地,他们成了当地财大气粗的人物。而煤老板陈远却因为本性谨小慎微,越发不思进取。他们之间慢慢就有了思路和方向上的分歧。一个求稳,一个求快,相互阻碍,矛盾日重。
有一天,陈远突然出车祸死掉了。顺理成章,煤矿就转让给了他们。对于陈远出车祸,他当时没有多想。他一心想着快速发展,想着把心中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先是做大做强,接着是兼并,后来又多业并举建立集团公司。
一切都如他所愿,一切都狂飙突进。
这时候,有人居心叵测地在背地里说是他搞死了陈远,他没有管这些议论。身正不怕影子歪,而且他实在是没有闲心搭理这些谣言,他的心全在集团公司上。这样一路下来,事业顺风顺水,如火如荼。集团公司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成为响彻一方的龙头老大。
凡事盛极必衰。他也正应了这句老话。倒不是说集团有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内心渐起波澜。摧枯拉朽般地一路走来,奔波劳累之苦倒也罢了,良心上的折磨渐渐让他寝食难安。
严重时,整夜都睡不着觉。
那些先前被他有意无意忽略的、没空想也不愿想的东西,像尖刺一样扎着他的心脏。
噩梦不断来袭。
那段时间,大概一年、两年……或许更长时间。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着。老婆也觉察到了,但她却无能为力。
她千方百计地规劝他。她小心翼翼地顺着他、迁就他,不能让他一气之下干傻事。
第三天下午,儿子从城里回来了。
他的大奔停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招来一群小孩子围着它转来转去。儿子没有驱散他们,冲他们笑了笑就回去了。太太高高兴兴地在门口迎儿子,他一个人在客厅里静静地品茶。
太太和儿子有说有笑地进了客厅。他没有起身,只抬头看了儿子一眼。儿子隔着茶几笑着说:“老爸,我回来了!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
他抬头盯着儿子看,还是没开口。
太太赶忙说:“哪能呢?你爸他不生你的气了,还天天念着你呢!”
太太说完,他冲儿子点点头,示意儿子坐下来说话。太太紧挨着儿子坐着。
“凯堂,儿子呢,那边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好。他这次回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太太先开口说道。
“是吗?”他问儿子。
“嗯!是的。从哪里说起呢?”儿子若有所思,“先说说我最近研究的事情吧!”
“研究的事情?”他有些疑惑,“你在研究什么啊?”他看着儿子。接着又问道:“那我的想法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时,太太又插话道:“凯堂,那个事儿先不说,不现实。”说完,看着儿子说,“你爸的想法是好,但是不切合实际,有点儿个人幻想的意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接地气,你说是吧?”
“爸!老爸!不是,不是……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也支持,现在先不说,好不好?”儿子显然是在讨好他。“我这次回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这会儿先不说,先听我说说我的最新研究,行吧?”
太太也示意他先听儿子说。他就不再说话了。
“这段时间呢!我认真地研究了乡村河流的变迁,可以说,我对此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儿子谈兴很浓,还不时用热切的眼神看看他,“通过对河流历史和乡村历史的对比性研究,我觉得很有必要挖掘和研究河流的歷史遗迹及其文化内涵,从气候变化、时空演变、资源变化,到远古传说、时代风貌、资本植入,以及整个流域内人们生存状况的更迭和文化心理的变迁、冲突……”儿子侃侃而谈,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他打量着儿子。
儿子继续高谈阔论着。
儿子的研究比他的“想法”复杂得多。他的“想法”其实挺简单的。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此时此刻,那个简单的“想法”好像也已经被儿子的“高谈阔论”给遮蔽了。
“所以,我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说到这里,儿子停顿了一下,并征求意见似的看着太太。
太太用赞许的眼光鼓励儿子说下去。而他呢,似乎是越听越糊涂了。老了哦!真的是老了哦!他在心里兀自感叹。
“老爸,我的想法其实本质上跟你一样!”
“什么?什么想法?”这样问时,他自己心中“那个想法”又从一片迷雾中浮现出来。但此时他更急于想知道儿子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在月湾潭上面建造一个空中大湖。”
“什么?什么?空中大湖!”他惊叹道。惊叹之后,他突然很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于是接着说道,“那我的想法呢?怎么办?”
“你的想法不现实。”太太看着他十分冷静地说。
“是啊!爸,你说要把整个村子改造成滨海小镇,真的不现实。这里没有海,又不是什么小镇,只是个破旧的小山村,怎么可能建成滨海小镇?再说了,改造需要的资金太大,还牵扯到地方政府、国家政策、土地使用、农户搬迁等等,都不好办。”
“别说了!”他打断儿子,“还是以前的陈词滥调。”
太太这时没有再插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盯着他看了一眼。而后,她又扭头用眼神鼓励儿子说下去。
儿子继续说道:“我所说的空中大湖,就是在你当年捕鱼的月湾潭上,建造一座超乎想象的水上景观……”
儿子看来已经谋划成熟了。可为什么要选那个地方呢?
“在月湾潭上面矗立几十根粗大的钢柱子,柱子上用钢化玻璃搭建起一个巨大的透明景观,里面有上百亩那么大,然后抽水、蓄水,水汇集起来就形成一片空中湖泊,远远望去碧波荡漾,是博人眼球的空中奇观。里面还可以建造成水上乐园,足以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照这个样子建起来,景象的确令人惊叹。他心里虽赞叹,嘴里却没有夸奖。
儿子说着,他在心里想象着。有一会儿,他渐渐融入进去,仿佛已经乘着一条梦幻之舟在湖中荡漾……
“儿子还有更精妙的想法呢!”太太接着说起来,“空中是大湖景观,下面的月湾潭也要深挖,把水底的暗洞和太子山的洞穴连起来,人们可以穿上潜水设备进行水下探险,体验水下迷宫,探寻历史传说,探宝金鸭子、金鲤鱼……”
太太的描绘更是令人惊叹。
他的梦幻之舟仍然在湖中飘荡……
水面上的风景无限美好,水下的奇观也令人心醉……
他简直已经忘记了眼前的一切,整个人都忘情地投入其中:迷宫、洞穴、探险、传说、金鸭子……
忽然,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仿佛一个突如其来的浪头,一下子就把梦幻之舟打翻了。他沉入水中,当年被渔网缠住而溺水的感觉又一次重现:恐惧、挣扎、窒息。他的脸憋得通红,腿和胳膊扭曲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漩涡攫住,一股巨大的吸力把他往深邃的洞穴中拽……
怎么了?這是怎么了?他强迫自己从梦幻中醒过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
他已经不能再听他们说话了。于是,他站起来,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走出了屋子。
外面已是傍晚时分。他又来到河边的大坝上。此刻他才发现,雄伟壮观的护河大坝像一条即将腾飞的巨龙,将可爱的山村一分为二。身后的村庄被落日染的一片橘红,安静祥和的气息弥漫在山坡、树梢、屋顶上。而眼前流逝的河水、近岸的草地、坝前的树林,这些构成整个河川景象的景物,由于被山影覆盖,再加上水汽和凉意的浸染,这时变成了一幅滞重、冷凝的画,看了叫人生出凄然之感。
夜里,他不由地把睡眠交给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它们交叉重叠,催生出一个个神秘而又惶恐的梦。他的脑袋好像就是一个巨大的空洞,什么人都往里钻,什么怪异的东西都往里钻,先前的噩梦也往里钻……
海良、良媛、陈远,他们一个个像怪兽一样张牙舞爪地往里钻。他看见了他们,心里又害怕又愧疚。他对他们说:“海良!良媛!陈远!我爱你们,我爱这里的人们,我爱自己的故乡!”
他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只管朝他扑过来。他吓得闭上了眼睛。等他睁开眼时,扑来的却变成了怪亚。它有蛇一样狰狞可怕的头,黑鱼一样浑圆鼓胀的身体,乌贼一样坚硬发达的尾巴。它又开口说话了:“我是你的兄弟海良啊!我要杀了你!”
太太!太太!他在梦里惊叫起来。太太用尖利的指甲狠命地掐他的胳膊,还用长长的牙齿咬他的下巴。太太后来又冲着他大吼大叫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怪亚!怪亚!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他不管不顾地叫着。
“你发什么神经啊!什么怪亚?什么海良?什么良媛?什么陈远?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全是你瞎想的,全都是假的。你就是怪亚,你就是海良,你就是良媛,你就是陈远,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太太冲他吼道。
她接着又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给我记住了,别再说什么梦啊啥的了,有什么用!幻想而已。海滨小镇不要想,空中大湖更是虚幻,是一种病,是一种可以治你的梦的病!都是病,你知道吗?连你也有病,你知道吗?你——有——病——”太太最后一句话的声音拖长了。她的蛮横、霸道、碾压和摧毁一切的统治力又重新出现。
他愕然。
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他禁不住在梦中感叹道:世界真是复杂,人们真是复杂。你看,有时候,你眼前的现实有多真切,可能它就有多虚幻。反过来呢,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