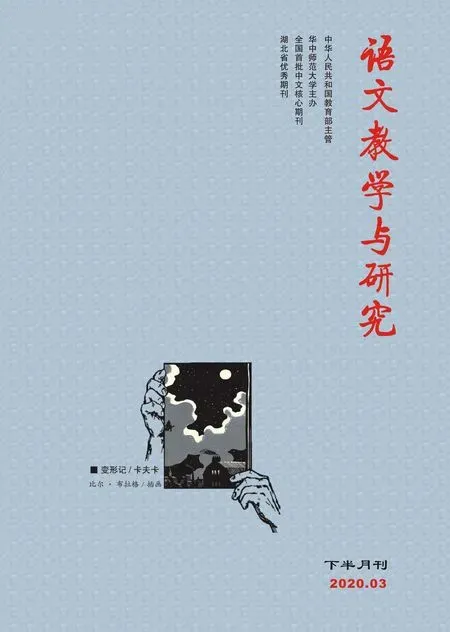从文言文“一体四面”探究志怪小说之“怪”
——以《干将莫邪》教学为例
王荣生教授在《文言文教学教什么》一书中提出:“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化’,一体四面,相辅相成”。
《干将莫邪》选自《搜神记》,被选入沪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第一学期第八单元。小说讲述了干将为楚王铸剑,被楚王所杀,其子赤在侠客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七年级学生在教材中首次接触“志怪小说”,文中大量荒诞的情节、大胆的想象与奇特的夸张是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而作者为何要将其写得如此之“怪”又是学生不理解的问题。本文试从“文言、文章、文学、文化”四方面探究志怪小说“怪”的合理性,从而让学生对“志怪小说”有更好的了解。
一、文学——从离奇情节初探“志怪小说”之“怪”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文,都是历久传诵的经典名篇。它们既是经世致用的实用文章,又是中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文学是其表现形式。
初读《干将莫邪》,我们第一时间便会为文中离奇的情节所吸引。很多文献对其做过分析,如张世才《干将莫邪》以及欧阳炎中《〈干将莫邪〉中“九奇”浅析》中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赤“即自刎,双手捧头及剑奉之”,客曰“不负子也”,“乃仆”;“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水中,踬目大怒”等这些想象和怪诞夸张的情节是志怪小说的典型特征,对于初次接触志怪小说的初中生来说无疑是新奇的,学生不禁为其中的情节所吸引,同时又会产生疑惑:明明这些情节都是现实中不会发生的事件,作者又为何把它写得如此之怪呢?我们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迷信吗?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需继续了解文章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二、文化——魏晋时期崇尚奇异的心理促进“志怪小说”发展
文言文多层面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王教授讲到四个方面:文言、文言和文言文所体现的传统思维方式、文言文记载着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风情等具体文化内容、文言文所传达的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即所言志所载道。这里我们主要从“志怪小说”产生的背景及文化基础方面来阐释。
“志怪”一词最早出于《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所谓“怪”,单从广义上来讲,它泛指一切神奇怪异之事。《说文解字》中,“怪”释为“异也”。通过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在古人眼里,那些反常于社会和自然界的现象被视为“怪”“异”甚至“妖”。正如《左传》中所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些怪事都是不吉祥的征兆。
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以及传统巫术便是志怪小说的源头,“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都通过大量的想象等表现了人类对于征服自然的愿望,这些都是志怪小说的重要源泉。中国传统的巫术大力宣扬鬼神观念,十分重视卜笠、祈祷、祭祀等迷信活动,这些都启发了志怪小说的想象与幻想。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魏晋文人负性带气而又无力回天,所以多借助清谈、闲谈、戏谈之风,寄情怪诞、侈谈鬼怪以求心理平衡。这就为志怪小说提供了产生的现实土壤。
干宝出生在东晋年间,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东晋时代迷信之风盛行,干宝本人也十分迷信,史书上说他“好阴阳术数”,他竭力搜集古今的神怪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把当时社会上千奇百怪的民间传说记录下来,写成了《搜神记》。《干将莫邪》就是其中一篇。
通过这一背景知识的了解,学生会了解到“志怪小说”中看似不合理的情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迷信,它是一种文学样式,它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要素,是现实的土壤、历史的积淀以及作者本人思想认识结合的产物。
三、文言——从文中用语看楚王形象
文章中三个主要人物:赤、侠客还有楚王。文章对楚王并没有过多描述,但是楚王的形象却彰显在精简的笔墨中。
1.三个“怒”,一个“大怒”揭露楚王的暴戾
文章开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从文章看来,短短百来个字中出现了三个“怒”以及一个“大怒”,属于高频词汇。那么作者为何要反复强调这一“怒”字呢?我们逐一来进行分析。第一个“怒”字出现在交代故事背景之后,“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这里文中对楚王为何“怒”并未直接说明,但通过前文的一个“乃”字,并结合着后文“王怒,欲杀之”我们可以推测,王生气的原因是干将铸剑时间久。因时间久而“怒”,且怒到了“欲杀之”的结果。由此可见,君威不可冒犯
第二个“怒”字,是干将对妻子所说的话,“王怒,往必杀我”,一个“必”字,表示“一定”,也就是说干将非常清楚自己此行凶多吉少,这应该是出于干将一贯对楚王的认知。干将携雌剑去见楚王,本来楚王就处于“怒”的状态,此时看到干将只带来一把剑,这进一步触怒了楚王,于是出现了“王大怒”的场面。后果也就由心理层面的“欲杀之”到了行动层面的“即杀之”。最后的一个“怒”字,其实并不影响行文,去掉文章也讲得通,但作者仍然重复一遍,可见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并未花大量篇幅去阐述和解释楚王的举动,但是将“怒”字反复言之,不断强调,楚王的暴戾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2.由一“即”字看楚王的多疑
文章第三小节,“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仅仅因为一个梦,“王即购之千金”,“即”表示“立即、马上”,可见行动之快,这一个字就将楚王的多疑暴露无遗。为了防止梦成真,“先下手为强”。现在再来看楚王因为造剑时间长便杀死干将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的多疑也进一步验证了他的残暴。
四、文章——从“三王墓”看作者的“民本思想”
本文是一个复仇故事。儒家伦理中复仇思想最重要的内涵就在于复仇的平等和正直,即孔子所言“以直报怨”,亦即孟子所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们现在看来,赤和侠客复仇的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似乎是有违伦理道德的,作为施暴者的侠客和赤可能是要受到制裁的。而文章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后,“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在这里,干宝明显表现出来一种快意恩仇的狭义精神。将作为平民的赤、侠客也称为“王”,与楚王合葬,也就是说干宝对复仇不是一般性的叙述,而是在叙述中夹杂着自己的肯定和赞赏。
当然我们认为这里除了有干宝自己的情感认同之外,还包含着底层人民的心愿。追溯到故事发生的大背景上——春秋时期。《孟子·尽心下》提出:”“春秋无义战”,指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儒家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义的战争。楚王铸剑是为了战争,楚王的残暴是导致干将被杀、赤为父报仇、侠客自我牺牲为赤复仇的导火索,这样的君主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自然也就使“以暴制暴”具备了实施的可行性。这正印证了孟子所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五、结语——志怪之“怪”本质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综上所述,我们将文章所有奇特情节梳理一下便能够明白志怪之“怪”本质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楚王的梦境以及表现是为了体现楚王的暴怒与多疑;侠客的一系列表现都是为了体现人物的侠客精神;而赤的表现则是为了表现复仇的坚决以及对楚王的憎恨!
另外,《干将莫邪》一文从文言用词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物形象以及作者的态度,从文章角度可以感受人们除暴去暴的愿望以及作者的民本思想,从文学角度可以感受志怪小说的大胆想象与奇特夸张,从文化角度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巫术以及儒家思想复仇精神与侠义精神。当然以上四个方面有时很难清除地划分,但是它给我们教学文言文提供了一个抓手,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一篇短短的文言文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元素。
文言文的教学任重而道远,讲解文言、解析文学、分析文章、传播文化这将是我们一线教师永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