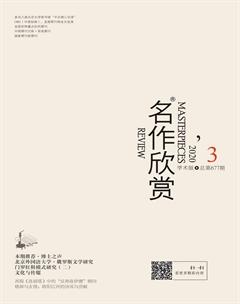抒情诗《麻雀山》的艺术特色
摘 要:帕斯捷尔纳克著名诗集《我的姐妹——生活》中的抒情诗《麻雀山》曾不止一次地引起帕诗研究者们的注意。该诗结构精巧,意蕴丰富,所涉主题在诗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文学修辞学角度对该诗进行分析,从章法结构、话语主体和文本间的联系三个方面分析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以期准确把握诗人意图,揭示“作者形象”。
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 《麻雀山》 文学修辞 艺术特色
《麻雀山》(Воробьевы горы)是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Л.,1890—1960)诗集《我的姐妹——生活》(Сестра моя — жизнь)中的著名诗篇,在诗集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诗集中很多重要的母题均首次在该诗中出现,并在其后的诗歌中得以发展与深化。作为一首蕴含丰富哲理思想的抒情诗歌,《麻雀山》得到了包括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加斯帕罗夫(М. Гаспаров)在内的诸多俄罗斯和欧洲学者的关注。他们对该诗的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与解读,如指出了诗歌描绘的圣灵圣神降临节的背景,揭示了诗歌表现的冷漠的大自然与有灵性的大自然、青春与年老的对立等主题。本文拟从章法结构、话语主体和文本间的联系三个方面来分析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以进一步揭示该诗的深邃内涵。
一、章法结构
所谓章法,泛泛而言,是指一部作品各部分的建构、分布及其内在联系。章法的概念普遍应用于各种艺术中,且在所有艺术门类中作用都非常显著。具体到文学作品中,章法是“一个复杂文学语言统一体中言语序列的动态展开系统”,换言之,文学作品的章法就是遣词造句谋篇的方法,即“主题沿着题脉展开的方法”。我国学者白春仁先生对章法的研究有如此评价:“章法与语言直接连在一起,是结构分析首先关注的课题。”
论及该诗的主题,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侧重,加斯帕罗夫将《麻雀山》一诗的主题总结为“趁年轻享受青春时光”,并称“这一主题是诗集《我的姐妹——生活》诗学中最抽象而又传统的主题之一”。除了青春与年老的对立,该诗的圣灵圣神降临节、大自然的神性等主题也不止一次地被帕诗研究者们提及。细读全诗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主题是在非常精巧的遣词造句谋篇中渐次得以展现的。
整首诗写的是诗人圣灵圣神降临节期间漫步麻雀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据叶莲娜·维诺格拉德(Е.Виноград)a回忆,麻雀山是她与诗人1917年春经常散步的地方。全诗共五个诗节,每个诗节四行,每行的词数为六个左右。第一詩节写了节日游园会的热闹场景,如亲吻、手风琴、跳舞等。同时,诗人发出感叹:“要知道,盛夏不总是连续不断地涌流如泉。要知道,手风琴不总能一夜一夜低声嗡鸣。”b“青春不是永恒的”这一主旨通过这句话得以出现。帕斯捷尔纳克将惯用的熟语“生命如泉涌般蓬勃”改为“夏天如泉涌般蓬勃”,于是此处“夏天”既如“泉涌”,又等同于“生命”,是“生命之泉源”。这使我们想起贝科夫(Д. Быков)在其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中用夏天的隐喻来记述诗人的一生:“他对世人而言终究是一种夏天的现象……构成帕斯捷尔纳克的元素,是洋溢着夏之欢乐的丰沛降雨、炽热的太阳、繁花盛开和果实成熟;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夏天——与恋人的相遇、最出色的构思、精神上的转变。”第二诗节开头一句紧接上文的慨叹:“我曾听说年老体衰的事。可怕之极的预言!”(166)正如夏天会不可避免地过渡为秋天,青春也必然会被年老代替。“不会有一丝泡沫能扬起双手触摸到星群。”(166)“звезда”在词典中不仅指“星星”,还可以指“命运”,因此此句除了直译外,还隐喻着命运的不可知。从第一诗节感叹青春短暂到第二诗节直接写害怕年老、命运的神秘,感情上又进了一步,青春与年老对立的主题更加凸显。第二诗节后两句则转入另一个母题——大自然的神性。“大家都在说——你却不相信。草地脸上神色大变。/池塘水泊也都冷酷无情,松树林并无神灵。”(166)与之呼应的是最后一个诗节,我们将在下文中做具体说明。第三诗节是全诗的顶峰与中心,写在麻雀山顶的所见:“看见不,在上空,思绪错乱成白色的沫溅开。那是啄木鸟,炎热与针叶树枝,乌云与松球。”(166)同时这句也是从第二诗节中“面无脸色和没有心肝”的世界通往第五诗节中“恳请相信”的世界的桥梁。在这一诗节中出现了贯穿全诗的“世界的正午”的形象。“正午”承上启下,既指时间概念上的一天之中的正午,也呼应第一诗节中出现的夏天,即青春时光,还指最后一诗节中的“圣灵圣神降临节”。联系该节第一句“你让心灵飞腾澎湃!今天就让它飞出泡沫来”(166),整个诗节流露了诗人趁年轻享受青春时光的思想。第四诗节转入对麻雀山地理位置及环境的描写:“市区的电车已走到了尽头,路轨在这里终止。”(166)此句意指麻雀山处于市郊,暗示这里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清净之地。“接下来提供服务的是松林。电车不再有可能。接下来——就要度过星期日。分开茂密的树枝,林间小径在青青草上滑行。向四面八方奔腾。”(166)这一句写麻雀山的自然环境,表明此处从人的世界转入大自然的世界。“воскресенье”一词可以有两种解释,“星期天”或者“生命的复活再生”。而“служить”在俄语中除了“任职、值守”的普通含义外,还有宗教色彩,指教职人员做礼拜、做弥撒。“松林值守”让我们想起“牧师值守”,联系“воскресенье”以及下一诗节的“圣灵圣神降临节”,帕斯捷尔纳克或许正是借词语的双重含义来表达麻雀山是人们放松心情、灵魂再生的地方。最后一诗节第一句中的三个词“正午”“圣灵圣神降临节”“游园会”分别与上文对应:正如上文所说,“正午”“圣灵圣神降临节”与第三诗节的“正午”呼应,而“游园会”则呼应第一诗节中所描绘的节日游园会的热闹场景。同时这三个词又均指圣灵圣神降临节,可见这一夏季节日的时间与氛围贯穿全诗。接下来写诗人在麻雀山顶的思考与感受:“世界原本这样天造地成。/密林也这样设想,这种授意林中空地也信守,/那不是,从云端筛子也是这样洒落向我们。”(167)这一部分意在表明大自然自古以来就是有灵性的,与第二诗节中无神性的、冷漠的大自然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词语“相信”的对应得以体现:“大家都在说,你不相信//同时它又恳请相信。”
此外,在该诗的俄语原文中,第二诗节包含三个表示否定的词нет(没有),而第五诗节则有三个表示肯定的词так(这样)与之对应,如果将其直译,我们就会看到如下呼应:
草地没有脸色,/池塘没有心灵,松树林没有神灵。//……密林也这样设想,林中空地也这样被授意,/从云端筛子也是这样撒落向我们。
综上所述,该诗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母题——青春与年老的对立,大自然的神性及圣灵圣神降临节,均是在诗人精妙的章法中一步步凸显。而章法的艺术,恰“在于组织巧妙,出奇制胜,从而增强表现力”。
二、话语主体
话语主体的确立在篇章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的叙述须有特定的视点和对艺术世界特定的态度立场。这种观点和态度,只能来自话语主体,随主体的更换而变化。”对艺术世界的特定态度是“作者形象”(образ автор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者形象”是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В. Виноградов)提出的著名理论,是维氏创建的文学修辞学的重要核心范畴。“作者形象”包括作家对艺术现实的态度和作家对全民语言的态度,是统帅一部作品整体的核心,堪称作品思想和艺术真谛的集中体现。因此,考察作品中的叙述主体,确定文学篇章中是谁在讲述,他对叙述对象的态度,他与他人语言的相互联系及他对他人(别的主体)语言的态度,对把握作者对所写世界的评价态度,进而分析“作者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麻雀山》一诗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叙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全诗中仅一处是以人称代词表现的人称形式,如第二诗节第一句前半部分说“我曾听说年老体衰的事”;其他各处均是以动词词尾来体现句子主体,如第一诗节中出现的人称形式是第一人称复数,即“我们”。第二,第二诗节和第三诗节中均出现了面向“你”的叙述,然而这里却存在着关于“你”的所指的不确定性。是谁“不相信”,谁的“眼睛”,谁“看到没”?很多研究者按其语法形式,将“你”解读为该诗中并未出现却贯穿整个诗集的女主人公,这是一种可能;同时,将其理解为从他者角度看的抒情之“我”也未尝不可——进一步讲,第二诗节与第三诗节中面向第二人称“你”的叙述是指全诗开头和结尾处的“我们”的单数形式。
诗中两种互相对立的“话语”与这个“你”不确定的所指有关。试比较第二诗节“我曾听说年老体衰的事。可怕之极的预言!/不会有一丝泡沫能扬起双手触摸到星群。/大家都在说——你却不相信。草地脸上神色大变。/池塘水泊也都冷酷无情,松树林并无神灵”(166),与第五诗节“丛林用筛子播撒三一节,正午时分,信步畅游/同时它又恳请相信:世界原本这样天造地成。/密林也这样设想,这种授意林中空地也信守,/那不是,从云端筛子也是这样洒落向我们”(167)。第二诗节中有个“话语”在讲无神性的、冷漠的大自然,第五诗节则与之呼应,另一种“话语”在说:大自然自古以来就是有灵性的。第一种“话语”来自“他们”,也就是动词говорят(说)的主体,同时也是“你”不相信的那个人;第二种“话语”则来自小树林,即大自然本身。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同时存在于一首诗中,我们有必要分析抒情之“我”对它们的态度,进而确定抒情之“我”的观点,但由于“你”的所指的不确定性,为我们做上述分析增加了困难:如果“你”指诗中并未正面出现的女主人公,那么第二诗节中的“草地脸上神色大变。池塘水泊也都冷酷无情,松树林并无神灵”可以理解为诗人借“他们”之口表达的自己的态度。俄罗斯文艺学家阿尔方瑟夫(В. Альфонсов)就持此种观点。他认为第二诗节和第五诗节中的两种“话语”均是诗人以他者面目道出自己的观点,该诗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态度的转变:从抱怨大自然之冷漠到相信大自然充满灵性。加斯帕罗夫也指出该诗“从头到尾”,“大自然世界神性的母题得以强化”。如果“你”指抒情之“我”,那么显然诗人不相信第二诗节中的“话语”,而赞同第五诗节中的“话语”。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布罗伊特曼(С. Бройтман)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第二诗节中“话语”的真正主体是不确定的,并不像阿尔方瑟夫认为的那样一定属于抒情之“我”,在诗中它“作为他者的声音被引入,然而這个声音与抒情之‘我的声音难以分离”。还应指出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所写的第二种“话语”同样不是诗人的直抒胸臆,而是属于大自然本身,而且它并不“要求”大家“同意”,而是“请求”大家“相信”。这暗示着帕斯捷尔纳克是站在大自然内部的观点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
综合帕斯捷尔纳克的整个创作生涯,我们可以发现帕斯捷尔纳克对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灵感,仿佛理解万物的语言。如在其著名的诗篇《镜子》(Зеркало)中,有这么几句诗,读了令人拍案叫绝:
花园里有三棵松树摇摇晃晃,/松脂把空气刺痒得怪难受;/篱笆因烦心事把眼镜丢到草地,/阴影却在那里悄悄读书。(118)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ев)所言:“世界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是由奇迹构成的——把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东西的奇迹,一切事物和所有现象都获得了人类理智而由麻木僵死之物复活的奇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这一赋予事物灵性的力量使一切行动、运动、抽象概念都能思想和感觉。”可见,《麻雀山》一诗中第五诗节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态度——大自然自古以来就是有灵性的——对于诗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对诗中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不同解释的可能,但第五诗节所写的大自然的声音似乎更符合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自然观,我国学者顾蕴璞先生也有非常精彩的表述:“在一般诗人的笔下,自然总留有明显受制于诗人的人化痕迹,可是在他的诗中,物象除折射诗人的思想感情外,它们本身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禀性和脾气,和诗人同样充当抒情情节中的行为主体,是诗人之外的另一位抒情主人公。”
三、文本间的联系
“文本间的联系”(межтекстовые связи)是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尔什科夫(А. Горшков)提出的术语,他对这一术语定义如下:“文本间的联系——是某个具体的文本中包含的、借助于特定的言语手段表示出来的对某个(或某些)其他具体文本的参阅。”这个定义让我们联想到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众所周知,“文本间性”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巴赫金(М.Бахтин)的“对话主义”,1967年克里斯蒂娃将其发展为术语“文本间性”,主要指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分的不同作者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然而戈尔什科夫认为,虽然这两个术语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一回事,但在今天的后结构主义者们的著作中,“文本间性”这一术语已远远超出了语文学的范畴。正如俄罗斯后现代理论家伊林(И. Ильин)所言:“这一术语今天更多地用于确定当代人的‘后现代感受。”戈尔什科夫由此认为用“文本间性”这一术语来作为文本间联系的语文学研究方法是不合适的,而“文本间的联系”则有具体的言语表达载体,完全可以作为语文学研究的特定对象,以“解决语文学亘古以来的基本任务——对文本进行正确的阅读与阐释”。遵循戈尔什科夫的理念,本文中我们将使用“文本间的联系”这一术语。
“文本间的联系”的方法包括引用、题词、引用的标题、引用典故、引起联想等。《麻雀山》一诗与其他文本间的联系主要运用了引起联想这一手段。所谓引起联想,是指“使用某些词语、词组和句子以引起对某个历史事实、神话或文学作品的回忆”。具体到这首诗来讲,其“文本间的联系”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分别是丘特切夫的《大自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和奥地利作家里尔克(М. Рильке)的《沃尔普斯维德画派》(德语Worpswede,俄语Ворпсведе),下面我们分别对其加以说明。
如《麻雀山》第二诗节的后两行:
大家都在说——你却不相信。草地脸上神色大变。/池塘水泊也都冷酷无情,松树林并无神灵。(166)
其中“神色大变”“冷酷无情”让人想起丘特切夫的诗歌《大自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中的第一诗节:
大自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图形,不是一张死板的脸,/它有自己的灵魂,它有自己的意志,/它有自己的爱情,它有自己的语言。
帕斯捷尔纳克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对丘特切夫诗歌中的“死板的脸”“有灵魂”进行了改写。并且,与丘特切夫不同的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麻雀山》中,由于“你”的所指的不确定,抒情之“我”对该诗节中“大自然是冷漠而没有灵性”的观点的态度并不确定;而在丘特切夫的这首诗中,大自然是“图形”,是“死板的脸”——很明显是他人的话语,而大自然有“灵魂”“意志”“爱情”“语言”则是诗人的观点。显然,丘特切夫对他人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大自然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充满生机和灵气的有机体。
除了丘特切夫的诗歌,第二诗节后两行还使我们想起里尔克的散文《沃尔普斯维德画派》中的相关表述。虽然里尔克的散文是用德语写作的,但这并不影响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熟悉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都知道,里尔克是对帕斯捷尔纳克影响非常大的德语作家。从大学起,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翻译里尔克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曾对里尔克本人说,他的整个精神构成都归功于里尔克。在一封致法国学者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曾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编他(指里尔克)的曲调而已,对于他那独特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一直都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在《沃尔普斯维德画派》中,里尔克这样写道:“我们习惯于考虑人物形象,而风景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我们习惯于从运动中推断一致行为,风景却没有意志,尽管它也运动……但是,风景既无手,又无面孔……”
在里尔克的这段话中,“风景”可以理解为“自然”。风景是没有人物形象的,风景没有意志,“风景既无手,又无面孔”……可见,里尔克在这段话中将自然看作与人不同、没有灵性的存在。显然,里尔克的思想体现在了《麻雀山》的第二诗节,并通过“草地脸上神色大变,池塘水泊也都冷酷无情”使人想起里尔克的“它没有面孔”“风景没有意志”。
四、结语
以上我们分别从章法结构、话语主体和文本间的联系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麻雀山》的艺术特色。此外,词语运用和格律也赋予该诗以丰厚的意蕴。如诗中崇高语体与口语体词汇的混合使用是帕斯捷尔纳克显著的诗学特征,该诗所运用的六音步扬抑格与同时代诗人同格律诗的对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主题。在诗集《我的姐妹——生活》中,“自然”“青春”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形象和主题存在的,《麻雀山》便是反映诗人对大自然、对生命态度的一首诗,诗中融汇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自然与生活的思考。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对这首诗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诗人的意图,把握作者形象。
a 叶莲娜·维诺格拉德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恋人,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26年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写道:“《我的姐妹——生活》是献给一个女人的。”
b 〔俄〕鲍·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卷)》,顾蕴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本文中所有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译文均出自此书,以下只在文中括号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参考文献:
[1] Альфонсов В.Н. Поэзи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M]. Л.,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2] Бройтман С.Н. Поэтика книги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Сестра моя — жизнь?[M]. M.,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7.
[3]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речи. Поэтика[M]. 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СССР, 1963.
[4] Гаспаров М.Л.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IV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тиха. Анализы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M]. M.,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2.
[5] Горшков А.И. Рус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M]. M.,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рель, 2006.
[6] Ильин И.П. Пост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Де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M]. М., Интрада, 1996.
[7] Лихачёв Д.С.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5-ти томах. Т. I[M]. M.,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9.
[8] 白春仁.文學修辞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
[9] 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上)[M].王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0] 顾蕴璞.饱含哲理的艺术逻辑[J].国外文学,2009(1).
[11] 莱·马·里尔克.艺术家画像[M].张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2]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卷)[M].顾蕴璞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3]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 莱·马·里尔克.抒情诗的呼吸[M].刘文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4] 费·伊·丘特切夫.丘特切夫抒情诗选[M].陈先元,朱宪生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
作 者: 于淼,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