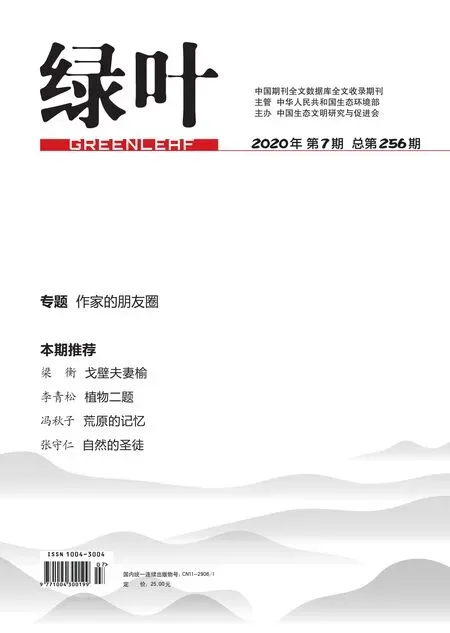自然的圣徒
——《深山已晚》序
张守仁
一
最近傅菲从江西上饶寄来一部书稿《深山已晚》,嘱我看看。这是一部自然文学的新作。
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三位专门从事生态、自然写作且卓有成就的好友——他们是苇岸、胡冬林、徐刚。我发现包括傅菲在内的这四位作家,虽然都以大自然作为写作对象,但由于性格、经历、学养不同,因而他们作品的侧重面,呈现明显的差异。
苇岸敬畏大自然,对于工业文明带来的污染、喧嚣、放纵,怀有天生的厌恶。他只写《大地上的事情》,写大地上的平凡事物,写蚂蚁、喜鹊、野兔、麦子、农田、桦林以及农历二十四节气。苇岸是个素食主义者,生性善良,佛陀般悲悯万物,不敢看屠杀牲畜、鸡鸭。有次胡蜂在他窗外筑巢,他便自觉关闭窗户,以免打扰小生灵们的正常活动,并衷心感谢上苍惠赐他亲密的邻居做伴。面对社会弊端,他因无力抵拒,苦思自伤,导致早夭,于1999年5月仅39岁就辞别人世。次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散文家齐聚北京鼓楼附近对他表达哀思。
吉林的胡冬林,蛰居长白山十多年,以写那里的动植物为业。名篇有《原始森林手记》《狐狸的微笑》《野猪王》《拍溅》《青羊消息》等。经过多年观察、研究,他已认识长白山180多种动物,200多种植物。我研究、编辑过《世界美文观止》,认为描写动物神态之精彩、生动,他可与布封、梭罗、普里什文媲美。冬林邀我去长白山住了七天,指导我辨认鸟鸣、兽迹、树种,给我讲中华秋沙鸭有趣的故事。走累了,我们坐在树墩上,他对我说:“山中的树林、花草、鸟兽,甚至一只纺织娘,都是我亲密的朋友。在山中花可欣赏,鸟鸣悦耳,绿色养眼,真是人间天堂。人们以为我像个野人似的待在山里苦熬。我内心窃喜:试问作家中谁能像我这样舒心、自在呢?”他一旦发现山火、偷猎,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有一次他看到有5头熊被人剖胆、割掌后尸横荒野,怒不可遏,便拍下照片,协同有关部门破案。当地猎人想谋害他,公安部门向他发护身工具,并派人保护他。为此他被评选为“感动吉林”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徐刚是我崇明岛老乡,离我家仅几里之遥。我们先后上同一所崇西中学、参军、到北京上人大、北大,毕业后又都留京编副刊,同时兼搞创作,因此过从甚密。1987年初夏,他正在编《中国作家》杂志,得知黑龙江大兴安岭5月至6月那场大火,过火面积达133万公顷,5万多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心痛欲裂。就在同时,徐刚的好友从武夷山下来,告诉他风景名胜区的树木,被大规模地盗伐下来出售,当柴火烧。看到、听到这些毁林事件,他坐不住了,毅然离开编辑部,南下采访,写出了《伐木者,醒来》这篇振聋发聩的报告文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了《守望家园》《中国风沙线》《长江传》《地球传》《崇明岛传》《大森林》。他眼看着江河污染、土地沙化、林地锐减的败相,心怀忧戚,走遍大江南北,从沙漠跋涉到西陲,从北方草原南下金沙江,从中年写到老年,从黑发写到白发,孜孜不倦地从事山河大地的写作,故被人誉称为我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先驱者。
傅菲跟以上三位有所不同。他从城市潜入闽北荣华山下,回归自然,安顿自己的心。他追求天人合一,体验人和自然的融合,感受人与外界的同频共振,考察生命的轮回,研究自然的法则。他尤其关注山中的气象,观察星星、月亮、日落、暴雨、彩虹、云、雪……仰望星空,使自己的心态平和。面对浩瀚宇宙,他感到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通过山居观察,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回归自然”是人类所能享受的十大奢侈生活方式之一。
傅菲深入山林草木之中,感受大自然的微妙,美不可言。只要你用眼注视,用耳谛听,就会发现天是云的居所,风是溪的翅膀,花是春的闺女,鸟鸣是林间的天籁。仔细观察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只鸟、每一条鱼,都有高度适应环境的形体、线条、色泽。即使是同一棵树、同一朵花、同一只鸟、同一条鱼,在迥异的气象、季节、光照下,都会呈现不同的姿态。他感悟到:山中的草木、昆虫、鸟兽,或者昙花一现,或长命百岁,各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它们自自然然,荣荣枯枯,既不欢欣,也不悲苦,生也至美,死也至美。这就进入了齐动静、等生死的生命哲学境界。
二
自然文学的称谓,有个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常说的是环境文学。当时在冰心、王蒙带领下,我们创办的《绿叶》杂志就是一份环境文学刊物。笔者和编辑家章仲锷、刘茵合编的近两百万字“碧蓝绿”丛书,就是作为环保读物,交给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笔者与王蒙、雷达、李敬泽等评委,曾在时任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先生领导下,举办过第一届环境文学评奖活动。当时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是环境保护总局,后组建为环境保护部,2018年3月又组建为生态环境部。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文学逐渐改称生态文学。但近年来的出版物、报刊、评论家们,更多地称生态文学为自然文学,也许这一命名更精确、科学、全面。
近20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多部自然文学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美国的《瓦尔登湖》《醒来的森林》《沙乡年鉴》等。
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毕业于哈佛大学。他认定自然是美好的,应以自然为师。人类应到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反对奢侈,主张过最俭朴的生活,认为财富越多,美德就越少。1845年起,他拿了斧头、锄头等几件工具,孤身跑进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中,砍木造屋,开荒种地,播种豆子、玉米、蔬菜籽,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同时观察自然万物、看书写作。根据两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思,写了一部自然随笔集《瓦尔登湖》,成为划时代的巨著。
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年生于纽约卡茨基尔山区,后长期住在哈德孙河畔的乡间小屋,过着农夫兼作家的双重生活,用锄头和笔在土地和白纸上辛勤耕耘。他最高兴的事,是让自己和读者长期待在原野上、树林里以及潺潺的溪流边。他的名作《醒来的森林》《清新的原野》受到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诗人沃特·惠特曼在内的广大读者热爱。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大自然,生命垂危才回到家乡。他去世后,美国成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每年4月他生日那天,向自然文学创作中有突出贡献者,颁发约翰·巴勒斯奖章。
奥尔多·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林业硕士学位,1935年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座废弃的农场,带领家人从事生态恢复和观察四季物候现象。根据多年详细记录,著有《沙乡年鉴》,在人类史上首次提出“大地伦理”观点。他在书中指出,传统伦理只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而大地伦理则是处理人与大地以及人与大地上生物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时,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里的“完整性”,指的是多样性。利奥波德在书中强调,如果我们能够把土地看成一个郡落,而了解到我们人只不过是这个郡落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就会对同一个地球上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百倍地爱护、珍惜。由于“大地伦理”观点的提出,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当之无愧地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经”。
三
荣华山位于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东南,属于武夷山余脉北端,南浦溪绕山而过。那里山峰绵绵,草木葱茏,方竹争翠,泉水甘洌,是个观察大自然的好去处。
傅菲客居于此,植树种茶,烧饭读书。他与种地的、捕鱼的、养蜂的为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了那里每一个野谷,翻越了每一个山梁,踩遍了南浦溪每一个荒滩。他观察风霜雨雪,细看鸟巢蚁穴,注视树叶间泄露的光线,听听布谷蝉鸣,闻闻溪水潺潺,喜见所栽秧苗渐渐长大。身在山中,自得其乐。一个人当他完全拥有自己的时候,也是他最充盈、最惬意的时光。
傅菲是个诗人。他诗意地栖居、观察、写作。他用诗的语言、拟人的手法,描绘他见到的春夜山中闪电雷鸣的情景:“戴着面具的人,在一朵荷花上舞蹈,裸美的肌肤涂抹了一层露珠。面具银白,如古老的铜镜。长发遮蔽的大地,在面具的照射之下,露出静谧的睡姿,山峦起伏,草泽随时会喷出泉水,鱼戏荷田于东。荷花在颤抖,舞者摇曳多姿。她的裙裾被风鼓起,随腰身旋转……她发出了一种飞瞬即逝的银光,穿透了云层、密林、虫洞和我们的恐惧。光消失之后,她开始唱歌,歌声由远及近,从天边雪球一样滚来。雪球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滚越大,从山巅碾压而来,落在我屋顶,碎雪在窗外纷扬……”
春夜的雷电,如银鞭般催发万物生长,让枯草发芽,花开枝头,泥土湿润。
有一次傅菲进入闽北浙西的深山密林,意外见到了一种名叫白鹇的珍禽。白鹇颊红羽白腹黑,翅短尾长,性机警,常栖止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绅士般悠闲踱步,民间视之为吉祥物。我的好友王星泉工艺美术大师,有幅大型漆画《珙桐白鹇》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这足证白鹇是多么珍贵、艳丽、高雅。
由此可见,你只有进入高海拔的密林里,才会欣赏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景美色;只有在原始森林里,你才能看到叠翠千丈、遮阴避日、藤蔓缠绕、落叶盈尺的林貌;只有在尚未被游人涉足的地方,你才会观赏到高树古木、珍禽异兽、奇葩硕果、灵芝妙药;只有在环境未被破坏的地域,你才会观察到松杉竞生、乔灌咸长、杂草茂盛、蕨类葳蕤的林容。在高山密林里,万物生存竞自由:巨蟒似的绞杀植物紧紧盘绕于树干,野雉在林梢上飞翔,猴子在枝丫间攀援,长虫在密集的空间里蜿蜒穿行,林间空地流泻着美妙的鸟鸣。只有在无人到过的荒蛮之地,你才能领略到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景观。
四
笔者阅读范围有限。请允许我把本文中谈及的苇岸、冬林、徐刚、傅菲四位文友,视作四根粗大的圆柱子,加上其他作家,合力顶撑起当代自然文学的大厦,巍然矗立在散文原野之上,组成一道被读者注目的亮丽风景。
读《深山已晚》,颇有收获,欣喜之余,写下几句点赞的话,权作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