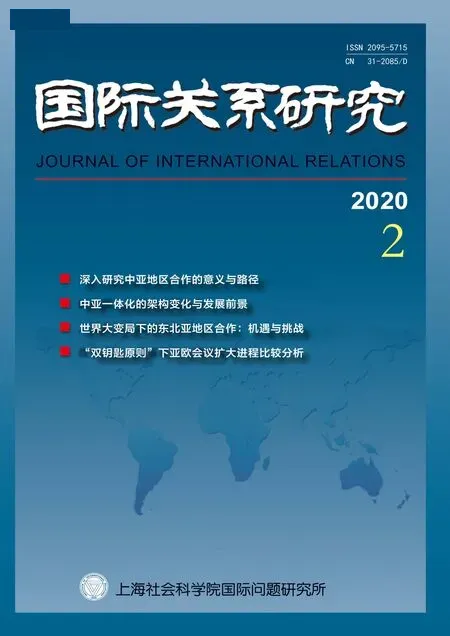深入研究中亚地区合作的意义与路径
曾向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现象具有诸多表征,比如国家对地区与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且资助力度得到显著加强,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加,学术界新创办的涉“一带一路”或沿线国家与地区学术刊物大量涌现,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智库建设、学术研究、资金投入、学科建设等方面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也在日益增强,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规模在逐步扩大,而与“一带一路”和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更是层出不穷。诸如此类的迹象,或许昭示着中国的地区与国别研究迈入一个新时代,有望就此生产出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诸多新知识。
不过,这种期望终究只是一种可能,区域与国别研究者能否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中超越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范式或实现重大理论创新,终究是实践和历史问题,而不只是口号和宣示问题。就当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来看,尽管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突破性的成果和具有开创性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新理论似乎仍未出现。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动的此轮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似乎并未彻底改变区域或国别研究者与研究成果分配不均衡的状态。这种状况容易理解,尽管国家、学术界、研究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大,但每个领域的研究都有其“路径依赖”,针对特定国家、区域的基础性研究文献,以及主要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主流范式等都有其继承性,再加上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成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故要想迅速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状况的改进显得过于乐观。
以中亚问题研究为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的确带来了有关中亚研究成果的增多,但该区域的研究仍没有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毫无疑问,自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中亚问题的研究并不乏相关研究成果。截至今日,中亚问题的研究者通过成果的相互交流、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已逐渐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该共同体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亚地区及五个国家的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中亚问题的研究,依旧与中亚在中国外交布局和“一带一路”中的地位有些不太对称。
首先,在中国外交布局中,中亚既属于周边地区,也属于发展中国家,且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四个中亚国家属于上海合作组织),还与大国外交息息相关(中俄美均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其互动被称之为“新大博弈”)。换言之,中亚地区虽然一般认为只有数量较少的五个国家,但其与中国“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多边是舞台,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布局息息相关。其次,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中亚地区是习近平主席最初提出该倡议之地——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而且中亚地区是贯穿“一带一路”倡议的枢纽地区,可谓“一带一路”倡议的“通中之重”。据此,原本可以期待中亚问题研究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取得突破性成果,然而,遗憾的是,中亚研究中此前既有的一些不足,并未在“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带来的中亚研究热潮中得到改善。
如以中亚研究的学理化研究成果为例,中亚国别或区域研究与主流理论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在国内学术界,中亚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然而,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中亚研究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或比较政治学存在严重脱节。中亚问题研究者较少参考国际关系学者或比较政治学者的成果,而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研究学者也很少借鉴中亚问题等区域研究的进展。当然,中亚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并非独有,除了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与亚太研究的状况稍好外,其他区域问题研究也程度不一地面临这种问题。相对而言,中亚研究的这种状况更为突出。
这种状况即使是在国内学者非常关注的大国中亚政策研究中也有体现。该议题吸引了众多中亚研究者,也产生了数量颇丰的成果。但是,多数研究者都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观点——强调大国出于追求权力或利益的动机开展外交活动,突出大国互动的零和性,低估或无视中亚国家在大国行动下的能动性,等——解读中美俄等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及其互动,很少使用联盟(管理)理论、霸权稳定论、安全复合体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认知或错误认知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等主流理论对大国的中亚政策予以分析,遑论利用中亚区域中的经验材料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如史蒂夫·沃尔特在研究中东地区国家间政治的过程中提炼出“威胁平衡理论”、东南亚研究在研究东盟的过程中构建“东盟模式”一样。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互动已是国内中亚研究中相对成熟的研究议题,该领域的研究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关于其他主题的研究状况。就此而言,学术界在提高中亚研究问题的学理化程度上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要想提高学术界关于中亚研究的学理化水平,一种可行的路径是对中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开展创新性研究。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亚地区经历了从原来的高度一体化到去一体化再到重新一体化的曲折历程。苏联解体之前,中亚五国原本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各国独立之后,为了推进国家构建和捍卫国家主权,再加上各国国家利益产生分化甚至冲突,中亚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地切断原本存在的密切联系,以加强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相互疏远以致各国经历了一个去一体化的历程。随着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乌兹别克斯坦执政,中亚五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领导下尝试扭转这一局面,并尝试通过国家元首峰会等形式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赋予中亚地区再一体化趋势以新的动力。中亚五国推进国家间合作的复杂历程,值得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入分析。
其次,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区。尽管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但新成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的一个重要诉求,在于借助这一平台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联系,以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就此而言,扩员后的上海合作组织或许并未改变中亚地区仍是这一组织的核心区这一客观事实或主观认知。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青岛峰会提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互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不仅如此,由于“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推进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行,具有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作用,对上海合作组织在推进地区合作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提供新的视角或启示。
最后,大国将介入和推动以己为主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作为扩大自身影响的重要方式。中亚地区传统上被视为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和枢纽地区。无论这种认知具有多少客观成分,其对大国决策者和战略家的影响不容低估。至少就当前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的中俄美,以及欧盟、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行为体而言,它们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离不开它们对该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认知。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除了双边支持,各主要行为体均构建并提出用以整合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俄罗斯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美国主导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构建的中亚五国与美国的C5+1机制;欧盟所借重的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土耳其和伊朗注重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日本则提出了“日本与中亚五国外长对话”机制,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机制对中亚五国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复杂难明。正因如此,才需要研究者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予以必要的澄清。
以上三个事实,意味着研究者在中亚地区合作的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学理研究空间。对其中任何一个主题开展创新性研究,都有望通过对具体区域或案例的研究做出新的学理解释,抑或提炼出新的地区合作模式。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亚区域合作的研究中,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学者做出了榜样。如有学者通过对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种地区合作组织(包括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比较,发现中亚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而不愿意让渡国家主权,以致它们只愿意采取最低程度的一体化措施推进国家间合作,目的在于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地区合作收益,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避免外部干预。基于中亚地区合作的这些特点,西方学界提炼出“虚拟地区主义”(virtual regionalism)、“保护性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昙花一现的地区主义”(ephemeral regionalism)等概念,用以描述和解释中亚地区合作进程的特点或类型。尽管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普遍性及其学术价值需要检视,但西方学者在区域研究中进行学术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值得学界同仁学习。如果国内学术界也能形成学术创新的意识和勇气,即使不能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但至少能为这种突破奠定必要的资料和案例基础。
如果中国学者能在中亚地区合作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将极大地提高中亚问题研究的水平。鉴于当前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的意义重大与该领域研究的学理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学术界有必要通过选择合适的研究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以尽可能缩减需要与供给之间的鸿沟。事实上,考虑到中亚区域合作研究有助于促进两者之间的联结和弥合,加上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密切关注和现有丰富的描述性研究成果),那么,从中亚区域合作研究入手进行创新性研究,不失为一条缩减鸿沟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开展该主题的研究,既可以从“制度复杂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规范竞争”(norm competition)、“制度过剩”(institutional overreach)或“机制冗余”(regional redundancy)等角度考察不同地区合作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可以仿照“东盟模式”(ASEAN Way)提出用以解释特定地区合作机制发展历程的创新性学术概念,如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概括为“上合方式”(SCO Way),或者从新的角度总结这些机制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如可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为“基于尊重的地区合作模式”);甚至还可以将特定国家主导或参与的地区合作机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总结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或“地区安全复合体”)、“责任共同体”等,在厘清这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讨论它们之间的竞争或演化关系等。尽管这里的讨论只是启发性而非论断性的,但它启示我们,针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特定议题的研究,我们有必要超越描述的层面,尽力通过具体案例的深入考察或通过开展比较案例分析,以提炼出新的学术概念或构建新的理论模式,从而为主流学界贡献更多的普遍性知识。
本组专题文章旨在为提升中亚区域合作研究的学理化水平进行初步尝试。本组专题包括三篇文章,涉及与中亚地区合作密切相关的三个层面。顾炜的《中亚一体化的架构变化与发展前景》涉及中亚国家之间开展地区合作的历程及其动力,并尝试总结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一般模式;周明与翟化胜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达成的历程、原因及影响研究》一文则在回顾《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签署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了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以及公约的达成对促进里海沿岸国家开展地区合作的积极效果;韦进深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设计与“一带一盟”对接的模式与路径》,在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框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合作的两种模式,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
尽管上述论文在概念创新和模式构建方面迈出的步伐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至少尝试从新的角度对中亚地区合作的历程或模式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毫无疑问,寥寥三篇文章不可能迅速改变国内有关中亚地区合作有待取得突破的局面,但它们的刊发或许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助于激励更多志同道合者对中亚地区或其他国别或区域开展独创性的研究,进而产出更多更富学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热潮,不只是带来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短暂繁荣和昙花一现,而是为其提供持续的动力、产生一系列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研究成果。未来到底会呈现出前一种场景,还是带来后一种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