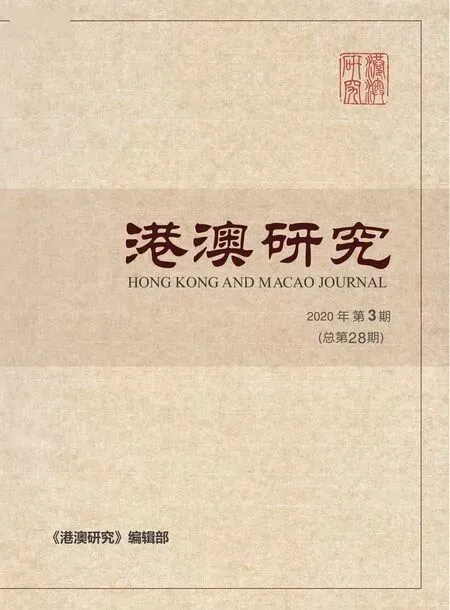“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问题
王万里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制度安排,是港澳同胞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制度渠道。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能否兼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涉及“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制度构建问题。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先生在参选行政长官前,曾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参选行政长官,2019年4月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请求。经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9年4月23日决定接受该请求,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也因此自动终止。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参选人须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主要原因是: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当然委员①,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法》规定,选委会委员不得被提名为行政长官候选人②,作为当然委员的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只有在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情况下才能丧失选委会委员资格③,没有可以保留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但辞去选委会委员的法律安排④。澳门这些法律规定主要对参选人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情况构成影响,对于参选及当选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行政长官在任职期间是否可以参选并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特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如果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参选行政长官,因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部分代表会成为选委会委员,故有两种情况:一是该委员如同时是选委会委员,则须丧失选委会委员身份后才有资格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二是如该委员不是选委会委员,则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法律上不构成他(她)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障碍。
香港特区在这方面的法律安排有所不同。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也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没有限制选委会委员被提名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参选人保留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在香港本地法律上是允许的;参选人当选并被任命为行政长官后,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也就是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在特区本地法律上没有障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亦如是。但在政治实践中,2012年6月,已当选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先生在正式就职前,辞去了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职务。他提出的理由是“为专注做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工作”⑤,这显示并非法律障碍所致。
在我国内地,已经形成省级行政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均出任所在省级行政区当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惯例。如果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不是全国人大代表,须安排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例如,2020年4月李干杰从生态环境部调任地方,在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山东省代省长,并被补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的代表资格有效。⑥如果有的省级行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职务跨省(区市)变动履新,其所在代表团会变更为新任职所在省(区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例如,2020年以来,内蒙古、上海、河南、湖北、宁夏等地的党政一把手,因职务跨省(区市)变动,已经变更了其所在的代表团。⑦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行政长官选举和任职资格的法律规定尽管不尽相同,但两地行政长官选举和任职实践中都曾面临参选人或当选人如何处理兼任国家参政议政职务问题。当事人或出于法律原因,或出于政治考量,均选择辞去国家参政议政职务。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突出的宪制实践现象,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宪制习惯构建问题,即行政长官作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双首长”及国家治理特别行政区的枢纽岗位,应否及能否通过兼任国家参政议政职务,从而在其按基本法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有关体制机制之外,再形成一个能将特别行政区更紧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途径呢?本文围绕全国人大代表这一重要的国家参政职务,重点从行政长官作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这一宪制角色及实然和应然两个维度来予以分析说明。
二、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宪制角色
我国宪法确认和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香港、澳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曾在历史上被外国强占,但主权从来都没有从中国手中丢失,港澳同胞的中国公民身份也不因受外国殖民统治而丧失。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港澳同胞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并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予以保障。这是主权在我、港澳不可分离原则在我国宪制实践中的确认。
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同胞侨界代表徐四民和工联会理事长张振南就作为特邀代表与会。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地区人大代表的人数只有2名,均是以邀请的方式产生。从1975年起,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加入港澳地区代表,隶属于广东省代表团,由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再经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⑧第四届全国人大香港地区代表人数为14名,第五届和第六届人数增加到16名,第七届、第八届分别是18名和28名。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澳门地区代表名额均为4名,1988年第七届至1998年第九届(回归前)均为5名。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不再隶属于广东省代表团,而是分别单独成团。北京人民大会堂也先后开辟了香港厅和澳门厅,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议事场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各届香港、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产生办法,明确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为36名,澳门地区为12名。2004年国家修改宪法,其中之一是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中增加“特别行政区”,⑨与内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并列。这一修改符合回归后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实际情况,也使香港、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及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中拥有了明确的宪制地位。
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宪制角色在回归前和回归后有所不同。回归前关于港澳地区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的安排,更多是对我国拥有港澳主权并对港澳同胞拥有属人管辖权的一种体现和宣示。尽管当时港澳同胞还处于外国殖民统治下,但其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不因殖民统治而丧失或变化,国家主权的属人管辖方面仍然且必须及于他们,故他们应当拥有和行使中国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这一点在台湾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安排上同样得到类似体现。
在回归后,港澳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宪法和港澳基本法共同构成其新的宪制基础,港澳同胞既对当地事务在中央授权下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权,又能作为中国公民名正言顺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是港澳融入我国宪制秩序的必然要求。因此,回归后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宪制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在国家治理层面。香港基本法第21条和澳门基本法第20条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分别在港澳选出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因此,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有关制度安排是我国国家体制的人民主权原则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重要体现,也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成为国家整体制度秩序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同时,这既具有在国家治理智慧中吸纳港澳同胞民意和视角的功用,也是民主集中制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的具体运用。
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依据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有关规定,履行代表职务,享有代表权利,承担代表义务。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包括:提出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权利;提出人事罢免案的权利;提出质询案和进行询问的权利;在全国人大召开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追究;在大会开会或闭会期间,非经许可,不受逮捕和刑事审判;对围绕人大审议议题及有关内容,有视察的权利;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和执行其他属于代表的职务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应根据实际需要为代表提供保障。相应地,也应履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义务,主要包括: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行使职权,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等。
两个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作为集体,也在参与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功能。根据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各代表团分别推选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全国人大代表团的职责包括:各代表团在每次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之前,讨论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会议的准备事项;在会议期间,对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并可由代表团团长或由代表团推选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上或大会全体会议上,代表代表团对审议的议案发表意见。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权利主要有:一个代表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一个代表团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质询案;三个以上的代表团可以提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成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并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另外,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代表团团长会议和主席团还可以决定在公开举行的会议之外,举行秘密会议。
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职责除了关于代表团的前述一般规定外,还在处理全国人大对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程序中,扮演重要而独特的宪制角色。特别行政区提出的基本法修改议案,须经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⑩可见,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巩固维护和发展完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是在特别行政区自身宪制层面。在组建特别行政区的创制过程中,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是各自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当然委员。11香港特区推选委员会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00人组成,其中香港地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8人为当然委员。香港推委会既产生首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又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12澳门特区推选委员会由具广泛代表性的200人组成,澳门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2人为当然委员。澳门推委会主要负责产生首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3香港、澳门首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过程中,推委会委员主要在提名确定候选人和选举阶段发挥作用。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至少50张推委会委员提名票;澳门首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至少20张推委会委员提名票。两者均须在选举阶段获过半数推委会委员支持票才能当选。14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也由推委会选举产生,每十名推委会委员可联合提名一位候选人,每名推选委员会委员在候选人名单的范围内,有权投六十人的票,得票数名列前六十名者当选。15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在香港推委会中所占比例为7%,澳门地区人大代表在澳门推委会中所占比例为6%,都能够在特别行政区的创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确定首任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和确定香港临时立法会候选人提名中,以人大代表所占比例而言,如能作出协调性行动,可发挥更为关键性作用。
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从第二任起分别按照两部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由选举委员会提名确定候选人并选举产生人选,报中央政府任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当届全国人大代表分别为各自选委会的当然委员。16就香港而言,选举委员会除了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外,还要选举产生第一届至第三届立法会中的部分议席。香港特区迄今已产生五届选举委员会,第一届至第三届选举委员会人数为800人,36名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占比为4.5%,占当时行政长官选举提名门槛所需100票的36%;2011年第四届和2016年第五届选举委员会人数增加到1200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占比3%,且占当时行政长官选举提名门槛所需150票的24%。澳门特区目前已产生四届选举委员会,其中2004年和2009年选举委员会人数均为300人,12名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当然委员占比为4%,且占当时行政长官选举所需提名门槛50票的24%;2014年和2019年选举委员会人数增加到400人,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占比3%,且占选举提名门槛66票的18%。
此外,按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澳门特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的规定,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推选委员会或选举委员会成员中的中国公民,自然成为本地区下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在选举本地区下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作中发挥作用。
除了上述这些法定角色之外,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在特别行政区本地事务治理中虽无法律的规范性要求,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的成员,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地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是爱国爱港爱澳的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在特别行政区政治生活中能够发挥积极而独特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确保特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实施基本法的过程中,他们应当而且可以扮演政治舆论监督者的角色。他们亦可运用其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渠道,乃至在全国人大开会的场合,向中央客观反映港澳情况,就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和基本法贯彻实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在政治法律实践中,中央政府在处理涉及特别行政区的重大宪制问题时,特区全国人大代表是征询意见的重要对象。例如,在历次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均举行座谈会,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其中听取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意见乃规定动作,必不可少。
三、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宪制角色
论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否兼任全国人大代表为主的国家参政议政职务,在考察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宪制角色的基础上,还需结合行政长官本身的宪制角色加以考虑。作为“一国两制”下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的首长,行政长官在宪制角色上具有多重性。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有这样几个宪制角色:
一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负责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是特别行政区首长,代表整个特别行政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凌驾于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之上,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的首脑。三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行政长官不仅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权机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定基本法予以创设并赋予职权。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中枢,是中央对港澳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机构。行政长官作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这一宪制角色往往被忽略或误读,加之这一角色与国家参政议政职务都具有国家性或中央职务性,故本部分着重分析行政长官的这一宪制角色。
香港回归前,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实行总督制,总督具有英王(英国政府)在香港全权代表的角色。17澳门在澳葡统治下,总督由葡萄牙君主或总统派遣,是葡萄牙中央政府的代表。英国和葡萄牙分别在港澳推行总督集权制,总督是实行殖民统治的代表。港澳回归祖国后,宪制秩序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特别行政区成为我国单一制结构形式下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成为中国国家主权的主体——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基于港澳新的法律地位,其首长行政长官既有地方自治所赋予的特别行政区代表的角色,更有因中央任命且须向中央负责的角色。
行政长官作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角色主要由两个方面的重要宪制要求所决定,即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以及维护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首先看全面管治权的有效落实方面。我国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必然的法律结果是中央政府拥有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为了更好实施全面管治权,国家根据宪法制定基本法,在港澳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授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构建了将部分管治权授权特区高度自治、中央行使最高监督权的在港澳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主要模式。同时中央在外交、防务、国家安全等与主权密切相关领域以及非特区自治范围保留并直接行使管治权,形成了“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崭新而独特的宪制关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部分授予,这部分管治权中央授予特区自治机关直接行使,因此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的高度自治权,其实质是中央拥有但中央间接通过特区自治机关来行使的管治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不仅具有自治机关的属性,也具有一定的国家机关属性,承担代国家治理特别行政区的受托者角色,因而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公职人员,既具有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身份,也暗含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18行政长官更是如此。在中央授权治理这一新的宪制秩序下,行政长官地位特殊,处于联结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主要枢纽位置,是确保中央全面管治权在特别行政区落到实处的关键岗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央人民政府管治特别行政区的代表,是中央权力与特别行政区权力的交汇点。19这一角色在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责。在我国“一国两制”宪制结构下,中央政府依法授权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部分职权,而行政长官是承接中央维护国家安全授权的最重要主体,可以说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就此向中央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20换言之,行政长官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权力来自中央,只向中央负责,行政长官显然是中央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领域对特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
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更加凸显了行政长官的这一宪制角色。“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并未改变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单一制下,地方没有固有的权力,所有权力来自中央政府授权。行使中央授权的地方行政首长,其所行使的权力在本质上不具有地方性,且其职权获得的关键因素是中央政府的任命行为,因而必然具有国家职务性。否则,行政长官完全成为一个地方的代表,那么他/她须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宪制要求的正当性基础就会严重受损,并损害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进而冲击和影响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是现实国家宪制秩序所不能允许的。与此相应,行政长官提名并经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区主要官员,均具有国家公职人员这一维度的角色。
基于以上宪制逻辑和理念,基本法设计了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双首长”(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特别行政区首长)和“双负责”(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向特别行政区负责)的岗位多重属性;在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上,实行当地选举或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双要素模式;在行政长官的职权配置上,赋予行政长官相对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更大的权重,使其处于特别行政区政权运作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同时明确规定行政长官须执行中央政府就基本法规定的有关事务发出的指令。21
基本法将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设计为行政主导,而行政主导的实质就是行政长官主导。这一点早在2007年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的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就鲜明指出,“基本法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的设置和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故也有论者将香港、澳门特区的行政主导体制概括为“行政长官制”。22对于行政主导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过往论者多着眼于特别行政区自身运作所涉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关系建构的层面,聚焦在治理效能所需的角度来理解,认为是对回归前行之有效的体制的承接,23即对总督制有利于实现管治效能的凌驾地位和权力集中原则在新的宪制秩序下的承继性沿用。其实,更重要的正当性在于这是行政长官宪制角色特别是其作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主要途径和抓手之必然要求。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有赖于行政长官在特区予以落实。如前所论,中央主要通过授权自治的形式间接行使特区管治权,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需要通过行政长官这个枢纽来落实好中央的法定权力,因此行政长官须具有主导特区内部管治的权能和权威。
中央意志通过行政长官来落实的法定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依据香港基本法第48条第8款和澳门基本法第50条第12款的规定,依法向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发出指令,行政长官须遵照执行。这里规定的中央政府指令行政长官执行的工作应当主要是行政长官权限范围内的特区事务,而非中央直接行使的外交、防务等非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因为非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可以直接办理,即使要求行政长官办理,那也是配合性的,而且不在行政长官权限范围内,其性质更多的是中央对行政长官新的委托授权,而非指令。也就是说,对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指令行政长官运用其自身权限按照中央的意图执行。这表明,特区被中央授权自治之事务,中央既拥有监督权,又可通过依法指令行政长官间接来行使。二是通过国家立法对行政长官有关重大工作作出法定要求。例如,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应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就维护国家安全特定事项及时提交报告;出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此外,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日常工作沟通等途径对行政长官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由上可知,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宪制角色具有多重性,既代表特区,也有代表中央行使特区管治权的一面。特区利益和中央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现实宪制运作中,万一特区的诉求与中央的意志出现分歧或冲突,中央的意志应当依法得到尊重和执行,同时中央也应广泛听取特区方面的意见。行政长官的功用和角色理所当然须体现这一原则,即既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指示,又全面准确地向中央反映特区社会各界对有关问题的意见。
四、构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安排
本部分首先回答应然与否(Why)的问题,然后探析如何构建(How)的问题。关于应然与否,主要以前述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行政长官的宪制角色为逻辑内核,从三个维度予以分析阐述。
第一,从规范要求的视角看,现行有效法律是否对这个问题存在清晰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国家宪法和港澳基本法等国家层面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内容均对此没有直接的明文规定,既没有要求应当兼任的规范,也没有要求不得兼任的规范。由此从表面上,法律对这个问题显示“中立”或“无涉”面相。但是,从前面我们对行政长官的法定宪制角色等分析显然可见,有关法律的内在精神将是更加倾向于支持行政长官兼任国家参政职务的,或者说,行政长官兼任国家参政职务更符合及更能体现“一国两制”有关法律规范的内在精神,也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实施这些法律规范。
第二,从功能价值层面看,这样的兼任安排有哪些宪制上或政治上的功用和好处。在回归前,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与港澳当时的殖民管治系统必然是分离的两张皮关系。回归后,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港澳宪制秩序发生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两个统合问题。一是国家治理体系要将港澳的当地治理系统纳入。这通过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将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和司法等管治架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港澳治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港澳同胞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制度建设和运作中,要更加制度化地参与国家事务,通过港澳同胞在国家治理中有效参政议政,从而在港澳地区更加体现国家治理事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强化港澳与国家政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此,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与特区治理体系之间应当探索并逐步形成某种适当的制度性对接联系,打通二者关系,而不是继续维持回归前的那种两张皮关系。行政长官的多重宪制角色及这些角色所附着的多重功用,特别是其作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的角色及其功用,决定了如由行政长官兼任国家参政议政职务,是实现上述两个统合价值及联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特区治理体系的最佳功能性人选。也就是说,由特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等国家层面职务,是将特区治理体系更紧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及完善“一国两制”实践体制机制的有效之举,也是更好地彰显港澳同胞参与国家治理、融通港澳民意与国家意志的有效之举。而且,这样的制度安排还能够更加巩固和提升行政长官在特区本地政权架构中的地位及权威,拓展其政治支持力量,有助于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更好落实。
第三,从实践经验方面看,有哪些已有经验做法可提供能类比参照的案例及正当性(legitimacy)基础。事实上,如前所述,我国内地已经形成省级行政区的党政首长兼任该省(区、市)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的宪制实践惯例,这种惯例可以对称性地参照并适用于特别行政区,以体现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国家宪法适用空间范围内的地区均衡性和一致性。事实上,从港澳回归以来,国家已经形成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邀请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闭幕等重要全体会议的制度性安排,其意义在于表明在全国性政治盛事中,国家组成部分的地方代表“一个都不能少”。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中央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均为小组成员,进入中央层面决策机构。这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亮点,是完善港澳治理体系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先例,对于我们考虑特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等其他类别的全国性职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综上,有必要探索构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安排,作为完善基本法实施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宪制惯例。
在明确了应当探索形成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惯例之后,接下来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一些重要的操作性问题。这主要涉及“保留”或“补选”两种情况。对于行政长官参选人已经是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当保留其代表身份,不必因参选或就任行政长官而辞去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如果参选人同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应保留该职务并继续履行有关职责。对于新就任的行政长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应当参考内地的经验做法,安排补选其为全国人大代表。行政长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可以争取被推选为所在代表团的团长(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为例,担任地方代表团团长的多数为省级党委书记,而省级政府的一把手多数为副团长,但北京、重庆、上海等代表团的团长并不是市委书记)。
要将上述“保留”或“补选”的设想落实,最重要的是扫清法律障碍,夯实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一是修改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法》,参考香港的同类法律规范,允许作为选委会当然成员的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或者允许其辞去选委会成员,扫除其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障碍。如果同香港一样,在法律上不禁止作为选委会当然成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有人可能会质疑存在“自己选自己”的问题。理论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未被法定剥夺或丧失的情况下,在同一选举中是可以同时拥有并行使的。澳门现行法律规定选委会成员不得成为候选人,其法律意义等于是享有被选举权就得丧失选举权,构成选举权的一种丧失情况。二是全国人大对关于香港、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作出修改,明确规定对于不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行政长官应当适时安排补选其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基础、正当性论证和具体制度安排需另作深入研究和设计。
另外,与特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问题相联系的是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问题。就此而言,如果行政长官就任时不是全国政协委员,则只存在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问题;如果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则不必辞职,同时需按前述分析考虑安排补选兼任全国人大代表。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即一个人可否同时既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答案是肯定的。国家宪法、有关法律以及全国政协章程对此均未禁止。而且在实践中,已有一些个人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案例。24
五、余论
本文认为,应当在完善基本法实施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推进构建特区行政长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最终将此形成“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的一个权威稳固的重要宪制惯例。
宪制惯例,也多被称作宪法习惯或宪法惯例,最初用作对不成文国家宪法渊源的描述,后来在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实施和政治实践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些宪法文本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得到认同和遵从的涉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等宪制性问题的实践做法,成为宪制习惯和传统,也被法学家称作宪法惯例。故“宪法惯例产生于政治实践之中,是政治实践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涉及宪法层次的问题的做法或习惯”。25能够成为宪制惯例的实践和做法有一个关键要素,即不得违反成文宪法的明确规范。“当有一些惯例是与成文宪法相抵触的时候,当人们遵从的是惯例而不是成文宪法的时候,宪法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26因此,能够形成宪法惯例的制度实践和做法在本质上是符合宪法规范或与宪法规范不冲突的。詹宁斯认为,宪法惯例的意义在于充实和丰富空洞的法律框架,使宪法得以发挥功能,使宪法与思想观念的发展保持联系,促使僵化的法律制度符合日益变化的社会需要和日益变化的政治思想。27
我国是成文宪法国家,在宪法实施中,也形成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惯例,涉及宪法修改、政党活动方式、立法及选举、国家领导机关人事安排等多个领域,28对于不断完善我国宪法制度、促进宪法“活化”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宪法实践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一国两制”领域,应根据需要,在宪法和基本法规范指引下,在政治实践中有意识有设计地适时形成一些有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宪制惯例。将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构建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安排可为其一。不妨以此作为试验和示范。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二条;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第十条第一款。
②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③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第十条第三款。
④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⑤中国政协新闻网:《新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辞去全国政协常委职务》,http://cppcc.people.com.cn/GB/45579/1826497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2月23日。
⑥ ⑦《职务变更多名地方党政一把手变更所在代表团》,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521/c209043-3171726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21日。
⑧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粤港澳关系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第二十五条。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1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
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
17 李昌道:《香港政治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8 香港特区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已明确表示,公务员是特区政府的公务人员,在“一国两制“下,同样是“国家公务人员的一员“,涉及两重身份,在执行职务时要考虑此两重身份。参见明报新闻网2020年6月7日报道。
19 李晓兵:《从港督到特首:兼论香港宪制秩序与行政长官的宪制角色》,《原道》第27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https://sns.91ddcc.com/t/109292,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21日。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等。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八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条第十二款。
22 肖蔚云、傅思明:《港澳行政主导政制模式的确立与实践》,北京:《法学杂志》,2000年第3期。
23 朱国斌:《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24 比如,2018年12月由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邹晓东获增补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此前,邹晓东已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如,时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在2018年1月30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在此之前,谢伏瞻的名字已出现在1月24日公布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并被分配在“中共界别”。更早前,在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至少已有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等5位省级党委主要领导同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201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们都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参见蒋子文:《两会常识:全国人大代表能否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3967,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22日。
25 26 侯健:《宪法变迁模式与宪政秩序的塑造》,西安:《法律科学》,2004年第4期。
27 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8 章志远:《宪法惯例的理论及其实践》,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姜明安:《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哈尔滨:《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