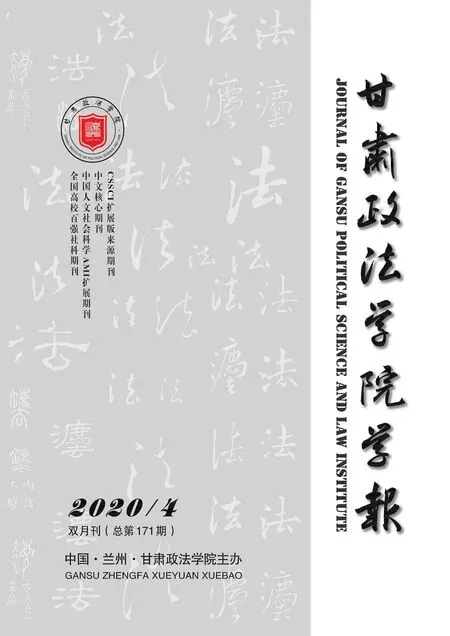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
——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熊晓彪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10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在第五编第三章中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这就意味着,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是否构罪进行审理并就定罪量刑等事项作出判决。缺席审判不同于正常的刑事审判,是一种特殊的审判模式: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有些情况下甚至只存在控、审两方构造。那么,如何在这种不完全诉讼构造的审判中既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又有效地做出准确的事实认定以实现公平正义、打击犯罪、诉讼效率这三种价值之间的平衡,(1)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实际上是刑事诉讼追求多元价值平衡的结果。参见邓思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将是值得深思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最终评价尺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应用无疑将是解答上述问题的核心与关键。一方面,证明标准决定了控方对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程度越高,控方的证明难度就越大,被告人就越难以被定罪,其合法权益也就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证明标准的高低还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刑事缺席审判判决的可接受性程度。证明标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分配错误有罪判决和错误无罪判决的机制在发生作用,其程度的高低体现了能够得到接受的真实无罪判决与错误有罪判决之比率的社会契约。(2)[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95页。同时,证明标准还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3)Richard S.Bell.Decision Theory and Due Process: A Critique of the Supreme Court’s Lawmaking for Burdens of Proof.J.Crim.L.& Criminology,vol.78,3,1987,p.557.证明标准越高,被告人被错误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小;高尺度的证明标准将错误判决的风险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被告身上转移至负有证明责任的控方,以实现降低错误定罪风险的政策要求。此外,证明标准还影响着缺席审判的效率。证明标准越高,控、辩双方需要举证消除法官内心关于案件事实的模糊性之处也就越多。然而,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设置仅仅是问题的开始,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深刻且复杂的问题:其一,证明标准能否在不完全的诉讼构造甚至是仅由控、审两方组成的线型结构中适用?一般认为,诉讼意义上的证明只存在于控、辩、审三方所组成的诉讼构造之中。(4)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陈卫东、简乐伟:《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问题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杨波:《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那么,对于在不完全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中是否也具备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尚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其二,倘若存在证明标准适用的空间,那么适用的又是何种尺度的证明标准?其尺度在不同情形下的刑事缺席审判中是否存在差异?其三,如何在不同情形的刑事缺席审判中实现证明标准达成与否的既可行又准确的判断?
要解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刑事缺席审判进行具体界定,明确刑事缺席审判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特征;其次,需要从诉讼构造的视角对刑事缺席审判作出类型划分,以厘清我国规范层面刑事缺席审判各种情形之间的关系并为探讨证明标准的适用和具体尺度设置奠定基础;再次,对证明标准与诉讼构造的潜在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剖析影响证明标准尺度设置与达成的实质因素;最后,基于错误分配理论分析不同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证明标准的适用空间、最佳尺度设置以及具体达成方式。
二、刑事缺席审判的界定及类型划分
(一)界定刑事缺席审判
对于刑事缺席审判的定义,因为有许多不同版本。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缺席审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缺席审判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日,控辩双方诉讼主体有一方未到庭或到庭但不为陈述、辩论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判决的诉讼制度;狭义的缺席审判仅指控辩双方有一方于开庭之日不到庭出席审判。(5)万毅:《形式缺席判决制度引论》,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有学者梳理世界各国法律规定后,也得出刑事缺席审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结论,认为狭义的刑事缺席审判仅指被告人不出席法庭的审判,而广义的刑事缺席审判还包括控诉方不出席法庭的审判。(6)邓思清:《形式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显然,上述两种关于刑事缺席审判的广义与狭义区分的标准不同,前者的范围更加宽泛,将控辩双方主体有一方到庭但不进行陈述、辩论的情形也纳入缺席审判的范畴。由于控辩双方到庭却不发表意见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多见,并且被告人到庭出席审判但始终保持沉默并没有影响控辩平等的实现,因此其不属于通过缺席审判制度规制的范围。(7)马贵翔、谢琼:《形式缺席审判制度的本质透视与程序设计》,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这种将控辩主体一方虽到庭出席审判但却保持沉默的情形纳入缺席审判的观点,后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学界主要在后者(即控辩双方主体有一方不到庭出席审判)的意义上定义刑事缺席审判,只是有的学者主张广义说,(8)刘柏纯:《构建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载《政法学刊》2003年第6期;欧卫安:《略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类型》,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而有的学者赞成狭义说。(9)刘根菊、李秀娟:《构建缺席审判外逃贪官制度探析》,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8期(下);张吉喜:《论刑事缺席审判制的适用范围——比较法的视角》,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田圣斌、麻爱民:《我国公诉案件缺席审判制度探析》,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而且,持狭义说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缺席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被告人而不包括辩护律师。(10)夏锦文、邱飞:《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切入点》,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邓思清:《形式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然而,即使在赞同刑事缺席审判的缺席主体是被告人的群体中,也未对刑事缺席审判的定义达成共识。例如,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在开庭日被告人未到庭出席审判,法院根据控方的陈述、辩论所进行的审理并作出判决即可称为刑事缺席审判。而有学者则提出,刑事缺席审判不仅是指被告人未到庭出席审判,而且还要关注被告人未出席的原因。具体而言,只有在被告人住所不明或身处国外不能到庭参加审判时,法院根据控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才能被称为刑事缺席审判。(11)王新清、卢文海:《论刑事缺席审判》,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3期。言外之意,其认为刑事缺席审判是建立在无法告知刑事被告人出席审判事宜或者难以强制要求其到庭参加审判的基础之上的,倘若有条件参与审判的被告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遭到控诉,需要到庭参加审判,那么对其进行缺席审判显然就失去了正当性。(12)甚至有的国家将刑事被告人缺席审判的自愿性作为是否适用缺席审判的主要考量因素。例如,当刑事被告人自愿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都可以对其适用缺席审判;而当刑事被告人非自愿缺席审判或者自愿与否不明时,上述四国对适用缺席审判都持审慎态度,德国、法国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缺席审判,英国、美国则对适用缺席审判持否定态度。参见张吉喜:《论刑事缺席审判制的适用范围——比较法的视角》,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知情权是弥补被追诉人未能亲历审判的方式之一,也是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的第一道阀门。(13)杨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法考察——以适用范围与权利保障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据此,审前的告知程序是对刑事被告人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在对刑事被告人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且难以强制其到庭参加审判的情况下,才能够对其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在此方面,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增设控方的证明义务和法院的查明程序。由此观之,刑事缺席审判的开启与审理过程都不同于正常审判,是一种特殊的审判模式。(14)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事项,指出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应适用不同于普通程序的特殊程序进行审判,包括开庭审理之前的特殊程序和庭审过程中应当采用的特殊程序,以及审理之后的特殊救济程序。参见王敏远:《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同时,还有学者基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了世界各国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不同案件类型,由此归纳出三种模式:仅适用于轻罪案件的美国模式、轻重罪皆适用的法国模式以及完全禁止适用的西班牙模式。(15)同前注〔13〕。这意味着,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与案件的不同类型(犯罪的严重程度、危害性以及量刑幅度)存在内在的关联——追究某种犯罪类型的价值是否足以导致对刑事被告人庭审参与权的剥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刑事缺席审判的界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其一,缺席的主体。刑事缺席审判中缺席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被告人。控诉方、辩护律师的缺席并不会对公正审判权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也不会导致对辩护权与参与权的实质性剥夺,由此导致的不完全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也能够通过法院要求控方出席和被告人更换辩护律师等方式进行有效恢复。其二,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前提。审前已经履行了对刑事被告人的充分告知并难以强制其到庭参加审判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前提条件。为此,控方负有证明已经履行了充分告知且难以强制刑事被追诉人到庭参加审判的义务,法院需要对此进行查明且在决定进行缺席审判之前履行相应的告知程序。其三,刑事缺席审判的案件类型。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无疑是一种价值抉择结果,只有当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超过刑事被告人的庭审参与权等价值之时,才能够对其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涉及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包括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诉讼效率、刑责追究的必要性以及实体正义的实现等价值。这些价值的具体判断基本都离不开刑事案件的类型,因此可以说,刑事缺席审判只能适用于那些在适用价值上超过了对刑事被告人庭审参与权保障的特殊刑事案件类型。其四,刑事缺席审判的诉讼构造。我们都知道,刑事审判是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结构,控、辩双方基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等事项进行陈述、辩论,法官居中作出公正的裁决以确定被告人的刑责。然而在刑事缺席审判中,由于被告人的缺席,导致辩护一方主体不再完整,有时甚至整体缺失。在此情形下,缺席审判极有可能沦为裁判者对控方关于刑事被告人刑责主张的审查与确认程序,这显然不符合审判对诉讼构造的基本要求。为此,刑事缺席审判在刑事被告人已经缺席的情况下应确保有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其进行辩护,以满足审判的基本三角构造。当然,由于刑事被告人根本不到庭甚至不到案,辩护律师难以通过刑事被告人视角获知具体的案情,以及难以掌握相关有利证据来对控方的指控进行有效的削弱,因此这种辩护无疑是“打折”的。但是,辩护律师的存在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以及公正审判的实现而言,仍然必不可少。
(二)刑事缺席审判的类型划分
对刑事缺席审判的界定不清导致我国学界在刑事缺席审判类型划分上存在诸多不一致的表述。例如,有学者以被追诉人是否曾经参与庭审为划分标准,将刑事缺席审判具体分为“完全缺席审判”和“部分缺席审判”,前者指的是被追诉人自始至终都未出席审判的情形,后者则是指被告人在审判开始时已经到案并出席过庭审,后因特殊事由而缺席审判的情形。(16)杨宇冠、高童非:《中国特色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比较法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23期。类似地,有学者根据被告人在审判前到案与否将刑事缺席审判区分为“被告人到案不到庭的缺席审判”与“被告人未到案也未到庭的缺席审判”。(17)胡志风:《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上述两种区分的唯一差别在于:第一种划分不仅关注被追诉人到案与否,而且还关注其是否出席过审判;第二种区分逻辑只关注被追诉人是否到案,而对于其在缺席审判之前是否出席过审判则在所不问。显然,与第二种区分的简单归纳相比,第一种划分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令人遗憾的是,其提出者并未进一步道出做此划分的深层次理由,而似乎仅仅是基于比较考察得出的直观结论。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一般意义上的缺席审判与特殊意义上的缺席审判,前者是指针对刑事被告人缺席时的定罪量刑程序,而后者则指称刑事被告人不出庭时对其财物进行处分的一种“对物审判”程序。(18)张书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形式缺席审判比较研究》,载《学术探索》2013年第11期;钱文杰:《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缺席审判——基于刑事诉讼特别没收程序的观察与思考》,载《河北法学》2018年第4期。上述学者之所以做此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认为该程序契合于刑事缺席审判的基本特征,只是审理的对象以及最终的刑罚方式有所不同,并且这种区别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种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没有进一步揭示二者内在的不同之处。所谓“对物审判”,又称“对物诉讼”,是一种区别于“对人诉讼”的审判程序,其被告是物而不是人,所要解决的是因该物而引发的诉争问题。因此“对物诉讼”并不存在被告人的缺席与否问题,也不以物的所有人是否出庭为前提。即使是我国学者针对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追缴程序所创设的“刑事对物之诉”制度,也认为其具有适用于刑事被告人在场的空间。(19)陈瑞华:《刑事对物之诉的初步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此外,我国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实际上要以被告人构成犯罪为前提,(20)对此存在一定争议。两高发布的《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17条规定,“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即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且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犯罪所得,就可以做出没收违法所得的判决而无需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而有学者认为,被告人构成特定重大犯罪是对其涉案财物加以没收的前提条件。否则,对被告人涉案财物系属“违法所得”的认定就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参见前注〔19〕。而“对物诉讼”却不以“物的所有人”构成犯罪为条件,其一般适用于“物”的侵权情形。在此意义上,“对物审判”与“缺席审判”是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
由此观之,目前学界对刑事缺席审判的类型划分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对刑事缺席审判进行类型划分,需要将以下事项纳入考虑:其一,导致缺席审判的时间节点,即刑事诉讼的哪一个阶段或环节导致了缺席审判。不同诉讼阶段导致的缺席审判对刑事被告人的庭审参与权和辩护权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被告人在立案侦查阶段就潜逃国外所导致的缺席审判与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因严重疾病不能到庭所导致的缺席审判相比较,显然前者对庭审参与权和辩护权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前种情形,一方面被告人以实际行为逃避审判,类似于主动放弃庭审参与权;另一方面,被告人基本上不可能聘请辩护律师,待到缺席审判阶段法庭为其指定了辩护律师之后,该律师也可能因为难以与被告人取得联系而获取不到被告人视角的案件事实信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由此导致在客观上很难实现为被告人的有效辩护。在后种情形,由于被告人在案且已经参与了审前的诉讼程序,在审前阶段其能够聘请律师并充分地告知其所知道的案件信息甚至共同制定好了辩护策略,所以在该种情形下辩护律师基本上能够像在正常的审判中那样为被告人进行有效辩护。其二,刑事缺席审判的诉讼构造。正常的刑事审判具完全的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构造,而在刑事缺席审判中,虽然也存在控、辩、审三方主体,但是由于被告人缺席,故而导致辩方主体的完整性和辩护效力都趋于弱化,形成了一种不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如前所述,在刑事被告人缺席的审判中,还可能会形成控、辩、审、异的四方诉讼主体或者控、审、异的新三方诉讼构造,甚至只存在控、审两方的诉讼形态。诉讼构造的不同,将会对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完全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会削弱辩护主体的地位和功能,阻碍辩护权的实现进而使被告人遭受不当定罪量刑的潜在风险。而在只有控、审两方的诉讼形态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完全剥夺,其遭受实体不利益的风险将更加凸显。
此外,导致缺席审判时间节点的不同对刑事被告人产生的影响,最终也能够通过诉讼构造的不同反映出来。例如,刑事被告人审前阶段缺席的缺席审判,其在审判阶段即使有指定的辩护律师而形成控、辩、审三方构造,然而该种情形下辩护律师很难实现有效辩护,因此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三方诉讼构造;而对于刑事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缺席的缺席审判,存在辩护律师且其辩护效力几乎等同于被告人在场的审判,所以可以将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构造称为实质上的三方诉讼构造。据此,可以基于有效辩护能否实现,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上的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上的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至于既无被告人、又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只存在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其并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审判结构特征,因此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而只能称为一种“审查确认”程序。诚如有学者所说,这种只有检察机关作为申请方与法院作为裁判方的两方诉讼构造,通常会演变成法院对检察机关的申请加以形式审查和实质确认的过程。(21)同前注〔19〕。
2018年10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其在第五编第三章规定了六种可以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情形,分别是: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贪污贿赂案件;2.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3.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4.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的案件;5.审判中被告人死亡,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6.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已死亡的。按照前述对刑事缺席审判的类型划分,前三种和第六种情形属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第四、五种情形属于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此外,2012年我国第二次《刑事诉讼法》修订在第280条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根据刑事缺席审判的界定,也可以将其纳入刑事缺席审判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倘若有利害关系人作为异议人参与诉讼,则可以形成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22)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现代刑事审判的稳定结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并不以参与方的数量作为界定依据,只要审判的参与者符合控、辩、审三方的角色与功能,即可将其视为三方诉讼构造。此处的“三方”代表在审判中扮演着三种不同地位和功能的诉讼主体,而非指称审判参与者在数量和称谓上的多寡。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作为异议人参与审判,其实际上属于辩护方主体,而作为受害人参与审判实际上属于控方主体。倘若没有异议人的参与,只存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此时需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该律师是由被告人近亲属聘请的,基于被告人近亲属对涉案被告人财物的了解知悉情况,辩护律师能够通过与被告人近亲属(近似被告人视角)甚至是被告人本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而获知关于涉案财物的相关可能信息,因此该种情形下趋向于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假如该辩护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那么其显然难以从被告人视角获知有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信息,因此该种情形下的审判属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至于既无辩护律师、又没有异议人,只存在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则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只能是一种对违法所得没收的“审查确认”程序。
三、刑事证明标准与诉讼构造之潜在关系考察
证明标准是关于案件事实的综合评价,但凡涉及案件事实证成与否的判断,都离不开证明标准的具体运用。(23)熊晓彪:《刑事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异同》,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通说认为,所谓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或要求。(24)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令人遗憾的是,该定义并没有深入揭示证明标准的具体意涵。要想真正理解证明标准,就必须进一步看到其具有分层性的特征。实际上,在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证明标准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回答司法证明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之认定属于何种性质的“真实”;第二层含义是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即在法律上如何表达法定证明应该达到的程度或要求;第三层含义是具体的、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25)何家弘:《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即证明标准从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性质层面、表述层面和具象层面。性质层面的证明标准,即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事实是一种“客观真实”或“法律真实”;表述层面的证明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以及“证据确实、充分”等多种表述;至于具象层面的证明标准,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证明结构内部层面的要件事实证成标准和整体层面的总体论证强度标准。在证明结构的内部,庭审证据能够对每一项要件事实予以融贯性证成,同时在案件事实总体论证层面存在最佳解释推论,此即为第三层次的具象标准。(26)同前注〔23〕。
证明标准与诉讼构造之间的关系就潜藏于第三层次的具象标准之中:
首先,对于证明结构内部每一项要件事实的融贯性证成而言,除了融贯性要求的内部命题(元素)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互支持之外,(27)[荷]雅普·哈赫:《法律逻辑研究》,谢耘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还建立在对从证据到要件事实的推论链条之似真性传递与保真判断。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推论前提的似真性评估,主要涉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概括的强度是否足以证成一项要件事实的判断;二是对这种似真性能否通过推论链条传递到最末端的要件事实并保持足够的恒定或韧性进行评价。(28)[美]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梁庆寅、熊明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6页。这两项内容的达成不仅需要控方提出相应的证据并就相应要件事实推论链条的融贯性进行论证说明,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经过对切身事项最为了解和重视的辩护方的对抗性检验,即在提出相反的证据或主张对控方的证据及推论链条上的每个环节进行攻击之后,仍然不能使要件事实推论链条发生断裂或减弱至不足以推论出该要件事实,才能做出要件事实获得融贯性证成的认定。
其次,关于案件事实总体论证层面是否存在最佳解释推论,更是需要事实认定者在综合对比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的两种竞争性案件理论(或故事版本)之后,满足存在似真的有罪案情且不存在似真的无罪案情这一条件下,才能作出控方的案件理论是最佳解释推论的认定。(29)[美]罗纳德·J.艾伦:《艾伦教授论证据法》(上),张保生、王进喜、汪诸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页。由此可知,证明标准的判断严重依赖关于案件证据和事实的对抗性主张的存在,其实际上是通过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官在对比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主张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关于案件事实的确信。没有对抗性的主张,就不存在对要件事实融贯性证成与否和案件事实总体论证强度的判断问题。并且,这种对抗性主张的产生应以控、辩双方居于平等的诉讼地位为前提。尽管将案件事实证明到法定证明标准的程度是控方的责任,但是只有通过比较控、辩双方的主张之后,人们才能得出控方的证明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的有效判断。(30)[美]伯纳德·罗伯逊、G.A.维尼奥:《证据解释——庭审过程中科学证据的评价》,王元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同时,还需要由一位无偏倚的事实认定者居中当面听取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的对抗性主张以及对庭审证据的竞争性解释,观察和评价双方的举证、质证等即时动态性信息,基于理性感知、经验常识和逻辑等,作出关于控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成法定证明标准的判断。此外,还需要设置有一套具体的举证和质证规则和程序,以规范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行为有序且围绕案件事实展开。显然,上述这些条件只有在由严格的控、辩、审三方主体组成的诉讼构造之中方能实现。
在此意义上,能够得出关于刑事证明标准与诉讼构造之内在关系的如下结论:证明标准只适用于具有严格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之中,这种稳定的诉讼构造所提供的平等的即时有效对抗性与他向证明是适用证明标准的必要前提,在该诉讼构造之下事实认定者才能够亲历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及主张并通过对比得出法定证明标准达成与否的确信判断。(31)同前注〔23〕。
四、证明标准具体尺度设置与达成的影响因素剖析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证明标准只适用于严格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之中”的结论。然而,这仅是回答了证明标准在何种条件下适用的问题。至于适用的是何种尺度的证明标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知道,证明标准存在程度高低之分,那么,这种高低程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晰以下三个事项:一是证明标准的功能;二是影响证明标准尺度设置的实质因素;三是证明标准达成与否的判断方式。对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功能,绝大多数学者只注意到其设置了定罪的门槛,通过增加定罪的难度从而促进定罪的准确性,以此避免无辜者被定罪。然而,证明标准还具有更为内在的功能,即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在起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越高,越会导致更多的错误无罪判决和更少的错误有罪判决。(32)[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在此意义上,其尺度取决于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错误无罪与错误定罪之间的比率(n值)。并且,两种错误判决类型所导致的不同社会成本之间的动态平衡实际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并使得达成某种得到社会广泛同意的n值成为可能。通过某种机制(如公民投票或者立法行为)能够确定公民或他们的代表对两种错误判决类型的接受程度,从而获得n值并以此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再根据以下换算公式即可得出证明标准的最佳尺度(SoP):(33)同前注〔32〕,第79页。
SoP = 1/(1+1/n)
错判无罪的代价主要有:1.真正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实施犯罪;2.被害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宽慰济偿,正义未实现;3.法的威慑力降低,潜在犯罪增加。而错判有罪的主要代价除了包括错判无罪的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一个无辜公民错误定罪的严重代价:良好的声誉受到永久玷污、自由被剥夺,以及因此丧失的其他一系列关键性权益。显然,将一个无辜的人错误定罪的成本要比将一个实际有罪的人错放的成本高得多。这里面不仅存在对客观物质利益的成本衡量,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倘若一个社会为了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而宁愿错放3个有罪的人,即一个社会认为1个错判有罪的成本等同于3个错判无罪的成本,那么n的具体值为3。按照上述换算公式,即可得出证明标准的最佳尺度是75%,这个尺度的证明标准基本等同于“高度盖然性”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为了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接受9个实际有罪的人被错放,即一个社会认为1个错判有罪的成本等同于9个错判无罪的成本,那么n值为9。相应地,最佳尺度的证明标准为90%,这个尺度的证明标准大致等同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34)如果用数字化概率来表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具体程度,英美证据法学者基本都赞同超过90%的可能性即可满足该标准。参见[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同时,证明标准还承担着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这是与社会在两种错误判决类型(错判有罪和错判无罪)之间的取舍相一致的。以三种不同尺度的证明标准为例,在优势证据标准之下,两种错误判决类型的风险大致平等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因为每一方都承担了事实裁判者可能错误地采纳对方主张的风险。更高的证明标准将使得错误风险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通常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转移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通常是刑事案件中的控方),其尺度越高,转移的错误风险就越多,其表达了对降低错误判决有罪这种错误类型而非另一种错误类型(错误判决无罪)的追求这一政策目标。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错误风险从被告身上转移至控方的量是最多的,而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对错误风险的转移则介于排除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标准之间。(35)Ronald J.Allen,Michael S.Pardo.Relative Plausibility and It’s Crit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 Proof,vol.23,1-2,2019,p.17.
审判过程的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事实认定者判断证明标准的方式,也会对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能否在具体的审判中实现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证明标准的尺度设置。设置一个高尺度的证明标准,但是其却不能具体实现,那么这种高尺度证明标准的设置显然就没有多大意义。首先,审判过程的对抗性强度是实现证明标准尤其是高尺度证明标准的前提。一方面,控、辩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辩方能够提出竞争性的证据或诉讼主张对控方可能编造、歪曲或偏离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指控进行有效质疑和制约;另一方面,控、辩双方的有效对抗,能够向法官展示和呈现关于案件事实的全面信息,从而降低案件事实的模糊性空间,促进法官形成事实认定的确信。“当事人是模糊性的丢弃者,而非创造者”,减少人类条件下棘手的模糊性之法律机制是当事人通过准确地确定所要进行诉讼的内容。(36)Ronald J.Allen.Factual Ambiguity and A Theory of Evidence.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88,1993,pp.604-609.
其次,证明的严格程度对较高尺度证明标准的实现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证明的方式和过程的不同,将诉讼证明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严格证明是指用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并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所做出的证明,其受到证据种类、证据能力以及证据调查程序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37)[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幕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而自由证明则是指对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以及适用何种调查方式法律不做拘束限制,交由法院自由裁量。(38)同前注〔37〕,第221页。证明标准的尺度与证明程序密切相关,较高尺度的证明标准往往需要严格的证明程序加以保障。(39)熊秋红:《比较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论刑事诉讼“第四范式”》,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在严格证明的审判中,法官的心证能够达到内心确信,而在自由证明下,法官的心证难以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因此,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分别适用两种截然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前者适用的是“确信无疑”标准,而后者适用的是相信具有可能性的“释明”标准。(40)康怀宇:《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有证明的具体运用》,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最后,事实认定者判断证明标准是否达成的方式也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尺度设置。数字化概率的证明标准评价需要法官了解掌握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获取以及运算等事项,这其中涉及统计学、概率论、贝叶斯定理等复杂知识,对于法官而言无疑是相当大的挑战。同时,对于事件发生可能性的数字化表达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即使有些案件勉强能够适用,也会因为难以获得关于事件的完整先验知识而得出相当局限甚至错误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将证明标准的尺度设置为50%、75%或90%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基于常人认知判断的庭审中难以有效实现数字化的概率评价。(41)[美]罗纳德·J.艾伦:《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汪诸豪、戴月、柴鹏译,载《证据科学》2016年第3期。证明标准评价的相对似真性(42)似真性是哲学家尼古拉斯·雷切尔提出的概念,其含义体现在一种由雷切尔命名并认为有别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第三种推理类型——似真推理之中。该种类型推理的特征为: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似然为真。但是似真推论是可废止的,因为大前提中的概括从本质上说是有例外的,而且这种例外不能被事先考虑到。同时,似真推论是非单调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被新引入的前提所推翻。See Nicholas Rescher.Plausible Reasoning: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usibilistic Inference.Assen: Van Gorcum Ltd.1976,pp.15-32.进路使得对层次性证明标准评价的有效实现成为可能。该进路认为,所有的最佳判断都是基于正确的参照组作出的,在庭审中存在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的两种案件理论,事实认定者只要相信哪一种更似真,就可以作出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判决。具体到关于证明标准的评价,当控方对事件和证据的解释优于辩方的解释时,即可作出“优势证据”标准达成的判断;当控方对案件事实的解释不仅好于辩方,且对于事实认定者而言控方的解释要明显比辩方的更似真(而不仅仅是侥幸的胜出)时,就满足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当存在有罪的似真解释且不存在无罪的似真解释之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可达成。(43)同前注〔35〕,第16页。需要强调的是,证明标准判断的最佳解释推论进路也是基于对抗性和比较作出的。
五、两种诉讼构造刑事缺席审判类型中的证明标准探讨
自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来,该制度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引起了学界持续的关注。不过,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证明标准应否降低这一问题之上,并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其一,同一说。该观点认为,刑事缺席审判涉及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其证明标准应与普通(对席)刑事审判中的标准保持同一,即适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44)樊崇义:《腐败犯罪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观察》,载《人民法治》2018年第7期;周长军:《外逃人员缺席审判适用条件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8期;李海滢、王延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其二,降低说。持此说的学者主张,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设立的目的与程序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应低于普通(对席)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45)屈新、马浩洋:《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法庭审理的缺陷与优化》,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只是有的认为应降低至介于“排除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的“高度盖然性”标准,(46)胡志风:《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而有的认为应降至民事审判的“优势证据”标准。(47)施鹏鹏:《缺席审判的进步与局限》,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6期。上述学者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他们仅仅局限于对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应否降低这一问题上,而忽视了对证明标准在刑事缺席审判中能否适用以及不同类型缺席审判中适用何种证明标准等问题的分析;另一方面,没有窥见影响刑事证明标准尺度设置的主要因素和证明标准达成的具体判断机制。因此,他们所得出的关于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应否降低以及降低的程度等结论难免欠妥。
如前所述,刑事缺席审判根据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两种类型,而证明标准的适用又与诉讼构造密切相关。那么,在刑事缺席审判的这两种不同诉讼构造类型中,证明标准的适用空间、具体尺度设置以及标准达成的判断机制等事项就必然存在差异。
(一)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
实质三方诉讼构造接近于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在具有该诉讼构造的刑事缺席审判中,虽然缺少刑事被告人,但是辩护一方主体的诉讼地位和辩护能力并没有因此遭受实质削弱。辩护律师已经或者能够通过与刑事被告人及其亲属之间的联系交流获取到被告人视角的案件相关信息,因此其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提出竞争性的主张来对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进行有效攻击,以此制约控方可能偏离于事实真相的指控行为并促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全面了解。当然,在被告人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还能否遵照被告人的意愿并尽心为其辩护从而影响到实际辩护的效力,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该问题一方面取决于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被告人亲属通过旁听审判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据此,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刑事缺席审判也能够像正常刑事审判中完全的三方诉讼构造那样提供平等的即时有效对抗性,确保法官亲历听取到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的竞争性主张和证据解释。是以,该种诉讼构造下的刑事缺席审判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和前提。
既然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其适用的是何种尺度的证明标准呢?在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中,虽然缺少刑事被告人的参与,但是辩护一方主体的诉讼地位和辩护能力并没有因此遭受实质削弱。辩护律师仍然能够获取到被告人视角的案件相关信息,并提出竞争性的主张来对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进行有效攻击,以此制约控方可能偏离事实真相的指控行为并促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全面了解。因此,该种诉讼构造的审判模式能够确保控、辩双方的平等诉讼地位并产生高强度的对抗;具备严格的证据规则和证据调查程序,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心证;同时也满足适用最佳解释推论进路的对抗性和比较判断这两项基本要素。所以,其完全具备适用高尺度证明标准的空间。至于最终适用何种尺度的证明标准,就需要具体考察一个社会对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所做出的两种错误判决类型的比例之可接受程度与成本平衡,这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调研与分析。不过,通过对比普通(对席)刑事审判中适用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和民事审判中适用的“优势证据”标准,结合其适用的具体情形能够大致得出该种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可以适用何种尺度证明标准的判断。
如前所述,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主要适用于以下四种情形:(1)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的案件;(2)审判中被告人死亡,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3)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有异议人参与审判的案件;(4)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有被告人近亲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参与审判的情形。基于常规意义上的审判主要是为了解决对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可将前两种情形称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一般情形,后两种情形称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特殊情形。在前两种情形中,缺席被告人被错判无罪的成本要比普通(对席)审判中刑事被告人被错放的成本低,因为在该情形下实际有罪的被告人基本也丧失了再犯罪的能力。缺席被告人被错误定罪的成本相对于普通(对席)审判中被告人被错误定罪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对于已死亡或者身患重病的被告人而言,基本已经不存在自由被剥夺的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显然不会就此认为一个已死亡或身患重病的被告人可以被轻易定罪。从错误风险分配的视角来看,一个已死亡或身患重病的人之清白与正常人的一样都如此重要,因此应设立最高尺度的证明标准,尽可能地将这种错误风险转移至负有证明责任的控方身上以实现对已死亡或身患重病的被告之保护。是以,这两种情形下的缺席审判证明标准不能低于普通(对席)审判中的定罪证明标准,即应适用最高尺度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其具体达成与判断方式为“存在似真的有罪案情且不存在似真的无罪案情”,即只有当控方的入罪指控是似真的,且辩方的无罪抗辩是不似真的之时,才能做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已经达成的判断。只要存在似真的无罪抗辩,那么无论控方的入罪指控有多么似真,该标准都没有得到满足。
对于后两种情形,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将这两种情形下的被告人财产错误没收导致的成本是极低的,且其并没有实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因此相对于普通(对席)审判而言还不存在被告人良好声誉受到永久玷污、自由被剥夺以及一系列因定罪导致的权益丧失问题。同时,被害人也会因此得到一定的物质救济。此外,被错误没收的财产是可以通过返还、等价赔偿等低成本方式进行回复救济的。至于错误判决不予没收的成本,相较于普通(对席)审判中的错判无罪而言并没有多大变化。真正有罪的人仍然逍遥法外,并可能受到激励而继续实施犯罪,被害人没有获得慰偿,法的威慑力降低。显然,这两种情形的缺席审判证明标准应低于普通(对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至于降低至何种程度,则可以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优势证据”作为参照。“优势证据”标准的含义是错误定罪与错判无罪的成本相同,那么,上述两种缺席审判中对被告人财物的错误没收成本是否降低至等同于错误判决不予没收的成本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错误没收虽然没有实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但却以被告人构成重大犯罪(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为前提,这也是一种加之于无辜被告人身上的沉重成本。被告人不仅因此长期背负污名,而且将会继续受到司法机关的长期通缉以及其在国内的一系列重要权益将因此遭到限制甚至剥夺。所以,被告人财物被错误没收的成本显然要高于错误判决不予没收的成本,也即,相应的证明标准应高于“优势证据”标准。从错误风险分配的视角来看,在该种情形下,被告失去的利益远比单纯的金钱财物损失更加重大,所以需要提高证明标准的尺度以降低被告这种重要利益被错误剥夺的风险。不过,与遭受定罪的最严重后果相比,被告所失去的这些利益又显得轻了一些,因此,证明标准的尺度还不足以提升至定罪的最高尺度。
由此可以得出,上述两种违法所得没收缺席审判情形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是一种介于“优势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的标准,从英美法系对证明标准的分层来看,处于这一层次的证明标准是“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该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为:一方面,为了满足该标准,当事人不必有唯一似真的解释(不像排除合理怀疑);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比仅仅提供可获得的最佳解释做得更多。当事人必须提供不仅比替代性解释更好的解释,而且要更有说服力,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要使其“清晰且令人信服”。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只要事实认定者决定哪种解释更好的问题只是一种“侥幸的胜出”之时,被告都应当胜诉(即使事实认定者认为原告的解释略微更好)。(48)同前注〔35〕,第28页。
(二)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
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虽然也存在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但由于刑事被告人不在案,导致由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难以从被告人视角获取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以至于难以与控方形成实际有效的对抗,因此该种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不具有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那样的对抗强度。作为事实认定者的法官也因为难以获得来自辩方关于案情的有效信息而无法通过对比的方式作出证明标准(尤其是高尺度证明标准)达成的确信判断。不过,该种缺席审判也基本可以确保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并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和证据调查程序,能够满足证明标准适用的形式要求。据此,可以认为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勉强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但是其显然难以具体实现对高尺度证明标准的判断。至于其适用何种尺度的证明标准,则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进行分析。根据前面的论述,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贪污贿赂案件;2.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3.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4.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已死亡的。前三种属于涉嫌贪污贿赂、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的被追诉人都在境外从而逃避审判的情形,后一种则与前三种明显不同,属于被告人已经死亡不可能实际参与审判的情形。结合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旨在实现境外追逃追赃的反腐要求,(49)陈卫东:《论中国特色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3期;顾永忠、张子君:《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意图与特色》,载《理论学刊》2019年第1期;施鹏鹏:《缺席审判的进步与局限——以境外追逃追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6期。据此可将前三种情形视为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典型情形,而将第四种情形看作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例外情形。在前三种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中,错误有罪判决成本包括真正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实施犯罪,无辜的人被错误定罪所导致的良好声名被永久玷污以及许多关键性的权益因此丧失。不过,相较于普通(对席)审判中错误有罪判决的成本而言,这三种情形下的错误有罪判决成本降低了许多,被告人的自由并未实际被剥夺(因为其并未到案),一些基本的权益也没有因此丧失(例如仍正常地工作和享受生活等)。
至于这三种情形下的错误无罪判决成本,与普通(对席)审判相比也会有所降低,因为该情形下的刑事被告人被错放之后不大可能继续实施新的(同类型)犯罪,其已经逃往境外或失踪并受到了司法机关的重点关注。总体来看,上述三种情形下的错误有罪判决成本与错误无罪判决成本之比率要低于普通(对席)审判。此外,由于这三种情形都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重大犯罪,因此相较于其他普通犯罪而言,整个社会更容易接受将其定罪。是以,其适用的证明标准应低于普通(对席)审判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当然,这毕竟涉及对人的定罪量刑,而且一旦被定罪基本都会被处以严厉刑罚(虽然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因此其错误定罪的成本必将高于错判无罪的成本。也即,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尺度要高于“优势证据”标准。从错误风险分配的视角来看,对一个人的定罪涉及对其最重要利益的剥夺,因此本应将证明标准提升至最高尺度以最小化对其错误定罪的风险。但是,在该种情形下,被追诉人外逃躲避审判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其错误定罪的风险相对而言要低得多。而且,错误定罪之后实际上也没有对其自由权利等重要利益予以剥夺。因此,在该种情形下被告人一方面要为其行为自承一部分错误风险,另一方面这种错误风险要低于普通(对席)审判的错判风险。另外,如上所述,在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的缺席审判中难以具体实现对高尺度证明标准的判断,所以对于这三种典型情形,无须也不能适用最高尺度的证明标准。
据此不难得出,上述三种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典型情形应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该种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之下,辩方难以提出竞争性的证据和辩护主张来对抗控方的证据和诉讼主张,导致控方的指控天然地优于辩方,所以该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不能再基于单纯的对比方式做出。法官在做出具体判断之时,除了要求控方对案件事实的解释不仅要好于辩方且要明显比辩方更似真之外,还要满足对每一项要件事实的证明都达到融贯性证成,即在辩方提出相反的证据或主张对控方的证据及其推论链条上的每个环节进行攻击之后,仍然不能使每项要件事实推论链条发生断裂或减弱至不足以推论出该要件事实之时,才能做出“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已经达成的判断。
接下来讨论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的例外情形。与前三种典型情形相比,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在错误有罪判决成本方面,都不存在被追诉人自由被剥夺问题(前三种情形是实际未剥夺,后一种情形则是不可能继续剥夺);在错误无罪判决成本方面,被追诉人也都不再可能继续实施犯罪(前三种情形是不太可能再实施同类型犯罪,后一种情形则是不可能再实施任何犯罪)。主要区别在于:在前三种情形下,被告人失踪或潜逃加重了其犯罪嫌疑,导致社会更容易接受对其定罪量刑;而在第四种情形下,对于被告人已死亡的案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新审判,意味着被告人可能是无罪的。(50)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97条规定:“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依法作出判决。”并且,对于一个可能是因为遭受了错误定罪而冤屈至死的人来说,朴素的正义观念认为还其清白有着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同等重要甚至犹有过之的价值。(51)“沉冤昭雪”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朴素正义观念。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人们总是希望有朝一日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洗去无辜者身上的冤屈。对于含冤而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在人们心里,只有还屈死的无辜者以清白才能让其亡灵得到安息。因此,社会显然更倾向于最小化错误有罪判决,这就需要增加定罪的门槛,尽可能地提高证明标准的尺度。另外,由于存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之一,并且被告人(或许还有辩护律师)曾经参与了之前对其定罪量刑的审判,使得通过查询过往卷宗以及与其曾经的辩护律师交流获取到被告人视角的案件信息成为可能。因此,在该种情形下辩方能够提出竞争性的证据和辩护主张与控方进行有效对抗,从而具备了实现高尺度证明标准评价的条件。据此,在第四种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这一例外情形中,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具体评价方式为:存在似真的有罪案情且不存在似真的无罪案情。
结 语
自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来,就引发了学界对该制度中应适用何种尺度证明标准的热议。有的学者认为刑事缺席审判涉及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因此其证明标准应与普通(对席)审判中的证明标准保持同一;有的学者则主张,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设立的目的与程序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应低于普通(对席)审判的证明标准。至于低至何种程度,有的认为是高度盖然性,有的认为是优势证据标准。然而,倘若没有窥见证明标准适用的空间与前提条件,没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内在功能、具体尺度设置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达成与否的判断方式进行深入剖析,那么所得出的关于刑事缺席审判中证明标准降低与否以及降至何种尺度的结论,显然其意义都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有的缺席审理程序可能因为不具备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条件导致其根本不存在证明标准适用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刑事缺席审判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也还要进一步分析证明标准设置之最佳尺度,以及在缺席审判情形下能否具体实现等问题。否则,将会导致设置过低或者过高尺度的证明标准,从而与刑事缺席审判和司法政策目标对最佳尺度证明标准的要求不一致,或者虽设置了高尺度的证明标准,但在刑事缺席审判中却难以具体实现等尴尬困境。
诉讼构造是打开证明标准适用空间的钥匙。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举证质证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错误有罪判决成本与错误无罪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方式与证明过程的严格程度,以及事实认定者具体评价证明标准的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由于不同诉讼构造刑事缺席审判类型的对抗性强度和证明程序的严格程度不同,导致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及其评价方式存在差异。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特殊情形下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下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