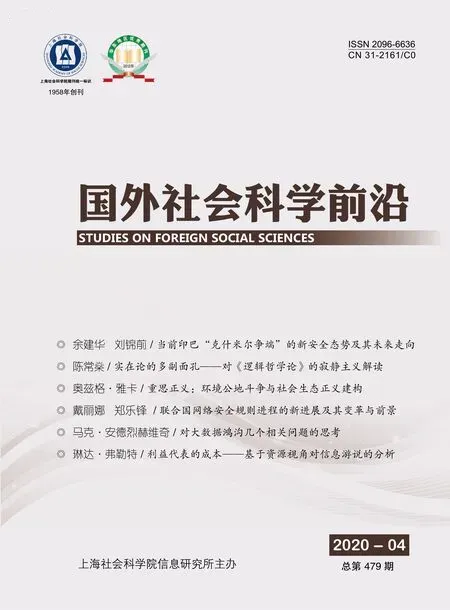实在论的多副面孔
——对《逻辑哲学论》的寂静主义解读
陈常燊
内容提要 | 在主流的“标准解读”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别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分水岭。问题在于,不管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假定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是可能的。然而,以赖特、麦克道尔为代表的第三种解读进路,即“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直指任何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论辩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种“非形而上学”观点看,《逻辑哲学论》在实在论色谱中的位置显得非常晦暗不明,不管是逻辑实在论还是语义学建构主义,不管是“非还原的实在论”还是“作为唯我论的实在论”,都无法支撑《逻辑哲学论》的实在论解读。此外,从维特根斯坦后期观点看,《逻辑哲学论》中的“非实在论”的不彻底性是难以掩盖的。
一、引 言
围绕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文本,当代学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解读进路。举其要者,其一是以戈登·贝克(Gordon Baker)、彼得·哈克(Peter Hacker)、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为代表的“标准解读”(standard interpretations);其二是以詹姆士·科南特(James Conant)、科拉·戴梦德(Cora Diamond)为代表的“坚决解读”(resolute interpretations);其三是以克里斯平·赖特(Crispin Wright)、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为代表的“寂静主义解读”(quietist interpretations)。在主流的“标准解读”中,实在论(realism)与反实在论(anti-realism)之别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分水岭。然而,从第三种解读进路看来,不管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假定了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是可能的。多数解读者认为寂静主义适用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特别是其关于遵守规则的评论。1John McDowell, Wittgensteinian ‘Quietism’, Common Knowledge, vol. 15, 2009, pp. 365-372.但也有论者指出,维特根斯坦前期在诸如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神秘之域”的性质,以及逻辑与世界的本性这些议题上,同样持有某种寂静主义观点。譬如,威廉·恰尔德(William Child)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自始至终都具有一种深刻的寂静主义或紧缩论(deflationism)特征,而在关于《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的本体论性质问题上,这一特征尤为明显。2William Child, Wittgenstei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11, p. 261.
何为寂静主义?学界较早提出“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Wittgenteinian Quietism)的布里安·莱特(Brian Leiter)认为,寂静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主张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论辩是不可能的。3Crispin Wright, Truth and Objectiv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2.科斯卡里·库塞拉(Oskari Kuusela)进一步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乃是通过针对独断论的坚决斗争而得以阐明的,即哲学中没有论题、学说或理论;与他前期的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al)不同,其后期提出了一种非形而上学(non-metaphysical)的哲学方法,拒斥一切哲学教条(philosophical hierarchy)。这种方法增强了哲学思维的灵活性,使之免于陷入僵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1Oskari Kuusela, The Struggle against Dogmatism:Wittgenstein and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1.鉴于《逻辑哲学论》对形而上学命题的整体否定态度,“反形而上学”构成了该书寂静主义的一个底色,但这里所讲的寂静主义并非与人们熟知的格言“对于不可说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2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77.直接相联,而是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对实在论的态度之中。本文拟从“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视角,揭示《逻辑哲学论》中的实在论的多副面孔,这使得我们很难将前期维特根斯坦视为一名严格的实在论者;最后我们结合其后期《哲学研究》中的观点来考察《逻辑哲学论》在“非实在论”问题上的不彻底立场。
二、《逻辑哲学论》在实在论色谱中的位置
在常见语境中,寂静主义是在当代西方哲学声势浩大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中,作为“第三方观点”而得以定位的。比如,亚历山大·米勒(Alexander Miller)在斯坦福哲学百科的“实在论”词条里如是写道:“它主张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论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这场争论背后最终不能发现任何实际的东西。”3Alexander Miller, Realis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alism/#8.“ 标准解释”通常将维特根斯坦前期与后期哲学对立起来,认为其前期是一名实在论者,后期是一名反实在论者。笔者不同意这种简单二分。诚如赖特所言,没有人非得是一名单纯的(tout court)实在论者。4Crispin Wright, Saving the Differences: Essays on Themes from Truth and Objectiv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 13.在最严格的实在论者与最严格的反实在论者之间存在一片足够宽广的灰色区域。依其所愿意承诺的对象的实在本性,在实在论的色谱上,据其从“坚硬”到“柔软”的程度,实在论依次可划分为:(1)严格实在论(strict realism),这是一种坚硬的、毫不妥协的实在论;(2)准实在论(quasi-realism),虽非坚硬无比,大致上仍属于实在论范畴;(3)半实在论(semi-realism),这是一种打了折扣的实在论,它可能同时承诺了某些“非实在”的对象;(4)伪实在论(pseudo-realism),表面上的实在论下面实际隐藏的是非实在对象;(5)反实在论(antirealism),公开承诺非实在对象的本体论地位;(6)非实在论(irrealism),从根本上拒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立场之争,并拒绝在两者之间寻求折衷或调和。
在实在论的色谱中,前期维特根斯坦究竟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描述《逻辑哲学论》中的寂静主义特征的一个出发点。在不同议题上,《逻辑哲学论》中至少暗含了三种面孔的实在论:“逻辑实在论”(logical realism)、“非还原的实在论”(irreducible realism)以及“作为唯我论的实在论”(the realism as solipsism)。它们都迥异于流行版本的实在论,借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表述,它们都属于“纯粹实在论”(pure realism)的不同侧面。在笔者看来,它们分别指向了寂静主义的四个方面:对象的非实在论地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显示”(manifestation)的寂静主义特征以及哲学自身作为“划界”和“澄清”的性质。
“标准解读”中最常见的是逻辑实在论,亦即关于事实—实在的逻辑图像理论。其关于世界的逻辑结构,亦即对于“世界是什么”(Being 问题)的逻辑分析,从“世界上有什么”(What 问题)着手,接下来追问“世界为何如其所是”(Why问题)。《逻辑哲学论》开门见山指出,实在(真实存在)的有完整意义的最小单位是事实(facts),而非引人误解的“事物”(things)。两者的根本区别是逻辑上的:逻辑上能够提供关于事实的独立完整的、有意义的图像,但没有关于事物的此类图像。事物,或对象,其图像只是作为对于事实的逻辑配置要素而出现的,缺乏独立完整的意义。换言之,(基本)事态(state of affairs)、(简单)对象(objects)仅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时才有意义。所以,物理学上的世界要素分析,即便到了微观的亚原子、基本粒子层面,其所对应的逻辑图像仍然是事实,而非事态或对象。事态在逻辑上刻画了事实的可能状态,它们在形式上通过逻辑联结词(如“与”“或”“非”“蕴含”“全”,等等),在实质上借助经验观察,从而确定一个事实的存在。实在只是逻辑上可能之物的一个真子集,进一步对事态进行分析,就得到了最简单的那个“逻辑原子”——(简单)对象。
仅当借助语言要素,譬如命题、基本命题、名称,才能对世界的逻辑结构有所刻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他称之为“图像”。这种对应关系是由逻辑所保证的,因为作为我们描述世界的语言以及作为被语言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同构关系。逻辑空间中存在诸如“思想”(thoughts)这样的东西,作为语言与世界沟通的媒介。对之相应,还存在思想要素、思想对象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层面分别与事态、对象相对应,在语言层面则分别与基本命题、名称相对应。他说:“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1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13.思想只是逻辑空间中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有所表达时,它就化身为语言。但若是没有思想,我们的语言就无所表达,世界就无法被刻画。由此看来,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似乎对一个传统的哲学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它就是存在与思维的“二元同一性”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存在、思维与语言的“三元同一性”问题。在他那里,开启同一性之门的秘密钥匙,就是逻辑。正是存在、思维、语言在逻辑上的同构关系,保证了世界的可思和可说,就此而言,世界上并不存在那些不可思、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正如我们在《逻辑哲学论》临近末尾时所看到的那样,维特根斯坦的确主张“神秘之域”的存在,但严格来说,它们并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外。据此可以较好地理解他的“世界”概念。
逻辑(空间)联接语言与实在,“思想”则是一个枢纽性概念:在《逻辑哲学论》中,我们首先能够在“实在—思想(有意义的命题)”两者之间找到一种逻辑同构关系,然后在“思想—语言”两者之间寻求命题的有意义性的限度,最终划出一条“可说(可思)”与“不可说(不可思)”的界限:不可思的东西即便字面上貌似“可说”,传统哲学家们对此也没少说,但在语义上仍然是不可说的。《逻辑哲学论》将广义的语言划为三类,并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对待它们:一是与事实的世界相应的有意义的命题的总和,二是那些毫无意义的胡说(nonsense),三是为《逻辑哲学论》一书的自身可说性而准备的“工具性”语言——这本书好比是一架“梯子”,它们则是一个个“梯级”。
为什么我们只能为思想的表达(语言)而非为思想自身划界限?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逻辑哲学论》序言对此回应道:
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思想划出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不能想的东西)。
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1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3.
位于思想界限之外的,乃是不可思之物,或曰“神秘之域”,它要求一种反实在论的解释——其命题的意义不仅无法显示存在的现实性,也无法显示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为之建立逻辑图像。但是我们可以在语言中——借助语言——为思想划界,也就是在那些可思的与那些不可思的东西之间划出一条语言上的界限。有些语言位于可思的划界之外,比如《逻辑哲学论》这本书自身的命题,它们不提供任何关于事实的知识,只是做划界的工作,作者称之为“语言批判”或“思想澄清”。作者只是借助这本书中的语言,在语言之中为可思与不可思划界的。这本书本身所包含的命题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思”,但仍然能在哲学上被人所理解。因为其中的命题不再表征事实或者表达思想,而是对事实的表征或思想表达的可能性以及局限性有所澄清:它要求一个人能够站在思想界限的另外一边。这种工作不再是反实在论的,而只能是非实在论的——就在“划界”这个问题上,非实在论超越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倘若没有这种超越,任何界限的划分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寂静主义的工作,正是它要求一种对于“可说—不可说”的非实在论解释。
三、实在论、语义学抑或寂静主义?
如前所述,“标准解读”认为,维特根斯坦前期《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是实在论的,后期《哲学研究》中的观点是反实在论的。“寂静主义解读”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管是其前期还是其后期,维特根斯坦都不是一名严格的实在论者,也不是一名严格的反实在论者——毋宁说,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都是一名“非实在论者”,其前后期哲学的分歧在于,前期哲学中的“非实在论”晦暗不明地隐藏于“逻辑实在论”“非还原的实在论”与“作为唯我论的实在论”的字面表述之中,显得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对于“非实在论”,在《牛津哲学词典》中,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如此界定:
非实在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传统论争,在问题域上存在某些不恰当的假定,比如,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反对实在论者的人,也无需承认自己是某种形式的观念论者、相对主义者、还原论者或者其他的“反实在论”立场。2 Simon Blackbur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91.
这种非实在论——不同于反实在论——并不是旨在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进行居间调和,寻求折衷策略。与其说它否认实在论或反实在论在实质观点上的可接受性,毋宁说它拒斥预设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二元区分的那个前提。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争更是经久不息,寂静主义的首要特征就体现在它在这些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看来,它对待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包括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态度是“取消提问,而非回答”(unask rather than answer)。
逻辑图像论直指世界与语言的逻辑对应关系。问题在于,既然这种对应关系是由逻辑来保证的,那么逻辑上为什么能保证这一点呢?这涉及我们对逻辑本性的理解。由于我们所有有意义的言说首先必须符合逻辑,所以逻辑就只能由其自身来规定。“逻辑必须照看其自身。”1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46.可是这么说意义何在呢?让我们换个角度提问。譬如,世界与语言,何者为先?对此有两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一:世界为先——实在论;
解决方案二:语言为先——语义学。
这个问题与对象的本体论性质问题类似。实在论方案认为,世界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实在,我们依照世界的组成与结构为其制造图象;语义学方案则主张,我们是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的终极要素及结构而推知世界必然具有的终极要素及结构的。就其强调世界的实在结构乃是依赖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结构而言,语义学观点是一种建构主义观点;就其强调语词的语义内容并不取决于其在实在世界中的指称对象而言,它是一种观念论观点。有学者指出,由于维特根斯坦不再将哲学看作一种理论,而是看作对思想进行逻辑阐明的活动,所以他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已超越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争论。2李国山:《语义学还是实在论?——评关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一场争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 年第1 期。由于世界与语言的关系是由逻辑所规定的,所以仍然离不开对逻辑本性的探讨。照《逻辑哲学论》中的唯我论解释,自我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鉴于你无法站到逻辑之外,所以就无法看清它的全貌。看清逻辑和世界的全貌,就要求一个人必须从一个全局的、永恒的角度看问题,这已经进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神秘之域”了:它们是不可说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任何一种积极的“解决”(resolve)方案,而只有消极的“消解”(desolve)方案:它并不试图去回答它,而是直接质疑这个问题本身的合法性——揭示其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而这意味着在图像论背后隐藏着某种“寂静主义逻辑”。
与逻辑的性质相关的,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真理和意义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命题的图像性质为其有意义性提供了逻辑解释,而真理在于一个有意义的命题能够在实在世界中找到与之相应的事实。
“如何”(How)的问题——实在论;
“为何”(Why)的问题——寂静主义。
我们看到,“Why 问题”同时也是“What 问题”,两者都是形而上学追问。关于意义是如何可能的,以及一个有意义的命题的真值是如何得到满足的,都可以求助于逻辑实在论。而关于何以如此,只能求助于“逻辑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logic),也就是逻辑的本性——它同时也是世界的本性和唯我论中的自我的本性。然而,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于命题的真值和意义之“如何”问题,这一点不神秘;但关于“如何”背后的根本机制,这个“为何”问题是相当神秘的。这种神秘性诱惑哲学家们去建构理论、提供解释,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逻辑形而上学”是不可说的,我们无法用逻辑为其自身提供理论化解释,当维特根斯坦说“逻辑照看其自身”时,借助的不是这种理论化解释方式,而是借助某种形态的寂静主义,它是理论和逻辑的尽头。由此看来,即便是逻辑实在论,也不算严格的实在论,因为其形而上学背景是寂静主义的。
四、作为“严格唯我论”的“纯粹实在论”
《逻辑哲学论》中的实在论以一种非常晦暗不明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点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下述文本之中:“这里可以看到,严格贯彻的唯我论(strict solipsism)与纯粹的实在论(pure realism)是一致的。唯我论的自我收缩为无广延的点,保留的是与它相关的实在。”1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64.“ 作为唯我论的实在论”,是《逻辑哲学论》中继“逻辑实在论”和“非还原的实在论”之后的第三副实在论面孔,它主要围绕一种“严格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之关系来展开,涉及“自我”与“实在”的本性问题,因此显得非常晦涩难解。
前期维特根斯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唯我论的世界观。存在种种事实的局部的世界(local world),是我所熟悉的、也是我与他人所共享的世界;但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又具有某种超越色彩,因为现实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那个由所有事实的总和所规定的世界。毕竟事实不能是一些被假定存在的东西,而是必须被证明存在的东西,但实际上每个人能够证明其存在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局部性的世界。那个整全性的世界(global world),只能是“我的世界”(my world),一种作为形而上主体的世界:《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是每个人的梯子,但如果我愿意拾级而上,也只是我一个人的梯子。如果我不去爬,没有人替我去爬;如果我去爬,我爬上去之后无需为后来者保留这架梯子,因为这只是一架属于我个人的梯子。世界本身(带着其界限)也只有爬上梯子后才能获得整体性意义。只有从“我”的角度看,世界作为整体才有意义。一方面,这种实在论是非常纯粹的,它非常谦逊地承认自己的存在有限性和知识的局限性,拒绝随意僭越证实性的界限,所以一种纯粹的实在论所能承诺的世界,只能是局部世界。另一方面,这种实在论又是严格唯我论的,因为它仍然承诺了一种只有将之视为“我的世界”才能被体验到的整体世界。
维特根斯坦这里的“主体”,既非生物学之“我”(肉身),亦非心理学之“我”(心灵),而是形而上主体,它是世界的界限,“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2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61.也就是那个“我”:“我是我的世界。”3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63.“ 自我”并非虚无空洞,相反它的内容相当充实。首先,世界是“我”的世界,人生也是“我”的人生。其次,语言是“我”的语言,意志也是“我”的意志。“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4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56.“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86.最后,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作为形而上主体的那个“我”也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活以及我的语言——有且只有一种“我的语言”,一种“形而上语言”。不管是我,还是我的语言,都只是作为世界的界限,而从世界之外才得以观照到的。换言之,我和我的语言都不是世界之内的任何“事实”,尽管作为事实的总体的那个世界(也就是实在),乃是形而下之物,但是,作为世界之界限暨人生之限度的那个东西,乃是形而上之物。意志是我的意志,并且,从唯我论角度看,世界之外的“神秘之域”也归属于我:我的审美、我的道德、我的宗教、我的形而上学,诸如此类。
《逻辑哲学论》中的唯我论是一种相当奇特的唯我论,而其中的实在论是一种唯我论的实在论。罗素等人认为它具有相当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6Bertrand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8, in John G. Slater (ed.),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 23.不管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维特根斯坦受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二书的深刻影响,尽管未必完全接受他们的立场。1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712~756 页。唯我论者所意味的东西是先天正确的,因为无需任何经验上的判断标准。但是这种正确性是无法被言说的,而只能被显示出来。下文我们会讨论到,“显示”不是任何一种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而是一种纯粹的生活态度(life attitudes)。“纯粹”意味着没有经验杂质,同理,维特根斯坦说他的实在论也是纯粹的。这表明《逻辑哲学论》中的实在论是一种相当奇特的实在论:它是纯粹实在论,以此区别于通常那些“不纯粹的”、依赖于经验观察或科学实证的实在论。这里的确存在某种令人费解之处。首先我们从该书第一个命题“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开始,就能领略到一股实在论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切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们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在之物,日月星辰、江河湖海、草木虫鱼、亭台楼阁、锅碗瓢盆……而这些便是实在世界的全部,它们既不是主观的“观念”,也不是超越的“理念”,而是那么地眼见为实或触手可及。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2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13.也就是说,直到他把“逻辑空间”(logical space)概念引进来,我们才逐步明白,他的实在论与传统上相对较为粗糙的实在论,还是有所不同的:这是一种可称之为“逻辑实在论”的东西。接下来的所有内容都直接或间接与逻辑相关,仿佛实在的概念是在逻辑上被建构出来的,反过来也可以对之进行逻辑分析,从实在开始,依次分析为事实、事态、基本事态、简单对象,诸如此类。逻辑为实在提供了可能性,它是对实在的描述(命题)之有意义性的理由。相较于可能性,实在的现实性在哲学上反倒不那么迫切,因为不管是偶然存在之物,还是对自然万物进行总结归纳的“自然律”,其在逻辑上的确定性都大为可疑。
这种“纯粹实在论”不仅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甚至最终还超越了逻辑,突破了逻辑的界限,进入唯我论。“我”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我”并非生活在逻辑之外,而是说,“我”就是“我的逻辑”,就是那个界限本身。这是维特斯坦前期对于逻辑之本性的思考结果:逻辑的可能性体现在实在世界之中,但逻辑的限度只能在世界之外。“唯我论的自我收缩为无广延的点,保留的是与它相关的实在。”3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64.为便于理解,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作为世界之界限的“自我”有些类似于当代物理学弦理论中的“奇点”,它被收缩为一个无广延的点,换来的是作为实在世界的宇宙万物;并且通过这个“奇点”,我们仿佛就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弦理论中称之为“反物质宇宙”,《逻辑哲学论》中称之为“唯我论的世界”。作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唯我论的世界”中栖居着种种“形而上学对象”(metaphysical objects):世界本体、伦理道德、艺术审美、宗教信仰、人生意义,如此等等。当然,毋庸讳言,它们皆属于“神秘之域”,它们是不可说的,其对于“自我”而言的“意味”(价值)只能显示出来。这是一种伦理态度,它要求我们“不要说,而要做”,在生活之中体验之、笃行之。
倘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在论乃是一种他自己所说的“纯粹实在论”,从而又与唯我论紧密相联,那么这意味着,即便对于《逻辑哲学论》中的最“硬核”部分,也就是与经验事实最为贴近亦即与“神秘之域”相隔最远之部分的解读,都能够与某种形态的“寂静主义”相互兼容,因为寂静主义恰恰主张对于世界的理论化解释存在一个限度,同时也特别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态度”而非仅仅“命题态度”的哲学之路。
五、不彻底的非实在论
根据语境论,字词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对句子的意义的理解要优先于对其构成部分的意谓的理解。在语义学上,字词相对于句子来说,缺乏一种独立性,在逻辑上依赖于整个句子,因此只能存在一种纯粹的无意义(mere nonsense)。1James Conant, The Method of the Tractatus, in Erich H.Reck(eds.), From Frege to Wittgenstein: Perspectives on Early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2, p. 381.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但是即便如此,有完整意义的最小单位仍然是命题而非基本命题,不管是名称,还是将名称通过逻辑配置而成的基本命题,其意谓都依赖于其所构成的命题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的下述命题对于理解对象的本体论对象非常关键:“对象只能被命名。记号就是对象的代表。我只能谈及(speak about)对象,而不能用语词说出它们(put them into words)。命题只能说事物是怎样的(how things are),而不能说它们是什么(what they are)。”2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1, p. 21.诸如“有一个对象”“对象存在”这样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诚如韩林合指出的:因为一方面,“对象”是一个形式概念(formaler Begriff),因而不可言说;另一方面,对象的存在是语言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因而它不可能经由语言有意义地说出来。3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27 页。我们无法抽象地说对象“是什么”,因为任何关于对象“是什么”的语言刻画,都超出了名称的范围,不得不进入命题或基本命题层面,即便“对象存在”这么简单的表述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用语词说出它们”。当我们不得不在抽象层面上讨论对象时,也就只能将它视为一个形式概念:就其是个形式概念而言,我们“谈及”了对象;如若要增加一些实质内容,那么就只能说它们“是怎样的”——对象可能是这样的:桌子、书、玫瑰花……它们以“实际情况”的方式例示了对象,但它们并不代表对象本身,因此不能说对象就是桌子、书、玫瑰花,或其他什么样子。关于此问题,恰尔德的结论是,根据紧缩论者的看法,真相就是如此。存在语言的简单成分,也存在实在的简单成分,它们是一一对应的。这些就是要说的全部。4William Child, Wittgenstei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11, pp. 56-57.
对象的本体论性质,同时也事关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对象是一个“伪概念”(pseudo-concept),与之相应的是“真正的概念”(real concept)。前者是那些用以刻画日常语言和世界(或逻辑空间)的一般结构特征的诸概念:命题、基本命题和名称以及事实(事态)、基本事实(事态)和对象;还指日常语言及其他符号语言中其他一些表示类型区分的重要概念,如性质、关系、颜色、复合体、复合物、主—谓语结构、函项、数,等等。而用表示属于诸形式概念之下的诸特定对象的那些特定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概念,如桌子、这本书、玫瑰花、红色、2,等等。5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371 页。据此我们认为,在对象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上,最多只能持有一种“非实在论”(irrealism)观点:我们承认对象的实体地位,但关于这种实体“是什么”,又为何与语言中的名称一一对应,对此我们无话可说,而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实在论和观念论的范畴。
在主流的“标准解读”看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别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根本分歧。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歧是有道理的,因为《逻辑哲学论》的确保留了“世界”“实在”“思想”“命题”“事实”“自我”这些形而上学中的常见概念,无非就是借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式给出了一套全新的实在论建构而已。至于伦理、审美、宗教、人生的意义、逻辑的本质等“神秘之域”,因为它们根本上是不可说的,对可说之物的实在论并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持有一种明确的反实在论观点,它不再主张我们能够为上述形而上学概念给出一套实质性理论,甚至不再认为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而只是一些彼此家族相似的语言游戏。
然而,正如近期以赖特、麦克道尔为代表的第三种解读进路即“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所指出的,不管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假定了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是可能的,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真正旨趣在于,任何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论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中我们唯有保持沉默。从这种“非形而上学”观点看,《逻辑哲学论》在实在论色谱中的位置显得非常晦暗不明,不管是逻辑实在论还是语义学建构主义,不管是“严格的唯我论”还是“纯粹的实在论”,都无法支持《逻辑哲学论》的实在论解读。因此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既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实在论者,当然也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反实在论者,而是一名隐晦不明的非实在论者。
从其后期观点看,《逻辑哲学论》中的“非实在论”岂止是隐晦不明的,因为除此之外,它的另一个特征即不彻底性也是难以掩盖的,这使得它在实在论问题上显得特别尴尬。笔者认为,《哲学研究》所要批判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彻底性所导致的尴尬处境。他写道,“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写在那第一本书里的思想包含有严重的错误。”1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4th Edition, G. E. M. Anscombe (trans.), Oxford: Blackwell, 2009, p. 4.如,《逻辑哲学论》中的逻辑实在论是以承认“神秘之域”的存在为代价换来的,其中不仅包括伦理、审美、宗教诸事项,甚至还包括“逻辑”“实在”这些概念本身的性质。其中的“作为唯我论的实在论”则显得更加怪异,它一方面承认了“自我”这个概念的非实在性,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这个超级概念。作为严格唯我论的“纯粹实在论”,也同样带有他一贯拒斥的形而上学色彩。正如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所看到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借助对心理语词以及其他语言游戏的语法考察,消解了“实在”“自我”以及其他语词的形而上学基础。
总之,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中仍然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其中应当包含寂静主义所强调的“非实在论”“非形而上学”旨趣。基于这种观点,哲学不是一门关于世界——不管是世界之内的诸多事实、世界的界限自身还是世界之外的“神秘之域”——的理论,而是一种看待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或方法。因此严格来说,哲学上没有理论。据此我们认为寂静主义也不是任何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哲学理论”,它同样只是某种看待哲学问题的态度或方法,毋宁说它是一种通过划界和澄清而“取消”或“消解”它们的方法。当然,毋庸讳言,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前期哲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其后期立足于语言游戏的意义理论,乃是对其前期逻辑图像论的颠覆。平心而论,其前后期哲学的精神旨趣是相当不同的,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回答诸如“形而上学如何(不)可能”“哲学如何可能”这些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寂静主义与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