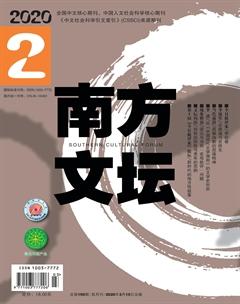王彬彬的文学评论

文学是人学,它后面藏的是深厚的文化。因此,对文学的批评就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其实它考验的更是一个批评家的综合素质,尤其他的世界观、人生觀、价值观,还有他对人性的理解。一个内心陈腐的人,和一个深具现代意识、心灵清明的人,面对同一部作品会有截然相反的感觉和结论。
在《鲁迅内外》自序里,王彬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思想演变历程,如何吐尽狼奶,进入清明、理性的境界的。这个过程,简略但清楚地呈现了一位优秀评论家是如何诞生的。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在《鲁迅:晚年情怀》一书里对胡适的“粗暴批判”,并说:“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①也深情感谢了徐友渔对他的“迎头痛击”,也促使他“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②。比如,《胡适文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著作,“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③。当然,他也同时指出:“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④经过这一番淘洗,王彬彬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清明的理性,这就让他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包括历史随笔等)有了不同俗人的境界,与那些常识不足、思维混乱、思想腐旧之流,截然划开了界限。王彬彬行文犀利,有时言辞过于尖刻,但心地善良,知错则改,他在自序里对王德威、严家炎的致歉,让人动容。我想,心地坦白,一片天真,也是王彬彬的文字那么打动人心,而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最大原因吧。
《鲁迅内外》是王彬彬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著作,收入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二十六篇,还有三篇附文。这些文章大多非常精彩,是目前鲁迅研究界难得的成果。尤其那些辩难文章,不仅胆识过人,而且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思想超前。当然,他为鲁迅辩护,但也尊重胡适,他明确提出,“在今天,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是值得鲁迅研究界认真对待的,我甚至想说,这种挑战是严峻的”。“鲁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并没有一种中国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应该如何的理念”⑤。他对那些给鲁迅泼脏水者严词痛斥之,但也不避讳鲁迅的缺陷,这种清明的境界,是让我们钦服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胡鲁互补”的观点⑥,但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还有很多盲区,王彬彬的文章,对我启发甚大。
王彬彬后来撰写的《月夜里的鲁迅》也是一篇角度很新颖的文章。他从月夜入手,从鲁迅小说、散文、日记里,搜索文字,谈论鲁迅的喜爱月夜,和上海前后的变化,力图揭示鲁迅感伤的一面,看到鲁迅精神上阴润的一面、柔弱的一面。文章角度奇特,很有意思。我有时想,王彬彬骨子里是不安心做一位评论家的,他很多时候是按创作来写评论的。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书写,可能也有一种对当代文学的失望吧。
本文主要讨论王彬彬的当代文学评论,他的鲁迅作品评论不做重点研究对象。
一、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文坛三户》一书里,王彬彬对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批评。既有翔实的资料梳理,也有深刻的思想批判。他认为:“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位是基本准确的。然后分三章,用了二十多万字详细分析了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存在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作为文学史家的王彬彬体现了自己优秀的史家意识,把他们的创作放到历史长河里,进行纵向梳理,比如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脉络及变迁,都极其到位。严家炎等人认为金庸小说有一种“现代精神”,王彬彬做了详细分析,否定了这个观点,指出他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文化工业下的类型小说、通俗小说而已。而且认为“所谓‘侠客文化与历史上的‘流氓文化往往难分彼此”⑧。
对金庸的崇拜和热捧,是当代文坛的一件趣事,也是闹剧。我曾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能说是武侠小说的优秀之作,最多就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如今很多学者想把他推为文学的大师。王彬彬《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就专门反驳徐岱、严家炎等学者的观点,是一篇杂文式的评论。严家炎晚年热捧金庸,无论如何都可以算作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王彬彬此文专就他提出的“金庸热”四大特点展开批驳:一、持续时间长,二、覆盖地域广,三、读者文化跨度很大,四、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文章有理有节,论证严密,调皮幽默,颇具力量。其实,严格地说,严家炎为金庸辩护而提出的这四点,都无法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相反,只是证明了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而已。而就这四点而言,他也远远没有超过罗琳的《哈利·波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罗琳等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作品的畅销、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而成为世界大师,他们的作品也还是限制在通俗文化之内。因此,也就可以看出严家炎先生的童真与可爱之处,完全是一个小孩的态度,不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样子。至于他提出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似乎颇有力量,我很期待他从文本角度展开深入分析,结果没有,却只提供一个证据,就是邓小平和蒋经国都爱读金庸的小说,由此来论证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真让人哭笑不得。王彬彬批评说:“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最美味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⑨可谓一针见血。
在论述王朔小说时,王彬彬提出了他的小说创作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似、相通性,这倒是颇具新意。然后从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小说内容、小说结构等方面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尤其对王朔与大院文化的讨论,很有见地。其中对平民文化、贫民文化与痞子文化的辨析,不乏思想的冲击力。倘若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深度浸染,是写不出这样精彩、透彻的文字的。
《“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就是一篇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互动结合得很好的论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文本的解读,讨论了“样板戏”的不断改和不能改,很有意思,颇富见识。尤其提出的“样板戏”的两个铁则:一、突出武装斗争、强调地下工作只能是对武装斗争的配合;二、强化和突出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解释一切,足见作者的史识。
作为一名1962年生人,王彬彬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情有独钟(当然不是对作品,是對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多次谈及,而且每次谈,都能自出机杼,言人之未言。《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就是一篇代表作。那个时代,以“阶级情”取代“骨肉情”,是重大的政治方针,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但王彬彬发现:
然后,有趣的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当“骨肉情”取代了“阶级情”后,自身又往往以“骨肉情”的名目出现。例如,“阶级兄弟”这说法,曾经十分流行。而“阶级兄弟”这种称谓,就很耐人寻味。这就让“阶级情”具有了“骨肉情”的名目。《红灯记》中的三代人,本无丝毫血缘关系,但却又以“一家三代”的名目出现。那个时代竭力歌颂的“阶级情”,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江湖情”的变种,或者说,是政治化的“江湖情”;而“江湖情”重于“骨肉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谙熟,没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要发现这个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此文也通过一系列文本的细读,如《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伤痕》等,详细分析了“阶级情”“骨肉情”的变化过程,也反思了人伦、良知的价值。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杰作。《1976—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梳理这两年间文艺界的政治修辞、话语方式。主要讨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拨乱反正的微妙处,既要维护毛泽东和“两个批示”,又要否定“文革”,回到“十七年”,其间的困难和睁眼说瞎话,都颇让人感慨。
《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角度特新,他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谈起,首先讨论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写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组织打狗队的故事。“从这些打狗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极权统治所赖以存在的某种基础。”22并结合《苦菜花》《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和胡发云的小说关于打狗的描写,对此做了深度思考。看似一个很小的小说细节,却谈出了大问题。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等收录了他的历史随笔,包括历史论文,其中不乏产生影响的名篇,很多是《钟山》的专栏文字。我觉得也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评论,很多谈史,也是谈文,但由于篇幅有限,容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三、文本细读的成与败
文本细读,必须建立在艺术直觉之下。没有艺术直觉,文本细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那就无法真正进入文学了。格非曾说过,写作这个职业,最高的禀赋是敏感性。一个不敏感的人是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去阅读的。我觉得这个“写作”应该包括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是需要敏感性的。
文本细读,首先需要的是评论者的艺术直觉,或者审美直觉。没有这个东西,一切免谈。我们很难对文学创作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一部作品的好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能够做好文本细读?另外,文本细读,也是一项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术活。
纳博科夫在美国大学讲授文学时,要求学生“一字一句地读”23,他的教学也是如此,“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24。他不太在乎小说的思想、人情云云,他认为小说的魔力在小说本身。而这种魔力是通过细节获得的。他说:“在阅读时,我们应当留意和把玩细节。”25“在我的教学岁月里,我努力为文学学生提供有关细节的准确信息,有关细节组合的准确信息,正是这些细节的组合才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效果,否则一本书就会死气沉沉。就此而言,一般思想无足轻重。”26
“为了阐释《尤利西斯》,他查阅了都柏林的街区地图,并在黑板上详细描绘了斯蒂芬和布卢姆有所交叉的漫游线路图,要他的学生加以掌握。为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在黑板上勾勒出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那只昆虫的形状,他说不是蟑螂,而是甲虫。”27
王彬彬是安徽人,长期居住、工作在南京,熟悉江南作家,他的很多评论是针对江苏作家的。他对本土作家有一种青睐,也有一种提携。《高晓声的鱼水情》,他说了,这里的“鱼水情”,是指高晓声对鱼和水的感情。这篇文章很特别,洋洋洒洒上万字,都在谈高晓声小说、散文中的关于鱼和水的描写。鱼、水对南方作家来说是最熟悉的了,而对于北方的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我小时候的那条家乡的河,里面只有很小的鱼,那是不能吃的。太小了。就我个人而言,对鱼、水似乎不怎么关注。所以,对这篇评论就感觉很奇特。
王彬彬认为,沈从文写水,写得很好,汪曾祺也善于写水。但写鱼恐怕没有人超过高晓声。他说:“可以说,高晓声是把水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28然后,全文旁征博引,论述高晓声的鱼、水描写。读来真是过瘾,也让我这个北方人懂得了很多道理,认识了很多鱼。
王彬彬是语言至上主义者。他说:“读小说,我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如果语言不好,如果语言没有特别的美感,如果语言对我没有吸引力,什么结构上的突破,什么思想上的创新,都是哄骗人的东西。”29他讨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依然是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我觉得语言肯定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语言好并一定就标明作品好。对于诗歌、散文来说,对语言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语言并不是唯一条件,似乎语言不好,小说就一定不好。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杰作,语言肯定要好,但像《红楼梦》那样语言绝佳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彬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切入进行当代文学的文本研究,也颇有贡献。
《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篇近似于批评宣言的文章。王彬彬在这篇文章里说:“语言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唯一正道。”他反对那种学院派的生搬硬套各种理论的所谓文学批评,他称之为“框架批评家”。这种对语言的高度认可,是有道理的。作为文学批评,不涉及语言,或者对语言没有敏感,是不够格的批评家。但是,说实话,一、当代作家的作品,有多少经得起那种严格的语言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已成经典的文学作品,是经得起语言分析的。但大多数当代作品是不配的。二、即便是经典作品,可以做语言分析,也可以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比如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研究鲁迅的思想,应该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不是一个语言所能包括的。三、语言这东西,有时候能感觉到,但谈论起来确有难度。王彬彬也说:“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的先决条件,对此我深信不疑。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但对语言的敏感,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仅有后天的努力是远远不成的,先天的禀赋起着很大的作用。”30文学语言,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有时候,“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但又是“不足与外人道也”。他在《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一书里,对鲁迅、汪曾祺等人的语言分析,就让人欣然忘食,但对有些作家,如毕飞宇、曹乃谦、鲁敏、余一鸣等的作品进行的语言分析,就不是很精彩。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还经不起语言分析,他们没有到那个层次。
不过,语言分析确实是王彬彬文学评论的重要特色,不得不谈。这一点,应该说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还有新批评的影响。我感觉,他的语文水平还真是过硬,他对字词、语法、修辞等的功力,当代文坛能及者不多也。他认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形式的写作,都应该终身就有一种语文意识,应该不懈地追求把话写得文理通顺,把意思表达得明白准确。”31
纳博科夫在美国时期,虽然被迫用英语写作,而且也非常成功。但他骨子里还是渴望用母语写作。他经常有一种用俄语创作的冲动,他说:“我是多么想用俄语写一本书啊。”32因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他的语言,他使用的语言,那才是文学的根本。为什么那些非常杰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几乎无法翻译,或最不可翻译?因为他们把那种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深懂那门语言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妙不可言的微妙、精妙之处。“果戈理是通过微妙的语言效果来成就他怪诞的倾斜和突然的变焦的,体味其神奇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学习俄语。纳博科夫正确地、惋惜地指出,此前所有的果戈理英译本都将那些怪诞之处抹平了,或者干脆消灭了。”为此,纳博科夫摘译了果戈理的部分文字,“英语世界的读者有些困惑,何以俄国人会高度推崇果戈理,纳博科夫的这些选段至今仍是唯一可以说服这些读者的材料”33。“他准备穷形尽相地研究天工,但不想条分缕析地对待凡品——他不想,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创造出佳构来。”34
对于王彬彬的文本细读来说,挑战的对象不是他的文本细读能力,而是他研读的那些文本,有多少经得起或值得他去细读。《孙犁的意义》对孙犁小说语言的分析很细致,引用了很多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真的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一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分析,颇具只眼。“赵树理的语言又让人感到有些质木、寒素、枯索,让人感到不够丰盈、蕴藉,不够灵动、温润。”35因为赵树理对语言的“大众化”追求,“不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一种功利追求”36。对此,王彬彬把赵树理的文字与孙犁的作了对比,孙犁的文字诗意,有泥土气息,但赵树理的太俭省,闲笔太少。
《“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是一篇关于语言分析的杰作。文章主要针对汪曾祺写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做了详细的语言分析。他首先提出汪曾祺的创作除了沈从文,也深受鲁迅影响,“我以为,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在情感、思想的意义上,汪曾祺无疑与沈从文更接近,然而,在‘文体的意义上,在遣词造句的意义上,汪曾祺可谓深受鲁迅影响。”37这个观点真是新人耳目,发人之未发。且看他如何论证?后面,王彬彬从几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证,一、特短单句的运用,尤其是奇特的句号使用法;二、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三、将单句省略到只剩单词或短语;四、繁复和口语化情境;五、虚拟对话。每一节都有文本分析,有理有据,读了之后只有信服。结论是:《羊舍一夕》实在是“十七年”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疏忽它是不应该的。
《钱钟书对比喻的研究和运用——以《围城》为例》,是一篇很有趣的评论,显示了王彬彬的机趣和独具只眼。尤其说钱钟书《围城》里的比喻使用表现了一种“书卷化的刻薄”,真是恰到好处,让人忍俊不禁。文章中的文本细读,也是趣味有加,而且极为到位。王彬彬提出文学批评的修辞艺术研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从人称的变化,分析这篇散文名作的小说手法,也是颇有眼力、新人耳目的。《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那种对阿城小说的语言分析之耐心,真是少见。在王彬彬看来,阿城小说,尤其“三王”,是应该能够成为经典的。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是一篇很有质量的关于语言分析的评论。因为分析的对象是鲁迅先生的名作《野草》,是绝对经得起文本细读,经得起语言细读的。文章第二部分对鲁迅文中虚词的分析,很有眼光,读之让人收获良多。比如: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为了与前面的“于是”形成对应,第二个“于是”也许是必要的。但按通常的语感,这“于是”应在“天地”这主语之后。将“于是”置于“变色”之前,實在是异于常规的做法,但语意也就有了奇崛之感,同样也将一句很普通的句子变得让人一读难忘。
……然后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
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38
王彬彬的语言细读功夫在这里展现无余,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后面他对鲁迅《野草》的“矛盾修辞”如“彷徨于无地”“无词的言语”等,还有单音词与三音词,做了详细分析,都很有见地。而在那些当代作家,包括江苏作家的语言细读文章里,就明显有一点蛟龙困小河的感觉。如《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很长的一篇论文,有时就感觉到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王彬彬对高晓声情有独钟,为他写了好多评论,都是好评有加,如《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这些文章角度独特,甚至可以说比较刁钻,读来颇为有趣,甚至让人读得兴趣盎然。但读完了,总觉得高晓声的小说语言没有他说得那么好。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那语言真是神妙,结果王彬彬却评价不高。《冷眼看“张热”》里对张爱玲的批评,我也觉得有点过分,如“张爱玲所缺失的,不正是一种深邃的艺术情怀,一种强烈的人文激情么?因为缺失艺术情怀与人文激情,所以便玩弄技巧,所以便只有‘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所以便终于没有更大的艺术成就”39。这个结论,我不是很能认可。张爱玲当然算不得伟大,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绝对当得起杰出,能及的恐怕不多。她的小说不是“玩弄技巧”,里面是有很深的東西的。我曾经说,张爱玲小说的黑暗、绝望,是可以与鲁迅作品一比的。40
纳博科夫说:“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但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伟大的道德,都必须被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语言。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王彬彬对小说语言的关注,是让我们佩服的。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语言的分析,他论述着它们的艺术高度。
2018年8月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
2019年8月16日改定
【注释】
①②③④⑤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1、2、4、104页。
⑥杨光祖:《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
⑦⑧⑩11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第3、109、3、3页。
⑨1415162237王彬彬:《王彬彬文学评论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第68、24、36、42、203、138页。
121318202131王彬彬:《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03、123、47、44、52、297页。
17杨光祖:《〈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19[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05,第10页。
2324252627323334[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 美国时期》(上),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87、188、188、188、189-190、54、58-59、194页。
28王彬彬:《高晓声的鱼水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930353638王彬彬:《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72、363-364、62、55、9页。
39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62页。
40杨光祖:《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天津文学》2012年第11期。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