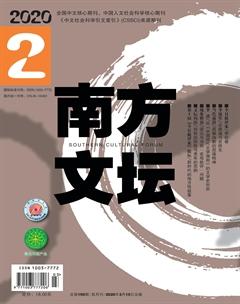一块特殊的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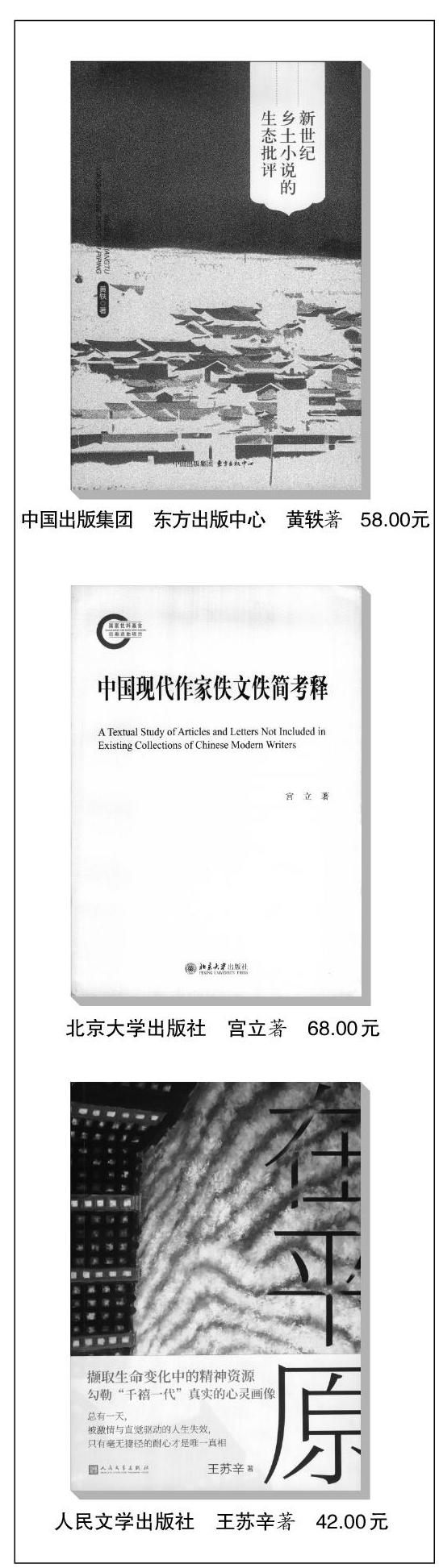
一
朱大可并非职业小说家,学者是其第一身份。他近期出人意料地出版的小说,都跟中国古代神话或历史传说有关。其中的“古事记”系列《字造》《神镜》《麒麟》,分别取材于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送麟。这批小说虽然采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但在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或动物)身上体现更多的,却是现代情绪。对神话传说的如此处理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但和《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辛辣甚至有意的“油滑”①大不相同,朱大可意欲用现代人的情感、欲望跟神话传说中或实或虚的人物相沟通,以人性为材料,去填补神话中几乎被丢弃殆尽的细节。所以,这三部小说在很多细节中,都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诗意。比如《字造》的开篇,当男孩颉躺在森林里做梦的时候,“他看见自己以鱼的姿势在水里游走,向一切水中的事物致敬”②。“看见自己”即是一种自我分裂式的现代情绪,因为现代主义境域中的视觉不仅要看见某物(即看—物或有所看),还需看见自己看见某物的那个看见本身(即看—看)③。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在现代性放肆游走的地方,“看的眼睛变成了被看的眼睛,并且视觉变成了一种自己看见”的神秘状态④。再比如,《神镜》中的“盗镜者”——镜鼠王——面对护镜师李阿的质问,淡然道:“无论偷盗还是守护,都是同一种迷恋。”⑤不从价值判断而从人性的欲望中提炼对偷盗行为的解析,亦是一种对人性剖析的现代手段,尼采对此所论甚明:“我完完全全是肉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肉体上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肉体的一种工具。”⑥
“古事记”系列小说的现代手法一个显著的体现就在于对欲望的处理上。在儒家统治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欲望往往以负面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私人欲望需要被包装成家国理想、仁者大爱等,才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文学创作,就更不用说罢黜欲望的道家、倡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⑦的佛家了。而小说《字造》中的造字大神颉的私人欲望却以美丽、高贵的形象出现。这个堪称欲望之镜像的美好形象,就是颉的妻子“妙”。妙为颉所创造,正是颉情欲的具象化(小说中,颉用自己的精液在龟甲上涂写出“妙”字)。朱大可没有用任何负面的手法描写颉的情欲具象,相反,他将妙塑造成整部小说中最完美、纯洁的形象——这简直是对颉情欲的礼赞;虽然颉在被沮诵打败,惶惶如丧家之犬时,还曾“怅然想到,看哪,你这没有灵魂的东西,为了自己的女人,出卖了这个世界”⑧。但终究,还是他的欲望成为战胜沮诵、重建家园的根本动力。朱大可对欲望做如此这般的处理,意在展现他对人类历史发展之观察的一个侧面:无论看似辉煌的史书对历史事件作出怎样华丽、精细的包装,欲望始终是人类的原始驱动力。这个被朱大可观察到的侧面或许暗合尼采的疯言疯语:“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⑨虽然这三部系列小说都有神话故事需要具备的完整性甚至不乏曲折的情节,但跳出故事情节、转向心理描写和细节分析的手法随处可见,朱大可似乎并不急于将故事中最扣人心弦的转折交到读者眼前,这正如他所说,“在我这里,写作只是一种存在的游戏,它没有像人们所宣称的那么伟大。小说写作也是如此,它是语词的游戏,需要一些公开和秘密的手法,以及一些推动文字的记忆和经验。仅此而已”⑩。这一系列小说就像朱大可写在学术边缘的文字,它们更多是作为朱大可研究中国神话之外,对其神话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生动补充;仔细观察,很容易从小说中窥见朱大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仓颉是在伏羲创八卦、神农结绳记事的基础之上造出汉字11;此外,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等古籍中也有仓颉的相关记载。从这些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可以了解到,传说中的仓颉是黄帝的左史,相貌异于常人,有四只眼睛,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察而创造了文字。但这些古籍对仓颉的记载都很简短,并且缺乏中国历代史书对人物家世生平进行描述的惯例,充分说明仓颉的存在像文字的起源一般神秘不可确定。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仓颉这个人?这是很多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都会碰到的问题。袁珂先生认为,“在原始时代,每种文物的创造发明,都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世纪,多少人的钻研探索、劳动实践,然后才能由极简单粗糙到逐步细致完善起来,绝非某个人一手一足、一朝一夕之功。把种种创造发明都集中在某些圣主贤臣的身上,这本身就是神话,也是传说”12。跟袁珂先生的看法相似,朱大可也认为负责缔造文字的,并非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祭司集团,仓颉正是这个负责缔造文字的祭司集团的官员13。在查阅历史典籍的过程中,朱大可发现了一个让他感兴趣的问题:“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14从小说《字造》对沮诵形象详尽的塑造可以猜测,正是这个充满悬疑的问题激发了朱大可的创作。
《字造》中的仓颉在被邪恶的女弟子打败之后的逃亡路途中,“身心俱疲地说:‘我……恐怕已经回不去了。”15对华夏神话稍有了解的读者在读到这个情节时,可能并不会太担心颉此后的命运——我们已经从如今的现实得知,颉一定会打败邪恶的女弟子,将人类社会带到一个有序的历史阶段。但这个不算引人注目的情节,却很有可能是朱大可对华夏文明作出的一个浓缩性的总结,即对华夏文明源头中流氓意涵的深刻认知。
朱大可所说的“流氓”,乃取其最原始的语义,跟如今这个词人人喊打的内涵迥然有别。朱大可明确地指出:“流氓指称着所有那些被迫丧失土地家园的人,而在这个词语的靠后一端,它将要成为丧失灵魂家园的游戏者的一个新的称谓。”16小说《字造》的主人公颉,在十四岁那年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乡”。童年时期一直陪伴身边的表妹和外婆相继离世,短暂的、桃花源一般无忧无虑的生活至此宣告结束。虽然他获得了以字创世的神力,但也只是一个被桃花源抛弃的忧郁灵魂。他从一个跟这个世界无限友好、内心充满巨大喜悦的小男孩,变成了有些傲慢的造物主,他用字造出城墙、宫殿、庙宇以及一个完整的城邦需要的各类事物,还听从内心的欲望为自己造出了一个美丽的伴侣,完成了从“失乡”到“获乡”的转换过程17。但他获得的这个“乡”,已然不复从前桃花源的模样,而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山寨版的神性世界:用字造出来的新世界不像神性世界(桃花源)一般完美无缺,它具有先天的缺陷,朱大可借用结绳记事派首领麻结之口,道出了字造世界的深层危险:“它(颉发明的文字)为事物下了定义,导致事物在语义上的固化。一旦形成大量坏字,就会败坏世人的道德。而结绳记事则没有这种危险。”18这句深谋远虑的话准确地预言到了千万年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语言拜物教”19,一眼看穿了字造世界中人类生活和话语的密切关系。回顾一下古往今来朝代更替、战争烈火,不难发现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事件无一不充斥着话语的热切参与。朱大可从“流氓”的原始语义出发,对这个先天不足的字造世界有过严厉的批判:“至高无上的权力,使流氓完全打开了自身,也就是打开了那些在苦难的流走中滋养起来的黑暗伦理”20。这份黑暗伦理被小说《字造》具象化为一名叫沮诵的女子,她是颉创造的光明世界中的黑暗部分,有如太阳黑子。她美丽却残忍,具备邪恶的字造天賦,因不被她的老师颉喜爱而心怀怨恨。心理扭曲的沮诵造出了一系列暗黑的字,终于被颉驱逐出青丘国,成为朱大可笔下典型的“第二代流氓——丧国者”21。
丧国者沮诵的复仇之路布满阴谋、暴力和淫乱,跟她造出的暗黑系文字十分匹配。她来到了歧舌国,跟野心勃勃的国王勾搭成奸,用自己的字造天赋将歧舌国打造成一个有实力与青丘国一决高下的国家。沮诵用阴谋将颉骗到歧舌国,囚禁了颉的妻子妙作为要挟,颉被迫为歧舌国造出“超级黑暗系文字”——“魔”。沮诵凭借“魔”的强大力量,打败青丘国;颉在流亡途中造出了能与“魔”相抗衡,象征正义的“龙”字,终于实现家国复兴,并存封了沮诵创造的坏字——至此,字造的故事接近完结,只是在故事的最后,颉的妻子妙在临死之前突然违背颉让她毁掉坏字的遗嘱,留下一个让人悬心的世界——流氓的语义在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变得十分牢固,小说用具象化的方式,书写了第一代流氓“丧地者”和第二代流氓“丧国者”的诞生。22
三
如果说《字造》书写的是家园重建,《神镜》讲述的则是桃花源的破灭:铸镜大师窦少卿得到日神少昊的启示,造出能通往彼岸世界的神镜。镜中的彼岸世界就是桃花源的另一种称呼。小说中说到了彼岸世界跟桃花源的渊源,陶潜是第一个记录彼岸世界的镜主,但他很快便受到了惩罚,因为据说“缄默是所有镜主必须遵守的共同原则”23。朱大可似乎也在遵循这一原则,他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对彼岸世界做出像样的描写,顶多只有一些笼统的侧面描述,越发显出彼岸世界(桃花源)缥缈不可捉摸的特性。神镜是往来彼岸世界的出入口,是连接现实世界和桃花源的神秘通道,它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书写对象,不仅因为自带神性,更因其珍贵的特性指出了彼岸世界的难以把握:“尽管有一条走廊(桃花溪)可以抵达,但鉴于两种时间的相对错动,走廊的位置在空间上是飘移不定的,这就最终导致我们无法两度进入。因此,陶渊明试图表明,在人与乌托邦的疏隔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乌托邦是否存在,而是我们能否找到通向乌托邦的神秘道路,抑或有关这种道路的线索。”24对桃花源(或名“彼岸世界”或名“乌托邦”)的追逐可以说是全世界不同国别不同种族的人类相通的梦想,“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内拉《太阳城》、培根《大西洋岛》,从大同世界到王道乐土到桃花源到太虚幻境到太平天国,古今中外乌托邦方案不胜枚举”25。
所以,在这篇小说中,神镜自然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所有人都默认通过神镜抵达的彼岸世界是美好的。然而,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彼岸世界出现了难以形容的动乱:从神镜中掉出死老鼠、婴儿尸体、新鲜而陌生的女尸……26长久以来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逃遁的行为突然失效了,神镜中的彼岸世界变成了一个和此岸世界没有区别的“黑乌托邦”。据朱大可解释,如果以离弃和归入空间作为标尺,那么“黑乌托邦”就是一个从黑到黑的逃遁模式,它意味着逃亡之人从非人的黑暗境遇中出走,但最终又重新归入黑暗,这是所有逃亡运动中最令人悲痛的事件,逃亡也因此被消解了意义27,“流氓”一词的语义在这里再次得到了加固。
其实在小说中,作者早就暗示过这个局面——护镜者李阿发现他最美丽的雇主苏娥从神镜中走出以后,身体出现左右反转的情况,而这并非孤立的现象,“所有出镜者的身体和服装,都具有某种显著的镜像特征——左右反转”28。——一个跟现实世界呈现镜像特征的桃花源,又能光明到哪里去呢?桃花源最终只能存在于纸上,它的特性注定它“以意念和图书为家,或者,只能被明亮的言辞所呈示”29。一旦被尘世中人捕获,就是它灰飞烟灭之际,桃源梦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小说的结尾,造镜者窦少卿、镜主苏娥、护镜者李阿纷纷离世,只剩下李阿那个亦敌亦友的盗镜者镜鼠王活着,他伤感地意识到,“大师们在纷纷离去,铜镜的黄金时代已经凋谢……镜子的幻象已经失效,而他要去改变的,是那热火朝天的现实”30。这正如朱大可在谈到乌托邦时说到的那样:“伟大的先知、光荣的梦想、永恒的逃亡,所有这些辉煌的事物最终都要黯淡下去,被黑暗的结构所吞没。离弃与皈依的循环就是如此。”31
“古事记”系列的第三部《麒麟》,以一对被认为是瑞兽麒麟(实为长颈鹿)的所见所闻为视角,展开了一场对明朝皇宫内权力游戏的书写:郑和下西洋带回一只产自非洲的雌性长颈鹿,并把她当成神兽献给朱棣,与朱棣皇宫中已有的一只雄性长颈鹿组成华夏神话中的瑞兽“麒麟”(雄性长颈鹿为麒,雌性长颈鹿为麟),以此作为朱棣权力合法性的证明。命途多舛的长颈鹿夫妇,一路颠簸从非洲草原被运到明朝皇宫,见证了这场以朱棣为主角的权力游戏的残忍和荒诞。非法篡位的朱棣一生都活在权力非法的阴影之中,制造再多的杀戮也不能缓解这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又催生出更多的杀戮。对于朱棣而言,屠杀和收集女人是两种完全同构的欲望,但“杀戮的快感犹如射精,尽管高潮汹涌,却极其短暂,而在每次屠杀之后,是更大的空虚,必须靠另一次屠杀填补”32。密集而短暂的快感很快掏空了朱棣的一切,纵然身在权力宝座的顶端,他依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33。快感之于人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实更多俗不可耐的性质,也充斥着人为的伪造。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制造了一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有关恶的快感”34。且不论快感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否拥有如此卓越的地位,单就小说《麒麟》而言,快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帝王对快感的追求很容易转化为对权力的极端欲望,而对权力的彰显需要通过对权力符号的建构。尽管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长颈鹿跟权力符号没有半点关系,但聪明的郑和却能将他们化作华夏民族想象中的瑞兽麒麟,参与权力符号的建构。
小说中的这对长颈鹿是一种敏锐又心怀悲悯的动物,他们能准确感受人的情绪,還能看见游荡在各处的亡灵,他们经历种种曲折终于在朱棣的皇宫中团聚,将在万邦来朝的隆重典礼上亮相。但在亮相的当天,他们在亡灵的戏弄下,以当众交配的羞耻方式嘲笑了朱棣的帝国,引发了帝国官员关于如何阐释这场交配的争论,最后还是朱棣一锤定音:“麒麟是至高无上的神兽,他们的作为,为的是神兽的繁衍,完全源自天意,用以向天下证明大明江山之不可摇撼。”35牵强的说辞表面上是为了掩饰神兽亵渎圣典的尴尬举动,实际上暴露了权力游戏中帝王最企图掩饰的部分——对快感的追逐。只有很早之前就被剥夺了身体快感权利的郑和才能清醒地说出,“麒麟在讽刺世人纵欲过度,损坏了天理。他们在示范我们的丑行。你要懂得,欲望是人最大的弱点。没有它,就没有了弱点,才能成就你的伟业,让你成为一个无欲的英雄”36。这条不适宜推广的建议,倒是碰巧指示了一条逃遁之路:身处在被欲望侵蚀的污浊世界,如果既无力改变也不想深陷其中,那么就让自己无欲无求,逃遁到较为纯净的空间(如深山、寺庙等,即朱大可所说的“灰乌托邦”)——“灰乌托邦正是这样一种痛切愿望的产物。它要尽其所能地维护住一个缺陷的好社会的状态,以便它既能被操作,又不至于沦陷为存在的地狱。这样的灰乌托邦曾经大量地实存于世界史中,像分布于时间原野上的河流与湖泊……尽管灰乌托邦弥漫着大量的尘土,对它的敬意却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人只要从污浊的名利之场中隐退和依山而居,他就能够成为‘仙人,享用一种非凡的生活。”37小说的最后,郑和的小随从马欢在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之后落发为僧,应该就是参透了郑和的隐秘指示,“流氓”一词的语义得以圆满而肃穆。
四
朱大可在《华夏上古神系》的后记中说到,“本书的目标,是试图穿越过历史叙事的铁幕,以一种跨文化空间的视野,借助全球文明的光亮,去探明中国神话的初始轮廓,而鉴于上古典籍的多次燔毁,以及两汉篡经运动制造的学术迷津,任何针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势必会引发更强烈的挫败感。人的穿越式触摸,只能抵达早期第二代神话的时段,而其中20位神祇的拼图式肖像,也只能停留在粗线条的素描阶段”38。作为一部体量庞大的学术研究著作,在现代学术规范下,去伪存真的科学思维是它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39。在科学思维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研究,天然就跟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而当下的很多学术研究更是因现实的种种影响,索性躲进象牙塔与生活彻底隔绝:“对于现实的无奈使得一些人只能选择逃避,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进学术的象牙塔中通过想象构筑起一道虚幻而又美丽的精神屏障。最终,对于学术的追求演变为对某种身份镜像的自我迷恋。种种原因使得学术——这个本来就是人的现实活动的精神表现——被异化为某种超越现实的绝对精神,而人反而成了对其顶礼膜拜的忠实信徒。一切仿佛都颠倒过来了。学术成了世俗世界中的另一种神学。”40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距离越来越远的当下,学者朱大可则选择“用不同的体裁(随笔、文论、学术专著和小说)解构它们(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和历史叙事等方面),打碎被谬见固化的硬壳,粉碎它们的僵硬形态,迫使其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41。马克思·韦伯认为,“科学的进步是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42。人类理智化的过程,就是韦伯所谓的“祛魅”的过程。如果按照韦伯的看法,作为一名专注于学术研究的资深学者,朱大可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大致可以被看作对其研究对象去伪存真的“祛魅”过程。而在面对华夏上古神系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时,因其时间太过久远以及资料的稀缺,很难做到确切的论证。“祛魅”的被迫失败,留下了神祇看不清真相的粗线条素描肖像;如何让这些粗线条细化,变成丰满而又不会离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的样子,朱大可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答案。
通过对“古事记”系列小说的粗略解读不难看出,这三部小说不单是对神话传说的现代演绎,更重要的是它们投射了朱大可的学术思想,并跟他的学术著作形成互文关系——这三部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具备或代表着不同程度的流氓精神。“流氓”是朱大可學术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有三个阶段的表现形态,分别为:丧地者、丧国者和丧本者。第一代流氓(丧地者)的代表人物,是神话中的“禹”。他发现自身与土地的分离,并将这种分离“引向历史的表面,使它成为一个种族总动员的依据”43。朱大可认为,正是这源自分离的痛苦,让第一代流氓“总是趋向于失乡的反面,也就是趋向于对土地家园的热烈拥抱”44,所以,他们制造出土地家园的一个极端形态——国家。但这个过程并非单向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循环状态:国家是丧地者建立起来的家园,同时也是让他们迅速腐化的精神墓室,为了捍卫这个家园,流氓开始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打开了那些在苦难的流走中滋养起来的黑暗伦理”45,至此,丧地者的反叛和征服宣告破产。朱大可总结道:“在某种意义上,流氓就是不断趋近于其反面的人,他的脚步尽管遍及广阔的空间,却不能与土地达成真正的和解。”46小说《字造》的结尾,以隐喻的方式预示了这样的结果:黑暗伦理早已存在于看似光明的世界中,“那些坏字躲藏在人间,被走私贩卖和复写,像风一样四下传播,变得不可阻挡。颉告诉妙,文字是龙与魔的复合体,它推动文明也埋下人类灭亡的种子。即便是龙凤之类的光明系正字,都无法避免暗黑化的命运”47。就这样,第一代流氓“实现了土地征服之后,国家(王朝)就开始诞生和衰灭的无限循环”48。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第二代流氓诞生了。他们是对国家怀有刻骨铭心之仇恨的反叛者,是走投无路的失国者。他们像《字造》中的沮诵一样,从自己的国家逃亡。但和小说化的纯粹邪恶形象不同,朱大可认为通过正义话语的分裂,在第二代流氓丧国者中有一小部分成为以侠士的名义诞生的流氓英雄,他们之中有四处奔走讲学、身兼流氓和圣人双重属性的孔子;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严密的流氓政党的墨子;有孤身刺秦,让死亡的短歌升华到文学层面的荆轲;还有将流氓诗学推向高潮的李白……这一小部分人身体力行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流氓英雄美学和暴力美学,国家的极权就是滋养流氓暴力的养分。《神镜》中的铸镜师窦少卿和护镜师李阿,即是朱大可笔下流氓英雄的典型。窦少卿铸造的神镜和李阿藏匿神镜的芦花津共同构成了他们的“黑暗王国”——朱大可认为,“对于一个流氓来说,他的黑暗王国就是他的光明。其中,黑暗不过是指它的政治隐匿性而已,而光明则是无比实在的,它照亮了一群孤苦无助者的生活”49。
第三代流氓(丧本者)的出现,是流氓英雄时代终结的标记。他们的两极分别是隐士和无赖。但无论是无赖,还是隐士,都跟他们所寄居的时代格格不入,是“流氓英雄的内在的敌人。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的倾听。他们是耳目俱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做出判决”50。他们是流氓进化到当代的终极形态,不光与国家分离,更与自身分离。朱大可认为,丧本者的出现,“基于一种与国家(有时是整个人类语境)关系的严重的精神性对抗,人的言说从他的本体中漂流了出去。人借此而成为他自己的流氓”51。第三代流氓(丧本者)的形象在小说《麒麟》中以马欢的身份出现,这个郑和的小随从最终的归宿充分切合了一个丧本者的结局:将自己的痕迹从时代中彻底抹去,隐匿在深山的寺院中。丧本者是古代的隐士,是当代的颓废主义者,他们是当代社会存在数量众多的流氓品种——“颓废主义者坚决拒绝他的时代,他只愿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和观察者……他们是一种特殊的隐士:他不是居住在终南之巅或渭水之滨,而是穿行在众人之中。”52至此,从古到今流氓谱系的发展得到了大致呈现。
朱大可对流氓的精神分析贯穿在“古事记”系列小说中,成为串联三部小说的暗线,更兼近二十年对华夏神话的研究,使这三部小说带有学者特有的审慎。“古事记”系列小说的创作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虚构,它们有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背景,在已无法得知历史的真实全貌之时,能运用到的只有在现有条件下的合理想象。这种想象跟天马行空的胡乱猜测不同,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对人性中一些亘古不变的特性的捕捉,作出合乎逻辑的想象性推测。可以说,“古事记”系列小说就是在朱大可用学术“祛魅”之后又“增魅”的一个手段,但却不是减一加一的无效动作,而是拨开作伪的迷雾,努力还原真实的轮廓之后再为其上色、丰富的行为。在中国古典时期,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在记录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带有个人印记的创作,大概是一种并不会引起争议的行为,反而会因作者自身的魅力增添传记的魅力。据张大春考察,《史记》中的一些片段就采用了小说笔法53,这种写法让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包裹在一层柔软的细节外衣之下,营造出近距离的现场感。到了唐代,甚至有了对小说史传渊源、史补功能的明确界定。有学者认为,“以史学家为主体形成的对小说文体‘史补功能的界定,便逐步成为中国正统文化,或者说是大传统文化对小说文体的基本认知。在此认知笼罩下,无论是小说作家,还是小说评论家,均始终难以摆脱面对史传的卑微心理,因而不论是对小说作品题材内容的选择、功能的论定,还是对于小说作品评价标准的选取,都出现了向史家所期望的‘史补角度的有意靠拢”54。小说有如此众多的功能,在中国古典时期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丛残小语”(桓谭语)。虽然“古事记”小说也有类似于史补的功能,但与古典时期小说和史传的地位悬殊不同,它们是朱大可学术思想体系当中一块特殊的拼图,一些组成朱大可学术体系的活泼材料。它们未必是这个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却是让人眼前一亮、饶有趣味的那部分。如果将朱大可的学术著作看作一种公共写作,他的小说则更具有私人化的性质。在一个访谈中,朱大可坦言:“神话故事仿佛是我内在梦想的一个外在映射……文学对我来讲是一种乡愁,我回到那个年代,梳理那些历史的神话,通过这种写作来疗愈我自己的灵魂。”55私人化绝不意味着重要性的减少,朱大可的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其思想的体现,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解释和重现让作者关注的问题,并无高下之分。在专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创作和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它们的相通之处。朱大可的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它们可以如此水乳交融地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们以各美其美为方式,最终达致美美与共的境地。
2018年10月21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注释】
①汪卫东认为,虽然鲁迅对“油滑”似有不满,但“油滑”与鲁迅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是解开《故事新编》之谜甚至鲁迅晚年思想之谜的一个绝佳入口。汪卫东《“虚妄”、“油滑”与晚年情怀——〈故事新编〉新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②⑧1314151847朱大可《字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5、102、141-145、142、103、45、123-124页。
③敬文东:《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以欧阳江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
④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等译,漓江出版社,2014,第92页。
⑤23262830朱大可:《神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03、33、132、86、147页。
⑥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7-28页。
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⑨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295页。
⑩朱大可《我跟神奇动物不得不说的故事》,朱大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zdsa.html,2018年10月17日20:05访问。
11《说文解字·序》中提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12袁珂:《中国神话史》,重庆出版社,2007,第80页。
164344454648495051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6期。
17關于“失乡”和“获乡”请参阅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6期。
19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写在前边”中对语言拜物教的定义:“语言拜物教是欧美20世纪的特有产物,是所谓的现代性发展到极致时的表征和装饰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20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6期。
21对于“第二代流氓”,朱大可有这样的解释:“对于国家的刻骨铭心的痛恨,这是滋养反叛者的盛大摇篮。最初的流氓实现了土地征服之后,国家(王朝)就开始诞生和衰灭的无限循环。它们象征着土地家园的最高形态。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国家就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一部毫无出路的历史。只有流氓有限地改变着它的容貌。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从未被思想和学说瓦解过,它的瓦解者只能是流氓。”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6期。
22关于两代流氓“丧地者”和“丧国者”,详见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6期。
24293137朱大可:《逃亡与皈依》,《芙蓉》1999年第1期。
25王康:《俄罗斯启示》,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9,第53页。
27朱大可认为,人类缔造的乌托邦有黑、白、灰三种形式,“黑乌托邦”即跟黑暗的现实世界几乎没有差异的世界。详见朱大可《逃亡与皈依》,《芙蓉》1999年第1期。
32333536朱大可:《麒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11页。
34敬文东:《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黄河》1999年第4期。
38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后记”,东方出版社,2014,第585页。
39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第31页。
40陈海静:《祛魅之后的谦卑与神圣——也谈学术规范问题》,《文艺报》2008年7月10日。
41朱大可:《我跟神奇动物不得不说的故事》,朱大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zdsa.html,2018年10月18日21:02访问。
42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第28页。
52敬文东:《颓废主义者的春天》,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第28页。
53例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死前的片段,即是司马迁运用想象填补的。因为从逻辑推断,时隔两百年的司马迁,是无法得知项羽在军队被汉军歼灭殆尽前对乌江亭长留下的那段话的。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4页。
54何悦玲:《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史学渊源与价值取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5期,2017年9月。
55《朱大可〈古事记〉:文学对我来讲是一种乡愁》,2018年8月6日,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45471479_1001910092018年10月18日21:17分访问。
(崔耕,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