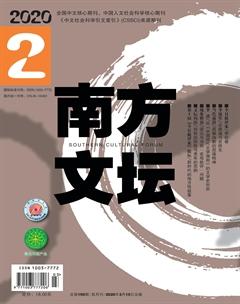今时代何为诗人、诗意?
《练习册》是田湘最新的诗集,但我觉得它的意义却是古老的,这个题目提醒我们:写诗,是一种练习;诗歌需要技艺、变化与成熟。
一、何为诗人?
田湘,1962年生于广西河池,著有诗集多部,有多首颇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沉香诗人”的称号(因诗作《沉香》)。但我也想说,作为“著名诗人”的他,也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在诗人与普通人之间,是真实的田湘。1936年8月23日,鲁迅(1881—1936)去世之前约两个月,重病期间,作一文曰“这也是生活”……这位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感叹“日常生活”之可贵,而许多人,对于名人、文学家,却常常是浪漫化的想象:“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癫,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癫,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癫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癫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癫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不仅是李白,有多少诗人遭遇了我们浪漫化的想象,我们一听说徐志摩,马上就是演员黄磊瘦时代的小分头、《人间四月天》这样的烂电视剧;我们一说起海子,就是他的不会骑自行车、和“四姐妹”的关系、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那些一听说你是诗人就想当然的认为你能喝酒的人,对文学家、对李白们的理解是让人无语的。
田湘走在南宁大街上,我要是不认识他,遇到了,估计是擦肩而过,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他没有像某些艺术家,非要整个光头或者长发或者着奇装异服。我记得一次在高铁站他约我,他未先到,特请一位年轻的民警安排我在接待室小坐等他。及至他来到高铁站,这是他的工作环境,我看到他在这里的言语、行为、神色,他与同行之间的对话,与诗会中的田湘有一些分别。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的田湘,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真实的属于自己的“日常”。
文学是一种说话方式,这种说话方式特别追求表意的效果,不仅是传达意思,更在乎传达的效果,在乎这表达是否让人感动、觉得有趣、意味深长、是否更深地呈现某种真实。当这种说话方式成为书面语,它就是文学作品。除了史诗、大型的叙事诗,一般来说,诗歌是文学里最简练的。任何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他可以与人交流,可以说话,当他有意识地追求语言在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诸方面的效果之时,他就是潜在的文学家;而当他以简略的方式来言说自己,以自己最擅长的语言方式、最自由地表达出他最内在的感受,他就可能会产出诗,他就是诗人。文学写作是一种能力,其存在决定于我们对自身属性的自觉。很多人觉得自己跟文学没有关系,至于诗人,非要李白杜甫、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海子骆一禾这样的似乎有特殊禀赋、特殊经历之人才是。我想说,每一个人都是文学家、都可能是诗人,关键在于你对言说自我、诗歌言说方式有没有自觉。
这也能够回答一个常见的感叹:这个时代还有读诗的人吗?当我们认为诗只是某些“天才”或“怪异”之人才能作出,诗歌只是用来表达一些浪漫情感、特殊体验和奇诡想象的文字(甭提那些歌咏今天是“好日子”接下来会“越来越好”的通俗歌词了),我们当然看不见好诗与诗人,因为诗是一种说话方式,因为诗人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对诗歌的“视力”决定了我们能否看到诗歌在何处。诗歌在我们自己这里。这个时代读诗的人少,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更多读诗的人,正是那些正在写诗的人,因为他有写作的经验,他才会成为真正的读者。诗歌在遇到真正的知己。
二、今时代的语言环境
诗既然是一种说话方式,那如何“说”,才有诗意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语言环境中,这个语言环境就是“口语”“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今天,这种民族共同语(在台湾叫“国语”)被民间俚语俗语、网络用语等语言资源填充得越来越通俗,但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中,我们正在用这些语言说话。当然,你也可以整天之乎者也、唐诗宋词式地说话,那你的写作只能归到旧诗词的领域,就很难与大多数以口语写现代诗、新诗的写作者对话。
嗍螺蛳
美味总是让人垂涎
年轻时,我带上你
在路边摊嗍螺蛳
我告诉你嗍螺蛳的诀窍
最爽口的,就是掀开螺盖
嗍螺肉上的那点汁
你照我的方法嗍了起来
多么鲜美啊,你一口一口地嗍
唇与舌忘情地游动
坚硬的壳里竟如此柔软
你一口一口地嗍
那种幸福感,那种满足感
我看见你的样子多么美
从此,每晚你都让我带你去嗍螺蛳
我也总是乐此不疲
但我却从未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初恋
我们今天的语言环境不是文言文、文学作品也不是唐诗宋词的样式,但是许多人评价诗歌,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语言环境中。比如我们面对一首诗,我们常常说:这首诗语词、意象美不美,意境如何如何……但很可能真实的情况是,口语化的现代诗并不“美”,甚至有的诗的价值,并不在于“意境”(比如郭沫若的《天狗》,岂是“意境”可以评价?)你若按照古典诗词的方式去读,它局部无任何可取之處。但是,你整体上会体会到它让人感动的地方。比如这首《嗍螺蛳》,它传达的是一种整体的感受: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所对应的内心的隐情——“我爱你,可是我一直没说”。这样的感受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同样的语言,也许我们也有写诗的冲动,但我们常常忘记了该如何使用语言,觉得已有的口语不能成为诗的语言,所以我们很多常常一写就成了辛弃疾李清照,作品缺乏当代性。由于不能很好地使用口语,作品无法言说出真实的生存经验。
三、何为诗意?
如果我们将“诗意”定义为语言在表意时所产生的让人感动,或者有趣有启发等效果的话,不同的语言系统,其诗意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五言、七言,其说话方式和诗意生成方式与今天的口语诗是不一样的。晚唐诗人温庭筠(约812—866)的《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杜甫(712—770)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里,基本上每一句话是三个意象,意象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说明的,你可以在这里调动自己的经验、展开自己的想象,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我想起的是初中就住校的悲惨岁月:礼拜一早上,鸡还在叫的时候(凌晨五点钟左右)就出发要去学校了,为了赶早读为了赶老师的点名,月亮还挂在天上,秋天的时候,我的脚印真的踩着地上的霜……不同的读者在这里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记忆的恢复,都能收获许多感动。
古代汉语形成的方式有很多原因,比如许多单音字在表达独立的意思、说话极为经济、简练。比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是今天我们日常用语中通常是几个词在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你好吗?”、How are you?……),语言系统、说话方式变了,诗意生成方式也变了,你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写作。你说唐诗宋词“美”,其实指的是它们的“空疏”,无论是境界还是情感,古典诗词的表达是非常“空疏”的,你可以将自己放在里面,所以你很感动,这是古典诗词的优势。
但古典诗歌有时显得缺乏情感言说的个体性与“精密”性,由于语言和形式的原因,其经验的传达是相当空疏的、抽象的,只有大概的意思(所以读者大都能将自己放置其中)。李白(701—762)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这里的送别友人,情感基本上是靠画面表达的,没有内心的深入呈现,作者到底是怎样的情感?我们无法获得其具体性。现代诗在人看来有时啰唆、没有想象的空间,但在情感、经验的表达上,更加具体、细密,现代人所获得的感动,正是从这里来。语言系统改变了,我们对诗意的生成方式应该另眼相待。(当然,新诗和旧诗还是有诸多一致的地方,这是另一个题目,在此不表。)如果旧诗我们常常以“美”来评价的话,那么新诗我们常常在其中寻求“真”。旧诗即使在局部字词都很“美”、很动人,故写作者要“炼”字,诗词有“字眼”;但新诗的效果是整体性的,你在整体阅读之后会收获一种触动。我们千万不要以对待唐诗宋词的审美程序来处理口语化的现代诗、新诗。
读特朗斯特罗姆
你的名字太长太长
特朗斯特罗姆
每个字读起来都很费劲
就像我坐过的绿皮慢车
我只能把有你名字的诗集
带到飞速行驶的高铁上
我从一个浮躁的城市
去到另一个浮躁的城市
只有高铁上是安静的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没有人打扰我
这样我就能静静地读你
读你
安静的高铁上
好像所有人
都在听我读你的诗
你的名字
好像也不那么长了
田湘的这首诗可能每个字、每一句读起来没那么有诗意,更谈不上“美”,但却呈现了一种“真”: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暂时的安宁给人心的安慰。“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omer,1931—2015)的名字不是长,而是我们没有耐心对待,但高铁上的安静让我能进入事物的核心,这时,许多阅读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这些平时我们漠视或者没有耐心对待的对象,现在和我们的内心有了交流,这对象也变得有意味了。现代人需要这种宁静和“慢”的治愈(虽然高铁并不是“慢”。这里的“慢”是空间性的)。这恐怕是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在飞机和高铁之间有时更愿意选择高铁的缘故。
现代人读诗,有时需要读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让久已忘却的自我在读诗中复活。人们期待在诗中看到真实的自我,这是当代诗很关键的地方,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言,你能否写出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类处境?读者在这里收获感动。
四、诗有何用?
这也涉及诗的功能的问题。诗有什么用?诗为什么存在?“文以载道”,这话没有错。但诗之“载道”,不是其首要目的,诗首先是写给自己的,你要问自己,“我必须写吗?”
1903年2月18日,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9—1926)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说到“写的缘由”的问题:“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躲开那些普遍的题材,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作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瘠不关痛痒的地方。”
诗首先是慰藉自己的;如果你的诗在传播过程中,有少数读者感动,这就构成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你的作品也慰藉了别人,这是第二个功能;在这种沟通当中,你传达的情感、经验或思想,影响了更多人,这时才可能形成“文以载道”之效果,可以说,第三种情况、第三个阶段,才是“文以载道”。如果你的作品不能慰藉自己,就很难慰藉别人。许多伟大的作家首先是为自己写作。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遗嘱中叫好友焚烧自己的作品。海子(1964—1989)说“我写长诗是迫不得已……”
我觉得田湘是今时代一位很有代表性的诗人,首先他是普通人,你我都是;但是这一点不妨碍我们成为诗人,关键我们是否有使用语言来言说自我的意识。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你正在使用语言,你从来不觉得自己也可能写诗,所以你当然离诗歌、离诗人很远。
田湘是當代诗人中在普通的口语表达中凝聚诗意做得非常好的一位。很多诗人很伟大,比如说海子、骆一禾(1961—1989),但他们你无法学习,更不能效仿,但是田湘这样的诗人,你能从他的生活和写作当中学习、效仿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借着他,你也可能成为诗人。我想,优秀的写作者其优秀的地方可能也在于:借着他,别人也能成为写作者。这样的诗人,是一位伟大的“中介”。
五、写诗需要“练习”
当我们有语言的意识、有写作的欲望,这时我们还需要练习。写作不完全是禀赋,它也是专业技能,因为我们在使用语言,因为语言又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和当代多种话语的交会之中,我们对语言和这种语言的文化传统了解得越多,对写作越有益。所以,我们需要阅读、需要“练习”。
练习册
我对河流一直怀着敬畏逢山绕行,遇崖就跳,又总是绝处逢生牙齿都没了,每天还在练习啃石头与坚硬的事物打交道。活着就认下奔波的命常常泥沙俱下,浊泪横流,越老越能包容谁投入怀里,都像他生养的,以此练就悲悯之心。认准一条路就走到底,一生都在练习跌跌撞撞,且乐在其中,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里的“一生都在练习”的“河流”,当然喻指诗人自身、喻指他的写作。《练习册》是田湘最新的诗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但我觉得它的意义却是古老的,这个题目提醒我们:写诗,是一种练习;诗歌需要技艺、变化与成熟。我很羡慕这个题目,在我的电脑里,一直就有“诗歌练习册”这样的文档,我将那些涂鸦放在里边,都是日常练习,也期待其中出现自己满意之作。文学写作不是天才才能做的事情,诗歌需要习得。诗人需要“历史意识”,应该有一点点意识: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在写作上正在朝什么方向努力。英国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就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他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的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
当我们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这话没错,但我们也要知道:哪一种艺术不是来源于生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说:文学来源于文学。在对文学的阅读与研习中我们获得更多的语言、思想资源,获得更多的使用语言和形式的方法,这样我们的写作才会有变化、更好的趋向、从一种成熟趋向另一种新态。
六、《练习册》中的新变
田湘成熟的作品常常表现为:在日常生活场景、在平常事物的叙述中,呈现一种生存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形态有时是相当明晰的,读者很容易把握,这也是他的作品让人喜爱的一个原因,他的“沉香诗人”绰号的获得,大约与此有关吧。《雪人》等名作大约也是如此。
小草不是风的奴仆
小草是風的语言
而不是奴仆
它用身体的语言说出风
它倒下,是让你看到风的方向
而不会像树枝折断自己
风没有故乡也没有离愁
而小草有,它有一厘米的国土
它害怕离别
它生在哪里,就会死在哪里
它会让你看到它的骨头
小草有翅膀,但从不飞翔
正如石头有门,却从未打开
风想带领小草云游世界
小草只在风中摇曳
绝不随风而去
请看
小草的腰如此纤细
却能与十二级台风共舞
风给予的一切
它都能承受
这是一首咏物诗,借着“小草”,作者表达了一种“绝不随风而去”的人生品格,读者在这里很容易收获文本的意义。整首诗的叙述线索是清晰的、结构和意义的呈现都恰到好处。但是,在整体上,作为现代诗,你会觉得有一些不满足感:现代诗的复杂性、语言和意义的混杂,在这里似乎缺失了。在这个意义上,《练习册》有些作品我觉得更有意味,它们可能意味着作者要寻求的改变:
大海不停地运送浪花
大海不停地运送浪花
她知道你想要:这盛开的孤独
这激情的泪,她知道你想要
这献给沙滩与岩石的祝福
太阳在清晨点燃自己
海鸥盘旋优美弧线
大海弹奏崭新的五线谱
她知道你想要:这恢宏乐曲
大海从未厌倦
不停地运送浪花
她知道你想要:这温情的玫瑰
她一直在阻止:这爱凋谢
这首诗局部的想象非常棒(“浪花”并列于“盛开的孤独”等)。一共是4个部分,中间的意思不甚连贯,每一个意义单位之间是断裂的(“……孤独”、“……祝福”、“……乐曲”、“……玫瑰……凋谢”),这是现代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独立性/非连续性的句法的说话方式,它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更有现代感。这样的诗我觉得田湘可以多多尝试,为此,甚至可以将诗写得晦涩一点。诗,需要练习,在无限的练习之中,好作品正在萌生。
(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