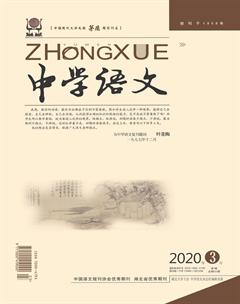写作素材:取之有道,用之有法
袁海锋
相比于阅读,写作是更为高级的语文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行为,它却不能凭空发生,而是需要外物具体而微的触发,需要外物、人心的多元酝酿与文字呈现。“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钟嵘《诗品序》)。古人的此类阐发正是对这种物我文学关系的强调。写作素材是支撑写作活动顺利进行的物质材料,它可以是一景一物,亦可以是一人一事,横跨在写作活动最初的激发与最终的呈现之间。
生活是写作素材的广阔来源地,生活内容大都是潜在写作素材。具体到文学写作最后的文字呈现,当情感酝酿已经成熟,写作者的情绪需要写作素材的导引才能凝固于纸面。外物人心交织的酝酿过程已经完成了一次写作者心性主导的素材选择。即便如此,留给文字呈现的写作素材仍是海量的。写作素材与文学效果有着密切关联:合适的素材可使酝酿成熟的情绪合宜地流露;错位的素材则使作者情绪的表达受限。写作素材选取合理与否关乎着写作成败,从写作效果反观,便可以明确素材取用的道与法。
一、素材视角:在眼前巡视与往回忆漫溯
文学反映人的生活,人借文学审视生活、考量自我。写作者的书写姿态就是他观察生活的方式,也是他取用写作素材的方向。写作者观察生活,无非存在“看眼前”“看身后”两种基本视角。由此,便可生成两种相应的书写姿态:“记录当下”式写作与“回忆过往”式写作。
“记录当下”式写作,观察视角立足眼前,选取素材多眼前景事。这种书写姿态适用于抒写娱游景事类的作品,素材选择以写作者情感偏好即时选取,以表现其当下情绪。彭荆风《驿路梨花》、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等作品都采用了如此素材处理方式。“回忆过往”式写作则将视角转向茫茫过往,选取素材多是前尘往事。这种书写姿态适用于记事写人型文章,素材选择则以笔下人事为纲,以突出人情世故为目。鲁迅《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朱自清《背影》、杨绛《老王》,乃至汪曾祺《昆明的雨》在素材处理上都属此类。
娱游景事类作品中,写作者的内心情绪是素材取舍的主导力量。眼前生活,景象万千,素材自身有着明净昏暗、清幽艳丽的内质倾向。素材倾向只有与情绪的喜怒悲欢契合,它才拥有进入作品的可能。极端之下,情之所至,甚至可对素材进行无中生有的变形。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例,苏轼被贬黄州、宦海沉浮,但情绪上偏有一種豁达洒脱之意。于承天寺中,苏轼的写作困境在于周围景、眼前事无一能承担情感对位的功能。借着心中情绪的“怂恿”,文学巨擘苏轼把天上月变成地上水,把寺内竹柏化作水中藻荇——他自己造景,自己创造素材!藻荇无根、随波逐流、漂泊无依的特征与苏轼有了相似性,藉此情感有了由苦闷到洒脱的升华可能。由此例可见“记录当下”式写作素材取用中,写作者情绪的“霸道”。
记事写人的文章中,人物的塑造是写作的核心,但形象的成长是历时性的。“回忆过往”式写作,则以倒叙的文学方案,将素材选取视角由短暂当下推进到茫茫的时间过往。这种素材处理方案妙处有二:将素材选取推进到过往时间,写作发生的空间维度扩张,人物形象的经典侧面、人物参与的经典事件也就随之丰富起来。像鲁迅笔下的阿长讲“长毛”的恐怖故事、送粗糙而珍贵的《山海经》,不在回忆中,便没有素材选取的这般优势。由当下推进到过往,还是意味着时间维度拉长。因为时间差的存在,由人物侧面、人物事件诱发的情感酝酿也就会越浓烈。越是从时间深处淘出的写作素材,越是熔铸着作者深沉的情感和至深的感悟,比如杨绛在《老王》里对着最后的香油和鸡蛋,在时间里感到的深深愧怍。
二、素材活性:从瞬间定格到历时跳动
活性是写作素材文学表现力强弱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写作素材取用的一大考量指标。在不同形式文学写作中,素材活性有不同表现。以摹形状貌见长的作品中,素材活性意味着写作者凝视于素材,素材瞬间定格,内部不断打开;在记叙人事为重的作品中,素材活性则凝聚在素材的历时属性——它有自身的动态展开与推进。
凝视是写作者对素材对象的深度观察。素材定格后,它的不同内部构成越是丰富多元,落脚于素材的凝视就越可能深入、延长。凝视之下,素材不同瞬间局部层面的潜能被打开,素材内容极大拓展;随着素材容量扩大,素材表达的可能也不断被激发,隐藏在素材中的情趣理悟随之喷涌而出。凝视之于素材,就是创作的一部分。以史铁生为例,可以说《我与地坛》便是他与地坛这样深度凝视的文学结晶。对别人而言,地坛不过是一座废弃的古园。但在史铁生的凝视下,地坛剥蚀了“浮夸的琉璃”,淡褪了“炫耀的朱红”,坍圮了“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如此深沉的凝视,地坛浮现出它繁华之后的衰败,这与作者“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生命状态有着某种宿命的相似。作为素材,地坛活性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之后,通过凝视地坛的草木虫蚁、落日古柏、雪上孩子的脚印、雨燕的歌声,地坛的内质不断被开掘、激活,作为素材的活性亦渐次升级,直至完成开解作者人生的文学任务。
记叙人事的作品中,素材常以事件片段的形式出现。事件片段可能是一个静止的叙事点,亦可是一个内部丰富的叙事段,其中区别在于片段历时之长短。叙事段,就其结构属性而言,内部自有情节发展能力;就其语言属性而言,其内部展开勾连记叙、描写、抒情等表达手段。作为素材,叙事段始终是历时跳动的,与叙事点相比,其活跃性高下立现。选择此种素材支撑写作,作品的文学性自然依托素材活性而张扬。朱自清《背影》中有父亲“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和翻越月台买橘子两个叙事素材。就实际价值而言,几个橘子和父亲为“我”做的紫毛大衣不可同日而语,承载的父亲情感又无天壤之别。但在素材活性上,二者差异巨大:前为叙事点,动作瞬间完成,素材深度发掘难以为继;后为叙事段,其内部包含爬月台、买橘子的情节发展,表达上综合着对父亲的记叙、描写以及“我”情绪的抒发。作为文学大师,朱自清肯定是考虑到了素材活性的。
三、素材尺寸:从恃强凌弱到见微知著
《庄子·则阳》有蜗角触蛮二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之事,可视其为文学写作的形象演绎。文学写作便是一场蜗角之争,要完成一次小大之辩。文学的本真是抒情达意,素材选择最终要依托情感走向。情感內质大致有二:感怀生命短暂、脆弱、无可把握的消极之类,与抒发生活美好、生命美丽、有意的积极之类。因为情感走向的差异,素材选择的“尺寸”也就有了相应的分野。
人的情绪不能凭空生成,它需要一个外在的激发媒介,正所谓“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物之感人”。情绪由外物刺激而生发,更需外物协力以显形。消极感怀往往关注自我之“小”,情绪下行走弱,这种情绪常因临场外物之强大、宏阔、恒久而激发。对此情绪的文学显现,自然需要强大宏阔恒久外物的助引,“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苏轼《超然台记》),进而形成“恃强凌弱”的写作效果。这种情形里,素材选择的尺寸宜往“强”的方向走,比如日月星辰、山川江海、长空大地等。所选素材尺寸欲强欲大欲久,写作者自我感越“小”,脆弱感越烈,此正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文学效果。《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陈子昂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孟浩然之“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苏轼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皆是此类。
相比于消极感怀,积极抒发是一种更正向、更高级的情绪。它不回避人生苦短的残酷事实,还要在此上看到生命的意义,找到坚守的动力。此时,从素材尺寸的“强大”处着笔定然行不通,因而只能走向素材尺寸的另一维:微小。微小之物易遭凌暴,易为忽略,微小姿态里更易见出外溢的神性风采。聚焦微小素材,写作则常能见微知著,在小小素材上开拓出广阔的精神空间,借此将写作者内心汹涌的生命感悟和盘托出,达到“以小博大”的写作目的。茅盾《白杨礼赞》“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一句淋漓地写出了微小素材的这种文学优势。贵族化楠木不平凡,这得之于它的少见,是自然而然,其物性之“强大”限制了它精神空间的开拓。相较楠木,白杨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普通、渺小、卑微的素材“微”特征,更能突出其笔直树形之艰难。由此深化,则可以深化到其刚直本性之难得,这就与写作者的积极抒发接续上了。就此而言,白杨的“普通”正是它的素材优势所在。
素材尺寸只是选择素材的一项外在指标。它只能指示选择方向,却不能直接生成文学表达效力。素材表达效力的达成不可单求一维一法,作文教学必须明确这一点。
四、素材契机:从顺势而为到力求突兀
素材视角是素材选择方案,素材活性、尺寸是素材质地描述,对它们的讨论皆在写作现场之外。在素材视角确定,素材活性、尺寸理清的基础上,素材在何时进入写作现场,是另一个需要清理的写作问题。素材契机是对素材进入写作现场时机的质性把握。从情绪与素材的关系看,素材契机有两种表现:一是写作者情绪不断酝酿成熟,素材顺势而为,进而达到水到渠成的文学效果;二是素材毫无防备地乱入,由物及情,皆是意外之喜。
顺情感酝酿之势,及时推出合辙素材,这在以描写见长的文学类型中极为常见。写作的开启需要外物媒介的刺激,需“物之感人”启动情绪。但“感于物而动”之前,写作者并非无情存身。此时,写作情绪已有基本雏形,只是不具体,只是喜怒哀乐的粗浅倾向。虽是粗浅倾向,但已足以实现素材选择——选定何物感动。此时,相应素材及时进入文字现场,粗浅的情感倾向才能借素材之形,拓展延伸细化,进而落笔定型,形成所需文学效果。《渡荆门送别》一诗“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一联将李白离蜀归楚的写作情境交代清楚,此时留恋故地、期许未来、前路迷茫几种粗浅的情感倾向交织,写作急需情感的明确与定型。李白顺势推出荆门风物这一素材。山尽平野,江入大荒,束缚尽去,渐入佳境。李白脱离过去的洒脱,渴望一方舞台的热切,借此表现得既含蓄又畅快。“素材及时入场,推进写作深入”,李白此诗淋漓地演绎了这一点。事实上,很多写景抒情的古典诗歌都有类似素材契机的演绎。
力求素材介入的突兀,以求文学效果的意外之喜,写人记事型的作品中多见此种素材契机处理。情感是发展的,写人记事的作品以呈现这种发展性为上。情感发展各个阶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不能形成绝对的钳制。相对于顺情感之势而来的合辙素材,不受钳制的情感发展更需要突兀素材的介入,以实现情感的发展与升华。《阿长与<山海经>》在阿长求祝福、讲“长毛”故事后,送《山海经》的桥段突如其来,鲁迅对她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甚至感受到“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这是鲁迅情感的升华;《老王》在送冰、送默存之后,垂死的老王毫无先兆地送来他的生命遗产——鸡蛋、香油,以致杨绛怕得不敢请他进来坐、急忙给他钱,以致杨绛心里久久不能放下的愧怍,这是杨绛的情感升华。《背影》里父亲“本已说定不送我”,最后来了;车上已经安排妥当,却又临时起意,去买几个橘子,这些临时的、突然的片段写出了父亲细碎深沉的爱,以致“我的眼泪又来了”,这是朱自清情感的升华。
素材是文学写作的基础构成,素材的选择决定着写作的高下得失。教材选文是名家之作,更是经典的写作范例,中有大量素材选择案例,隐藏着素材取用的视角、活性、尺寸、契机之法。将它们析出,生成写作教学资源,这是对阅读写作的横渡,是对作家作品的尊敬,也是对文学规律的尊重。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