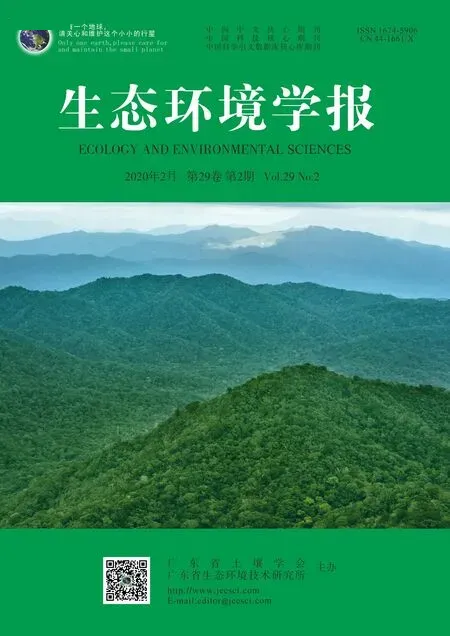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城市化发展的响应
何媛婷,王石英,袁再健*,郑明国,黄斌,梁晨
1.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2. 广东省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070;3.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工程中心,广东 广州 510650;4. 华南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50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表现尤为显著(刘纪远等,2014;刘纪远等,2018)。1979—2009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快速发展,建设用地扩张快速,在此过程中被占用最多的土地类型是耕地,耕地与建设用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薛俊菲等,2012;黄滢冰等,2017),其次是林地(徐进勇等,2015;施利锋等,2015)。近年来,许多学者就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在经济、政策、人口、生态、环境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和政策变革是促进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牟凤云等,2007),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虹吸效应,促使城市空间加速扩展(蔺雪芹等,2015),城市扩展改变生态用地空间格局,对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张骞等,2017),城市气候和环境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植被覆盖区域与高温呈负相关而与裸地则呈正相关(Xiong et al.,2012),基于土地利用与城市化相关性可以预测人口的增长(Liu et al.,2016),根据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可预测城市未来的土地利用(Xu et al.,2016;Jiao et al.,2019),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发展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不同城市群建设用地动态程度(Cao,2014)及城市化对不同阶段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因子(戈大专等,2018)存在差异;根据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研究各类土地类型的动态变化和转换过程(Yang et al.,2018),城市化进程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城市迅速发展,伴随着显著的土地利用变化(Dai et al.,2018)。鉴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以及其对城市化发展的敏感度,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多是从全面性或单一性的城市分析中择其一,不利于进行城市群间的对比及共性研究。基于此,文本以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对2000、2005、2010、2015年4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进行整体分析,其次,细化到各市进行城市化水平分析,深入探讨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揭示各土地类型对城市化发展的敏感度,以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1 研究区概况
珠江三角洲(21°30′—24°N,112°—115°30′E)(图1),以下简称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肇庆、江门9个地级市,总面积约56000 km2。境内水系众多,由西江、东江、北江组成,以西江为主;八口入海,自西向东依次为崖门、虎跳门、鸡啼门、磨刀门、横门、洪奇门、蕉门、虎门(陈金月,2017);。珠三角以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海拔多在200 m以下,地势平坦,高温多雨,动植物种类繁多,经济发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图1 研究区所在位置示意图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1.2 数据来源
本文高程数据(DEM,30 m×30 m)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2000、2005、2010、2015年土地利用30 m栅格分类数据来源于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该分类系统从土地利用类型遥感监测实用操作性出发,紧密结合全国县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系统,在适用性方面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新良等,2012);城市化水平计算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16年)。
1.2 研究方法
1.2.1 土地利用度量方法
“土地利用动态度”用土地利用在一段时期内变化的模型加以表述(刘金花等,2012;赵健等,2001),即:

式中,Sa为初期某类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km2);Sb为末期某类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km2);T为时间段(a);A表示与T时期对应的某类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正值代表土地面积增加,负值反之,动态度的绝对值代表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值越大变化程度越大。
“土地利用变化率”用以计算某土地类型在某段时期内土地的消耗程度(汪东川等,2019),即:

式中,Lcu表示某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率,Cij表示从i时期到j时期某类土地改变成另一类土地的面积和,Ui表示i时期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T为i时期到j时期的研究时长,以年为单位。
1.2.2 城市化水平
珠三角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多,根据实际情况,本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比(P1)与非农产值占总经济的比重(P2)的综合指标,对研究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测算。P1和P2的权重分别为0.8、0.2,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到城市化发展水平P(鲁春阳等,2010)。

根据表1的判断标准,可以分析研究区不同时间段的发展阶段(陈永林等,2015)。
1.2.3 最大信息系数
最大信息系数(Maximum information coefficient,MIC)可以衡量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与一般相关系数相比,MIC不依赖于变量的分布假定,同时能够识别更广义的相关关系(Zhang et al.,2014),MIC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David et al.,2011):

表1 发展阶段判断标准Tab.1 Criteria for judging development stages

其中,x是城市化水平,y是土地类型变化,H(x,y)是条件熵表示y对x的期望;P(x,y)为X和Y的联合概率密度,p(x)和p(y)分别为X和Y的边缘概率密度;n为数据点数量,nx,ny分别是x轴、y轴各区的箱子数目。MIC值域为[0, 1],当变量MIC趋于1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MIC趋于0则两者互相独立。
1.2.4 弹性系数
弹性概念只要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则可以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度。

其中dX和dY分别是变量X和Y的变化量;e为弹性系数。弹性反映是变动的相对值,斜率是变动的绝对值,因此将弹性系数进行绝对值处理,更易于比较说明,弹性系数无量纲,通过X(城市化水平)与Y(各土地类型)之间弹性系数大小反映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的敏感度,土地利用类型的城市化弹性系数越大敏感度越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4个阶段的土地利用分类(图2),计算每个时期土地类型面积的比例(表2)。结果发现,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林地、草地、水体和未利用地面积变化不大;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部地区,耕地主要分布于建设用地周边,多数林地分布于珠三角东西两翼。

图2 2000—2015年珠三角土地利用分类结果Fig. 2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0 to 2015

表2 2000—2015年珠三角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与土地利用动态度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land use types and Land use dynamic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0 to 2015 %
根据3个时段土地利用的动态度(表2)可知,建设用地在 2005—2010年期间变化程度大,扩张速度快,另外2个时段建设用地的动态度相对保持缓慢增长状态;耕地在 2005—2010年期间变化幅度最大,在此期间大量耕地被侵占;林地在2010—2015年期间缩减幅度远大于2000—2010年的增长幅度;未利用地占地面积小,变化程度大,在2000—2010年期间面积增长幅度大,2010—2015年期间面积缩减幅度相对较小。分析表明,建设用地与耕地的变化成负相关,城市发展意味着人口的增多,促使建设用地的扩张,导致其他类型的土地被侵占,在 2010—2015年期间建设用地的扩张速率有效的得到控制,在此期间城市对未利用地的开发使用力度也得到提升。
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建设用地占用最多的土地类型是耕地,林地次之,转移面积逐年减少。利用 ArcGIS统计出珠三角不同时段的土地利用转换矩阵(表3—5)。表格中行、列分别为土地利用类型初期面积和末期面积,对角线为没有发生类型转换的数量,变化率是土地类型转换面积占该类型总面积的百分比。

表3 2000—2005年珠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矩阵Table 3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0-2005 km2

表4 2005—2010年珠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矩阵Table 4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5-2010 km2

表5 2010—2015年珠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矩阵Table 5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10-2015 km2
由上表可知,2000—2005年未利用地变化率最大,面积呈增长趋势,主要转化类型为耕地和林地;2005—2015年草地变化率最高,但总面积没有太大变动,主要是与林地之间的转换。建设用地变化是城市化发展最直观的表现,珠三角在2005—2010年期间建设用地变化率是 3个时期最大的,其变化率分别是前后两个时期的1倍和3倍之多,耕地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率是与建设用地最一致的土地类型,2000—2015年期间,耕地是建设用地主要的来源地。
分析表明,从土地利用变化角度可知珠三角近15年的发展进程中,2005—2010年期间城市发展迅猛,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可能是城市加速扩张的重要因素;城市前期发展进程中建设用地的扩张最先占用周边的耕地,在 2010年后建设用地扩张速率减缓,耕地的占用得到控制,城市更加理性化的发展。
2.2 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
2.2.1 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的相关性
从整体分析了珠三角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对珠三角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全面了解,将继续对珠三角各市的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深入剖析。根据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阶段可将珠三角9市分为三类(图3):后期成熟阶段城市(A类城市,包括深圳、广州、珠海和佛山),中期加速阶段跨入后期成熟阶段的城市(B类城市,包括中山和东莞),以及中期加速阶段所属城市(C类城市,包括惠州、江门和肇庆)。

图3 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Fig. 3 Urbanization level of the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分析表明,珠三角9市是在2000—2005年期间城市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步入2005—2010年期间大部分城市进入稳健发展状态,深圳、佛山、江门仍旧保持城市的快速发展,跨入2010年珠三角整体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建设用地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根据珠三角整体土地利用变化已知建设用地在 2005—2010年期间变化率最大,城市化发展水平在 2000—2005年期间涨幅最显著,在2005—2010年期间延续增长形势,由于珠三角9市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需要分门别类的对珠三角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细致性的进行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性分析。将各类土地类型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逐一应用式(4)计算两者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A类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整体偏低,MIC值大于0.7的仅有建设用地、耕地和林地;B类城市建设用地、耕地和林地的MIC值大于0.9;C类城市建设用地和林地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相对较高,MIC值大于0.8。建设用地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最强,未利用地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最弱;A、B、C三类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6类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性最强的 3类土地类型依次为草地>耕地>建设用地,耕地>建设用地>草地,建设用地>林地>耕地。

图4 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相关性Fig.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land us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2.2.2 城市化水平发展过程各类土地利用敏感度
城市化水平发展导致土地利用的变化,每种土地类型对不同阶段城市化水平的响应存在差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只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关联性,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敏感度来说明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各市根据所属城市类型相关性最佳的3种土地类型,运用式(5)计算并绘制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水平弹性系数图(图 5),斜率与敏感程度成正比,斜率越大则敏感度越高。

图5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水平发展过程土地利用类型敏感度Fig. 5 Sensitivity of land use typ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eve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类城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经济地位首屈一指,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圈发展已经趋向成熟,其中珠海较为特殊,在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化发展的敏感度达最低点前耕地敏感度最大,最低点后建设用地敏感度最大,草地最弱;广州、深圳、佛山随城市化发展草地是敏感度最大的土地类型,广州耕地敏感度最弱,深圳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敏感度相差不大,佛山的耕地、建设用地的敏感度小且先降低再增加。
B类城市属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代表城市,其中建设用地对城市化发展敏感度先降低后增加,耕地在城市跨入后期稳定阶段前的一段时期敏感度最低,城市进入后期稳定阶段耕地对城市化发展敏感度逐渐增强,东莞草地对城市化水平发展敏感度先降低后增加再次重复,城市进入后期稳定阶段敏感度持续增大,中山草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先降低后增大,在后期稳定阶段敏感度持续增加。
C类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加速阶段,中江门、肇庆建设用地对城市化发展的敏感度最大,增长幅度显著,耕地次之,肇庆在此期间建设用地、耕地的敏感度持续增加,江门建设用地和耕地敏感度先降低后增加在重复,林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先减弱后增强。惠州的耕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逐渐增大,城市化水平敏感度经历第一次低谷再次到达高峰值之前,林地对城市化水平敏感度高于建设用地,在此之后,建设用地对城市化水平敏感度持续增强且敏感度高于林地。
分析表明,A类城市中广州、深圳、珠海建设用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偏高,佛山建设用地的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几乎没有响应,相较于其它3市佛山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与当地政策或经济发展模式有关;B类城市中建设用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高,东莞、中山的建设用地对城市化发展的响应程度几乎一致;C类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度高,江门、肇庆、惠州的建设用地的变化对城市化发展的一直保持积极的响应状态;三类城市中B类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是最密切的,同时B类城市也是城市发展成长速度最快的,建设用地也是城市加速扩张中最直接的结果。
3 结论
(1)2000—2015年期间,珠三角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明显变化。从数量上看,建设用地增加1.75%,耕地减少2.66%,其他土地类型变化幅度小;从变化的速率来看,2005—2010年期间,耕地的变化率最大为19.74%,建设用地在2005—2015年期间扩张速率降低近2倍,变化率从10.97%降低至5.8%;从变化的程度来看,在2000—2010年期间,耕地和林地得到集中开发,在2005—2010年期间,建设用地拓展力度大,土地利用动态度为4.21%;从变化的类型来看,建设用地的补给主要来自耕地,其次是林地;珠三角遵循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原则,占用耕地和林地的同时给予补给。
(2)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建设用地是与城市化水平关系最密切的土地类型,其次是耕地。A类城市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是三类城市中最弱的,表明城市发展成熟稳定,城市建设受到当地时效性政策的影响和控制,更加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对农用地采取保护措施,未利用地的开发力度增强,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B类城市,在城市化水平跨阶段后,耕地及建设用地受城市化发展影响大且敏感度持续增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土地需求的逐步扩大,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在城市化水平最大阶段时敏感度达到峰值,说明城市化发展是影响建设用地和耕地的关键因素;C类城市,建设用地逐年平缓增长,耕地缓慢减少,城市发展速度相对A、B类城市缓慢。
(3)建设用地的变化是最能反应城市发展实况的外在表现形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优质经济增长越迅速,人口的虹吸效应可能越严重,城市扩张最先占用周边耕地以及草地。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发展经济攀升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共同的土地利用问题,城市外扩占用耕地,“不健康”的城市发展,存在许多隐患。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已经趋于成熟,2010年后城市发展得到控制,城市扩张大幅度减缓,在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扩张速率减缓,说明政府对生态红线的保护措施力度加大,城市用地受到了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城市发展用地与农地利用、保护的相关政策,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对珠三角城市化发展的响应实情来看,珠三角受政策监管城市与生态保持和谐的可持续理性化的发展状态,但珠三角城市仍不断成长经济持续攀升,现有的相关政策在未来城市负荷量达到临界状态时可能失效,需要及时的因实制宜、集约化发展,因此未来应持续关注土地利用变化对珠三角城市化发展的响应。本文主要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推算出城市化水平对土地类型的影响程度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的敏感度,对于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这类耕地和建设用地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较弱的城市,将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