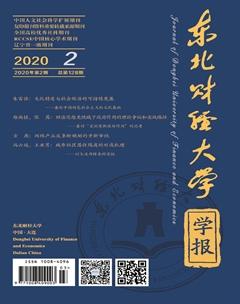城市社区居住隔离的形成机理
冯云廷 王亚男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002010
〔引用格式〕 冯云廷,王亚男城市社区居住隔离的形成机理——以大连为样本的实证[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2):89-96,封三
〔摘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不同人群在居住社区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居住隔离与居住分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侧重于居民经济地位引起的社会等级分化在城市内部空间不平等的表现。在对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进行审视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多维度的城市社区居住隔离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大连市小区居住情况”的问卷调研数据,从邻里选择及迁居流动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下,作为外生效应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效应的社会资本收益及其对社区的期望,是引起居民家庭在城市社区空间上分层的重要原因,迁居流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住隔离分化的严重程度。
〔关键词〕社区居住隔离;经济地位;邻里选择;迁居流动
中图分类号:F293;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20)02008909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住房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居民逐渐从单位大院为主导的居住区走出,在自由选择住房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居住品质。收入对住房的选择越来越重要,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够买得起高档的公寓或豪华别墅,城市住房空间开始出现差异化,这个阶段称之为居住分异。第二阶段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很容易形成富人社区、平民社区和贫民社区共存于一个城市的现象,它使得社区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微妙暗示,这个阶段称之为居住隔离。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居住隔离是居民经济地位引起的社会等级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体现。
在过去传统的居住选择中,人们大多关注房价与通勤时间,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区的潜在收益开始得到关注。一般来说,社区空间利益包括居住条件、共享资源和附加利益,居住条件指社区或住宅本身所能提供的基本居住收益,共享资源指社区周边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交通、医疗和治安等,附加利益指社区所能带来的荣誉、自豪感和社会网络等无形收益[1]。由于市场机制、社会分工的不同,致使劳动社会越来越独立化、专业化,一部分人率先获得了超额收益,资源、财富从之前的“大锅饭”逐步走向了不平等,而住房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形式,不同的居民获得的社区空间利益也有较大的差距。由于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让富有的人变得更富有,同时贫困区“示范效应”的匮乏、贫困的人集聚产生的不良文化氛围,也会让贫穷的人陷入贫困陷阱中,这将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
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如美国、欧洲、南非等)率先对居住隔离这一现象做出研究,但大都是基于历史维度,重点讨论种族、政治、社会福利等方面[2],与中国现实条件十分不符。现有文献对于居住隔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居住环境、城市圈层规划入手,聚类分析居住在不同地区居民的特征,得出的结论大都是环境通过影响房价进而导致了居住上的分隔[3]-[5]。但是,这种讨论依然基于收入引起的住房差异化的视角,而没有深入讨论经济地位引起的社会等级差异化在空间上的映射,因而更像是基于居住分异视角,而非真正的居住隔离视角。二是以空间错配理论为基础,从通勤时间、收入、就业分析居住隔离[6],但人们在实际挑选住宅时,看重的社区利益远不止这些。三是重点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或流动人口为切入点,从市场分化、生活方式、职业表现等方面进行研究[7]-[9],但农民工、流动人口只是一部分人群,并没有从一个整体角度讨论居住隔离。尽管有学者论述过社会等级、社会资本与居住隔离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详细说明其中间的形成机理。
本文主要对Schelling[10]提出的居住隔离模型进行重新审视,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重新评估社区价值,详细地剖析居住隔离的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而将如何能进行空间重构,进而减弱居住隔离对城市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对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的质疑
1990—1940年,由于白人种族歧视等原因,美国逐渐出现黑人集聚区。1970年之后,集聚区环境恶化,普遍存在贫穷、失业和犯罪等社会问题。Schelling[10]发现了这一现象:白人、黑人和亚裔的集聚区表现出明显的种族隔离,同时富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各自也出现明显的集聚,于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他构造出两种居住隔离动态模型,分别是空间邻近模型和有界邻近区域模型,模型中分别定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各自有各自的居住偏好,并假定有一个初始的失衡条件(如种族歧视等)。空间邻近模型强调关注邻居的具体位置,并假设每个家庭都希望周围的邻居是和自己同类型的人;有界邻近区域模型的重点在于只关注周围邻居的构成比例,并不关心周围邻居的具体居住位置,如果邻近区域内与自己类型相异的居住者所占比例超过他的容忍度时,他就会搬离此社区[10]。一个邻居的迁居可能会引发邻居的迁居行为,从而引起连锁反应,不管怎样,如果所有对邻居构成不满意的居民都迁居到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小区,那么会达到一个极限状态,这种由微观行为引发的宏观层面居民迁居的结果,就容易出现同类型家庭居住的聚集,相异类型的家庭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出隔离的状态。
但是,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或许还有需要继续探讨的空间。一是其定义的两类人群,中国的社区是由不同收入、学历、工作单位、偏好的人群组成的多類型群体,尽管收入在社区的选择中起到了很大的分化作用,但一个人的身份不仅仅由收入标明,学历、工作单位等也对其有影响。二是像种族歧视这种初始失衡条件,这个在中国可能表现并不明显。从中国住房市场的演变来看,经历了从单位大院、居住分异,再到居住隔离的过程;从消费者主体来说,居民的选择在这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居民的选择似乎又取决于个人收入和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等,所以对于初始失衡条件,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三是对于迁居问题,由于对周围邻居的构成比例或位置不满意进行迁居,这没有对理性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邻居与自己的身份不符而进行的迁居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自身需求的变化,或空间利益的改变,这需要结合居民迁居的现实原因做出探讨,也要对不同的人为何迁居做进一步研究。
(二)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中,对于邻居类型的要求,暗示了身份地位是造成居住隔离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背景下身份地位也许可以用种族或收入进行简单的判断,但随着社会分工、经济不断发展,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就不能简单地由种族或收入进行判断。社会等级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11],而哈丁和布劳克兰德[12]提出社会等级的分层由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社会经济地位包含收入、教育、信息网络和社会资源等方面。Bourdieu[13]将社会经济地位简单概括为是由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界定。所以,本文将一个人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作为本文的逻辑起点,基于对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的重新审视,以及前文中对该模型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反思,本文构造了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图,如图1所示。
居民的集聚行为如何赋予了社区独特的意义,使之成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要从居民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对社区的选择谈起。设想生活中的场景,一个人在挑选社区住宅时,不光要看住宅本身,一般还关注周边的公共服务,如交通是否方便、有没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以及购物的市场或商店等,与此同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收入是否与房价匹配,从而理性地选择购买。
从经济学的视角,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于任何选择都是基于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对社区住宅的选择也不例外,其居住效用包含了外生效应和内生效应两个方面。社区住宅作为固定资产,构成了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在既定经济资本的约束下,将决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社区住宅的居住效用应该从一个较长时期去考虑。由于城市地理空间的差异,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虽作为外生效应出现,但其完善程度决定着未来生活的舒适便捷,影响着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的效用,所以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酌情考虑,如上班族可能更看重交通,老年人可能喜欢医疗较为发达的社区等。不可否认,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着房价,而通过价格机制的筛选,影响到社区居民的整体层次。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居民一般会在收入范围内尽量选择好的社区,而不会选择价格便宜的公租房、棚户区。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邻里效应带来的影响,即使棚户区等住宅价格低廉,但富有的人也不会选择融入这样的邻里。社区邻居构成了居民的邻里社会资本,影响着居民内心对社区邻居的认可度,这称之为内生效应。社会资本指社会关系网络,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人,可以获取别人得不到的帮助,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中国有句古话:与凤凰齐飞,必为俊鸟。同理,在一个社区中,周围的人群也暗示着自己与什么样的人为伍,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如果仅仅是从收入差距或是地理环境的视角出发,那么居住隔离的问题似乎就没有那么难解决。
文化資本可以指国家或地方的教育制度,在个人层面也可以指文化程度或内在的精神。但是,从社区的角度来看,附近的学校、社区文化氛围都可以算是一种文化资本,这更是一种可以使贫穷代际积累的因素。其实,这一层面解释了很多家庭愿意选择学区房,想要融入好的邻里的原因。哈丁和布劳克兰德[12]认为不良行为会有传染性,会产生与主流文化相悖的社区价值观,形成贫民区特有的文化,如犯罪、诈骗和辍学等,即邻里效应,这无疑会对人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不管怎样,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选择购买社区住宅时会考虑的因素,也会根据自身收入水平等进行合理的选择。对于邻里的选择,有直接影响的是房价、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有间接影响的是周围的邻居和社区文化等因素,这就造成了不同人群在城市空间的分层。关于邻里选择造成的分层,可以用一个函数关系式表达出来,更加简单明了。社区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社区住宅时是基于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求解:
maxV*(xi,Yn,ρn)(1)
其中,V*表示社区住宅的居住效用,xi表示居民个人特征,Yn表示社区公共服务水平,ρn表示地租。
令效用水平不变,对ρn和xn(xn表示社区邻里特征)求偏导,即:
V*xn(xi,xn,ρn)dxn+V*ρn(xi,xn,ρn)dρn=0
R(xi,xn,ρn)=dρndxn=-V*xn(xi,xn,ρn)V*ρn(xi,xn,ρn)(2)
其中,R(xi,xn,ρn)的特征决定了邻里在均衡时是否会分层,如果对于更好邻里的支付意愿会随着个人属性xi递增,那么唯一稳定的家庭均衡配置就是分层的。关于外生效应或社会资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往高处走”的理性,所以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社区住宅选择时,会造成在城市空间的分层。
从迁居选择上看,迁居依然会遵循上述邻里选择的原则,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迁居是改变目前居住效用的一种方式。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提出居民通过不断优化自己的居住位置,达到空间中的极化状态,从而引起了居住隔离。因为不论是需求的变化还是空间利益的变化,每个居民都在向更好的社区场所转移,而居住在贫民区的居民也许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居住状况,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居住隔离。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会通过价格机制的筛选影响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
假设2:邻里选择时,外生效应和内生效应会同时对社区的期望起作用。
假设3: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会趋利避害,迁居行为会导致居住隔离程度的进一步加大。
三、数据来源、模型选择和变量描述
本文以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内在逻辑,对提出的相关假说做出实证分析。利用调查问卷的数据,首先从邻里选择的角度实证假设1和假设2,其次从迁居流动的角度实证假设3。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8年以“大连市小区居住情况”为主题的社区抽样调查活动。在大连市区范围内随意选取5个社区,通过对物业的调查中了解到这5个社区大约有8 500户居民,以1∶20的比例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450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数为430份。经计算,检验信度的Cronbachs α值为0773,检验效度的KMO值为0819,均大于0700,且Bartlett统计值均显著。因此,问卷满足信度和效度的要求。
(二)模型选择
1居住隔离指数——P指数
本文要研究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那必先用数据验证作为研究样本的大连市当前是否存在居住隔离的现象。由于中国社区是由不同收入、学历、工作单位等不同身份的居民组成,所以本文采用考虑空间维度和多群族居住隔离的P指数来验证,其计算公式如下:
P=∑kN2k·(1Nk)2∑i∑jniknjkf(dij)N2·(1N)2∑i∑jninjf(dij) (3)
其中,Nk表示研究区域内k群体的总人数,N表示研究区域内的总人数,Nik表示分析单位i中k群体的人数,ni表示分析单位i的总人数,njk表示分析单位j中k群体的总人数,nj表示在分析单位j中的总人数。f(dij)表示的是两个分析单位i和j之间的空间距离函数,通常用e-dij表示。若P指数大于1,证明相同族群的人更愿意聚集在一起[14]。
2基于邻里选择的线性均值模型
对于邻里选择引起的空间分层,本文采用线性均值模型实证验证,即:
wa=z+cXa+dYb+Jmb(a)+ζa(4)
其中,Xa表示可观察的个人特征,Yb表示作为外生效应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mb(a)表示邻里成员的期望值。这一等式通常被称为线性均值模型,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假设所有内生效应通过期望起作用,当消费者是主观理性时,wa=mb(a)。那么移项可得:
mb(a)=z+cXb(a)+dYb(a)1-J(5)
其中,Xb(a)表示Xa的邻居平均特征,可以得知每个社区中邻居的整体平均情况,如果不同社区的邻居平均特征存在差异,且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或房价有一定的对应,即可说明不同人群在空间上是分层的。
3基于迁居选择的Logit分析
从迁居选择这一角度来说,本文调查了社区居民的迁居意愿,问卷中选项分别为当前无迁居意愿、想迁居至公共服务完备的社区、想迁居至志同道合朋友的社区、想迁居至环境优美的郊区别墅和想迁居至能够彰显身份的高档社区5个选择项。由于这5个选项作为因变量没有固定的排列顺序,且作为选择态度、行为的事件是离散的、虚拟的,因而本文采用多类别Logit模型,从而能够较好地区分不同人群的迁居意愿,并分类总结。
(三)变量描述
对于邻里选择引起的空间分层,核心自变量是作为外生效应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作为内生效应的社会资本收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以问卷打分(以1—5分进行评价)的方式对常见的医疗、教育、物业管理、零售和交通5个方面具体分析。社会资本收益是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出现,而个人特征与社区共服务水平影响社区居民的身份地位,对此,将采用路径分解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用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为社会资本收益的代理变量,以邻居的平均月收入、平均学历、平均工作单位类型三个方面来具体表示,并且以最能代表一个人身份特征的月收入、学历、工作单位三个变量表示个人特征,为缩小月收入的绝对数值,本文取其对数后进行回归分析。核心因变量为居民的期望,即社区居民购买住宅时期望的社区档次,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所调研社区的档次按1—5赋值。
对于迁居选择,从之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影响家庭迁居的因素很多,如家庭的生命周期、结构与规模、社会关系等,但考虑到影响居住隔离经济地位的逻辑起点和改善性住房等现实的因素,所以在考虑个人特征和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房屋面积这个自变量,因变量为迁居意愿。因此,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居住隔离的存在性分析
对于居住隔离指数中所说的k群体进行划分,可以用收入、职业、种族等来定义,简单起见,本文以月收入来定义k群体,并按月收入5 000元以下、5 000—10 000元、10 000—15 000元、15 000元以上四个收入区间段划分,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每个群体的人数,通过地图可以获得不同社区之间的距离,带入公式中计算出居住隔离指数P为3510,大于1,这说明了大连市存在居住隔离现象,本文可以继续做下一步的研究分析。
(二)邻里选择与居住隔离
表2为路径分解结果。由VIF检验可知,模型1中社区邻居平均学历、平均月收入及平均工作单位类型的VIF值远大于10,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但出于对整体负责的态度,不继续对单因素变量标准化深究,去除不显著的路线。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各变量VIF检验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1总体来看,F值为9 554800,模型整体拟合较好。衡量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医疗、教育、物业管理、零售业四个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交通在5%水平下显著。衡量社会资本收益的社区邻居平均月收入、平均学历、平均工作单位类型三个变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而个人特征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作为内生效应的社会资本收益和作为外生效应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对社区的期望起直接作用,假设2成立。在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中,除了零售业之外,其他四个变量都呈显著正向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连市的部分商圈规划较早,周围老社区较多,居住舒适感相对来说不如其他新社区。
模型2的因变量为社区居民的平均学历,月收入、工作单位在1%水平下显著,医疗、教育、物业管理和零售业四个变量显著为正;模型3的因变量为社区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学历、月收入和工作单位都在1%水平下显著,医疗、教育和物业管理显著为正,交通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模型4的因变量为社区居民的平均工作单位类型,月收入和工作单位在1%水平下显著,医疗、教育、物业管理和零售业四个变量也都在1%水平下显著。尽管由于选择的样本城市、样本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样本的“个性”,个人特征与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不同身份的人对社区公共服务看重的侧重点也不同。综上,个人特征和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会影响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因而假设1成立。但是,从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横向来看,个人月收入显著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因为收入是购买社区住宅的必要條件,通过价格机制的筛选,会影响到社区居民的整体层次。
本文在结果中发现了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与社区居民的平均层次对社区的期望起直接作用,因为社区不仅包含地理空間的意义,还包含社会意义。Denton[2]认为一个人住在哪里,尤其是他生长的地方,对其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地理空间上来说,选择便捷的公共交通,工作地点就可以不必拘泥于社区周围,能够寻找更好的工作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不少家庭愿意择校而居,因为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对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着以后的人生道路及命运。这些物质基础导致的居民空间不平等分布其实既是贫富差距的结果,或许又是新的一轮贫富差距的来源。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虽然作为一种外生效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人们对社区的选择会格外看重。从社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围墙文化,演变到今天,或许是现在所看到的社区“门禁”。尽管社交电子网络越来越发达,邻里之间的物质利益渐渐消失,彼此之间的情感也比较疏远,从邻里社会资本的层面来说,它包含着工具性网络和情感价值网络,即使平日接触不多,但拥有相似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的个体,会因为居住地点获得不同经济社会成功的比率,并且它对于个人的满足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种社会优越感的存在。不少学者针对邻里效应做出研究,陈宏胜等[15]以广州市保障房为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对周围社区的消极影响不大,但“贫困符号”的存在,商品房居民与保障房居民接触很少。所以,不论是外在的公共服务还是周围的邻居,都对人们选择社区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公共服务通过影响价格导致了不同居民在居住地点的差异,但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的存在使得不同社区的居民平常没有来往,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一般,所以彼此“隔离”了起来。
(三)迁居流动与居住隔离
由于多类别Logit模型要区分不同特征变量发生的概率,因而要选取相应的对照组,所以本文选取学历为高中及以下、月收入为5 000元以下、工作单位为政府/事业单位、住房面积为60平方米以下这四个变量为各自的对照组变量。迁居意愿结果如表3所示。
从五组数据的整体来看,LR chi2(18)的值较大,整体回归拟合效果较好。对表3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第一,对于当前无迁居意愿的结果中,专科、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居民相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不迁居的概率更大一些。从收入来看,月收入为10 000—15 000元和15 000元以上的居民无迁居意愿的概率分别是对照组月收入为5 000元以下的1407和2020倍,这间接说明了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居住稳定性差一些。从工作单位来看,虽然国有企业、外资/合作企业、民营/私营企业、个体自营的居民不迁居概率都比政府/事业单位的居民大,但这一角度的解释力比较弱,因为迁居这件事终究要和收入挂钩。从住房面积来看,居住房屋面积为60平方米以下的居民,相比居住房屋面积较大的居民,不迁居的概率较大。从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来看,社区物业管理水平较好和交通便利的社区居民不迁居的概率较大。这一组结果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低学历、低收入水平的居民,居住流动性高。二是居住房屋面积较小的居民,或许没有能力迁居至更好的社区。三是居住在物业管理水平较好和交通便利的社区居民,可能满足于现状,对于迁居的意愿并不大。
第二,对于想迁居至公共服务完备的社区的居民,本科学历的迁居概率是对照组的1142倍,月收入和工作单位无显著的选项。居住面积为60—90平方米和90—120平方米的居民对比于居住60平方米以下的居民,迁居至此类型社区的概率低,可能自身所居住的社区本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而周围零售业发达和交通便利的社区,迁居至公共服务完备的社区概率越大,虽大连交通比较发达,但教育等公共服务并不是特别完善,不少家庭有进一步的需求,而且靠近商圈的社区规划都比较一般,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
第三,对于想迁居至志同道合朋友的社区,这一选项看似在现实生活中不现实,但可能为本文解决社区居住隔离提供思路。因为这项结果涉及的人群种类比较多,迁居意愿比较大的有月收入为5 000—10 000元和10 000—15 000元的居民,国有企业和民营/私营企业的员工,也包含着现在所居住的社区公共服务也比较完善的社区居民。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志向、兴趣,这似乎就与身份、地位联系没那么密切。
第四,对于想迁居至环境优美的郊区别墅,结果显著的变量只有一项,即个体自营的居民;对于想迁居至能够彰显身份的高档社区,结果显著的变量分别是月收入为15 000元以上,现有住房面积为120平方米以上的居民。其实这间接说明了,在原有住宅的基础上,这部分居民有迁居至更好社区的意愿。
从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想迁居至能够彰显身份的高档社区来说,这既是个人需求的改变,也是进一步对空间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对于个体自营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这不仅仅是事业成功的体现,还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优越感,因为在这里可以获得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多的社会资本收益,也更能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说,在当前无迁居意愿的结果中,本文得出低学历、低收入水平的居民,居住流动性较高的分析,之前的学者有专门针对棚户区等住所居民的探讨,发现这部分居民的住所与工作地点极为相似,且经常跟随工作地点迁居[16]。结合邻里选择模型,可以看出,在经济基础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迁居至更好的社区,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依然是为生活所迫四处流动,这就导致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分化,居住隔离程度也愈加严重。因此,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假设3,迁居行为会导致居住隔离程度的进一步加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Schelling居住隔离模型虽给了本文很大的启示,但由于中国现实条件的特殊性,使得种族或收入无法简单地解释大城市现存的居住隔离现象。虽然个人收入水平造成了住房差异化,但这更多解释的是居住分异,是一个表象,因为从最初的理论模型中就已经暗示出身份地位是造成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居住隔离终究隔离的是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于是本文构造了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实际提出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是造成居住隔离的逻辑起点,并从邻里选择及迁居流动两个方面具体实证分析。
从个人角度来看,收入是构成购买住宅的刚性条件,但学历和工作单位会影响到个人收入,这三者不仅构成个人层面的经济地位,还影响着进入社区的门槛,但公共服务的完善程度又影响着“进入门槛”。而社会资本收益的存在,更多的是影响着居民内心对邻居认同感,甚至荣誉感,以及社区文化资本,是否有利于个人及儿童成长,这使得富有的人不会选择贫穷的邻里,也不会主动来往,造成了居住隔离。关于迁居流动,验证了迁居会导致居住隔离程度的加大,其实这也在侧面反映了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果不及时遏制,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居民个人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与职业素养。如积极参加各类学习活动、线上教育等,通过各种培训,提高技能素质、职业道德以挖掘自身的潜质,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于获得与心仪的住宅价格相匹配的收入。
第二,政府或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服务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价,也影响人们对社区的选择。完善的公共服务,一方面会惠及更多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会降低社区的相对价格,吸引不同层次的人群融入小区,降低城市内部由房价带来的隔离程度。
第三,构建新的社会资本网络。培育非正式的社会资本网络和文化形态,强化邻里之间以兴趣爱好为主线的互动,既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示范效应”,又可以增强邻里间的感情,这将对城市社区空间的重构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冯云廷居住隔离、邻里选择与城市社区空间秩序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2018,(9):71-77,158
[2]Denton,MNA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J]Social Forces,1988,67(2):281-315
[3]黄怡住宅产业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以上海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2001,(4):40-43
[4]陆佩华,王英利江苏城市居住隔离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36-141
[5]李倩,张文忠,余建辉,等北京不同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状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12,(6):693-700
[6]张可云,杨孟禹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5,(12):99-110
[7]杨菊华,朱格心仪而行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16,(1):78-89
[8]戚迪明,江金启,张广胜 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4):141-148
[9]孙秀林,顾艳霞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以上海为例[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20-129,148
[10]Schelling,TCModels of Segreg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2):488-493
[11]李春玲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J] 江苏社会科学,2004,(6):108-112
[12]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对21世纪权力、城市和城市主义的批判性介绍[M]玉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8-126
[13]Bourdieu,P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J]Theory and Society,1985,14(6):723-744
[14]White,M J ,Wang,R ,朱格,等居住隔离论: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16,(1):96-106
[15]陈宏胜,刘晔,李志刚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周边社区为例[J] 人文地理,2015,(4):39-44
[16]齐心 北京市内流动人口迁居研究[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2,(4)17-2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Dalian
FENG Yun-ting1 ,WANG Ya-n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However,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s that it is more focu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hierarchy caused by economic status in urban spatial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isolation model,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ial iso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Dalian City Community Living Situ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neighborhood selection and reloc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under the choice of rational economic people,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and endogenous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gains as an exogenous effect and their expectations for the community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strat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families in the urban community space The flow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severity of community segreg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residence isolation;economic status;neighborhood selection;relocation
(責任编辑:尚培培)
收稿日期:2019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居住隔离、邻里选择与城市社区空间重构” (18YJA790022)
作者简介:冯云廷(1958-),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Email: Fengyt330@tomcom
王亚男(通讯作者)(1993-),女,山东蓬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Email:155423467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