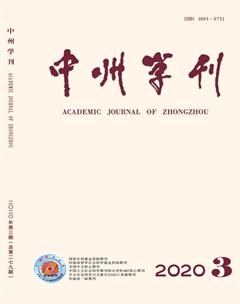阶段性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路径构想
徐楠
摘要: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止论与保留论都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与不足,以保障人权为基础的阶段性废除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路径。现阶段应从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明确以死缓为主、死刑立即执行为辅的死刑适用机制;下一步应剥离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先行废除罪质较弱的受贿罪的死刑,为全面取消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创造条件;在影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的诸多社会疑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全面废除该类犯罪死刑就水到渠成。
关键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逐步废止
中图分类号:D924.3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072-04
作为死刑存废之争的议题之一,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存废一直备受争议。面对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路径是刑法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需要长期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一、逐步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法理依据
1.废止论与保留论均存在缺陷
现行刑事立法方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预防。有学者认为,作为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复,刑罚蕴含两种不同的报应思想:一是等害报应思想,即刑罚与犯罪行为的损害形态应当具有对等性;二是等价报应思想,即对犯罪人刑罚的强弱程度应取决于其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①等害报应思想注重形式对等,等价报应思想则要求价值上的等同。就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而言,支持废除论者大都赞成等价报应思想,因为贪污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及公私财产,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尽管严重,但与个人生命受到侵害相比明显不具有等价性。保留论者则从社会接受的可能性出发赞成等害报应思想,认为与精英阶层的认识不同,基于我国悠久的死刑文化传统以及目前仍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现实,一旦出现重大贪腐案件,市民阶层往往基于其朴素的正义观,赞成适用死刑。这就造成不同群体从不同立场出发对罪责刑相适应中“报应”的理解存在差异。从应然的角度看,保留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但从实然的角度看,当前保留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符合大多数公民的正义观念,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可见,废止论或保留论的论据都没有深入剖析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的本质问题。笔者认为,以保障人权为基础的阶段性废除论才是我国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必由之路。
2.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
作为制定刑事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含义之一是刑罚谦抑,即刑罚的界限应是内缩的,刑罚仅作为其他手段不能达到保护法益之目的时的补充。目前,刑罚方式已经由残忍报复型转变为相对谦抑型,彰显教育感化的功能,给予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贪污受贿犯罪而言,该类犯罪中并没有暴力行为,并不危及他人身体权与生命权,而且犯罪人大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与能力积淀,判处其死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的损失。可以通过判处长期自由刑和相当数额的罚金,以没收财产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方式替代死刑,使犯罪人在监狱中悔过自新,发挥其剩余的社会价值。
3.综合多方面国情的选择
与有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全面废除死刑不同,当前我国并不具备完全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环境和条件。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根植于其社会文化。延续几千年的死刑文化一直是我国刑罚文化的主流,死刑具有报复与威慑功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决定了我国废除死刑不能一蹴而就,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废除自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制度改革处于民意感性认识和立法者趋于理性认识相互影响的阶段。尽管民意不能干扰立法或司法,但立法和司法要充分考虑民意。贪污受贿犯罪破坏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众对此类犯罪深恶痛绝,国家也一直对此类犯罪保持零容忍的态度。此类犯罪中犯罪主体曾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经历,难免会使个别案件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会造成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为遏制此类乱象,通过立法引入终身监禁刑作为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犯罪死刑废除的过渡措施具有合理性。
4.符合国际司法协助需要和人权保障潮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死刑犯不引渡是国际司法的通行原则,如果国内贪污受贿者外逃所至国家的法律对贪污受贿犯罪只规定处以自由刑与罚金,而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中设置有死刑,就会给引渡或遣返外逃贪污受贿者带来法律上的困难,极大地阻碍追逃追赃工作。并且,我国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必须与有关国家的司法机关达成协议,承诺对被引渡或遣返的贪污受贿者不判处死刑或者判处与按该国法律相同的刑罚,这极易使我国司法中出现同案不同判或者同案不同罚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与数额相似却没有外逃的贪污受贿犯罪人而言显然不公,在某种意义上会助长贪官外逃。可见,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有助于打击贪腐行为,促进相关国际司法协助。另外,人权法理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重要依据之一。逐步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可以展现我国保障人权的决心,也能使我国追逃追赃工作获得更多国家的更大理解和支持。
二、现阶段从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条件
我国人口众多,犯罪基数大,社会治安状况还比较严峻,贸然废除死刑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混乱和危害。现阶段应从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条件,这样既能保持死刑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威慑功能,又可以有效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1.对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进行司法控制
从立法上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制度设计耗时较长且面临多方压力,在此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进行司法控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只有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才能使立法上限制死刑的精神得到贯彻,从而切实推动死刑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个案比法律条文更具有指导和教育的作用,对个案中死刑的从严裁判更能使民众感受到慎用死刑的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严格把握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的条件。首先,充分发挥“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中个案裁量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贪污受贿案件中死刑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其次,从严把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一法定情节。明确裁量标准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的客观要求,但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未对“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一裁量标准具体化。在当前情况下,法官必须对个案裁判从严把握死刑适用标准,以实现控制死刑适用的目的。最后,适度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预防情节的认定。特殊预防原则上不得逾越罪责刑均衡的界限,量刑时应贯彻目的主义,协调责任和预防的关系。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或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以及自首、坦白、立功等都属于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预防情节。②具体而言,一是从严认定死刑预防情节。以《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第3款为例,该条款将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事实法定化,正是基于这些事实构成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现实依据。二是合理认定法定预防情节的作用。《刑法》将自首、坦白、立功作为法定从轻减轻预防情节具有正当性,只有对法定预防情节进行单个情节的作用认定,才能避免情节竞合时重复评价。③三是重视酌定预防情节的认定。对于全额追缴赃款和拒不认罪两种情节,在个别案件中存在司法机关不承认其应有地位,致使审判中出现对从宽处罚情节评价不足④和对从严处罚情节重复评价⑤的情形。裁判者只有综合全案,考虑所有预防情节,才能充分发挥从宽处罚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功能。
2.建立死缓和终身监禁刑适用的常态化机制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特别严重的贪污受贿犯罪设置了终身监禁的刑罚制度,最大限度地适用该制度,可以对严重的贪污受贿犯罪进行有力有效的刑事处罚。因此,可以将死缓和终身监禁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阶段性替代措施。首先,死缓和终身监禁制度符合严惩贪腐犯罪的民意诉求。对严重贪腐犯罪人适用死缓制度,既从形式上沿袭对重大贪腐行为适用最高刑罚的传统,又符合民众要求严惩贪腐犯罪的愿望,同时给予贪腐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和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次,死缓和终身监禁刑适用的常态化为废除死刑奠定基础。《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提升了处以死缓的犯罪人被执行死刑的标准,使死刑的执行更加严格和谨慎。将死缓和终身监禁制度在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制裁中常态化适用,可以使社会公众逐步适应事实上无死刑的刑罚机制,为事实上废除死刑奠定基础。再次,废除死刑不影响防治贪腐犯罪目的的实现。贪污受贿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并不直接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综观国际通行做法,职务犯罪不属于必须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⑥并且,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中几乎包括所有刑罚措施,即使废除死刑,刑罚结构仍属于重刑主义,足以实现惩治和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法益保护目的。⑦最后,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对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比率极低⑧。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死缓和终身监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三、先行废除受贿罪死刑的设想
很多国家在刑法分则中对罪名的形式安排是,通常在单一罪名后设有独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应的法定刑。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受贿罪共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贪污罪和受贿罪尽管同属职务犯罪序列,但在行为方式、侵害法益、犯罪数额与利益损失的比重等方面均不相同,二者共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不尽合理。可以尝试先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相分离,再逐步废除受贿罪的死刑,进而实现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
1.贪污罪与受贿罪存在明显不同
贪污犯罪往往有较多直接证据,随着我国会计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财政制度的健全,贪污犯罪行为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但受贿犯罪涉及处于利益共同体中的行贿、受贿两方,行贿方式具有多样化、隐蔽性的特点,使得受贿案件的侦破和查处都较为困难。另外,贪污罪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受贿罪主要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⑨通常情况下,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整体上小于相同数额的贪污罪。在对贪污罪定罪量刑的场合,侧重于体现此类犯罪“计赃论罪”的本质,先考虑数额因素,再考虑情节因素;而在对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场合,侧重于体现此类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先考虑情节因素,再考虑数额因素。因此,在受贿罪死刑裁量过程中,要适度降低受贿数额对死刑判决的影响,合理加大利益损失等情节对死刑适用的调控力度。
2.分离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决定罪行轻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刑事责任大小则由反映行为客观危害(即违法性)及行为人主观恶性(即有责性程度)共同决定。特别巨大的数额和特别重大的损失构成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的责任情节,量刑时要重视责任和预防的关系,科学评价责任情节,这有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⑩贪污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既取决于数额大小,又表现在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情节中。B11确立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标准,将加大利益损失情节对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的调节作用,有利于死刑裁量的均衡和限制死刑的适用。B12因此,剥离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可能更为合理、更加科学,针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受贿犯罪更易于制定较为宽松的定罪量刑标准。
3.先行废止受贿罪适用死刑的规定
虽然实践中受贿犯罪的发案率较高,涉及的犯罪金额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受贿人就应当被判处死刑。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逐步健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类犯罪呈现出贪污罪数量较少、受贿罪占比增大的局面。B13如果取消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死刑配置,将引起司法实务中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率骤降,这有助于调整民众对腐败犯罪等非暴力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观念,进而为全面取消贪污受贿犯罪死刑乃至全面废除死刑创造条件。另外,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而隶属于职务犯罪的贪污受贿犯罪显然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域外针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刑事立法通常规定受贿罪的处罚方式是自由刑和罚金刑。B14笔者认为,在分设贪污、受贿二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基础上先行废除受贿罪死刑的立法配置,是比较可行的选择。
四、適时全面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
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废除和整个死刑制度的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可以待时机成熟时全面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死刑观念的转变也必须以司法实践为载体。通过司法实践的逐渐推进,最终全面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这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和方向。一方面,长期以来以死缓为主、死刑立即执行为辅的死刑适用机制以及先行废除受贿罪死刑,会大幅度削减贪污受贿犯罪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终身监禁刑的确立与适用又使死刑立即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替代措施。另一方面,在进行充分的学理论证及舆论宣传、强化司法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回应公众的疑惑,先行废止受贿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有助于培养民众对废除贪腐犯罪死刑的忍耐度、适应力与接受力。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废除不只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难题。大力整顿吏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将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废除创造外部环境。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废除必将极大地推动死刑制度改革向更加科学的方向迈进。
注释
①陈金林:《从等价报应到积极的一般预防——黑格尔刑罚理论的新解读及其启示》,《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
②李冠煜:《刑法方法论视阈中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基准——以“张中生案”为切入点》,《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③孙国祥:《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④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6页。
⑤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
⑥葛海、夏芬芳、毛育军:《职务犯罪轻刑化实证分析》,《法制博览》2015年第31期。
⑦王志祥:《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⑧刘雪斌、钱伟强:《死缓适用影响情节的实证研究——以614份故意杀人罪一审死刑判决书为分析样本》,《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陈俊秀:《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法治逻辑悖论——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⑨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⑩李冠煜:《刑法方法论视阈中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基准——以“张中生案”为切入点》,《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李冠煜:《贪污罪量刑规范化的中国实践——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的案例分析》,《法学》2020年第1期。
B11雷建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B12王瑞剑、张兆松:《贪污贿赂犯罪二元定罪量刑标准的情节适用问题——基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分析》,《天津法学》2017年第2期。
B13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守护国家法治生态——2014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分析》,《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7日。
B14赵赤:《中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法治的要素比较与启示借鉴》,《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林墨
Conception of Gradually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
Xu Nan
Abstract: There a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theory of abolition and retention of death penalty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 The gradual aboli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uts forward a more reasonable path of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 At present, we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and make clear the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suspended death and supplemented by immediate execution of death penalty; next, we should separate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for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 of bribery with weak quality of crime in advance,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an all-round way; finally, when many social issues a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are properly resolved, it is natural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for such crimes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death penalty; gradual abol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