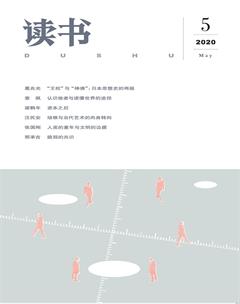潘光旦笔下的“冯小青”及其他
曹晓华
潘光旦(一八九九至一九六七),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其时,潘家在宝山颇有声望,潘父潘鸿鼎(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五)为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进士,五年后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任宝山县清丈局局长。潘光旦天資聪颖,幼承家学熏陶,十四岁入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期间,潘光旦学术涉猎广泛,据他自己回忆,对其影响最深的还是霭理士(Haveloc kEllis)的性心理学。当时他在图书馆里看到的还是六卷本的《性心理学研究录》,二十年后他翻译了霭理士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性心理学》〔原名《性心理学:学生手册》(Psychology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并逐章加注。《性心理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研究录》,相当于《研究录》的简化版。潘光旦认为这更适合作为中国人的入门书,因此选择了这本书进行翻译。在《性心理学》的译序中,潘光旦回忆自己读霭理士之前唯一接触到的关于性心理的书,是自己十二岁时父亲去日本考察带回来的一本关于性卫生的书。见潘光旦翻阅此书,潘鸿鼎并不阻拦,而是觉得读之无妨,潘光旦多次回忆这件事,引为自己走上性心理研究道路的铺垫。
一九二二年,就在成为霭理士的“私淑弟子”后没多久,潘光旦读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Psychoanalysis ), 旋即在梁启超“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的课堂上交出了一份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自恋人格的作业—《冯小青考》。冯小青, 明万历年间人,十岁有老尼口授心经,一遍成诵,聪慧非常。老尼担心小青早慧早夭,一语成谶。小青嫁与冯生作妾,大妇善妒,将其囚禁孤山别室,断其与冯生往来。小青终日顾影自怜,对镜而妆,虽有友人杨夫人相助,得以诗书相伴,两年后仍郁郁而终。文章根据支如增的传记展开推断, 认为冯小青婚后不幸,有佛缘却无宏量,死于极度病态的“影恋”(自恋,arcissism)。这篇作业获得梁启超的激赏:“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这段评语对潘光旦而言意义重大,当时他因意外受伤而截肢,一度耽误了赴美求学的行程。一九二四年,就在潘光旦留学两年后,《妇女杂志》刊登了这篇《冯小青考》,后又有新月书店邀约,加上“精神分析之性教育观”等内容,整理成《小青之分析》,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一九二九年再版该书时,潘光旦不忘加上梁启超昔日的评语,并更名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

《冯小青》再版内附的梁启超评语
这是冯小青这位扬州女子第一次出现在潘光旦笔下,却几乎包含了潘氏毕生治学的线索。若是换作别人,对冯小青之死的分析可以成为一个父权压迫的典型案例,但是潘光旦却另辟蹊径,由性心理分析而及其他。他对门第和社会阶层的认识,决定了他会从其他的角度切入这个历史事件,也预示着学成归来的他会用另一种眼光观察中国的社会万象。
一、从个体心理到社会群体观察
潘光旦曾认真解释过《冯小青考》的学理来源,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虽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也涉及“影恋”论述,但这部分内容要在一九二八年霭理士增订的第七卷上才能看到。而在潘氏翻译的《性心理学》中,第三章就涉及了“影恋”的内容,潘光旦表示经过对照,觉得在霭理士认真论述“影恋”之前,自己在《冯小青考》中用的分析方法和霭理士后来面世的论述方向大体无差。从潘光旦所译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霭理士的“影恋”论述,不如说是霭理士梳理了精神分析学派对“影恋”的认识。而潘氏自己在这节加的注释,不仅详细回顾了自己研究冯小青的过程,还意犹未尽地摘录了宋代薛琼枝的“影恋”之症。
潘光旦并不只是对性心理学好奇,他更强调以性心理学研究窥得国人两性观念的症结,继而对相关的中国社会问题给出解答。这种学术旨趣也贯穿了他的留学经历,虽然在达特茅斯学院通过学习生物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时,他从动物学转为研究与社会现实更加贴近的优生与遗传学。在《 冯小青考》里,潘光旦认为中国社会常认为女性“不祥”,或为“玩物”,“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这是放在文章余论中的主要观点。社会偏见致使女性留下的文字也郁郁寡欢,于是,潘光旦还对清代女性词作中的“愁”“病”等“消极词”做了词频统计,以《女子作品与精神郁结》附于《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书后。
至此,对冯小青个体心理的案例分析,成为对整个女性群体乃至中国社会女性观念的观察。“性心理—性别群体—社会问题”的观察线索,对于潘光旦来说还有治学之外的意义。作为一个嗅觉敏锐的报人,他对社会新闻的关注也带上了研究冯小青的影子。一九三二年,西湖艺专女生刘梦莹被同学陶思瑾杀害。两名女生原是挚友,一动一静,性格互补,陶思瑾虽内向却有暴力倾向,刘梦莹则控制欲极强,无法容忍陶思瑾有异性恋人,最终陶思瑾勒死了刘梦莹。一时间闺蜜反目、女生同性恋、精神异常等夺人眼球的报道屡见于沪杭报纸。同年,潘光旦主编的《华年》正好在上海创刊,他数次撰文报道分析这起凶杀案,却并未落入标题党的窠臼,而是从妒杀案的心理背景入手分析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他先是用性心理分析“陶刘的同性爱,和因恋爱而引起的强烈的妒意,都是事实”,“陶思瑾杀刘梦莹,不但出乎嫉妒的心理,并且出乎因嫉妒而生的被迫害的幻感”(《华年》,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一期,4-5页),接着“用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又可以作三方面分别端详:一是精神病专家的缺乏,二是精神病疗养院的亟宜组织,三是学校教育的心理卫生问题“(《华年》,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二期,25页)。学生情杀的案件,不仅可以作为被害妄想和同性恋的案例,还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国人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疏导的漠视程度。陶刘妒杀案由此及彼、管中窥豹的研究路径,与冯小青的“影恋”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潘光旦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对女性生存的影响,他也并未将自己的考察视角上升为一种“五四”断裂式的伦理批判,而是从优生和遗传的角度对传统社会机制加以分析,从中获取合理的机制阐释。
二、优生学与自我“归咎”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潘光旦在美国留学期间除了先后完成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常规课程,还在其他机构选读了一些课程,包括在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的优生学馆(EugenicsRecord Office)学习了优生学、人类学和人体测量的相关课程。在冷泉港的学习使潘光旦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学术重心,与优生学馆负责人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的结识使他接触到了美国优生运动的理论核心。达文波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优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以A 先生的事例说明优生运动清除精神失常者的合理性—“A 先生疯癫的原因可能是生意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工作太过繁重,但是成百上千的人都遭受过巨大打击,而他们继续工作,并没有精神崩溃,所以A 先生发疯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抗压力不够”(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Heredityin Relation to Eugenics ,NY: Holt, 1923, p. 254)。达文波特将个体身心素质置于社会环境之上,这种强调优胜劣汰、筛选不合格个体的想法深深影响了潘光旦。
对于潘光旦来说,留学过程中感受到的不仅有种族偏见,还有自己的身体残疾带来的歧视,这种双重的心理落差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对国民的身体素质极为关注。优生学家认为遗传和婚姻都可以起到改善人种的作用,潘光旦也不例外,只是他更倾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适者“各安其位”的理由,比如释“位育”:“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ion 或adjustment 的现象。我们很早(好像是跟了日本人)把它译作‘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原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生物,尤其是进入文化的人类,尤其是今日适当中西新旧之冲的中国青年,往往有不能安其位不能遂其生的,这种现象以前叫作‘顺应失当,如今我们叫作‘位育失当。”(《华年》,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二期,1页)潘光旦口中的“不安其位”,已经不只是教育意义上的“位育失当”,而是种族在文明和生理上的全面劣势,而这种劣势是可以通过婚配扭转的。
潘光旦认为性心理失常导致“中国女子之体力脆弱,精神郁结者,为数必大”(《冯小青》,84页),继而又因为自恋推及为对恋人“性的过誉”,如此种种“主观”因素都会影响择偶婚配(95页)。小青之死,在潘光旦看来,虽有外因的逼迫,但更重要的是她体弱,罹患心病又不愿医治。潘光旦虽然也写到了社会对女性的“不谅解”,但却用另一种指向个体自我的“归咎”方法为小青死于自己体(心)弱找到了证据。对国民身体素质和文明落后程度的“耻感”,也不仅是潘光旦一人的想法。清末一直到民国时仍屡有提及的“人种改良”,为急于找到“治病良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加速国族“现代化”的灵感,周氏兄弟三人以及严复、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陈长蘅等人都发表过优生优育以实现人种改良的言论。达文波特笔下神经脆弱、无法抗压的A先生,成为要被淘汰的劣势群体象征。
三、性别角色期待与社会阶层流动
一九二四年,就在发表《冯小青考》的同年,《东方杂志》刊登了潘光旦最新的理论成果《中国之优生问题》。当时有优生学馆的研究生认为中国的包办婚姻是优生婚姻的一种,潘光旦深以为然—“个人选择易偏于浪漫的恋爱一方面,其于对象之适合于相家生子之事与否则易于忽略不顾,家长之选择反是。”(《东方杂志》,一九二四年第二十二号,21页)家长对子女婚姻的介入有利于个体繁衍的质量,优化了社会选择,这种观点在潘光旦日后的治学中逐渐强化。在民国三四十年代“妇女回家”的宣传下,他进一步提出了“新母教”。“新母教”包含“择教之教”“择父之教”“胎养之教”“保育之教”和“品格之教”,其中“择教之教”重新阐释了“学养子而后嫁”,“择父之教”则教育女子如何慎重选择夫婿,至于“胎养”“保育”和“品格”则分别对应了女性怀孕、育儿启蒙、入学后的德育培养等阶段(潘光旦:《优生与抗战》,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七年版)。作为潘光旦优生学研究的一部分,“新母教”可谓优生学在地化的一种尝试,保留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性别伦理剧变的强烈关注。如果回头再看潘光旦留学期间的这篇《中国之优生问题》,可以发现他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包办婚姻、望族联姻、科举取士等种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描述,对其中合理性的开掘和取舍,包含了潘氏后来多部论著的雏形。这些论说的基本立足点,便是对西方舶来的个人主义和德谟克拉西持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些迅猛的思潮对重视家族繁衍的中国社会来说并不合适。“新母教”在抗战期间提出,是潘光旦作为优生学家对战火中中国家庭教育陷入困境的回应,但其中对女性相夫教子角色的期待,有性别固化之嫌,一度引发争议,遭到女界挞伐。
潘光旦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关注,与中国社会阶层的现实紧密相关。优生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是达尔文的表弟,他很早就关注中国科举,并以一母二父先后产生两状元为例,指出天赋来自遗传(Francis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 DAppletonandCompany , N.Y.:1884:335)。对高尔顿这段论述的引用不仅出现在一九二四年的《中国之优生问题》里,还出现在潘光旦一九三四年完稿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甚至在一九三七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里也能看到类似观点的影子。潘光旦通过分析伶人因为外人歧视等原因而产生的“阶级的内群婚配”(classendogamy),总结出培育伶才的社会文化和生理因素。他熟知苏洛金(Pitirim Sorokin,今译索罗金)所著《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中关于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的观点,不仅借以分析伶人家族,提出要适当拓宽伶人的社会交际和择偶范围,还继续分析了明清两代嘉兴望族,认为望族联姻积累了教育资源和身体素质优势。
潘光旦眼中的传统社会制度,有“优生”之用,且对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起到筛选和优化的功能。如他与费孝通在一九四七年联名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指出科举选拔促成优秀者婚配,以保证后代的质量。这种分析结合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对世人冲击很大,其中做的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对今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正如周建人批评《中国之优生问题》时所说:“天才是遗传的,这是事实,但天才之在当世并非即社会阶级最高的人,和中国科举中举出的状元、举人也完全是两件事。科甲中有才能者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历代以来科甲得意的人们中,有才能者却是不多。”(《东方杂志》,《读中国之优生问题》,一九二五年第八号,19页)社会运转的方式毕竟与生物演化规律有所不同,社会制度若不能因时而变,便会成为社会痼疾。周建人犀利地指出:“中国的家族主义、门第主义、科举制度,甚而至于节烈贞操,既然都是合于优生学的,那么这样合于优生学的制度行了几千年,中国民族一定应该进步了,现在中国人的文明創造力怎样,和别国生存竞争的能力又怎样呢?”(同上,22页)以科举为例,科举取士最后成为门第主义的温床,本为寒门之子提供的阶层流动可能性因为望族世家的党同伐异而变得微乎其微,阶层流动变成了阶层固化,分析其中的起伏嬗变,优生学仅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一九三五年,潘光旦收到友人所寄的《冯小青全集》。他对小青已有“情结”,只恨小青遗作甚少。友人投其所好,见有抄本搜罗诗篇比潘氏本人所考多五六倍,便寄给他翻阅。潘光旦读后发现该抄本为伪作,愤然作《书“冯小青全集”后》上下两篇,从地理、人物、诗品逐一证伪,文末又试图考证作伪之人。此时距潘光旦在清华写下冯小青文,已过十余载,而潘氏证伪以文言书就,文笔峻急,其小青“情结”可见一斑。毕竟,冯小青研究不仅是潘光旦治学生涯的起点,也是贯穿潘光旦思想嬗变的草蛇灰线。以小青研究而及其他,亦可回眸百年来近现代学人治学形态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