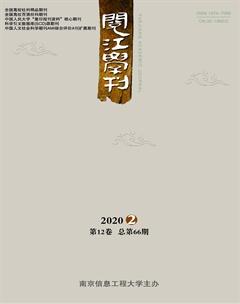伽达默尔“效果史”意识的互文性阐释
摘要: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意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同时也是理解阐释学独特内涵的一把钥匙。真正的阐释学思想不可能对自身的历史性视而不见。只有在理解的范围之内显示出“历史效果性”时,它才会成为“适宜的阐释学”,即伽达默尔所谓的“效果史”。事实上,阐释学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有关“理解”和“解释”的“效果史”。从广义阐释学的意义上说,即便“拒绝阐释”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阐释,例如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无一字绝对缘于阐释,从阐释学批评的意义上说,她的“反对阐释”更像是一种“强势阐释”。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效果史”意识是一种倡导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阐释学观念。质言之,那就是任何阐释都是某种互文性的理解与阐发,都是某种基于“效果史”的“再创造”。
关键词:伽达默尔;效果史;阐释学;互文性;《反对阐释》;《真理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2-0005-10
作者简介:陈定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效果史”与阐释学
作为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关键词,“效果史”意识是一个颇令人疑惑的复杂概念,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解其阐释学独特内涵的一把钥匙。伽达默尔对“效果史”有各种各样的表述,其中广受关注的说法如下:“理解(Verstehen)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Sein)。”而基于“理解”的“效果史”意识,其基本内涵是“历史在其中不断发挥作用的真正意识”。这一界定的意义貌似清晰明确,但是“效果史”意识这一术语本身就不能说是恰当而精准的汉语翻译。事实上,伽达默尔拈出的德语概念“Wirkungsgeschicht”,就连美国著名阐释学家帕尔默也承认它根本“无法找到任何适当的翻译。”为什么找不到恰当的“翻译”?主要原因还是它难以得到精准而恰切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译著中,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解”“解释”“说明”往往都被表述为阐释,虽然看上去似乎并无违和之感,但若细究起来,怕是难以撇清“强制阐释”的嫌疑。有趣的是,如果按照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意识理解,上述大而化之的翻译恰好是翻译的一种常态(姑且忽略那些浑水摸鱼式的偷懒或任性的翻译)。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莊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禅宗标榜“不说破”,说破了就不是禅。因为禅的奥秘是说不尽的,它像雨像雾又像风,模糊反倒是精确。所谓大道无形,真禅无相。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理解都是误解,任何阐释都是误释。因此,也可以说一切阐释都是“强制阐释”。当然,这种极端的说法并未否定阐释的必要性。毕竟,无论道还是禅,抑或真理,都离不开阐释。从广义阐释学的意义上说,“拒绝阐释”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阐释,例如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无一字绝对缘于阐释,从阐释学批评的意义上说,她所谓的“反对阐释”更像是一种“强势阐释”。因此,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效果史”意识是一种倡导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阐释学观念。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任何阐释都是某种互文性的理解与阐发,都是某种基于“效果史”的“再创造”。
系谱学阐释学(Genealogical Hermeneutics)创立者戴维·霍伊说:“一时代的文化成就在后续时代里显现的不同,会甚于更后的时代。我们看柏拉图不同于笛卡儿或康德看柏拉图,但可以肯定,我们不同地看柏拉图是由于笛卡儿和康德。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坚持本文的效果(Wirkung)是其意义的构成要素。由于这一效果因不同时代而不同,具有历史和传统,对此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史。”随着自然和社会的不断改变,现代人很难像古代人理解其自身那样理解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历史客观主义所谓“达到过去之自我理解”的设想早就被“效果史”贴上了浪漫主义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学术界形形色色的“还原历史”的探索,或许应作为“历史目的论”的理想来看待。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大胆假设还是小心求证,任何历史都是“效果史”积淀与消弭的结果。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因此,我们既没有“还原历史”的可能,其实也没有“还原历史”的必要。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不应该责备克罗齐把历史相对主义绝对化了。
就阐释学自身的发展史而言,有关它的最初起源和终极目的的研究一向广受关注,但相关探索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因为任何作品都没有终极意义,任何解释都不具有绝对准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其本质上对于漫长系列的世代来说都是相对的,只是逐步地趋于完善,或者如宇宙论、地质学和人类史,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阐释学也不例外。
第一,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对神话的理解与阐释,“阐释学”(Hermeneutics)就不会获得这个源于赫尔墨斯(Herme)的名字,当然,这门学科也可以有其他名称,但“名正言顺”的学科名称,必然会产生另外一种景象。源远流长的阐释学传统“以其古代关于荷马的解释这一光荣的起源为骄傲。后来它诉诸一种引导阐释基督教《圣经》作品的广泛理论,并将校勘和评论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文本当作文艺复兴以后值得骄傲的光辉文献。”可以说,阐释学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有关理解和解释的“效果史”。
第二,如果没有中世纪兴起的《圣经》阐释热,阐释学的基本方法和理念就难以拥有深海般的丰富资源。但如果没有施莱尔马赫创立的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阐释学的种子或许仍然隐身于权威教义诠释者的斗篷之下而无法萌芽。没有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对这株幼苗的辛勤浇灌和精心呵护,它又如何扎下认识论的根基并生长出方法论的枝干?正是由于海德格尔使阐释学立于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才使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获得了大展身手的平台。
如果抽空希腊神话、圣经解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效果史”,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大厦便立刻成了“空中楼阁”。如果把阐释学的发展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这条长河的每个河段都有代表性支流为其增添流量。
二、“效果史”与“解构主义文本”
伽达默尔的“效果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海德格尔阐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被捕捉为主体“在世之在”的道路,即主体先于任何认知或思想活动而存在的那种根本方式。尽管理解先于认知而存在,但不能最终保证捕捉到“当下处境”,不过,它可以促成进入未来的“投射”。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解释都要植根于解释者预先拥有的东西,即“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执”(Vorgriff)。“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此在现象学的逻各斯(Logos)具有诠释的性质,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将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上了。”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扬弃式地阐发了海德格尔思想。他认为,海德格尔探究历史诠释学问题并批判之,只是为了从这里按本体论的目的发展“理解”的前结构。海德格尔所关心的是如何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执”以偶发奇想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执,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海德格尔认为,警惕“前概念”以确保科学性始终是理解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
伽达默尔则强调自己更为关心的是:“诠释学一旦从科学的客观性的概念本体论障碍中解脱出来,它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待理解的历史性。”在对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结构”拨乱反正式的“再阐发”过程中,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历史性”加以整合。伽氏认为,既然“存在”已被带向任何文本或与他人相遇的偏见之中,那么,人的“处境性”就理应是阐释学理解的一个基本方面。与以前的阐释学理论不同,解释者的历史性并不是领悟的障碍。真正的阐释学思想不可能对自身的历史性无动于衷或视而不见。只有在理解的范围之内显示出“历史效果性”时,它才会成为“适宜的阐释学”,即伽达默尔所谓的“效果史”。伽达默尔放弃了那种关注影响和冲击力的新型阐释方法,转而关注一种新的“类型意识”,即“效果史”意识。“因为,在我们与过去的文献相遇时,它可以识别出业已发生的事情。它可以涵盖,不论什么情况下我们与过去对话时都会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阐释学处境。这样一来,效果史的意识就同伽达默尔的视域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传统往往被人们想当然地当作一幅毫无中断而独立发展的有机连续的平常画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传统并不存在无间断的线性发展的必然性,更不存在什么“有机生活的纯一性”。非但如此,任何传统都有丧失生气、出现僵化的可能。倘若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用革命的热情来抵制和改变僵化的传统。
事实上,传统的延续与传统的改变总体上是一种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古人强调参伍相变、因革为功,将参伍因革视为通变之术,其内在奥秘正在于此。当代文论倡导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等理念,其核心内容依然是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从理论依据上看,今人所说的“守创”与古人所说的“因革”可谓同出而异名,二者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分野。从整体性的文学发展史看,改變传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统,传统一经常态化,其内部革命的种子就开始发芽生长,“被继承”的传统会悄然转化为“被革命”的传统。传统的改变与改变的传统组成了一个类似于生生不息的耗散结构,与传统相关的千头万绪无不是促成其结构与解构的力量。“唯变为不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传统!任何传统都是各种因素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吐故纳新的“效果史”。
有道是“日往月来,时移世易”“无物永驻,万物皆流”。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传统变迁如白云苍狗。与其说历史和传统“并不像一堆能够称为意识之客体的事实,毋宁说它是一条长河,于其中,我们活动着,并参与每一理解行为。因而传统并不是对立于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置身其中并通过它而存在的某种东西: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如此透明的媒介,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它乃是不可见的东西——正像对于鱼来说,水是不可见的一样。”人类生活在传统之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
对于以虚构与想象为特色的文学而言,其历史和传统的流变更是波诡云谲,气象万千。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等观点至今仍被奉为至理名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历史与传统的变化规律。文学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以文学创作为例,大多数教科书将创作定义为创作主体的精神生产活动,即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审美体验,以语言为媒介创造出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的艺术生产活动。按照字面理解,创作的意义就是生产出具有创新性意义的作品,因此,作者必须精心“考虑做新鲜的事情,尝试做那些一直希望成为‘首创者的同时代人没做的事情。”但是,这种首创冲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尤其是随着文学艺术资源越来越丰富,创作对传统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烈。传统固然是作家期望超越的对象,但它同时也是创新无法回避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伽达默尔“效果史”所依赖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的依赖性。这种首创冲动与传统依赖的矛盾性,也为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历史的“暂时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例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不再存在任何单一的、本质的、超然的‘历史真实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霍伊对秉持“效果史”意识的伽达默尔阐释学有不少不同看法,但他基本认同伽达默尔“一切诠释皆片面”的论点。伽达默尔曾经宣称,诗歌充满了语言要成为“它所表意的东西”的愿望。这一观点对诠释理论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即诠释必然把一首诗放在诠释者提供的语境文本中:“因此诠释的词语是诠释者的词语——它不是被诠释的本文的语言和词汇。”
伽氏这种诠释者主体优先的论点,对传统文论中某些经典观点提出了挑战,如王夫之“以庄解庄”的诗学致思路径和海德格尔“以时论时”的存在论视角。因为“庄”已作古,“时”已非时,即便诠释者“设身处地”“想见其为人”,这一“设”一“想”,自然难以避免主体的偏见。有趣的是,伽达默尔“一切诠释皆片面”的结论居然成了其“自反性”的例证。
从一定意义上说,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意识与中国文论“诗无达诂”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它多少显得有些过激与偏颇。有趣的是,伽达默尔所突出的“诠释者”观念,在罗兰·巴特那里有更为激进的表述。巴特宣称,没有一个诠释是“清白的”——因为批评家是把本文置入“上下文”中的人。而意义的上下文来自批评家或读者,而不是本文!也就是说,意义是诠释者的产物,是批评家主观性的产物。
表面上看,伽达默尔和巴特在诠释的“上下文”性质和反对“纯粹客观主义”这两方面意见完全一致,但实际上,二者在相关问题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巴特认为,任何写作都可以说是对既有文本的“互文性阐释”,对于这个观点,许多像巴特一样锋芒激进的理论家基本上是当作常识接受的。他们相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的文本,那些自以为创新的人,只不过是对前人文本缺少足够的了解而已。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所有文本都只是在文本与文本之间无限的“循环阐释”过程中得以存身的。任何新生作品一经问世就必将融入既有文本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是如大江奔流的史詩巨著,也无非是为文本海洋的“循环相因”增加了些许活力而已。
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巴特貌似彻底否定原创,他的激进与偏颇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巴特的著作《恋人絮语》的中译者所言:“理论支点的有失偏颇并不意味着整个建筑的崩坍,比萨斜塔的绰约风姿不更自成一格,令人惊叹吗?思辨的过程也许更富魅力。”
巴特的《恋人絮语》与网络小清新所喜爱的恋爱小说不同,它是一部文体学上“类无归属”的奇特作品,既像哲理小品,又像散文诗,既可以称之为美学思絮,也可看作诗学随笔。其最大的文本特性就是文体的不确定性。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根本找不到进行明确界定的依凭。更为离奇的是,在巴特的这本书里,“语言不是主体意义的表达;相反,是语言铸就了主体,铸就了‘我。因此,《恋人絮语》中的‘我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无性别的、流动的、多声部的……胡话、痴言、谵语正是巴特所神往的一种行文载体,一种没有中心意义的、快节奏的、狂热的语言活动,一种纯净、超脱的语言乌托邦境界。沉溺于这种‘无底的、无真谛的语言喜剧便是对终极意义的否定的根本方式。”巴特的“絮语”有如一曲多中心、反套路的无主题变奏,它既为阐释学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新标本,同时也对以寻求终极意义为目标的阐释行为构成了绝妙的反讽。
巴特用一个副标题对这本奇书进行了定性——“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巴特的关键词显然是“解构”,他想要解构什么?是从古希腊流传至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是文艺复兴宣扬的人文精神?是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话语霸权?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只要被说成是传统的,只要被尊为权威的,就都在“恋人”的鄙视链中。巴特一向乐意在秩序井然的文本殿堂中扮演一个类似于孙悟空式的破坏者角色,他沉浸在狄奥尼索斯的精神狂欢氛围中,与读者分享狂热的“文之悦”。他既是“既有传统”的掘墓人,同时又是“新生传统”的建设者,他无意于避免尽人皆知的自相矛盾,却有意制造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奇谈怪论。他的一系列著作都充满了奇怪的悖论。“巴特宣布作者死亡,压低作家的个人性,是想冲淡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强化的个人意识,而巴特神往的摆脱一切俗成羁绊的、放纵个性的自由写作方式与自由阅读方式又陷入了一种极端的个人性,实际上,强调读者的个人阅读自由体验像强调作家个人中心一样,同属强化个人色彩,抬举个人位置。这是个悖论格局。”但是,正如巴特的学生隆巴多所说:“悖论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表达情感的修辞手法吗?”
巴特将自己的著作贴上“解构主义”标签,他高举“解构之锤”,试图一锤砸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千年铁锁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解构现象是,一直高调地自我解构的巴特,却始终未能真正地解构自我。相反,他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嘲讽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事实上,在不少学术场合,巴特是作为解构主义的一面“旗帜”出现的。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说,巴特在《文本的快乐》中劈头盖脸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我们想象一个奇特古怪的家伙,他全不怕自相矛盾,号称综合了诸多不相容的语言,说他不合逻辑,也泰然处之。巴特说,我们传统习俗的种种规矩,会使这么个人物成为无家可归的弃儿。因为说到底,谁能一无愧色地生活在矛盾之中呢?”
卡勒的《论解构》是从巴特抵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着手的。他接着对巴特的文本理论进行了探讨,并直接将其互文性理论的名言作为解构传统的武器:“文本不是一条词语的直线,释放出单一的‘神学意义,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其间无一不是独创的各类文字的交合与碰撞。文本是从无数文化中心中抽取出来的引文组织。”以创新为使命的文学艺术原本蕴含着“抵抗互文”或“颠覆传统”的潜能,但创作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任何创作者都只能在传统文本的密林中穿行,当作者披荆斩棘试图开辟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林间小道时,却发现所到之处,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前人层层叠叠的脚印隐伏其间。行文至此,可以肯定地说,结构主义的这套说辞实际上就是互文性理论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视角看,巴特的解构主义文本就是其“效果史”意识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三、“效果史”意识的互文性阐释
托多罗夫在总结文学史发展规律时曾提出过“植物式”“昼夜式”等比喻性概念,这些有趣的概念自然会有很多开放式的理解与阐释。如果借用托氏的妙喻比照一下“效果史”意识和互文性理论的关系,不禁感叹,如同植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一样,各种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效果史”意识。若以季节说比附一下艾布拉姆斯的“四因素”理论,会发现在20世纪文论与批评的舞台上,“四因素”之间存在着激烈的“领导权”竞争,结果出现了季节性的“轮流执政”。当厚德载物的“世界中心”被代神立言的“作者中心”取代后不久,诗人的“立法者”地位很快就遭到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挑战,新批评的“作品中心”论乘势而起,但随着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渐成气候,作为“用户”的读者开始掌握话语权。尽管“四因素”的“执政”顺序未必严格“顺应天时”,但它们毕竟各有引领文论风尚和批评主调的时候。
更令人惊叹的是,即便某些如同白天与黑夜一样对立的学术观点,往往也如同昼夜的自然交替一样,根本找不到黑白分明的界限,不同理论之间的“权力移交”实现了水乳交融式的无缝衔接,犹如海天尽头、云水之间的视界融合。即便是海德格尔的“3v箴言”(即前文所谓的“前有”“前见”“前执”),在伽氏的“效果史”意识里也被不分彼此地融汇到“从之出”与“向之归”的混茫“此在”之中。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意识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都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二者的共同点是对一切文本及其“相关关系”的大水漫灌式的无差别渗透。在网络时代,互文性渗入超文本领域,似乎已成为理解和阐释网络时代“文学行动”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尽管超文本源于现代技术的推助,而互文性思想则得益于人文思想的涵化,但是二者的发生、发展及融合过程都为“效果史”学说提供了新鲜的例证。
超文本和互文性概念问世不久,就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一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通过互文性理论打开了本体论的领域,使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系起来。”例如,巴特认为,“文本的意思是织物;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意义或真理。现在,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的编织之中,文本被织就、被生产出来了;主体消隐于这织物之中,消隐于这纹理之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隐伏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之中。”如果说巴特的这些奇思妙想在传统文学体系里多少有些别出心裁的话,那么,在网络文学领域里,则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老生常谈。
巴特的文本理论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即“可读的”(Lisible)文本和“可写的”(scriptible)文本。可读文本拘泥于词语的字典意义和规范,可以按照明确规则阅读,是一种“封闭的”定型文本,其解释方式相当有限,读者与文本处于一种分离状态,读者犹如一个吃桌餐的客人,一切都有既定的遵循,缺少吃自助餐的自主性。可写文本则不同,它不必按照明确规则来理解和阐释,常用的解码策略不适合于这类文本。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定的动态文本,它把作者从文本意义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所以可写文本的表意方式无可限量,因为它是一种开放性和生产性的文本,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理解,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在巴特看来,任何(可写的)文本都是互文本,其周围所有的其他文本都不同程度地“以多少可以辨认的形式——先前的和环绕(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这种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理论色彩的论断,一方面泛化了“效果史”意识,另一方面也给互文性理论涂上了一抹阐释学的釉彩。
有学者注意到,巴特的文本理念在当今互联网世界中得以实现。互联网上的多端口介入无疑使得作者对读者的控制性减弱。当处于文本的海洋中时,读者根本无暇顾及文本的书写者,因为万花筒一样变化万千的文本本身,早已使读者眼花缭乱。
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正是这种“可写的”文本,它们突破了单向意义结构的限制而走向无限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正是互联网文本即超文本的最重要的特征。将互文性与“效果史”潜能发挥到极致的超文本,既无所始,亦无所终,既无中心,亦无边缘。在互联网上,“读者畅游于文本的世界之中,既无政治使命,亦无功利之欲。读者在自由阅读的同时还可以书写文本,阅读、批评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
卡勒在《符号的追寻》中指出:“互文性对于文学的表意功能是一个核心问题。根据互文性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它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特征:1.引用语;2.典故和原型;3.拼贴;4.嘲讽的模仿;5.‘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如果将卡勒的这些说法与巴特的相关言论稍加对照便不难发现,前者的互文性理论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症候。但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卡勒所描述的互文性表意功能的五大特征几乎每一条都适用于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意识。在这里,无论是“引用”“典故”“拼贴”还是“模仿”和“追溯”,其主体都必须有一个包含历史和传统的客体作为行为对象,否则所谓的“引用”“模仿”“追溯”等,都只能是凌空高蹈的虚妄之举。由此可见,互文性在作品中的种种表现,实际上都与“历史在其中不断发挥作用”的“效果史”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与同一性。
美国文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性与差异性有极为精深的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都从反方向对抗现代主义的特征: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意图 游戏
等级 无序
中心 无中心
主从关系 平行关系
生殖/阳物崇拜 多形的/雌雄同体
本源/原因 差异/痕迹
确定性 不确定性
影响 互文性
在哈桑编著的这个著名的对照表中,互文性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志性术语之一。如前所述,卡勒对互文性问题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他认为:“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后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
如今,互文性已经衍生出了许多相似的新概念,如互视性、互介性等,这些新概念有时为相关研究领域带来了超乎想象的阐释能量和理论影响。从伽达默尔阐释学的视角看,将这些能量和影响视为“效果史”在网络语境中的扩充与放大似乎也未为不可。其实,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效果(Effect)与影响(Influence)都被认为是同义词或近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