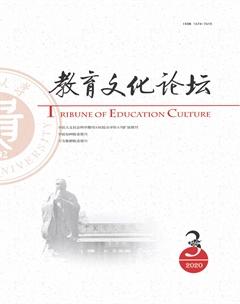王阳明的生命哲学和实现真我的教育论
摘 要:以现代教育危机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三大命题所包含的丰富而生动的主体性、实践性及有机体的人生观和生命观,强调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生命哲学,可以为实现真我的教育观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并进一步讨论了王阳明实现真我的教育观的内容和意义,分析了实现真我的教育方案,指明了阳明教育理论在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整体教育危机中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生命哲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3-0033-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3.005
Abstract:Taking the modern education crisis as a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ich and vivid subjectivity, practicality, and outlooks on life and views of life for organic bodies contained in the three propositions of the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emphasizing that Yangmings ideology of mind, as a very vital philosophy of life, can provide a powerful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uthentic-self education thought. This paper also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WANG Yangmings the realization of authentic-self education thought, and analyzes the way to realize authentic-self education thought, pointing out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of Yangming education theory in solving the overall education crisis existing in the society today.
Key words:WANG Yangming; life philosophy; education thought
教育危機是当今韩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教育危机背后,根深蒂固的是越来越激烈的以学历论资排辈和高考竞争日益激烈的风气,只认可名牌大学,蔓延着唯智论、千篇一律、强压式教育。这种教育风气压抑着学生的身心,抹杀了孩子们的自主性、创意性以及自律性。学校教育的危机长期影响着学生家庭、社会及整个国家。当务之急,教育应走向“自律”和“生命”。其实,阳明的生命哲学和实现真我的教育论可以为当前的教育提供借鉴和启示。12岁的阳明曾与塾师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等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1 346-1 347
阳明从小立下大志,他并没有把科举仕途、立身扬名当作读书学问的目的乃至人生的最终目标,而是把“真我”视为学问的最高境界。阳明一生为了实现真我(圣人)的梦想,不怕百死千难,追求独立自主、积极向上、努力创新,树立了独立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倡导了“实现真我的教育理论”。阳明批判了当时的教条主义、唯智论的学风和千篇一律、强压性填鸭式教育,呼吁德才兼备的教育和增强能动性、自律性、创意性的儿童教育,以及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合一教育等,符合有机社会整体及实现真我的教育方案,还以身作则,积极创建学堂,开展各种讲学活动。阳明不是单纯的理论家或理想主义者,被誉为用实际行动呈现自己理想的实践哲学家。
一、王阳明的生命哲学
阳明心学思想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命题组成,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它们包含着丰富而生动的主体性、实践性、有机体的人生观和生命观,具体内容和特点如下。
1.“心即理”和主体性人类
阳明从小立志做“圣人”,为了实现做圣人的志向,实践朱熹的格物说和读书法,阳明按世俗专攻词章学,修炼道教的导引术,学习佛经等,把儒、佛、道三个学派融会贯通,打造了不受学派或教条主义束缚的自主、积极、创新的生命哲学的基础框架。37岁时,在贬谪地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龙场镇)悟到了“格物致知之旨”,宣称“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进而提出了“心即理”学说,这是自主性、能动性、实践性,也是塑造创意性人生的最根本的基础。
朱熹主张“性即理”说,“理”既是事物世界的客观性存在法则和原理(所以然之故),也是人类应该实践的义务性道德规范(所当然之则),因此,“理”具有绝对性和先验性。同时,理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性,以“性”的形式存在于心。在朱熹看来,只有“性”才是“理”(性即理),“心”只是知“理”,并把它应用于“气”的存在而已。“心”不能主宰“理”,也不能创造“理”。“心”反而不能自主,只能归属于“理”。阳明与朱熹相反,认为“心即理也” [1]2, “心即性,性即理” [1]17,把“心”“理”“性”进行了一体化。阳明主张“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 [1]137,“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 [1]308。阳明认为的“理”,是人类在感知天地万物的过程中,为迎合状况,人总是从“心”里创造全新的“实践条理”。于是,“心即理”成为了一体化的契机。进而,阳明主张“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1]48。阳明认为的“性”,意味着根据面对的对象和不同状况,像孝道一样创造出具体实践条理的“心”的本源性“有机属性”。总之,“性”是创造实践条理的“心”的有机属性(心即性),“理”是“心”的有机属性“性”所创造的实践条理(性即理),因此而成为“心外无理”的“心即理”。
阳明认为“心”通过感应天地万物,痛心于万物的生命损伤。“心”以对万物的关心和抚养,积极、自主、能动地引导万物生命的创造、养育过程,是人类先验性的生命本质。同时,“心”是把人类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感应主体,面临任何对象和状况,自觉地正确判断对生命完整性的对错,创造实践条理,主宰实践行为,是一个自主、能动、创造性生命主体。阳明的这一“心即理”说,不仅把人类从外在的规范中解脱出来,还强调是天地万物的感应主体,也是核心中枢,并整体地勾勒出了创造实践条理“自主”“能动”“创造”的人类形象。
2.“知行合一”和实践性人类
阳明38岁在贵阳时,依据心即理说,批判了朱熹在心外求理的“格物说”分为“知”和“行”两种而削弱实践性的问题,提倡“知行合一說”,指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1]15,“知行合一”被提示为成就“圣人”的方案。对阳明来说,“心”不仅是创造实践条理的“能动的创造性”和理念以及判断局势是非的“自觉的判断力”,而且也是引导实践行为的“实践、意志”,同时还是以身体的一元化体系为基础、履行实践行为的“能动的实践性”,因此,事实上“知”和“性”在“心”内已有“合一”的契机。阳明认为:“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1]103“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1]86-87例如,若目睹小孩儿要落井的瞬间,因惊吓而恻隐的“心的自觉”和想救小孩儿的“意志的发动”意味着先验性的“心灵明的知”,从心中发出的意志通过身体直接导出救小孩儿的“实践行为”,这就是“行”。恻隐之“心的自觉”和想救小孩儿的“意志发动”及救小孩儿的“实践行为”,是人类心和天地万物之间无隔阂形成的一系列感应过程,原本就是“合一”。
阳明主张“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5,认为若导出实践行为的实践意志的“知”是直接实践行为的开始,则只有通过实际的实践行为才能成就发动“心”的自觉和意志的“知”。并且以“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为前提,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1]47。消除私欲,恢复本心,并自觉判断面对的事态的对与错,激发维持生命完整性等固然重要,但“知”终究只能通过实践行为才能成为真知。这就说明,所谓“实践性人类”是以坚定的实践为基础的。
3.“致良知”和有机体的人类
阳明50岁在江西时宣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 [1]1 141,确定了“致良知”才是成为圣人的实际性方案。阳明主张:“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1]89对于孟子来说,“良知”是能动实践性的“良能”和先天性自觉力“良知”的整合体,成为人类“天地万物之心”即成为核心中枢的基础。这种先天性、先验性、能动性良知是是非之心,即体现为万物一体之仁(怵惕恻隐之心、不忍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1]1 066,“对与错”(是非)即是对天地万物生命完整性的对与错,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是自觉判断天地万物的生命完整性、生命损失感知为自身疼痛的先天自觉性判断力的人心“有机生命性、生命力”。这种良知并不像朱子学一样根据普遍、外在的规范和格式,用固定的定理事先设置是非判断准则,而是通过与面对的对象、情况的感应,经常重新创造是非判断准则,具有是非判断作用的“随时变易性”和“恒动性”[2]。人类天生内在的良知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是人人都能成为“天地万物之心”圣人的关键性基础。
仅仅只有良知的内在性,还不能成为圣人。因为人类往往只执着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把人类自身和天地万物分化为自、他、主、客、内、外,进而为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做斗争,达到极端后还成天骨肉相残,内在有最终毁灭人类的私欲可能性[1]90。因此,需要自觉消除私欲恢复良知来实现的过程,此过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并不停留于“良知的自觉性判断或实践条理的创造和实践意志的发动”阶段,而是通过“实际的实践行为”,实现由良知形成的判断和实践意志,因此,可以理解为“实现良知的总体有机生命性”。人类就是通过这种良知达到真实的人类“圣人”。“圣人”消除自己的私欲,根据先验性良知,认识包括自己与天地万物是一体,不区分自、他和物、我,正确自觉判断对天地万物生命完整性的对与错,亲身感受他们的痛苦或饥饿等万物生命损失,认识自身责任,进而通过安全地照顾和教养他们等具体实践,以达到“天地万物成为一体的世界,即完整养育苍生的终极境界”的真实人类。
如上所述,阳明通过“心即理说”,从对心外的外在和权威性理的束缚中解放了人类,树立了“主体性、创意性的人类形象”,通过“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摆脱了当时教条主义、思辨、主旨主义的学风弊端,确立了“律动、实践、有机的真实人类形象” [3]。
二、实现真我的教育观
实现这种主观、创意、实践、有机体的真我是阳明教育论的最终目的。阳明追求学问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外在知识的探索和立身扬名,而是通过主观自觉和实现天生的生命良知达到“真我(圣人=大我=无我)”。阳明以这种人生观和生命观为基础,提出实现真我的学问和教育出发点的“立志”,察看实现真我和立志的相关性。
1.教育目的和立志
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天地万物同为一个生命体,因此,人类社会要持续维持生命力,需要社会成员的不断创新,在此过程中最看重学问和教育。阳明营造所有人类可以实现天生内在生命本质良知的契机和环境,通过社会成员自己的主观能动的学问磨练,实现真我作为教育目的。以这种教育目的为前提,阳明反对桎梏人类生命的划一、教条主义教育和为科举考试而进行的教育以及注入式教育等,增强社会成员天生的才能和德性,为了造就社会有机体的人类社会,提出增强成员创意性、能动性、自律性的教育方案。
阳明首先把“立志”规定为学问和教育的先决条件,主张为了成就人间诸事,应先立其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1]1 073因此,在学问和教育中首要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是“立志”,阳明在做学问方面如下阐明“立志”的重要性:
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1]65
作为学问先决条件的立志状态左右着学问的成败。这种立志并不是因为外部的逼迫或外在标准形成,而是被教育人根据自己的主体自觉和判断设置学问的目的和方向性,按照自己设定的立志努力成就学问。
阳明把这种教育和学问中的立志喻为树根,认为若人类掌握好树的生理,给予树成长的良好环境,树会自然而然生长旺盛,树枝和树叶会日渐茂密。同时,在树木成长过程中去掉不必要的茂盛树枝,树根和树枝会更加健壮。这种树根被喻为初学者的立志[1]37。因此,“立志”可以说是被教育者的学问之树根,被教育者的学问性过程就是培养立志到成就立志的过程。教育如同为树木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一样,为了使被教育者自己实现自己主体设定的立志,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是树木自己成就树木的成长。因此,立志的设定和成就立志的问题在于学问的主体人格。对此,阳明认为若树木无根,即使给它提供良好的环境,树木也不能成长,人类也一样,若自己不立志,就无树根,最终什么也成就不了。按照自己的主体自觉和判断立志,即若不设定人生的方向性和目的,则可能被喻为无舵的船或无嚼子的马,不立志的人漂泊、挥霍、张狂、懒惰,最终还会破坏生命的本质。他指出:“今学者旷废隳惰,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1]1 073根据这种主张来看,立志不仅在学问和教育方面,还在人生自身也成为根本的根基。那么,成为学问和教育之树根的“立志”意味着什么?从下列问答中可以类推立志的本质: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为善去恶否?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1]22
存善念时就是天理,培养和树立这种善念就是立志。阳明还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1]13。对于阳明来说,天理是源于天地万物生命本质的人类生命本质,意味着与天地万物共鸣并可成为一体的人类“有机生命性”。另外,“存天理”亦在无为、无事、静、未发状态下,并不是用心去认识外在存在原理和当为规范或为了心适应于这些存养,而是意味着在与天地万物的实际感应过程中完整表现和展开有机生命性天理的全部过程。因此,立志不止于学问和教育的出发点。在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持续共鸣过程中,不间断地存养和扩充这种心的本质属性天理的过程亦是立志[1]13。立志就是成为真我圣人的出发点,同时包括全部实现过程。教育就是提供可以实现这种立志的环境,为了不断成就真我而“教养”的过程。
2.立志和实现
阳明说:“天理即是良知。”[1]116“存天理”即意味着“致良知”。因此,以立志为基础的学问和教育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是在于“实现良知”。阳明对学问和实现良知的关系阐明如下:
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1]80-81
学问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追求外在知识,而是在于实现人类生命本质良知;但并不完全否定学问过程中的知识本身,只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应与实现良知关联,应在实现良知这种学问的最终目的之内进行,并且通过学问掌握的知识,应通过实现良知的过程转为实际的实践。实现良知作为学问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背离日常生活的高远修养或理论学习成就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实际的实践成就的。这是源于良知自身而不是基于形而上学存在原理或当为道德规范的人类生命本质的有机生命力的事实。人类有机生命力根据日常生活中所处的情况表现在每一瞬间,因此,作为有机生命力的良知若脱离日常生活就无存在的意义,也不能发挥任何能力。对此,阳明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与实现良知有關的教育必要性如下:
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1]136-137
教育开始于帮助孩子在打扫卫生、对待大人等日常生活中实现他们的主观良知。由于良知是人类的有机生命力,因此,实现良知的教育实际上不能通过被动和强制的学习来实现,也不能通过脱离现实的高远修炼或形而上学性探索来实现;这是根据被教育者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状况,依据自身的良知,自觉判断事态,设定实践方向,通过与身体的有机统一,进行实践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实现良知的教育就是被教育者自己消除遮蔽良知的私欲,根据良知自觉判断自己面前新展开的事态,自觉强求实践方案,是培养实践基础的教育,不是强制性、被动性教育,而是“自律、能动的创意性教育”。
如上所述,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通过实现自己的天生良知成为圣人,这不局限于孩子,卖柴火的人、公卿大夫、天子都一样,各自根据自己的良知判断和自己所处的状况去实践,都能成为圣人[1]110-111。阳明追求的学问和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主动地完成天生良知,所有人类都成为“真我”的“圣人”。
三、实现真我的教育方案
从上述内容我们认识了作为学问和教育先决条件的“立志”,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主体性、实践性地实现天生内在于所有人类的良知来实现“真我”(圣人)的事实。那么,为了实现真我,具体的教育方案有哪些?
1.才德一致的教育
首先,强调统一才能和德性的“才德一致”教育方案。阳明追求“万物一体的有机体大同社会”,他在“拔本塞源论”中主张“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1]61,为了体现有机体性大同社会,阳明提出了如下的“才德一致”教育方案: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1]61-62
在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提高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才能,但教育不仅仅只是提高知识和技术的教育,事实上他们的“才能和德性”应相互符合。只有才能和德性相一致的学校教育,才能实现万物一体的大同社会理想。
其次,为了维持万物一体的有机体性大同社会,需要可提高每个社会成员天生才能的教育。阳明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礼乐、政治、教育、农业等各自不同的才能,根据天生的不同才能,可担任农业、工业、商业、管理、饮食、教育、音乐、礼仪等不同的多种职位。这意味着积极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互相不同的多样性才能,人类社会由具有不同才能的成员构成。若人类这个有机体只由相同功能和作用的成员构成,则这个社会不仅不能存续,而且其成员都要面临灭亡。因此,这种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才能多样性和自身才能的功能與作用的多样性,是圆满维持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为了维持这种万物一体的有机体性大同社会,不能无视每个人的个性,不能只进行一样的技术知识教育,而是需要提高每个人天生才能的多样性教育。
但是,单靠提高才能的教育不能实现真我,也不能完整地维持有机体性大同社会。为了社会成员的完整性,需要才能和德性划一的教育。人类不仅具有可体现万物一体至善生命本质的有机体性生命性(天理=良知=仁),还内在具有遮蔽此种本质,以自身形体标准区别内外,断绝和无视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而互补的关系网,执着于自身利益与欲望,有发动私欲(物欲)的可能性。因此,如果通过教育只提高社会成员才能,只依据出众的才能委任职责,就不能完整维持有机体性大同社会。即使是通过教育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才能并录用符合职能的有能之士,若他们不能以生命本质为依据,将自身才能应用于完整存续有机体性人类社会,而用于满足自身个体欲望,他们的才能反而会桎梏人类社会成员的生命,进而混乱人类社会[1]90。因此,阳明主张学校教育以成就社会成员的德性为目的,但提高才能的同时应符合德性,在政治上提拔人才时应根据德性,应评价其才能是否适于其职责。
“德性”是与引发人类相互之间对立和斗争的个体欲望相对立的相互饶恕,以及相互养育的同心一德即“万物一体之仁”。在有机体性人类社会,提高成员们才能的教育应以这种德性的成就为基础。学校教育需要才能和德性缺一不可的“才德一致”教育,对此,笔者想表述为社会成员的“完整性”,只有以这种完整性为前提,以才能为基础的社会成员多样性才有其意义,为完整展现有机体性人类社会,还可以正确发挥多种才能。
最后,才能和德性划一的教育以对社会成员的“平等意识”为前提。在有机体性大同社会,每个人的职责不是依据相关人士身份的上下、尊卑、贵贱,而是依据他们的才能和德性层次。因此,在有机体性大同社会,以才能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为依据的每个成员平等性为前提,职责等级的高低并不重要,或并不是根据职责等级决定身份。对此,阳明提出如下的“四民同道异业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1]1 036
这种以德性平等为基础,主张才能、个性发挥是阳明思想中主张“人类平等论”的主要依据[4]142。通过教育培养好每个人天生才能的特殊性和人类普遍的固有性,从事适于自己的职业,不失自豪与本分,一生职守,职守自己的本分,扬弃与他人的对立,成就和谐世界。从此,社会成员都消除个体欲望,成就“万物一体之仁”,达到“天地万物一体=异物同体=物我一体”的境界。
2.增强能动性、自律性、创意性的教育
阳明未停留于提示实现真我的教育论阶段,而是通过创办学校、积极讲学等方式积极进行教育活动。例如,嘉靖七年(阳明57岁)四月,阳明在广西田州创办学校,六月在南宁创办学校,早晚给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讲课[4]367-368。特别是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47岁),平定了与南赣(江西)相连接的四省边境之乱,回来后鼓励属于南赣的各县人士创建学社,颁布了《训蒙大意示教续刘伯颂等》和《教约》[5]。
在此文中,阳明首先强烈批评了扭曲被教育者——儿童生命本质的划一性、强制性注入式教育,提出了可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生命本质并成为基础的增强能动性和自律性以及创意性的教育方案。他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弊端:
若近世之训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1]100
在此,阳明批判了形式主义和划一的教育以及以入学考试为主的强制性的教育方式,认为这种划一性、被动性、强制性教育压抑儿童的情绪,使儿童对教育产生反感,并扭曲他们的善之本性,使孩子成天虚伪和伪善、诡辩,最终使孩子变得愚钝、庸俗、卑劣,让其丧失可体现自身本质的契机。
那么,阳明提出的理想的儿童教育是什么呢?针对适于儿童自然情绪的教育方向,阳明提出了如下意见: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1]99
阳明对儿童的教育批评了外在标准,否定了划一性、强制性的方法,指出应该根据儿童朝气蓬勃的情绪,营造可尽情享受“生命力”的环境,应给他们提供自发、自律学习的契机。对此,阳明主张圣人的学问不是拘束和束缚、痛苦,也不是像道学一样装扮,圣人教人不会通过束缚他们统一为一种形态,而是根据他们不同才能和气质教育他们,使其成为相符于才能和气质的人类。“圣人敎人,
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
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118以这种主张为依据,教育不能拘束和束缚被教育人,应该根据被教育者的才能和气质,提供增强他们“多样性”的教育。
阳明以增强社会成员“能动性”和“自律性”以及“创意性”的自主教育观为依据,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具体提出了发展儿童本性和才能的能动、自律的教育方案:
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裁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覆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黙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1]99
儿童的教育以启发德性为基础,应通过具体吟诗、掌握礼节、读书方法,启发意志、纠正态度、启发知觉。这是基于本性的“歌诗意志”“习礼威仪”“读书知觉”关系,不偏于人类情感、态度、精神三种中的任一方,均匀启发、创造有机体的人类的教育方案。例如,通过诗歌教育启发儿童意志、培养情操,增强儿童的自律性,通过习礼教育保持健康的体魄和精神,通过读书教育让孩子自己认识知觉。自觉心的本质,基于自身情绪展开自己的抱负,应增强孩子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教育顺利地引领意志,调节性情,消除卑劣和吝啬,教化粗糙和愚钝,可以创造自己实现良知的有机性社会成员。
阳明的儿童教育重点可以说是实施适于被教育者情绪的教育,修养他们的自然情绪、增强德性、启发知觉的同时,为了使他们最大限度发挥自发性、自律性、能动性、创意性,创造有机体性人类社会成员。阳明以这种提高儿童能动性、自律性、创意性的教育方案为基础,在《教约》中更具体地提出了自发性生活教育、修养情操为目的的音乐教育、修养德性为目的的礼仪教育、启发创意性的教育、自律性教育等[1]100-101。阳明的这种教育思想是亲民的具体实践方案之一,其重点在于造就可贡献于良知的人类和形成那种社会的条件[6]。
3.学行合一教育
阳明实现真我的教育论中重要的教育方案之三,可举“学习和实践合一(学行合一)教育”。主张知行合一说,最重视“实践行为”的阳明在口传习录口(中)“答顾东桥书”136条中,把《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看作“学的过程”亦是“行的过程”,主张学与行的合一,即通过“学行合一”实现良知。
阳明首先认为:“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老道,然后谓之学,丰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 [1]51“学”并不是与实践经验无关的学,学包括在现场直接实践经验的过程。学和实践经验无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同时开始、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合一的过程。“笃行”也并不是通过理论学习先知、后在现场笃实实践的另一个实践过程,而意味着笃实履行同时性的学与行进行合一的过程。“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1]51因此,“学与行的合一”是指学与行同时开始、进行、完成的综合过程。
在学行合一的基础上,仔细讨论学的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慎重思考(慎思),清醒地辨别(明辨)过程都规定为“学”“行”。“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1]51这是源于包括实践行为的学——阳明所谓的“学”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在学的过程中,若有疑问,则询问、慎重思考、明辨的思考过程亦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也可以看作是行的一面。因此,在行的过程中进行的思考过程,是纠正行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或持续提示行的方向性,以使行更明确和正确。从这方面来讲,学、问、思、辨别、实践互相关联,时间上无先后顺序,并不是阶段性的五个阶段,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五个方面,即在行的过程中学、问、思、辨别的同时性过程,也可以说是同时开始、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合而为一的过程。
这种学和行的合一教育,最终目的在于实现良知。朱熹认为,《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中学、问、思、辨是探索外在事物内在理(物理、事理)的认识过程(知),笃行是从修身到处事接物的实践过程(行),知和行是先后关系。针对朱熹的这种主张,阳明提出反驳,认为不实践就不能学习,不实践就不能另外穷理。王阳明指出:
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尙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1]52
穷理与实践并没有先后顺序或分离,穷理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穷究仁或义之理”是指真诚实践仁和义,使仁和义达到最终境界,可以说是完全实现本性后,穷究仁或义之理。因此,未经实践就不能称为学,未行也不能称为穷理。朱熹认为,穷理局限于事物内在的存在法则(所以然之故)或认识当为的道德规范(所当然之则)过程,与朱熹相反,阳明认为连穷理也是通过实际的实践体现自身内在本性的过程,将学行和穷理整合为一个实践过程。
穷理可以整合为实践过程的依据源于心对实践条理的无限创造性。“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1]52对于阳明来说,“穷理”的“理”并不是指客观事物内在的存在法则或外在的当为道德规范。理是指人类与天地万物感应的过程中从心创出的实践条理,因此,不需要像朱熹一样另外认识心之外理的穷理过程。从心发出的实践条理反而不受私欲的阻挠,为了完整实现实践条理,需要通过实践行为的主体性和自发性努力。因此,穷理的“穷”并不是对外在理的认识过程,而是可以转换为实现从心到发出的实践条理的实践行为。这种心的感应力和创造性、实践力的主体就是良知,因此,学、问、思、辨、实践、穷理都成为实现良知的具体实践方案。“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1]52可以说,学甚至是穷理、追求与行合一的教育方案最终目的,亦在于通过良知的实现来实现真我。
四、阳明教育论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着教育危机,特别是本应培养健康学生、真诚人类的教育场所变成了扼杀自律和生命的竞争场所。这种扼杀生命的教育危机源于以学历为主的社会环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味阳明所主张的学习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真我”而不是立身扬名。在阳明生活的年代,学问和教育只不过是考中科举享受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手段,教条主义、主旨主义和扭曲儿童生命的划一、强制性注入式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对此,阳明批判当时成为教条主义和主旨主义基干的朱子学,通过“心即理说”,把外在而权威的性理收摄于人的内心,树立了主体性、创意性的人类形象,通过“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摆脱了当时思辨、主旨主义学风的弊端,树立了律动、实践性、有机体性的真实人类形象。实现这种主体性、创意性、实践性、有机体性的真我(圣人),就是阳明教育论的最终目的。
阳明追求的学问和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外在知识探索的立身扬名,而是通过自觉、实践过程实现人类天生本心(良知)的“真我”。教育就是营造学生“实现真我”“成就立志”的环境,为了使学生不断成就真我,主体、自律、实践性地进行教养的过程。
为了解决当前的教育危机,必须重视以立志为基础的“实现真我”的阳明教育观,在此强调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才能与德性相符的“才德一致”教育。每个人都是有机社会的一个成员,为了健康延续有机社会,需要成员不一样的多种才能和技术。因此,不进行社会成员划一的才能和技术教育,而需要进行增强学生不同的天生才能和技术的教育。这种增强才能的教育应以发扬和培养的德性(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成就为基础。
第二,增强能动性、自律性、创意性的教育。形式性、强制性、划一性的注入式教育扼杀儿童的天性和自律性,应提倡适于儿童自然情绪、实施自律性的教育,在培养他们的自然情绪,增强德性,启发认知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自發性、自律性、能动性、创意性,才可以实现真我,才可以培养有机体的人类社会正直的成员。
第三,学习和实践合一的“学行合一”教育。人类是身与心的统一体,因此,只靠单纯的主旨主义理论学习不能实现真我。学习不只要用头脑,还要用全身体会(体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不以理论为主,而应采用以体验为中心的教育、体验后自己清醒的教育[7]。人类还处于很多关系场内,就如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慈爱和孝道这种具体实践行为才能实现一样,关系场只有通过不属于学习认知阶段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最终,有机社会成员的真我不是在认知阶段成就,而是基于良知的自觉,通过实际的实践行为,只有通过实现良知才得以体现,因此,需要学习和实践的合一教育。
一句话概括阳明的教育理论,就是人的“主体性” “创意性”及“实践性”,即拯救生命的教育。我们应摆脱扼杀自律和生命的注入式教育,树立拯救生命的新的教育目标和方案。当然,不能回避发展国力的实用教育,如学习、创造尖端技术,适于全球化时代的外语教育与学习,科技时代提高信息技术等。但是,不以德性成就为后盾的才能和以技术为主的实用教育,稍不留神可能会用于扼杀生命。因此,教育应以相互拯救的“同心一德的德性”(万物一体之仁)为基础,成为增强才能的教育。这样,它的才能和技术才不会成为扼杀生命的才能,而可以完全执行拯救生命的功能。
把扼杀自律和生命的他律注入式教育转变为拯救生命和自律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被教育者自己确立正确的志向。立志是学习和教育的根基。如同无根的树无法正常生长一样,自己未立志的被教育者无法成就真我。教育从现在的强制式教育中解脱出来,为学生自己立志,自主、自律、实践性地增长自身德性和才能,全力营造环境。
现今社会的教育问题之一是不能培养实践力。不仅在知识能力方面,还在道德品质方面也无法培养出自创独立的人才。周围虽有很多知识分子,但实践的人少,自主独创的人少[8]。因此,现在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教室里的纯理论学习,而要在生活中自己感受,逐渐增加启发自己的实践学习。只有通过身心统一的学和行的主体合一教育,才能成就主体性、创造性的真我。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金世贞.人间良知的有机生命性[J].儒教思想研究,1998(10):412-418.
[3] 金世贞.王阳明的生命哲学[M].首尔:清溪,2006.
[4] 崔在穆.吾心是灯光[M].首尔:理学社,2003.
[5]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277.
[6] 金吉洛.王阳明的经世思想研究[J].儒学研究,1994(2):212.
[7] 崔在穆.阳明学和共生、同心、教育的理念[M]. 大邱: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1999:169.
[8] 李银善.儒教、基督教和女权主义[M].坡州:韩国知识产业社,2003:341.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