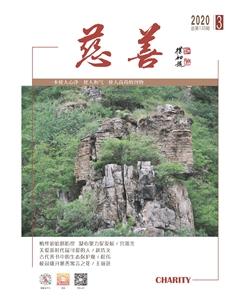舅 舅
赵浩义
清明时节,走进郁郁葱葱的田野,看见拽耙扶犁的老者,就想起了舅舅。
(一)
舅舅一米八的个头,体型魁伟,面色红润,浓眉大眼,嗓门洪亮。穿一身粗布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活了85岁,历经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他的人生留下了三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印记。
1903年8月22日的清晨,随着几声婴儿的啼叫,南秦川道的一个杏林之家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外公秦仲珍望子成龙,为婴儿取名秦俊杰。
舅舅生逢乱世,童年在惊恐中成长。外公是南秦川道远近闻名的中医先生,在县城开间“秦记医堂”,家有几亩土地,略有家资,遭到了“土匪”的觊觎。舅舅5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个蒙面大汉破门而入,把舅舅抢走,劫匪留言:“拿出200银元赎人,否则撕票。”外公卖了县城一间药铺,才托人到歇马店岭“土匪窝”将舅舅赎回。
民国初年,舅舅上了几年私塾,到县城跟外公学医。那个年代民不聊生,外公行医药费常有赊欠。外公乐善好施,穷苦人家到年终账就免了,对富裕人家的欠账派舅舅上门催要,结果却常遭一些劣绅的毒打。从此,舅舅发誓再不学医。
离开药铺,舅舅回家种地。人常说人勤地不懒,家中的几亩地被舅舅耕种得颇有收成。乡公所看舅舅老实,就把保长的委任状送到家中,强迫舅舅当保长。那时保长干的事就是抓丁、征粮、收款,欺压百姓。舅舅心地良善,接到乡公所抓丁通知后就提前通知乡邻,乡公所上门抓人时,青壮年全都跑了,一个壮丁也抓不住。村子里多是贫穷人家,粮、款交不出来,舅舅就自己垫付,干了半年垫付越来越多,付不起了,舅舅就跑到乡公所请辞,乡公所主任把桌子一拍:“你这个窝囊保长,壮丁抓不住,粮钱自己垫,不干可以,但必须交50块大洋。”舅舅忙跑到县城向外公要钱,交了50块大洋后,才辞去了这倒霉的保长。
辞去保长后,舅舅专心务农,起早贪黑在自家坡上垒石坎修地,每年修出一亩多,七八年竟修出了十亩石坎田。他就在这些石坎田种核桃、栽柿子树,几年后,果树长大,每年收获季节核桃、柿子在家中堆成了山。他就分给乡邻、亲戚,请大家共享他的劳动成果。
1949年年初,68岁的外公去世。当时,我的大姨和母亲已相继出嫁,表哥尊贤还在读书,表嫂刚娶进门,外婆健在,加上继舅母一家五口人的生计全压在了舅舅身上。他更是起早贪黑,跑到马路上拾粪,到自家坡上开荒地,终日劳作,甚是辛苦。
1949年7月商县解放,舅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听母亲说,新中国成立后,舅舅就像换了一个人,整天乐呵呵的。成立互助组他第一个参加;合作化时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交给集体;人民公社生产队干活他最卖力气,集体的事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年年被评为“模范社员”,奖状贴满了一堵墙。生产队选队长大家都投他的票。他笑着说:“我可再拿不出50块大洋了,当一个好社员就行了。”群众不依不饶,无奈当了生产队的会计。
记得我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随母亲到南秦川上游西坪村的舅舅家看望外婆,进门后,看见墙上挂了一块黑板,舅舅拿着粉笔在板上写了十几行字教孙子建华念。建华与我同庚,已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我俩一同读了出来:
我中华,在东亚,
人口多,面积大。
共产党,新中国,
我们都要热爱她。
陕西省会在西安,
东边临潼并渭南。
西有周至和户县,
南有蓝田北三原。
共产党,像太阳,
人民翻身得解放。
社会主义就是好,
家家都穿新衣裳。
读完后,建华问爷爷:“陕西北到延安、榆林,南到汉中、安康,东到华县、潼关,西到宝鸡,你咋把陕西说的只有几个县大?”舅舅迷茫地问:“在哪里?这些地方我没去过。”
我说:“舅舅,你这诗写得很好,可以向陕报投稿发表。”舅舅憨厚地一笑:“这哪是诗,是我编的顺口溜,说的都是心里话。”
是啊!这首诗尽管不大押韵,对仗也不工整,但却是一个普通农民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过了一会儿,表嫂喊大家吃饭,舅舅问几点了,建华回答:“1点啦。”舅舅眉头一皱:“不对,刚才都12点了,这会才1点,咋倒回去啦。”大家哈哈大笑。我纠正:“舅舅说的是标准北京时间,现在应该是13点。”舅舅得意地笑了。
20世纪七十年代初,商县建设“两库一路”(二龙山水库、南秦水库、麻街岭公路),年近花甲的舅舅积极报名参加,在二龙山水库干了两年,在麻街路上干了一年,三年不回家,吃住在工地,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捧了三张奖状回家。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舅舅如魚得水,他把责任田拾掇得能挤出油来,庄稼长势总比别人好,打得粮食总比别人多,成为全村的“庄稼把式”。75岁后,地里的活干不动了,他又主动到村子后面山林里当义务护林员,一直干到82岁,在他护林期间,林子里没有一棵树被偷盗。
(二)
舅家书香门第,读耕传家。一家人菩萨心肠、乐善好施,在南秦川道广为流传。
外公秦仲珍,生于1881年,饱读诗书,又钻研中医,是县城闻名的“秦先生”。有次去朋友家奔丧,朋友的父亲都收殓入棺了,他上前把额头一摸:“抬出来,人还有救。”家人把死者抬到床上,舅舅一阵针灸推拿,又开了一剂中药,让家人熬好灌进口中,过了一个时辰,死者喘过一口气竟坐了起来。从此,外公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神医”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的药铺前,常有一些无钱治病的人躺在门外,外公就把病人抬回药铺放到床上,免费精心医治,管吃管住,直至能下地行走才让离去。因此,外公获得了“行善先生”的美名。
外婆李观灯生于1880年,是本乡北秦湾的大家闺秀,识文断字,终身奉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受封建礼教熏陶的传统女性。外公在县域行医,她在家伺候父母双亲,管教子女,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听母亲讲,小时候她们兄妹三个都念过私塾,每天晚上外婆拿着戒尺让她们背《女儿经》《道德经》,背不出来外婆就用戒尺抽打,打得手肿得老高。外婆积德行善,常接济穷苦人家,且略通医道,家里有个中药斗子装满了各种草药,村上谁病了到家来,她配给几剂草药,从不收钱。村里人都叫她“好心大婶”。童年时,她到我家来过几次,来了后总是帮母亲做针线活,缝缝补补,一刻也闲不住。对我们姊妹更是疼爱有加,我们犯错了她耐心指教,不许母亲体罚我们。1964年,这位满头银发、面目慈祥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享年85岁。
舅家子嗣兴旺,也是一个大家族。舅舅娶过两房妻室,原配张引从邻村嫁来,生下一子取名尊贤。前舅母1943年去世后,舅舅又迎娶了继舅母崔念娃,1909年生人,终生未育。我们去了,她总是拿出许多好东西让我们吃,非常贤惠。老人1976年去世,享年67岁。尊贤表哥生于1934年,新中国成立后从商县干训班毕业,分配到榆林专区佳县乌镇完小教书,1962年调回商县银行工作,银行分家后担任县农行办公室主任,于1998年患脑淤血去世。表嫂王爱玉生于1932年,名门闺秀,秀外慧中,精明能干,是个女强人,曾担任不脱产的公社妇联主任。表哥在外地工作期间,她在家上孝敬父母,下管教三个子女,家中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三个孩子在她的管教下个个聪慧,学业有成。恢复高考后,大儿子秦建华、二儿子秦卫华,女儿秦晓婷相继考上中专、大学,都参加工作,如今88岁的表嫂精神矍铄、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三)
舅父一家人对我家时常接济,关爱有加。我们姊妹7个,加上母亲、奶奶,一家9口人全靠父亲每月38元工资养家糊口。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当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舅舅来了,一根扁担挑着两大竹笼,一笼放着粮食,一笼装着柿子、核桃,吭哧、吭哧,喘着粗气担进了我家,母亲接过舅舅的扁担,含着泪说:“哥,咱家也不富裕,你把这都担来了,屋里咋办?咱家人岂不饿肚子。”舅舅狡黠地一笑:“饿不了,柿树、核桃树还在(当时政策规定经济林果树仍归个人所有),我又在山里邊开了几块荒地,偷偷种了些粮食。”就这样一担一担的接济,使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场大饥馑。在以后的岁月里,多少次睡梦中我都梦见舅舅那吃力地担着粮食进门的身影。
在那困难的岁月,爱玉表嫂是我家的常客,她每次来从不空手,不是给我们带来几件衣服,就是为家里送一点钱,而且每次都买一些水果糖发给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习惯叫她“大嫂”,那时候水果糖可是农家孩子的奢侈品。农村的孩子一年都吃不到一块糖。兄弟姐妹们都盼着大嫂来,因为大嫂来了有糖吃。
表哥秦尊贤继承了舅舅的遗风,性格豪爽,终生乐于助人,在单位和村上威信很高。1977年恢复高考,十月份的一天,尊贤哥骑着自行车来家对我说:“收拾一下,带上书本到城里去和建华一块复习高考。”当时我欣喜若狂,背上书包坐上他的自行车到了城里和建华一起复习功课。在那一个多月,尊贤哥每天买菜为我们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忙里偷闲喊一声:“你俩要争气,一定考个好学校,跳出农门。”两个月后,我和表侄建华一同走进考场,他被西安公路学院中专部录取,我考上了商洛师范学校。
建华和我都是1955年出生,同在一所学校念小学,读初中,上高中,他聪慧好学,字写得好,学业优秀。西安公路学院中专部毕业后,分配到洛南县交通监理站工作,1982年调回地区交通监理处,开始担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工会主席。建华为人仗义,写得一手好文章,爱喝酒,善交朋友。我和建华一块玩泥巴长大,互为知己,高兴了或遇到烦心事了都会一块喝酒,谈论人生、互诉衷肠,一吐为快。如今,他也65岁了,两个女儿学业有成在省城工作,他在商州城照料年迈的母亲,帮女儿带孩子,含饴弄孙。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每一步都有舅舅一家人的帮助和关爱,他(她)们都是我的至亲!
1982年的秋天,82岁的舅舅上梯子挂柿子不小心栽下来摔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期间我陪同母亲看望过几次,见大嫂为舅舅端茶送饭,擦身体,帮排便,像亲生父亲一样伺候,我深为感动。我母亲当面夸奖:“爱玉,你比他的亲女子都孝顺。”
1986年10月25日,舅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噩耗传来,我们一家人前去奔丧,看到满村人都来吊唁。入土埋葬之日,全村人齐出动,孝子成群结队,孝幡遮天蔽日,纸钱漫天飞舞,数百村民前来送别这位憨厚、贤慧的老人,祭灵的秦腔声韵响彻云霄。
一个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后能有这么多的乡邻前来送葬,此生足矣!
我甚感欣慰:这是舅舅穷尽一生乐善好施的积淀;是他老人家平凡人生的功德!
舅舅,安息吧!◎
202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