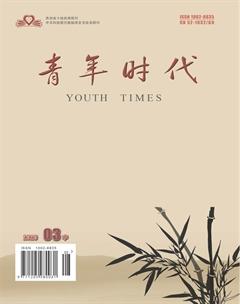“跨国史”与“国际史”异同刍议
陈郁晗
摘 要:“跨国史”与“国际史”是近年来史学界尤为关注的两大史学范式,但两者相近的关注主题,模糊了其真正的概念内涵,它们间的异同尚有待分明。就诞生背景而言,“跨国史”与“国际史”视角是对全球化热潮的回应,但“国际史”的诞生是对传统外交史范式的扬弃,而“跨国史”欲实现对“美国例外论”的超越和民族国家史学的补充。“国际史”仍以国家为单位,探究国家间的多向互动,以及国家框架下个人与群体的历史活动;而“跨国史”侧重于研究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与联系。在空间维度之下,“国际史”将外交事务置于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中看待的视角,与“跨国史”的内涵相一致,但“国际史”不具备“跨国史”中跨国网络和跨国空间这两大维度。
关键词:跨国史;国际史;史学理论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区域共同体、非政府组织等超国家实体力量逐渐凸显的现状,美国史学界率先兴起了一股包含“跨国史”“国际史”在内的“跨国转向”潮流。这一潮流旨在突破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叙述重心和关注焦点的研究范式,力图将以往被禁锢于国家疆域内的历史现象,放置于更为广阔的跨国背景下,探究其背后超国家范畴的历史诱因、动力与影响。同时,其力图探究移民族群流散、思想文化传播等显而易见的跨国流动现象,及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跨国非政治实体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学术界逐渐关注到在国外已注重探究商品技术流渐成规模的“跨国转向”潮流,国内学者们或在引入国外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论,或借助“跨国史”“国际史”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然而,国内学术界中许多学者在使用“跨国史”和“国际史”概念时,常出现概念混同或表意不清的情况。本文在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尝试性地从诞生背景、词源辨析和视角范畴等方面,探究“跨国史”与“国际史”的异同。
二、“跨国史”与“国际史”的异同
无论是“跨国史”还是“国际史”,都提倡以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宽广视野看待历史现象,这种超国家的视野无疑与近几十年来逐渐勃兴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然而在20世纪之前,已成规模的世界联结仍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主导下的不平等的联结。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使全球化陷入停滞,而冷战初期各国经济文化联系虽逐步加强,却未能逃脱出美苏冷战的两级格局之外。随着美苏冷战局势的缓和,屡次遭遇阻碍限制的全球化趋势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真正从牢笼中挣脱。
全球化浪潮之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推动人员、商品和资本等以往受限于国家疆界内的事物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循环轮转,思想、文化和技术等无形之物更以润物细问声之势流向世界各地。在国际政治领域,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实体在国际事务中逐步掌握一定话语权,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被视作“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和“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在非国家行为体分担全球治理责任,为国际秩序稳定贡献力量的同时,全球化浪潮也为现有国际秩序带来新的“挑战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借助全球化时代下紧密相连的人员、物资网络而逐渐兴起,并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诱因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搅动者。“新世界”在呼唤史学家突破民族国家史学的局限,以新的解释框架、探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同时,交错纵横的全球经济、文化网络又为史学家们提供了解决问題的灵感和方法,即超越民族国家疆界,将传统国家事务放置于更广阔的跨国背景中考察,关注跨国现象与非国家行为体力量。另外,信息时代下,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推动形成便捷的全球电子资源获取渠道,相互交联的人员流通网络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使得跨国学术交流合作成为可能。
“跨国史”与“国际史”中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是对于当今全球化热潮的回应,二者又同样受益于全球化时代提供的新问题和跨国交流的机会。然而,“跨国史”与“国际史”的诞生又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国际史”的诞生是对传统美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范式的扬弃,而“跨国史”则欲以其丰富多样的跨国主题,实现对“美国例外论”的超越和民族国家史学的补充。
传统外交史学或国际关系史学,在诞生之初“是作为对国家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出现的,旨在记录已发生的事实,揭示君主和政治家秘密战略的模式”。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外交史学因其浓重的现实关怀和“最直接地支持和捍卫美国冷战事业”的热情而一跃成为美国显学。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外交史家逐渐意识到传统外交史学“缺乏理论的严谨性和方法论的创新”,“问题意识狭隘、视野逼仄、不熟悉外国语言和资料”,史学界对“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范式中狭隘的白人精英视角,过度关注国际局势中的危机事件以及政治军事问题,强调决策精英个人能力的发挥以及国内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问题的批判更是蔚然成风。
外交史学在进行自我革新的过程中,率先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学中吸收其“自下而上”看问题的理念,关注决策精英以外的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而后“国际化”与“文化转向”使得外交史学逐步重视多边档案和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将外交史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和文化经济关系中考察,“外交史”从而发展为“国际史”。“国际史”从产生至发展都围绕着批判革新外交史的主题,它将传统外交史学中“兰克史学”研究方法树为标靶,从新社会史、文化史与“国际化”潮流中吸收精髓,从而实现对外交史学的扬弃和自身研究视角方法的确立。“国际史”的诞生背景使得它与“跨国史”共享着超越国家疆界,注重交流互动的跨国视角,但其所重视的“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文化关系、意识形态,都并非“跨国史”强调的重点。
“国际史”的诞生发展是对传统外交史学的“拨乱反正”,而“跨国史”的兴起则是美国史学界对“美国例外论”的集体反思和超越。民族国家史学因其在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和巩固国家统一方面的特殊作用而长期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20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迅速增强,越来越多美国史学家们宣称美国的发展进程规避了存在于欧洲大陆的阶级冲突、革命剧变和独裁政府,并为世界提供了“自由”的榜样。然而全球化潮流下世界联结的增强使得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强调国家差异,力证自身独特性,忽视人类依存性的民族国家史学和“美国例外论”的局限性,由此史学家呼吁美国史学研究应突破民族国家史学框架,使“民族主义情景化,将美国历史描绘为跨国主题的变体”。
当探究视角转向两者的词源时,也可看出“国际史”与“跨国史”两者内涵的明显分野。“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中英文“inter”作为前缀一般表意为“在两者或多者间”,而“international”则传达出两个以上国家间的交互联系的含义。然而这个词也表明“国际史”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所以称其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乃是源于它扭转传统的外交史学只从国家本身看问题的视角,将国家间交流放置于变化动态的国际背景下考察,但其内涵中“去国家化”的意义甚微。学者亚历山大·迪肯认为外交史家、国际史学家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认同一定的基本原则,即“将重点放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入江昭(Akira Iriye)作为“国际史”早期倡导者之一,他将“国际史取向”阐释为“把一国的外交事务放在国际的框架,主要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国际体系下来考察”,这一国际体系既可以是传统的权力体系,也可以是经济体系与文化体系。因此虽然“国际史”日益重视普通人的历史活动,但在这一视角中个人的活动仍带着其从属国家的标签,“个人和团体依然是作为某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成为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反观“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詞义,入江昭曾解释说“trans-”是超越、跨越以及穿越(cut across)的意思,即跨越国界、跨越边界;“transnational”在表示越过国境的同时,也被用以形容“在国家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的全新的特性”。因此,从字面与词源意义上对比“国际史”与“跨国史”可以发现,“国际史”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在此基础上探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多向交流互动,以及国家框架下不同身份的个人与群体的历史活动;而“跨国史”则侧重于研究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与联系。
以上仅是从语言本身分析“跨国史”的含义,然而事实上国外学界对于“跨国史”的内涵与研究范畴说法不一,“跨国史”本身仍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伊恩·泰瑞尔(Ian Tyrrell)认为“跨国史”的目的在于“把国家发展置于背景之下,并从国际影响的角度来解释国家”②;它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塑成国家的国内因素和超国家因素,同时关注国家机构的形成”。而托马斯·本德认为,不应以“大陆”和“朝里看”的视野看待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上,而应将其视作形成全球联结的海洋世界的一部分。泰瑞尔与本德作为较早回应入江昭“国际化历史”倡议,并积极推动“跨国史”研究,两人都强调“跨国史”研究关注国家之间关系,并努力把国家历史放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将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传统国家事务视作国内外因素共同塑造下的产物。
《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编撰者之一皮埃尔·索尼耶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将“跨国史”界定为囊括“跨越国界的运动和力量”在内的种种叙述;在他看来,跨国史“是指商品,是指人员,是指观念、话语、资本、威权和制度”。相较泰瑞尔和本德,索尼耶对“跨国史”概念的界定更加宽泛,他不仅将国际权力关系与国际背景下的国家建构容纳在内,还将跨国运动与跨国行为体,不断流动交换的跨国商品、人员、资本以及观念都视作“跨国史”的研究课题。由于“跨国史”概念本身仍处于争论之中且相关研究课题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学术界在介绍“跨国史”概念与研究范畴时的基本做法是采用入江昭与索尼耶在近年来所提倡的更为宽泛的定义①。
与“跨国史”模糊的定义不同,国际史学者对“国际史”的研究范畴的定义较为清晰。冷战史是近年来从“国际史取向”中受益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冷战国际史以其研究视角、主体、史料的多元性,与跨国机构、人员间频繁交流而与传统冷战史研究相区别,其研究范畴与主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际史”的研究特点。冷战国际史著名学者梅尔文·莱弗勒在其论文中曾谈到,“国际史学者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因素编织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叙事中”,他们既重视“观念、价值、语言和文化”以及“种族和性别”,同时也探究强国与弱国间的关系,将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相结合,评估“意识形态对权力、威胁和机会的认知的影响”,考量“国内政治文化在塑造战略、外交、战争和和平中的作用”以及“军事能力和外交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国际史”研究范畴开始更多地考量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国家间关系与国际局势的影响,其中对观念、意识形态与种族性别的重视更体现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其产生的影响。然而,莱弗勒所谈到的“国际史”研究叙事中显然并不包含广义“跨国史”所探究的跨国移民与族群流散,思想文化、商品技术跨国流动,劳工、环境与社会正义等跨国运动,疾病传播、环境变化等跨国事务以及跨国行为体活动等课题。
借助“跨国史”与“国际史”研究者的论述,可以看到两者在研究范畴和课题上存在区别,而空间层次分析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二者的异同。按照空间维度去看待“跨国史”,其研究课题本身可以被划分为跨国框架、跨国网络、跨国空间这三个维度。其中,跨国框架所强调的是将国家历史放置于跨国背景下探究考察,一国事务之形成不再是简单国内动因的叠加,而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国家从诞生伊始便是整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一不在参与塑成世界,而它们在影响着别的国家的同时也承受世界给它们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跨国框架是用“上帝视角”审视国家如何被世界洪流所形塑又反作用于洪流本身,而跨国网络则是指跨国移民与族群流散,思想文化、商品技术跨国流动所留下的足迹,在世界勾勒出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无论是移民商品这类有形之物,还是思想文化等无形之物,它们的流动是不受国家疆界束缚的。除此之外,由于非国家认同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所领导的劳工、环境与社会正义等跨国运动,以及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政府组织,都活跃于一个非民族国家单位的空间范围之内,即跨国空间。
相较于“跨国史”多层次的空间维度,“国际史”的空间维度显得更为单一。“国际史”的内涵是以多国且多元的档案代替单一国家政府档案,以国际化视角考察国家间关系与国际局势,将外交事务置于变化动态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之中,并将“‘高端政治以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人权、对外援助、疾病控制、环境治理等纳入外交史研究”。其中,将外交事务置于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中,考察国家间双向互动交流对外交事务的影响的国际化视角与“跨国史”中在跨国框架内看待国家事务的内涵相一致。然而,“国际史”研究并不具备跨国网络与跨国空间这两个维度,“国际史”虽然提倡“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并努力挖掘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但它仅仅是运用这些因素去分析外交事务与国家关系,而并非撕下“国家”标签,考察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本身的流动过程;它所关注的经贸交流、环境治理与疾病控制等议题,大多属于国家主导下国际合作的范畴之内;它对联合国、欧盟与北约的关注,更多地源于其遵循外交史学重视探究国际政治中占据一定话语权的行为体的固有传统,而并非像“跨国史”那样是出于对非国家认同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视,而去关注那些凭借超国家界限的利益关切进行自我建构的跨国非政府组织。
三、结语
“跨国史”与“国际史”都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回应当今全球化热潮,且又都受益于全球化时代提供的新问题和跨国交流的机会。然而从诞生背景上来看,“国际史”的诞生发展是对传统外交史学中存在的固有弊端,如过度关注政治军事事件,强调白人精英决策者,忽视中下层群众等问题进行“拨乱反正”;而“跨国史”的兴起则是美国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狭隘的视野以及“美国例外论”的集体反思和超越。而若从词源意义上辨析二者,“国际史”并未摆脱民族国家的单位限制,是在此基础上探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多向交流互动,以及国家框架下不同身份的个人与群体的历史活动;而“跨国史”则侧重于研究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与联系,其相较“国际史”而言拥有更为丰富的“超国家”内涵。最后,运用空间层次结构看待“跨国史”与“国际史”的内涵可以发现,“跨国史”中包含跨国框架、跨国网络、跨国空间这三个维度;而“国际史”中将外交事务置于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中看待的国际化视角与“跨国史”中在跨国框架内看待国家事务的内涵相一致,但“国际史”范畴的研究显然并不具备跨国网络和跨国空间的维度。
注释:
①亚当·纳尔森:《冷战后美国史的转向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陳希 整理),本文为纳尔森于2017年6月7日,在北京大学所做题为《科学、教育和贸易:威廉·麦克卢尔和“矿物垄断者”:1800-1820》的演讲的整理稿,并于2017年7月6日刊发于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5698 (2018年2月9日)。
②Ian Tyrrell:《What is Transnational History?》,本文为作者于2007年1月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摘录,http://iantyrrell.wordpress.com/what-is-transnational history (2018年2月9日)。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新视野下的20世纪国际史——入江昭和他的《全球共同体》[J].世界知识,2009(6):65.
[2] Juliet Gardiner. What is History Today…?[M]. London: Macmillan, 1988.
[3]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4] Charles S Maier, “Ma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mell Univ. Press, 1980, p. 355.
[5] Dorothy Ro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4(4):909–928.
[6]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4):1038.
[7] Alexander DeConde.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8(2):286.
[8]入江昭.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历史研究的新取向[M].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4.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 1989), pp. 4-5.
[9]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J].美国研究,2008(1):26-46,34.
[10]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M].王勇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9(4):460.
[12]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13] Pierre-Yves Saunier, “Going Transnational? News from down under: Transnational History Symposiu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4.”[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vol. 31, no. 2 ( 2006), pp. 118–131.
[14]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J].历史研究,2014(1):153,144-160.
[15]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9(2):501–502.
[16]王立新,景德祥,夏继果.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N].光明日报,2017-02-13.
[17]牛可.超越外交史:从外交史批判运动到新冷战史的兴起[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