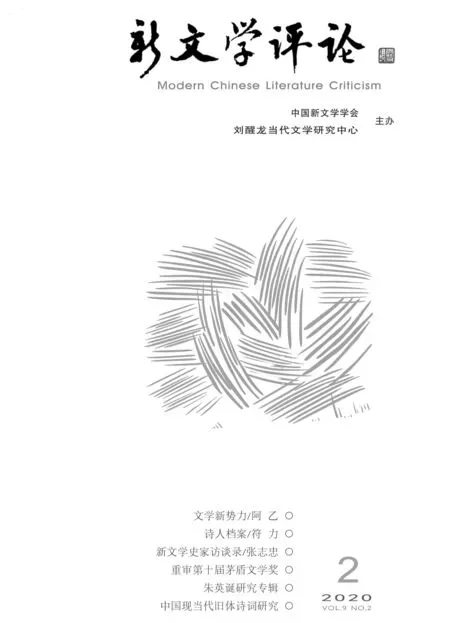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把诗意的核心部分放到语言的深层”
——符力访谈
□ 江 非 符 力
江非:符力兄好,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首先谈一下“身份”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身份”不是政治身份,也不是社会身份,而是与“海南诗人”这个称谓有关的文化身份或者说是地理身份。因为据我观察,作为海南本土出生的诗人,你以及稍后成长起来的90后诗人陈有膑、洪光越、陈三九等青年诗人,都在诗歌中表现了一种同样的气质,这种气质我只能用“自然”或者是“天然”这种概念来概括。在早年论及你诗歌作品的一篇短文里,我曾称之为“符力的新神供奉”,在谈及陈有膑的另一篇短文中,我称之为“陈有膑的直观诗学”。我个人认为,这种气质,应该就是海南本土诗歌的地方性,或者说是方言性。作为一种比较集中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诗学特性,这也是海南本土出生的诗人在写作上有别于其他任何省份诗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我想问问你本人是如何看待这种特性的?你觉得“海南方言诗学”为当下诗歌创作现场提供了什么?
符力:海南四大名菜声名远播,几乎人人都能叫出菜名来:“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和乐蟹”。这四道菜的制作方法,不是清蒸,就是白切,使得菜肴清淡、原汁原味相当突出。这样的特色和风味,称之为“琼菜”。此菜系脱胎于粤菜,又自成一家,根本特质是自然而然,不赞成因过分加工而失去原材料的滋味,反映了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海南美食主张与追求。绕了这么远,我想说的是,海南人的餐饮喜好和习惯大致相同,做人做事的风格特点却是千差万别。同样,湖南人和四川人都爱吃麻辣,但湘人不见得像川人那样酷爱打麻将。这表明了人们在物质满足上的趋同,在精神追求层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海南诗人不少,写作倾向和特点堪比热带雨林:草木纷繁、花叶多样。我跟陈有膑、洪光越、陈三九等90后诗人,都有到内地求学的经历,但总的来说,都是生在海南、长在海南;我们的诗作有“自然”或者“天然”气质,只能说是我们的诗歌认知和趣味相近,或者说是我们走在差不多相同的诗歌路上。因此,我们几个不能作为海南诗人在写作面貌和气质上的代表——我们的作品也不能说具有海南本土诗歌的地方性——海南诗人的诗歌创作,几乎不可能有、不应该有一个突出的面貌和气质,如果有,那就不是百花齐放、各自芬芳的自然的诗歌生态了。小范围内的少数几个诗歌同仁,倒是比较容易做到面貌相似和气质略同的。这里,举几个文学范围里的例子:众所周知,清代初期,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写“学人之文”;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人写“文人之文”,散文都富有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文风却有所区别;清代中叶,理学抬头,考据成风,方苞开创“桐城派”散文写作,影响了刘大櫆,姚鼐继承并发展了前者的文学创作,使之成为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当下诗歌现场,湖北诗人当中的张执浩、小引、沉河、林东林等人,以及多年生活在海南三亚的湖北籍诗人衣米一,他们的表达路数还真是比较接近的。由此可见,作品写成什么样,是作家诗人对文学的理解、趣味和追求的问题,相互交流,互相影响,说说笑笑着走在一起,有这个可能;但不是多数,很难具有整体代表性和普遍影响力。在这里,我提一下博尔赫斯的诗学观点。1972年,他在诗集《老虎的金黄》序言中写下:“我不相信文学流派,认为那都不过是把教学内容进行简化的方式。”这样,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在1975年出版的诗集《深沉的玫瑰》序言中说:“我多年从事文学,但没有什么美学原则。我们已经受到习惯的自然限制,何必再添加理论的限制呢?”是的,我支持博尔赫斯的这些观点,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路子,是我自己看好和自己决定的,是有比较清晰的个人印记的。只是,我至今也没能做得让自己满意。不过,我赞成你从“诗学特性”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几个人的诗歌创作,我希望海南本土出生的诗人都能野性十足地生长,各自写出有别于其他人的作品;也希望我们几个人各有各的秘密花园,确实有“一种比较集中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诗学特性”也不是坏事。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品质是真实、自然,像草木长在海岸,像巨浪扑向礁石,像美酒从蒸炉里流出,那样真实,那样自然,哪怕是由想象或虚构而来,其形象、颜色、气味、声音、光影、感觉等等,都能让读者认为那是真实存在的,愿意相信的,不是空洞、虚伪、造作的,不是一看就感到逆反甚至厌恶的。比如,杜甫写《春望》,说安史之乱导致长安城破败,民众流离失所,为此感到沉痛、抑郁、无助、无力,忧愁得无以复加。对此,用我们当下的日常口语来说就是:愁死我了!而杜甫是极好的诗人,他写的是诗,是语言的艺术,是文学的皇冠,所以,在这首诗的尾联,他是这样写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想想,在战乱背景下,一个人的“国”说毁灭就毁灭了,“家”也没有亲人的音信,能不备受打击、万分忧愁吗?能不渴望安宁、向往幸福吗?读了《春望》,我们会从内心里相信杜甫的经历和体验是真实的,他的思想感情是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古希腊著名诗人萨福这样写她的《守夜》:“今夜我守着/月亮,/七姐妹/下沉了/此刻,夜已/过半;青春/溜走;而我/独守空床。”(张文武 译)萨福把自己的经历、感触和思想,陈述得坦诚而又明白如话,因此,我们信任她,认为她的触景生情是出于真心诚意,她的精简表达是脱口而出,是信手拈来,于是,不加怀疑与设防,不知不觉地受了她的诗意的感染。对于萨福的诗歌,希腊文学史家C.A.特赖番尼斯在《希腊诗歌:从荷马到塞菲里斯》一书中指出:“(萨福)从未错误地使自己的诗歌依赖于理智,因为她知道真正的诗歌并不直接地需要思想,而是更加需要情感和直觉的敏锐。”是的,萨福有很高的诗意捕捉敏感和传达能力,这为她的好诗创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同样,杜甫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里的“深”字的使用,也是好得令人拍案叫绝。这里的“好”,由语言的精准或精确表达而来。博尔赫斯提过“精确”这个词,他是这样说的:“诗歌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精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王永年 译)可见,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度,真正好的诗人在语言艺术表达上,是有相近或相似的认知和追求的。从杜甫和萨福的好诗来看,我们明白,他们的真实、自然依赖于诗人高超的语言艺术,而不仅仅是选取了实实在在的创作题材。这就是我所理解和追求的真实和自然。下面的句子,可作为我这种取向的例子:
午后的山坡上,我遇见了
一群奔跑的青草
从南往北,青草们不停地跑着,跑着
风吹得越猛,他们就跑得越快
…………
风停下来的时候,青草们
齐刷刷地站住了,他们呆在山坡上
呆在浮云的阴影下,如同受了欺骗的
年轻人:一脸迷茫
——《奔跑的青草》
当时明月在,长椅
也还在。那里放过一本诗集
留下一对年青人的身影
和体温。谷雨过后
从条形坐板底下,越长越高的青草
坐满了长椅,坐满了
一个人的春天
——《青草坐满了那把长椅》
“青草奔跑”,“青草坐满了长椅”,标题中的两个动词,很寻常,却相当符合我呈现主体形象和传达诗意的需要。或者说,我凭直觉找到这两个词,收到了这样的表达效果:形象、生动、传神……因此,我可以说,我看到、听到、感知到、想象到的青草奔跑和青草坐满长椅,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我想达到的真实、自然效果,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这就是我的精准或精确。敏锐的读者看了就会透过语言表面,去发现、理解诗意的内涵和外延——不管什么年代、什么地域、什么人种所写的好诗,其所具有的持久能量,就是吸引阅读,激发思考和想象,从而发现诗歌高超甚至神妙的语言艺术,并从诗意核心找到思想或精神的钻石。我用诗歌的形式写人物,写山川草木、禽兽鱼虫、春花秋月,最终,都是借助文字符号记录人生,记录与人生紧密联系的时代,并提供乏善可陈的语言创造,以及浅陋的思考和理解。
谈到我的写作,有人认为:“他的一些诗体现了天然纯朴的传统美学,以及较为新颖的独创性。”我想,从以上两首诗的语言表现、诗意传达和整体印象(感觉)来看,可能比较符合你看到的“自然”或者“天然”气质吧。我说不清自己的诗歌写作达到了什么位置,但我会按自己的想法,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江非:我知道,你在多年来的诗歌研习和实践中,一直非常注重当下写作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把对古典诗学的揣摩与传承,视为自己诗歌写作和认知的命脉。这在你全部的作品中都有显要的呈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古典传统的?你觉得我们的最高传统是在唐宋,还是要继续上溯到先秦?有何区别?对于传统的理解,事关我们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吗?传统到底是一种建立在语言表象上的趣味,还是一种精神?对于传统的理解方式,据我所知,有孔子述而不作式的,有尼采重新诠释式的,还有奥古斯丁和布克哈特审视即创造式的,你愿意选择哪一种?近年来,在国内的诗歌现场,也兴起了一股追溯古典的风潮,甚至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你觉得这股风潮的得与失是什么?有人把这股风潮称为不完全理解之下的“伪古典主义”,你同意吗?
符力: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涉及两千多年的文学艺术积累,是什么,又如何学习、理解和继承,话题巨大、巨复杂,谁都三言两语说不完,也说不清。大家都知道,先秦诗歌包括《诗经》《楚辞》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传统民歌和部分原始社会歌谣,那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源头,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源头。其中,《诗经》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楚辞》则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我们后人学习中国文学,理所当然要回溯到这个源头,去注视,去触摸,去闻,去嗅,去感觉,以及去想象那无比智慧、无比光荣的先人留下的丰富家产。而中国传统文学的巅峰在唐宋,最高的古典传统也在唐宋,只是,如果想理解诗歌的本质,就要老老实实地琢磨先秦诗歌,因为,那里有我在上文提到的诗的最重要的品质:真实、自然。来,请听古人的叙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再听古人的感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采薇》)显然,这是无限贴近读者心灵的朴实、自然、真诚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来自千百年前的人类,如今听起来却仍像风吹、雨落、花开一般清新扑面,一般纯粹、自然而然,让人怎么听都觉得舒服。我想,最高级的声音就是这样了。而发出这样的声音,居然是忘掉所有的技巧,仅凭摸着胸口、贴着内心,就做到了。当然,聪敏、有悟性的人才干得动这活,笨嘴笨舌的人就难以胜任了。毕竟,文学艺术是人为的作品,分寸把握得好,就收到不着痕迹之妙,反之,就暴露了创造力之不足。
我们的古典文学传统,既包含你说的“是一种建立在语言表象上的趣味”,也包含“一种精神”,是文学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我们从古典文学传统里学习什么,是我们的需求问题,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就去里面挖掘什么,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所愿,不存在什么强制力量的作用。不过,我们是中国文学的后人,我们应该像一代代先人那样,自觉地去研习、吸收,承担起了解传统文化、传播文化精髓的光荣使命,并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使整个中国文学之河奔流起来,水光潋滟、波浪激荡、声响迷人起来。
在对待传统文学的方式上,我希望学习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尊重他们,把他们的东西弄清楚,不任意发挥,不至于自作聪明歪曲了他们的原本。只是,在吸收和利用上,我试图从中获得启发、变通,使之既有旧的保留,又有新的创造。
你提到的近年来国内诗歌现场追溯古典的风潮,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无妨视为当代诗人的新诗探索倾向之一。探索,与静守、固化相对立,是积极作为的表现。人类社会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意味着文化、文学也在新生,也在变异,并一点点地累积和丰富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支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种种探索,只是,应该把一双明亮的眼睛放在未来,并从未来看向当下,即用超前的眼光倒回来观察今天,从而追问我们探索的得失和意义何在?如果一直低头往前走,可能抵达辉煌的顶峰,也可能坠入幽暗的深谷。这个道理,几乎人人都懂,而可贵的是时时反观和审视,并及时做出调整。只有这样,探索本身才会散发出金光,而不是成为徒劳、伤害和遗憾的因由。
江非:在中国的古代诗人中,你非常看重杜甫,每每谈起诗歌,经常引用杜甫的诗句。你为何如此喜爱这位诗人?他给了你什么样的诗学启示?有人曾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指称概括杜甫的诗歌,你觉得准确吗?在“写我之心”和“写现之实”这二者之间,你觉得杜甫首先是写了什么?它们二者有何关系?杜甫到底是为我们树立了人的形象,还是描摹了时代具象?我曾认为杜甫代表了“人之善”,李白代表了“人之真”,王维代表了“人之美”,但后来经过批判还原,我又发现由于对存在的拷问王维乃是代表了“真”,李白由于他的前定和谐却代表了“善”,而杜甫由于他的崇高庄严却代表了“美”,可以说,王摩诘、李太白、杜子美才是他们诗歌的真正指称。你觉得我的这种看法对吗?当下的诗歌写作现场,近年来也兴起了一股“现实主义”之风,但是有人却因为这股风气中生产的大部分作品,仅是来源于简单的直接经验的,没有经过杜甫一样的至善之心审望,没有经过至美之镜的检视,也没有经过以历史普遍性为依据的反思和批判,而把它们称为“伪现实主义”,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符力:稍微夸张一点地说,答完你这些问题,都可以出几本书了。我还是挑几个问题来简单说说吧。

杜甫的精神之光,在人学上,为我照亮了一个口子。他的诗学,也为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意义。为什么写诗?写什么?怎么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文学悟性高超的中国古人的回答。杜甫极其注重日常情景和细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他常常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写细微的日常即为写宏大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写作,是仰头望苍天的,也是俯身向下,让心灵贴近苍生和大地的,凡是能捕捉得到的,他都有可能写,写所见所闻,写思想感受,写晨昏,写春夏秋冬,一直写到生命的尽头,只要能拿得起笔,只要还有思想感触,他就有诗。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用一生去换来的绝唱。易言之,杜甫的写作,是与人生经验紧密联系的,他的写作路数决定了他有写不完的诗,不像当下的一部分诗人,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写着写着,就因无话可说而写不下去了。
从杜甫那里获得启发,也是借鉴了唐诗里常见的表达技艺,我偏爱这种看似无比寻常实质上魔力无限的语言表达方法:叙述。叙述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背景下叙述?带着什么思想情绪在什么地理环境下叙述?叙述什么?为何又如何叙述?一首诗歌涉及这么多问题,便是自带解读吸引力。诗歌里的叙述,天然具有这样的能量:把诗意牵引到人文历史的彼岸,从而丰富作品的内涵,或拓宽其外延;叙述,可以有多种角度,其中,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很容易收到不动声色,却情思隽永、意味深长,乃至玄妙的艺术表达效果。在明清以前的诗歌宝库中,因叙述兼描写而产生迷人光华的诗句不胜枚举,美如盛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2018年8月,我走访海口市周边的几个古村落,在《过谭昌村》里记录了以下观察和发现:
七个黑衣老人:七块火山石/堆坐一圈,墙边烤火/……/我踩着落叶离开火山村,已是黄昏时分/烤火老人只剩下其中的五个/明天,后天,海风越吹越寒凉/一起取暖的将是谁跟谁/列车从南港那边开来,朝琼山那边驶去/我听见的,是呼的一声,不是缓慢的/咔嚓,咔嚓,咔嚓
从诗歌抒写的意境里,有阅读耐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乡村,是城市的边缘;从列车运行的声音里,读者能听出——从谭昌村附近经过的,不再是几十年前的慢吞吞的绿皮火车,而是速度飞快的动车。动车,为这首诗交代了时代背景,也为主体的生存状况提供了暗示:时代变得太快了,老人们不可挽回地退出生活的舞台,来到了人生的冬天,只能像石头那样“堆坐一圈”,在“墙边烤火”,听凭死神的发落了。这就是“老人”在这个时代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这用笔轻浅、看似无意的叙述,呈现了我对时代生活的观察,对人物生存的体味,以及对其命运走向的忧虑。但是,在这个巨变中的大时代,我也仅仅是一个不知道跟谁“一起取暖”的,无能为力的小人物,只能“踩着落叶”,从城市的边沿离开,也是从时代的边沿走远,除了旁观和侧听,我还能做什么?谁能给我指引?上天?此思此想,此情此意,已无须言传,留待读者意会便罢了。
2018年10月初,我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海南岛,来北京工作,开始新的人生。不久,我大致了解了山东、河南、河北的乡镇居民生活,通过叙述平原上的黄昏景象,来反映我对当下北方民众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民众命运和乡村前景的忧虑:
园子外的天空下,柳树、栎树、桦树、杨树/如此贫穷:叶子掉光/上无片瓦,哪里都去不了/榉树、朴树、椴树、栾树、槐树、枫树/如此无助:人人自危,不可自拔/哪里都去不了/七叶树、白果树、合欢树、悬铃木/勉强度日,都在那里/等着// 等着。暮色四起/寒风一遍又一遍地搜刮/麻雀饿死/落日砸向平原尽头的群山/溅起满天星斗
我罗列了很多种北方树木,清楚地叙述或者描述了树木们艰难的生存状况。我在文字表面明着写树木,却在文字背后暗合了北方民众的生存现实,以及时代信息。我动用的这种修辞方法,是“隐喻”。我一般把话说得轻淡一些,或者婉约一些,因为我已经把诗意的核心部分放到语言的深层,就没必要用蛮力在语言外部敲锣打鼓,担心读者把我想说的话忽略掉了。
是的,我私下认为,诗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言外之意”。因此,我偏爱诗意的“隐含”,而不喜其“显露”。我反复琢磨金昌绪的《春怨》、王维的《辛夷坞》、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唐纳德·霍尔的《赶牛车的人》、詹姆斯·赖特的《在明尼苏达州的松树岛,躺在威廉·达菲农场的吊床上》,以及雷蒙德·卡佛的《邮件》等诸多杰出诗篇,试图理解我所倾心的人类的诗歌语言悟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时光中,我获得了作为诗歌读者的幸福感。
江非:到现在,你已经有两次长时间地离开海南岛。第一次是当年到重庆上大学,第二次是2018年到北京工作。第一次离岛可以说对你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形成了重要的几乎波及一生的影响,那么,第二次离岛到北京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和思想有何变化?这种新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影响?它导致何种的新趋向?你是如何认识这种当代社会中人在生活中的城市游牧的?你在北京所从事的工作是诗歌编辑,会接触到全国各地诗人的大量作品,在你看来,目前的青年诗人,尤其是80后、90后诗人的写作所表现出的大致趋向是什么?他们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以及70后诗歌有何关系?这样的趋向,对你的诗歌写作有何启示意义?如果“小传统”就是在场的前辈诗人作为榜样,影响到了后辈诗人的写作,你作为诗歌编辑,观察到哪些前辈诗人(比如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了这个“小传统”?“小传统”能否作为一个考察诗人写作的重要尺度,让我们来拨开当下诗歌界的种种认知乱象,来认识那些真正的作品和诗人,尤其是帮助各位诗人来认识自身?你想对那些更年轻的诗人说些什么?
符力:对一些朋友来说,我这次到北方工作,是一件让人疑惑不解的事。难怪有人直接问我:“你已经是中年人了,还北漂啊!”在听到这个朋友的询问之前,也就是在这次出岛之前,我已经把要不要换一个地方生活的问题想过很多遍了,我告诉自己:出去了,尽管还是做文学编辑,领紧巴巴的那么一点工资,但生活变了;如果不出去,那就得延续二十年来年的生活——在海口,从西向东,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安心舒适地把半个小时放在那里。于是,我只好匆匆退回那间逼仄的小屋。在老家,虽然双亲身体健康,买米买菜的钱刚刚够花,我们几兄妹用不着太忧心,但他们日渐衰老,而每年清明过后,南风把干枯的苦瓜叶吹得沙沙响,我禁不住心慌。是的,每年的那个时候,就不是种瓜种菜的季节了,乡亲父老都把自己空置起来,只等上半年早稻成熟了。这样看天吃饭的生活,很快就会把一整年时间耗尽!想到光阴虚度,我就焦灼不安,父母也不愿把我留在身边,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返乡离乡,不知不觉,就到了这个泼洒出去就不可收拾的人生的危险时期。因此,我忐忑不安地把自己放出去,蒙上眼,不看他,愚也好,蠢也罢,让他去经历,去体验,去浪几年。上天知道,他还能有几年可浪呢!
到了北京,我多次在小区门口遇到一个徒步上早班的外国人,他的头发全白了,估计快到六十岁了。一个比我老得太多的人,都有勇气离开欧洲或美洲,来北京打拼。我不过是在自己的国家,在两个省市之间挪了一个窝,又有什么可怕的?而你江非兄,十二年前就从山东去了海南,蒋浩兄从北京去海南的时间更早,想到你们的经历,我怎么说都要给自己鼓劲啊。在这里,亲眼看到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坐地铁、搭公交。他们穿戴新潮、仪表讲究,早出晚归,总是能给人与时间赛跑的紧张感。置身于这样的氛围,我感到安宁了很多,在岛上消耗时间的那种焦灼和恐慌感淡化了;也意识到,北京是让人来紧跟时代、奋力追梦的,而不是一个让没有理想的人在这里吃饱了就睡到自然醒的地方;并更加明白,我们这个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变化,是全体奋斗者只争朝夕、辛劳苦干的结果,跟那些久久躺在海边晒太阳的人,一直坐在骑楼老街吹风喝椰子水的人,早晚都睡在七仙岭山间吊床上闻鸟鸣的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北方,我已经生活了一年半。诗歌写作积极主动了一些,其原因,是环境变了,经验新、感触多,有话可说;也是时间催逼,不能枉自荒废。这里的生活对我的诗歌写作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那么明显,但几首短诗让我感到比较心安,我没有白写:《我为何》《平原上的黄昏》《空气的回答》《松果》《没看见,也要相信》《站在山峰上眺望》。我从来没有像小说家那样预先做规划、搭框架,一步步地完成创作,一步步地抵达目标。我的诗歌写作,是随机、任意的,也就是像李白、杜甫、苏轼他们那样,活到哪写到哪,与自己的人生挂得上钩的。
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在于语言方式和语言效果,也就是在于你怎么写,而不是你写什么。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城市生活,诗人的创作资源没有太大区别。不存在你选了一个不多见的题材,就决定了你的作品比我的好上几万倍。比如,遭逢安史之乱,长安衰落,民众苦不堪言。当时的诗人,人人都可以写那个题材,但能够把作品质量拉开距离,让诗人的思想境界和品格修养凸显出来的,是一个诗人的语言艺术创造力。习诗多年后,我才看到了这一点。此后,我逐渐有了提炼语言、提纯诗意的自觉,能从寥寥几句诗里看出一个诗人大致的诗歌悟性和语言功力。
在当下中国诗歌现场,60后诗人是不可动摇的巨无霸军团。相比之下,70后诗人弱很多,但他们是正在出场的未来的主力军。目前最活跃的是80后、90后诗人,他们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还获得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是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诗人群体。正因为如此,在诗歌练习和上升阶段,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诗人都热衷于向外文诗歌汉译本学习,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传统诗歌,使得这个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人未能形成纯正的诗歌认知和观念,以致倾向“学院派”诗歌写作。“学院派”诗人的生活圈子较大地局限在校园或文学教育机构,使得他们较少体验纷繁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时代生活,直接从现实中获取细节、发现诗意的能力相对较弱。或者说,他们的兴趣不在从现实中获取细节、发现诗意这上面。他们倾心于书斋写作,耽于词汇组合,每一个作品都是文字烦琐芜杂,徒有文本形式,而常常是前一句跟后一句毫无关系,整体表达不知所云,根本谈不上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诗意也不集中、清晰、突出。这样的现象,虽然只是出现在较小的诗歌圈子内,但其中的一些诗人,已经在当代诗歌的发表、批评、传播和出版等方面,占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有些偏颇的诗歌理论,难免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注意。
未来的中国诗歌主流难以预知,但有必要清楚:文学因其功用而存在,对人的生存和时代的进步有价值的作品才不会被抛弃。这些认知,对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写作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年轻的诗人,我这里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相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做无用功。
江非:2008年来到海南岛,至今我们已经认识了12个年头了。时光飞速,不觉已老。如今你已去了北京,我还留在海岛。但是朋友间因诗歌而结下的友谊依然如初,12年间,我们也和海南岛的诗歌兄弟姐妹们,结成了一个干净健康的“诗歌圈子”,虽然见面谈论诗歌的时候很少,但是大家会经常聚聚和相互记挂、惦念。在你看来,这样的诗歌圈子或团体的存在,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对一个地方的诗歌发展有何影响?你更期望一个什么样的诗歌圈子或团体?离开海南岛一年了,你最想念的是什么?
符力:我记得,你是那年6月21日到海口的,那是汶川地震一个月后的事。而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还未停止肆虐,死亡的消息令人寝食难安,春暖花开成为一场正在到来的巨大的浪费。我们这时候谈诗,回忆往事,适合吗?可是除了捐款买口罩,我们又能做什么?既然你起了头,我们就重温第一次相聚吧:
当晚,我们在南海大道见面,你居然连啤酒也不喝!我猜想你是在哪里把胃喝坏了,被吓怕了吧?十余年过去了,现在想来还是历历在目:少君老师先去餐馆等你,我买水果随后上楼。你见我进来,便起身给我打了一碗米饭……从那时候起,岛上有了我们的一个诗歌圈子,每隔一段时间,不是你到海口,就是我们去澄迈,我们吃街边饭菜,喝福山小镇的咖啡,天上地下想啥就说啥,但你更多地是把你的文学欣赏分享给大家。很快,陈有膑、洪光越他们出现了,他们多么优秀啊!如果你不在海南,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简直是个奇迹。我是2005年10月才上网交流诗歌的,身边没有诗歌朋友,网上是虚拟世界。我上初一时就开始发表作文,可是那么多年没人点拨,没人指引,读不通好诗,写不出好文,一直在孤身游荡。唉!智慧来得太晚了。
2008年,你上岛了,少君老师在《天涯》发我的诗,海南作协给我一份兼职的工作,我终于比较安心地走在读书写作的路上了。是的,2008年是我的人生转折年——尽管吃不饱、饿不死,我也不用去为做业务等客人而心慌了,我不情愿把时间耗费在那上面。
我习惯了孤军奋战,诗歌圈子给我的是朋友间的日常往来,文学上的影响比较小,就是说,我确实需要指点,但对我有帮助的东西是我主动去接受的,而不是别人推给我的。比如,你的《我在傍晚写下落日》,我读了很多遍。你对 “埋没”这个词的使用,给了我语言表达上的启示,非常难忘:
我在傍晚写下落日、麦子,和收割一空的麦田/……/但我又写到了花朵,写到了土豆,以及/那些像花朵一样开败了的、那些像土豆一样被埋没的/我就一下子说不清了——我们的一生究竟要忍受的是什么
不过,诗歌群体的存在,增加了互相交流和碰撞的机会,能够激发一个有上进心的诗人的竞争意识,从而推动他积极地向自己的创作目标走去。互相竞争的人多了,这个群体的创造力就自然加倍聚集起来了。很多人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简直是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毕加索、庞德、海明威、乔伊斯、菲茨杰拉德、T.S.艾略特……都在那里生活过,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彼此的朋友,生活上有照应,创作上有交流——庞德为T.S.艾略特改过《荒原》,T.S.艾略特在《荒原》题记中写下: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人是群居动物,需要对话交流,文艺上有个圈子,互相联系又彼此独立,是好事——强大得像狮子,只能独行,那也未必不可。只是,海南很奇怪,一直没有什么力量去激励人们做一个精神世界的追梦人。极少有人甘当冒险者,安稳度日的饮食男女倒是满街盈巷。如果多一些人读书写作,玩好听的音乐,拍好看的电影,做迷人的美术……那样,岛上的时光就有意思多了。只是,文化艺术上的作为,是需要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来做支撑的,所以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保障生活上。而今年,受病毒传染的打击,谁的工作生活都不容乐观,我们现在还是注意防护,争取安安好好地渡过这个难关吧。我们都多加保重!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