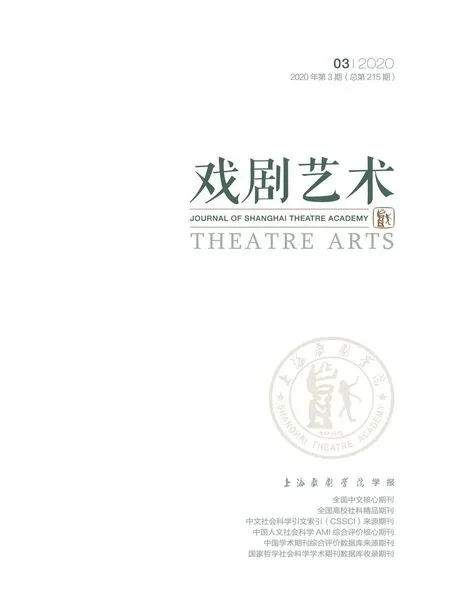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张协状元》的文本性质
——兼谈《张协状元》的时代断限问题
戚世隽
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进行断代和鉴别,有多种方法。如有以为“一是文献学的、文学的方法,一是语言学的方法”。(1)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有总结为三种:一、哲学、文学和史学方法,从思想内容、时代背景入手;二、文献学方法,从版本目录、作者生平、校勘辑佚入手;三、语言学方法,从语音、语法和词汇入手。(2)方一新 :《作品断代和语料鉴别》,《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2004年第1期。对于不署名的戏剧小说作品,常苦于并没有确凿的外部文献材料,所以还是要采取内证的手段来探讨。有“南戏始祖”之称的《张协状元》(本文简称“《张》”),其时代断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在检讨诸种论证角度及结论的基础上,对《张协状元》及古代民间曲本的文本性质作进一步思考。
一
清代乾嘉学者已熟练地运用文本中涉及的名物制度,来考订文本年代。现代学术史上如明史专家吴晗利用《金瓶梅》中出现的太仆寺马价银等来讨论小说的成书时间及地点等,都是典型的例子。(3)吴晗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读史劄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该文最初发表于《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在论及《张协状元》的时代问题时,仍有不少学者在延续这一思路。如持北宋说者认为“从剧中提及的宋代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引用宋人作品中的成句看,当作于宋代末年。这是因为剧中所提及的宋代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引用宋人著作中的成句,皆属于北宋”(4)俞为民 :《宋元南戏考论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6页。,由于论证角度的不同,所得结论也各有差别。
近年来又有如从剧本中的民俗现象、物价、避讳等来进行考察。如从剧本涉及的占卜术出发,提出《张》剧中相士最擅长揣骨听声,而宋代揣骨听声术最为流行,与宋代术数氛围一致;剧作还引用了北宋测字大师邵雍的名言,邵雍在民间产生影响主要在南宋中前期,由此推断《张》大概作于南宋中前期。(5)杨秋红 :《〈张协状元〉编于宋代说补证——以张协占卜为视角》,《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此段当化用宋杂剧中的“揣骨听声”。也有研究从分析《张协状元》中出现的物价水平入手,考察最吻合的朝代。论文涉及日常消费、货币使用和棉织业的发展,得出《张》成书于南宋嘉定年间的结论。(6)黄婧 :《从物价角度考证〈张协状元〉成书年代》,《曲学》第二卷,2014年。或从《张》剧中存在不避宋帝讳之处,认为剧本当作于元初。(7)刘怀堂 :《〈永乐大典〉之〈张协状元〉应是元初作品》,《戏剧》,2008年第4期。论文提出如第27出“里姮娥爱少年”及【斗虼麻】“枉教姮娥,谩爱少年”,“姮”字犯了宋真宗赵恒讳等例证。
不过,利用名物制度来进行断限,一是一般只能证明作品的时间上限,却不能证明作品的时间下限,即叙事作品的时代标志并不绝对等同于作品出现的时间。(8)如杨栋即提出“文中提到历史人物,只可说明它不早于此时,而不能证明它产生于此时”(《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如主南宋中后期说者,提出《张》剧第三出“村南村北梧桐角,山后山前白菜花”两句念白,出自南宋中叶人曹豳的一首诗,但也有学者认为,剧白与曹诗不存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可能分别摹写浙东风俗景物,也可能同出前人成句。(9)胡雪冈和孙崇涛据曹豳诗,考证该诗作于曹氏成年(1189年)至中进士(1202年)这十年间,断定《张》剧成于南宋中叶。俞为民则以为剧白与曹诗不存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可能分别摹写浙东风俗景物,也可能同出前人成句。参见胡雪冈 :《南戏〈张协状元〉的编剧时代——对〈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的商榷》,2013年第4期;孙崇涛 :《〈张协状元〉与“永嘉杂剧”》,《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俞为民 :《宋元南戏考论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6页。
二是名物断限法,在有效性方面易存在争议。胡适曾指出顾颉刚等人 “用文字,术语,文体等等来证明《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这个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用的,但胡适同时指出,这个方法也是很有危险性的,“因为,(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总而言之,“同一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悬想某一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例证存一点特别戒惧的态度”,“至于摭拾一二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那种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险”。(10)胡适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3-399页。比如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物价,未必与历史真实一一吻合,通俗文学作品也常常并不严格遵守避讳等。
胡适从证据的有效性和严谨性出发,指出用文本、术语、文体来断限的危险性。但是,戏剧文本确有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质,戏剧的表演性特征使得观众的接受与交流度,是构撰作品时的重要考量标准,特别是《张协状元》这种源自底层、一直活跃在表演中的民间文本,其表演方式不能滞后于时代,而诸凡笑话、俗谚、科诨等桥段,也要让观众能够理解与共鸣,故选择离表演时代较接近的人事或观众都熟悉的典故。《张协状元》中关涉的核心历史人物是王胜花之父王德用(980年-1058年)。王氏为一时名贤,欧阳修《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称其“状貌雄伟动人,虽里儿巷妇,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11)(宋)欧阳修 :《居士集》卷二十三,《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7页。第二是柳永(987年-约1053年),剧中称“这官人曾做三百单八只词,博得个屯田员外郎”,又云“耆卿也吟得诗,做得词,超得烘儿,品得乐器,射得弩,踢得气球”。此二人当为剧作表演时代观众熟悉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该剧中有不少的宋杂剧段子,如胡忌《宋金杂剧考》,《张》第24出“赖房钱麻郎”,很可能就是宋杂剧“赖房钱啄木儿”,“同类形式演出,惟‘麻郎’和‘啄木儿’是曲调之别罢了”。(12)胡忌 :《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前述学者讨论《张协状元》中的占卜情节,但此点也业已见于宋杂剧的《揣骨听声》。(13)此为张勇风揭出,见《宋代杂剧形态与〈张协状元〉的文本生成》,《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也有相近名目《卦铺儿》《问前程》。《张协状元》选取王德用和柳永,亦并非作者直接取材于生活,而是他们也已进入当时的杂剧段数,成为调笑对象。(14)王德用从历史人物变化为嘲讽的对象,已见于宋杂剧《不及垛箭》和《打王枢密爨》。《不及垛箭》见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页),由任中敏发现并命名,参见任中敏 :《优语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打王枢密爨》由薛瑞兆揭出,参见薛瑞兆 :《宋金戏剧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6页。“宋官本杂剧段数”中又有《变柳七爨》,疑即第四十八出净脚所扮柳耆卿与丑脚所扮王德用调笑逗乐情节的源头,参见赵山林 :《宋杂剧金院本剧目新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近有学者指出,《张协状元》的核心情节“榜下捉婿和进士富娶”,也都来自宋杂剧。(15)张勇风 :《宋代杂剧形态与〈张协状元〉的文本生成》,《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对流行的宋杂剧如此高频的使用,而且有部分并不具备叙事功能,颇让人疑心这本就是一部民间以“攒戏”的方式捏合而成的剧。类型多样的宋杂剧段数,已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单元,只要稍作缀合,便可结撰成较长篇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确信,至迟至南宋,《张协状元》当已在戏剧舞台上演。
二
由于戏剧作品的特殊性质,除名物制度以外,也有学者使用《张协状元》中的曲牌,来论证其写定的时间。
关于《张》剧中的曲牌,钱南扬以为“剧中用的全部都是南曲,尚未受到宋亡后北剧流入南方的影响”,韩国学者梁会锡《〈张协状元〉写定于元代中期以后》一文,排比了《张协状元》中对于北曲同名曲牌的运用,发现《张》剧与元曲存在诸多共有现象,从南北曲大量交叉的现象,得出南曲化自北曲的结论,继而断定《张》剧不可能早于元代,当作于元统一以后。(16)梁会锡 :《〈张协状元〉写定于元代中期以后》,《艺术百家》,2000年第1期。该文由于未注意到南北曲的“共祖”现象,把某些南北曲“共祖”的旧曲调混入“共有”,如【粉蝶儿】【迎仙客】【醉太平】本为唐宋词入曲,而“共有”不能证明张《剧》晚于元曲。因此,后又有杨栋在剔除了二者“共祖”的唐宋词牌、诸宫调牌等古曲之后,“发现《张》剧至少有二十多个南北曲同名的原生曲牌。明代学者多据此认为北曲早于南曲,南曲为北曲之变。现代学者均对明人之说不屑一顾,一般笼统地认为南北原生曲牌分别出自南北地方俗曲,各有其渊源。这就遮蔽了南北大量同名本生曲起源的难题。《张协状元》如被认定为早于元曲的南宋作品,其中所用【山坡羊】【叨叨令】【红绣鞋】等,历来被认为北曲原生的众多曲调,就只能认作出自南曲。这样,南曲为北曲的源头,就将是一个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事实”。(17)杨栋 :《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杨栋通过将【叨叨令】【斗黑麻】【红绣鞋】【山坡羊】等曲牌与出土文物相对证,判断其源出于北曲,由此推断“《张》剧的编写年代不早于元初,应在关汉卿等早期元杂剧家之后”(18)杨栋 :《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又有武迪从【红绣鞋】【斗虾蟆】【沉醉东风】三个曲牌入手,并借鉴出土文物相关材料,进一步论证这些曲牌产生于元代(《补证〈张协状元〉编成于元代——从【红绣鞋】曲牌入手,《昭通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补证〈张协状元〉编成于元代(二)——从【斗虾蟆】入手》,《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补证〈张协状元〉编成于元代(三)——也谈【沉醉东风】》,《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陈姗姗从【复襄阳】入手,论证《张》不会早于南宋末年(《从曲牌〈复襄阳〉看〈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但这一思路与结论也引起较多异议。
《张》剧与北曲共有的七支同名曲牌,既同名异调,字数、韵脚、平仄均不相同,究竟是北先南后,还是南先北后?或是同源异流,一入戏文而唱南曲,一入杂剧而唱北曲呢?
比如【叨叨令】北曲正宫定格合在结句之前要用“……也么哥,……也么哥”两个重叠句,而《张》剧第三出也用两支【叨叨令】,但并没有“也么哥”这一标志句型,按杨栋的理解,“这只能解释为元曲南化所致”,问题是究竟是“元曲南化”,或是“南曲北化”,还是只是同名的另一个“叨叨令”,原本就没有所谓的“原始性的标志句型”呢?
本文以为,同名曲牌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我们讨论的前提,如果都以同源异流来解释南北曲同名曲牌的不同,那么,我们讨论南北曲源流时,追寻其唐宋大曲、教坊曲和民间曲子词源头的做法,也都失去了理论基础。王灼《碧鸡漫志》中的对词牌的解释,可以作为更为具体的注解:
《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当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调《念奴娇》,世以为天宝间所制曲,予固疑之;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而近世有填连昌词入此曲者,后复转此曲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19)(宋)王灼著,江枰疏证 :《〈碧鸡漫志〉疏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可见,一曲可多变,可多调,可不断填入新词,是曲牌的基本特征。杨荫浏在解释【满江红】时便说,“以词牌《满江红》为例……六种形式,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严格说来,可以说,无一相同。曲牌又如何呢?《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满江红》,分别属于北曲之仙吕调和南曲之南吕宫及正宫,词句间虽仍有相似之痕迹可寻,但变化之大,则又远非一般词调可比拟”,“又同一牌名,其词句形式的同中有异,其曲调旋律之大不相同,后面数例,已可说明。我国古人,用了同一曲牌,何以能写出许多不同音调来表达许多不同情调,而不至于像那些只知西方音乐的人那样,死死地视同曲表达相异的情调为不可能了”。(20)杨荫浏 :《曲牌——同名异曲问题——重读1979年的资料想到一些问题》,《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即如【叨叨令】,在北曲也还有另一种叠字体,以“兀的不”“X杀人”(“X”指该字可换,如“愁”“闷”等)为常用标志,因此,虽然《张协状元》中的与北曲同名曲牌,在词格包括字数、韵脚、平仄方面并不相同,但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
但是,具体到这些同名曲牌,究竟是南传北,还是北传南,而这种影响的产生时间,是否要晚至元代初年呢?北曲的形成,学界有以为金朝前、中期。如廖奔以为,“北曲的成形,大约可以早到金朝前、中期。距靖康之变(1126年)四十余年的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出使金国,在真定(今河北保定一带)看到的都是带有异域风格的歌舞,因而感叹‘虏乐悉变中华’。金国地界里盛行的民间俚曲,其音乐旋律很多采用这些所谓‘虏乐’,因而与宋朝音乐的距离越拉越大,北曲就在这个过程中奠基了”。(21)廖奔 :《北曲的缘起》,《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2001年3月。这里的理由是南宋乾道六年范成大出使金国,在真定看到了带有异域风格的歌舞,因而感叹“虏乐悉变中华”,而金国地界里盛行的民间俚曲,其音乐旋律很多采用这些所谓“虏乐”,因而与宋朝音乐的距离越来越大,北曲就在这个过程中奠基了。这一说法过份强调了胡乐在北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北曲中的大部分曲牌仍来自于唐宋大曲、教坊曲及唐五代曲子词的事实。(22)在讨论隋唐曲子的兴起和盛行时,文学史家亦以“胡乐”兴起来论说。但音乐学者以为:“这种认知不无道理,但是过分强调胡乐的地位和作用,则好像曲子是因胡乐才得以生发、壮大的,这多少显得胡乐有点‘救命稻草’的意味。事实上,从先秦的‘四夷之乐’到秦汉以降散乐百戏(尤其是幻术),‘胡乐’既从来没有断绝与中原的交流,也不曾兴盛到取代中原音乐。”参见郭威 :《制度承载:古歌 乐府 曲子》,《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黄翔鹏认为:“后出的‘胡乐’,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也确曾有过盛行的阶段或时机,但在宫廷的盛行,未必便是社会的‘泛滥’,在宫廷的‘销声’也未必是社会上的完全‘绝迹’。”参见黄翔鹏 :《两宋胡夷里巷遗音初探》,《黄翔鹏文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南北曲在形成的机制上,并无本质不同。南曲是在吸纳词调、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北曲亦如此。且北音南来,也早在金章宗之前便已发生。如《宣政杂录》有: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于朝。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23)(宋)江万里 :《宣政杂录》“词谶”条,《全宋笔记》第七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又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云: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24)(宋)曾敏行 :《独醒杂志》卷五,《全宋笔记》第四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臻蓬蓬歌》是女真歌舞,汴京人模仿其声调歌唱,可见北宋末年在汴京便已流行番曲,而【异国朝】等,都是汴京人依据番曲曲调唱出的曲牌,带有北地民族特色。且称“番曲”,当原本亦已存在非“番曲”。
北曲的形成以至成熟,有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受胡乐影响的北曲曲牌,大规模的出现并稳定当在南宋后期,但有部分源自唐宋词曲的曲牌,在北宋末年当已有存在的可能。
《续资治通鉴》记载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臣僚奏疏:
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朝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合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25)(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140《孝宗纪》,《续资治通鉴》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745页。
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靖康之变(1127年)之后的四十年,按此条记载,在十数年前,临安好为北乐已成流俗,则北乐传入南地,又必远早于此时。作为以口头传播方式的曲之流行,远比文字要更为迅捷,虽然古代通讯远不发达,但曲随人走,宋金之际的时局变更,更加给音乐以流播交汇的良机。
南方也同时在对北方发生影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丁未》条:“出宫人三百十九人。”注云:“赵甡之《遗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乐女二百余人。上闻渊圣讣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传金人欲来索仙韶院女乐,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绝塞,乃尽遣出宫。甡之所云,或即此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诏书有云,‘乃者放嫔御、罢教坊,惟是约己裕民,而浮言胥听,几惑众听。则甡之所记,乃当时传闻之词,非实事也’。”(26)(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82页。此条为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之事,按李心传所记及对赵甡之《遗史》的驳正来看,放仙韶院乐女,减轻财政负担为其主因,但钦宗之死,对战火又起、金人索女乐的担心,也说明此事亦当存在。所以也有学者以为,《张》剧中的南北曲同名曲牌,是南曲影响北曲的结果,当然,此论断的前提是南曲早于北曲,但是,此前提亦并未能证明。(27)李昌集认为,“《张协状元》产生之时,北曲尚处在酝酿阶段,这些南北曲合用之曲牌,必是‘南先北后’”,即认为是南曲影响北曲的结果。由于论者认同钱南扬先生的看法,将《张》认定为南宋早期作品。参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第二章“南曲之渊源与形成”相关论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95页。
因此,王国维先生以为:“然宋金之间,戏剧之交通颇易。如杂班之名,由北而入南,唱赚之作,由南而入北(唱赚始于绍兴间,然《董西厢》中亦多用之)。又如演蔡中郎事者,则南有负鼓盲翁之唱,而院本名目中亦有《蔡伯喈》一本:可知当时戏曲流传,不以国土限也。”(28)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 :《宋元戏曲史疏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亦有学者推断《张协状元》中的“宦裔”指宋教坊乐人及其后裔,随宋室南渡,将宋杂剧与当地村坊小曲结合而形成了南戏。(29)黄婧 :《“宦裔”与南戏体制渊源》,《戏剧艺术》,2015年第6期。则南戏中北方戏剧及音乐成份,在此时已流入南方,已完全可能。祝允明《猥谈》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徐渭《南词叙录》以为“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都强调“南渡”对于南戏的重要意义,应是值得相信的。
然而,如上文所说,由于音乐首先是以口头的方式流播,所以若以曲牌出现在文字或文物上的时间,便推定其源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性,曲牌的出现与进入文物或文字被记录会有一定的时间差,这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难题。(30)与此相类似的是,对于南戏的产生时间问题,陈多先生曾提出“宋无‘南戏’说”,因为“‘戏文’一词始见于南宋灭亡后撰写的《癸辛杂识》《钱塘遗事》《中原音韵》《青楼集》和《录鬼簿》……然而在写于南宋未亡前的著作,甚至包括详尽记述南宋行都临安(杭州)风俗掌故、瓦舍众伎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此书成于宋亡后),都一律没有提到过‘南戏’或‘戏文’”。陈多进一步认为:“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口中、笔下的‘杂剧’,有些其实已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戏’。”见《宋无“南戏”说》,《艺术百家》,1992年第2期。仅依书面史料来推测,恐也根据不足,南宋史料未出现“戏文”或“永嘉戏曲”之称,并非其戏剧形态不存,只是未形成概念进入书面记载。先有名,后有实,是戏剧史上的常见形象,如同三国时的优戏已基本等同于参军戏,但“参军戏”名称的出现,要迟至五代。明清曲谱文献在论述曲牌源流时,也很少论述某曲牌起源及时间,清人研究词律时,业已说得很清楚:
调名原起之说,起于杨用修及都元敬。……愚按宋人词调不下千余,新度者即本词取句命名,余俱按谱填缀,若一一推凿,何能尽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自命稽古学者,宁失阙疑,毋使后人徒资弹射可耳。(31)(清)邹祗谟 :《远志斋词衷/调名原起辩》,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6页。按明人杨慎以为“唐人小说《冥音录》,载曲名有《上江虹》,即《满江红》,红窗影,即《红窗迥》也”,此当为杨氏臆断。见杨慎 :《词品》卷一“上江虹红窗影”条,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页。
所以, “‘寻求’一支曲牌的‘原生’或‘母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通过曲牌(或板式)音乐在传播中产生的诸多变体去‘寻求’子体的千变万化规律”(32)冯光钰 :《曲牌音乐研究要重视“论”与“证”结合》,《中国音乐》,2004年第1期。(除非某个曲牌在文献中明确记载出现于何时,或者如【大影戏】等带有明确时间标志的)。
本文并不赞同以一句同源异流去抹杀曲牌之间的血缘关系,但认为要具体而清晰地论证曲牌之间的具体影响途径,因为确实时常存在证据不足,无法确断的情况。
如杨栋以为,【红绣鞋】一牌,北曲中同名曲牌又名【步履曲】,冀南出土瓷枕有【红绣鞋】曲文,证明此曲在北方流行甚广,故《张》剧【红绣鞋】出自北曲概率较高。比如【山坡羊】,杨文以为:“从出土的陈草庵与无名氏的作品样本看,均题【山坡里羊】,与元人选元曲的《乐府新声》一致,可证此名最为原始。【山坡羊】和【苏武持节】后出,应是文人作家接手民间文学之后,追求文字精炼或文雅所致。‘里’字在这里只是口语化的衬字,有无都不改变意义,故可省简。”(33)杨栋 :《山坡羊曲调源流述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但唐曲有【牧羊怨】,词有【苏武慢】,【山坡羊】为南曲曲牌,并且影响了北曲的情况,或二者实同源异流的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存在。
因之,以文字与文物作为确立曲牌出现的时间,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是我们研究戏剧音乐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之语,虽然可能有陷入不可知论之嫌,但也说明曲律的相关研究中,“尽信书”的问题。正如叙事性作品中出现的名物词语,只能作为作品成书时间的下限,同样,文字或文物形式记录的曲牌,也只能说明它出现的时间下限不晚于此,却不能推论它出现的上限。
随着北方教坊艺人的南下,诸宫调与宋杂剧的流行,它们带来的北方音乐,完全有可能被正在成长中的南戏吸纳,诸宫调的形式的南下,促进了里巷歌谣向曲牌体的转化。限于地域原因,《张》吸纳北曲曲牌不多,并经过了本土化,但吸纳的过程完全可能在南宋末年即已产生。
三
在讨论《张协状元》的时代断限时,学者们有曰“编剧时代”,也有曰“成书年代”。严格来讲,这并非同一概念,为表达之便利,本文使用了“时代断限”一词,但“时代断限”也包括编剧时代和写定时代两个不同的内涵。剧本写定时间,应该晚于编剧时间,这也是戏剧文本不同于其他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以往的讨论,有时忽视了这是两个存在时间差的概念,因而变得夹缠不清了。
《张协状元》这个文本的独特意义在于,作为早期民间演剧,又经文人写定的戏剧文本,在一个本子上,叠加了一个长时段不同时期的影子。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历史层累说”,提出历史与传说是层累叠加而成,其某些具体结论,虽然被今天的出土文献资料在局部上有所修正,但至今研究民间传说者,仍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进行。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顾颉刚告诉他,在北大做学生时喜欢看戏,“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越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越详细,枝节越多,内容越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伪造的部分,经过写历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愈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愈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34)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32页。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一再强调观赏戏曲的心得对他后来研究古史的助益,从戏曲到史书,因版本各异,改动无数。
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表明顾颉刚的理论受到地质学及考古学的影响,但在考古学领域,学者利用地层学原理,来判定文物遗存时代。(35)考古地层学最初来自于地质学的“地层学”,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完成《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标志着地质地层学的成熟。其研究目标是地层层序的建立及确立不同层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地层划分、地层对比、地层年代确定、地层岩石岩相研究、地层生物研究、地层磁性、地层事件、地层系统建立等。考古学的地层学和地质学的地层学最终都是要通过地层研究来达到恢复历史,包括地球地貌演变史和人类史的目的。一个堆积丰富的遗址也如同一部历史书,一页(层)一页地被发掘,每一页就是一个地层层位,每个层位都包含着一个时代的故事,考古学者依据不同层位堆积土的颜色、质地和其中的包含物(如陶片、瓷片等),来确立不同地层的相对时间,并研究不同时间断层上发生的事件,以及不同地层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关系。(36)一般情况下,从上到下为逆时间打开,上一个层位的时代总会相对晚于下一层位的时代。1931年由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后冈区的发掘,便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三种考古学文化自下而上的“三叠层”,并形成了以土色、土质和陶片、瓷片区分文化层的基本方法。考古学分层和故事传说层累说的基本理论,不仅有助于故事传说的层层厘析,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民间剧本断代的一些基本问题。戏剧的舞台表演性特征,决定了一个作品在舞台搬演时,未必有文字文本,而一部戏曲作品,从艺人形成故事搬演,到写定为文本,也会有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演出的延续,最后形成的文本,也会叠加剧本在舞台搬演过程中,形成不同时期的影子。
《张协状元》第一出副末开场时所念【满庭芳】词有:“《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清代徐于室、钮少雅编撰的《南曲九宫正始》中,收录了“元传奇”《张协状元》的十二支佚曲,与《永乐大典》所录《张协状元》曲文存在异文,据学者研究,《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传奇”《张协》,“要比《张协》本合律”。(37)参见俞为民 :《宋元南戏考论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页。这些本子虽然皆不可见,但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协状元》,只是《张协状元》若干版本中的一种。
笔者曾比较《拜月亭》的不同版本,指出随着时间的变化,演出本会使用观众熟悉的语言系统,包括人物称呼等。如明代演出本将古本中的“小人”改为“小兄弟”,“老小人”改为“老臣”等。(38)戚世隽 :《古代戏剧的版本形态与表演形态——以〈拜月亭〉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流变,仅以一个本子中出现的指称来作为标准,判断“编剧时代”,恐有一定误差。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文本在时间点上出现如此矛盾的现象。我们能判定的,只是具体的某一个文本的写定时间。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民间口头表演到最后写定的叙事文本,也会如考古学遗址断层一样,叠加了不同的文化层位。徐朔方先生在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时,曾提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概念,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前,已有不同文学作品。这也是为何几部古代小说如《水浒传》等,对其创作时间至今无法形成统一结论的原因,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与结论相反的例证。而《张协状元》,也存在世代累积而带来的时间“混杂”现象,只不过此之前的各本《张协》(此处之“本”,不仅指文字本,亦指舞台本),未能留存下来。
那么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的抄写时间,是否可以有一个接近准确的结论?本文以为,在诸种论证方式中,以语法现象来判定文本年代,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

太田氏的另一个检索要素是助词“的”的前身“底”“地”,根据语言学界的研究,助词“的”的用法始于元代以后,元代以前用“底”和“地”(47)宋代不使用“的”,顾炎武《唐韵正》卷十九“的”字说:“按的字在入声则当入药,音都略反,灼酌妁芍之类也。转去声则当入啸,音都料反,钓杓豹之类也,后人误音为滴,转上声为底,按宋人书中凡语助之的皆作底,并无的字,是近代之误。”(《音书五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观稼楼仿刻本。目前学界对“的”“底”“地”的使用时间段没有歧议,只是其来源尚在探讨中,如“底”字,有以为来自“之”,有以为来自“者”,有以为来自指示代词“底”,有以为来自方位词“底”等。参见章炳麟《新方言·释词(第一)》(《章文丛书》,浙江图书馆校刊,1919年)、胡适《记“的”字的来源:“之”“者”二字之古音》(《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梅祖麟《词尾“底”“的”的来源》(《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吕叔湘《论底、地之变及底字的由来》(《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江蓝生《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来源》(《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太田氏的考察结果是,在《张协状元》中,“地”50例,“底”112例(内误用19例),“的”2例。其结论是:假如把它当作宋代的作品来看,“底”误用的19例,“的”2例,“们”1例,“每”9例就都是错的,占全体的15%强,但这个比率跟他书比起来绝不算多。
所谓“绝不算多”,当是语言史研究当中的“量的观念”,梅祖麟讨论《窦娥冤》《救风尘》等剧中的宾白是否关汉卿本人所作,认为:“我们从语言史的角度去考订文献的作期,一般只有新兴和衰落这两种语言成分可以利用……而且考订新兴成分出现的准确上限以及衰退成分消失的准确下限也总会碰到种种困难。大多数文献往往是新旧两种成分并存兼用,但它们的比例却因时而异。过去总注意新成分的有无,是质的观念。如果改用比例多少这种量的观念,再计算各时代新旧成分比例的数据,或许能把可以用来断代的语言资料的范围扩大。”(48)梅祖麟 :《从语言史看几种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1984年。梅祖麟提出了文献中有新旧语言成分并存的现象,但比例却因时而异。(49)元代文献中虽然也有“们”,但只是少数例外,大多数作“每”。吕叔湘指出臧晋叔《元曲选》间有“们”字,“而且似乎并非明人传钞之误,如‘那秀才每谎后生……嘱咐你女娘们休惹这样酸丁’,每与们互文;‘那里象喒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猢狲’,‘我使尽金银,投托你们,说起原因,有救命之恩’,们字都叶韵”。(《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由于《张协状元》中新语言成分和旧语言成分的比例悬殊,因此虽然未直接下断语,但太田氏当认可《张》剧为宋代作品。对于15%的不合宋代的用例,太田氏以为“因为是排印本,总是要多少打一些折扣才行”。其实,所谓“折扣”,更准确一点讲,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作为一个层叠式的文本,《张》的主体形成于宋代,但底本当写定于元代,因此带上了元代才有的语法痕迹。(50)杨栋 :《〈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文中提及《张》剧有“旦出科介”之语,而北剧用“科”,南戏用“介”,论证《张》剧应迟至元代,其实也当是层叠式文本的特点。
结 语
从《张协状元》中出现的大量的北宋名物制度及所见宋杂剧段数来看,这一故事的主体当产生于北宋年间,此时未必有文字文本出现,但舞台上已有张协故事在搬演。南宋末,随着北方艺人的南下,带来成熟的曲牌体音乐体制。而复数“每”和助词“的”的少量出现,说明《永乐大典》所录文本的底本写定时间,当为元代初年。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张协状元》这一文本,使我们看到了北宋、南宋以迄元初的三个年代断层,如同考古挖掘,利用年代地层学原理,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影子,这是在后来的纯文人文本上比较少见的,因而亦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