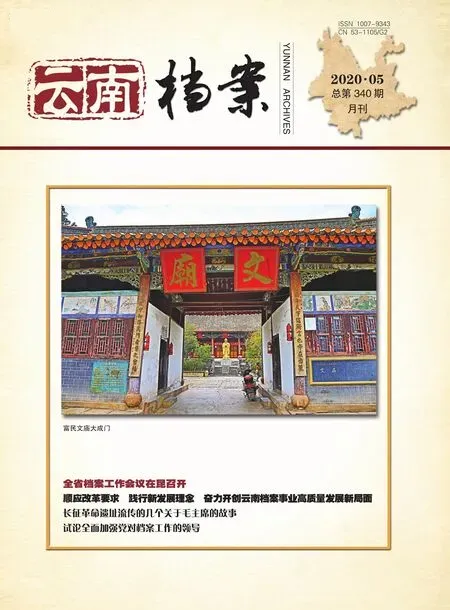昆明时期同济大学地下党研究(1939—1940)
■ 章华明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因为校舍毁于日军战火,无家可归,审时度势之后,同济大学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开始辗转西迁。1937年9月,同济迁至浙江金华。中共同济特别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留在浙江参加革命工作,同济党组织暂时中断。1937年11月,同济从浙江金华迁至江西赣州、吉安。1938年7月再迁广西八步,未及复课即于当年冬迁往昆明。从1939年春在昆明办学到1940年10月开始迁校四川宜宾李庄,同济在昆明办学两个春秋。虽然形势险恶,但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以西迁以来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为基础,同济地下党组织得以重建,确保火种不灭,并为学校迁至李庄后的组织建设创造了条件。
一、西迁途中的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
1998年,曾任上海正风中学校长、领导过昆明同济地下党支部的九旬老人胡昌治[1]撰文回忆:当时正风学生中共青团员人数不多,由于党组织曾遭受破坏,教师中已经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也很少,而正风学生终于能持续不断地掀起接一连二、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其主要原因不能不是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得人心,以及当时党在群众面前提出的正确口号诸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等,都能打动人心,符合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愿望。这是值得深思的[2]。胡昌治关于正风中学这段历史的评价,同样也适合同济。
同济迁校浙江金华后,虽然中共同济特别支部及部分进步青年学生留在了当地,但同济广大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不减,活动不断。由同济地下党员在金华发起成立的战时服务团则继续扮演着同济地下党组织联系广大学生的重要角色,成为进步力量的象征和进步学生的精神家园。在赣州,以韩忠山、陶亨咸、翟立林、赵正心、董林肯等积极分子为核心,同济战时服务团重新活跃起来。到昆明后,战时服务团成员一面读书,一面以演戏、歌咏、夜校、儿童剧团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为前方将士募集款项。1939年“一·二八”纪念日,同济战时服务团联合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以及部分中学在昆明市区组织了一次支援前线的声势浩大的游行[3]。游行队伍经过昆明主要街道时,沿途散发宣传品,高唱救亡歌曲,吸引了道路两侧大量市民百姓。在队伍前面,旗帜如林,由10位同学分列两旁用手执持平铺的一块长宽约三四米的大红布上,堆满了市民百姓捐献的金银硬币和纸币,见者皆为之动容。这次游行,从傍晚开始到晚上9点多结束,为昆明市民津津乐道,社会影响极大。同济战时服务团还曾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借用该部大礼堂,演出抗日话剧[4],他们的相关活动也频频见诸报端,如:
1939年4月16日:同济大学战时服务团特往慰劳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以表崇敬。该会在昆华大操场举行,首由主席致开辞,继以各种游艺,除歌咏合唱抗敌歌曲、口琴合奏外,并演《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最后由该团赠侨胞每人纪念国旗一面,以示为国牺牲之意,后侨胞推代表向该团致谢,同极兴奋。当时各团员慨捐四百七十余元,作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之用云[5]。
1939年4月25日:国立同济大学迁滇后,该校战时服务团即积极筹备公演,闻该团将于五月四日开始公演,剧本为《烙痕》《三江好》《重逢》《死里求生》《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云[6]。
1939年5月13日:同济战时服务团此次为征募戎衣,在云瑞中学已公演话剧六天,成绩优良,现为普遍宣传起见,爰于今明两日做宣传公演,剧目为《死里求生》《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票价概售五分,以限制人数,时间准七时半上演,凡爱好话剧民众,幸勿失之交臂[7]。
1939年5月22日:又同济大学战时服务团,前演话剧为前方将士募集戎衣,现已整个结束,所得票款计二千一百余元,连同各项义卖等零星收入,约共合国币二千五百余元,除提出一部分开支外,悉数均为购置戎衣之用云[8]。
1939年9月28日,因“连日大雨,昆明四野一片汪洋,安宁城郊变成泽国,省市积极防洪,派员赴安宁救济。安宁水灾惨重,死亡不下百人。”[9]同济战时服务团也参与了救灾工作。据《益世报》报道:“除官厅已派员携款放赈外,并闻同济战时服务团,以灾区贫病者多,已派医疗队携药前往救治”[10]。
1939年5月,战时服务团在工学院教室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在研究今后工作的同时也改选了部长[11]。在1939年10月之前,战时服务团仍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积极开展活动。校内三青团、力社等顽固势力虽活动频频,但他们所能控制的公开学生组织只有学生消费合作社。但1939年10月之后,由于国民党频频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形势发生了变化,进步学生在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时也因此失利[12]。在领导权被“三青团”窃取后,战时服务团逐渐陷入瘫痪。但就在这个时候,在同济地下党员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儿童剧团和读书会另辟蹊径,坚持开展活动,成为新的团结、凝聚、引领同济广大学生的重要组织。
知名儿童文学家董林肯生于上海,从小热爱文艺。从同济附中毕业考入本校工学院后,与文艺就渐行渐远。但在国家仇、民族恨的时代激荡下,经过学校民主爱国运动的熏陶和进步诗人冯至、作家杨晦的谆谆教诲,董林肯的文艺细胞被激发。在赣州,他担任同济战时服务团话剧股副股长,还兼任导演和主要演员,对剧务和“跑龙套”角色也很热心[13]。到昆明后,董林肯和上海育才学校初中同学徐守廉,及竺伯康等在中共地下党员况礼文、刘光琚等支持下[14],依靠小学进步教师动员家长,让他们的孩子参加演出,同时争取民主人士楚图南、冯素陶等的大力支持,组建了儿童剧团。这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昆明儿童剧团。他们希望通过孩子们天真的呼唤,进一步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扩大和巩固团结抗日阵营。
在儿童剧团里,董林肯和徐守廉相互支持,紧密合作。董林肯负责编剧、导演了街头剧《难童》、三幕抗战儿童剧《小间谍》(和于同尘合作)等轰动一时的作品;徐守廉负责作曲、指挥与培训工作,包括讲授乐理常识,为剧团演出的各类剧(节)目配音并创作主题歌。儿童剧《小主人》主题歌《小主人》《表》的主题歌《表》、抒情歌《杜鹃花》都是由董林肯作词、徐守廉作曲的[15]。除儿童剧团的工作外,徐守廉还走出校门,积极参与社会歌咏的组织工作,成为昆明抗战歌咏活动著名的组织者和合唱指挥:他参与组织的“云南全省歌咏协会”于1939年2月成立[16];他是昆明“歌岗合唱团”指挥和教员;作为“新音乐社”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西南暑期音乐培训班”和“新音乐训练班”教学工作,同时为《新音乐》(昆明版)、《音乐报》《大众活页歌选》这些在昆明乃至全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重要影响刊物的编辑发行作出了重要贡献[17]。
1939年“八·一三”两周年之际,儿童剧团在昆明近日楼街中心花坛正式公开演出。他们演唱抗日歌曲,演讲救国道理,并演出《难童》短剧,深深感动了众多市民群众。10月,在昆明第一届戏剧节期间,儿童剧团公演的《小间谍》在昆明引起轰动。除剧场开支外,演出收入大部分捐给了抗敌后援会,部分用作昆明26所小学贫寒学生的助学金[18]。嗣后,儿童剧团又先后公演了3幕剧(后来改成四幕)《小主人》。1942年夏,董林肯和徐守廉从同济毕业后又先后回到昆明。暑假期间,已经升入中学的儿童剧团小演员们都热切希望恢复剧团活动,举行第三次公演。在西南联大部分同学的支持下,董林肯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中篇小说《表》(鲁迅译)改编的5幕儿童剧被搬上了舞台。当时,李公朴住在昆明青年会集体宿舍里。他不但全力向各方面推荐《表》,推销戏票,而且还推荐自己的儿子李国友扮演了剧中的一个角色[19]。儿童剧团的存在及其开展的活动,使昆明广大儿童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动员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读书会是同济迁至赣州时,由赵正心、陈志德、刘光琚等发起成立的。当时只有八九人,到昆明后部分成员离校,但梁建民、刘儒英、陶亨威、翟立林、徐瑞芳、朱洪元、沈延发、况礼文、薛崇本、宋鸿鼎、宋鸿鼐等几十人[20]先后加入,成员从大学部扩展到附中、高职,其中部分是共产党员。大家在自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众哲学》《新经济学大纲》及高尔基的小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等文艺书籍基础上,组织讨论,交流心得体会。读书会编辑的壁报经常刊登抗日救亡的报道和评论,也发表诗歌、散文,形式活泼,深受同学们欢迎[21]。继1938年春战时服务团主要负责人之一陶亨咸被开除后,1939年底,读书会主要负责人赵正心也被开除[22],但共产党员刘光琚、况礼文等继续组织读书会,包括发展了工学院部分低年级同学入会[23],一直坚持到了1940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等职的张宝锵,在同济附中读书期间也曾参与组织读书会,1940年考入同济工学院后不久随校迁至四川宜宾李庄,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庄瑞源在昆明就读同济医学院期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协助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成立了南荒社[24]。潘世和十分喜爱阅读中外著作和文艺创作。他在昆明就读同济医学院期间曾在后方各大报刊、杂志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鼓吹革命,宣传抗战。随校迁至李庄后,因受到监视,他采纳了况礼文的建议,转移至昆明[25],继续战斗。
二、况礼文的回归与中共同济地下小组的成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根据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1939年1月下旬,以原中共云南省特委为基础,中共云南省工委宣布成立。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着重加强党的建设[26],还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将青年工作列为重点[27]。而在此前的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作出指示,要求“猛烈发展党组织”,所以同济迁至昆明时正是中共开始在云南全省开始建党的时期,可谓恰逢其时。而从金华到昆明,同济战时服务团的活动从未中断。它实际上也成了同济广大进步学生的共同精神家园,为同济地下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温床。
同济地下党的重建和况礼文密切相关。况礼文,四川重庆(今重庆市)人,在重庆联中读高中期间,由钱寿昌介绍入党[28],同济工学院学生。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认识不足,同济暂迁市区,内地学生大部分被动员回家,不能回家的暂时集中在医学院后期学生宿舍,听候通知[29]。同济开始西迁时,况礼文从上海返回重庆,继而考入西南联大[30]。1939年春,况礼文的组织关系转入西南联大。同济在昆明开学两周后,况礼文转回同济,于1943年毕业[31]。
因为同济当时尚未恢复党组织,故回同济时,况礼文仍然在西南联大过组织生活。根据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指示,况礼文开始在同济秘密发展党员。1939年初夏,况礼文发展了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表现突出的附中同学薛崇本、肖庆熹、任天润3名党员,建立了党小组,隶属于西南联大党支部,由西南联大经济系二年级同学刘忠渊负责联系、领导[32]。刘忠渊还是薛崇本、肖庆熹入党宣誓时的监誓人[33]。
不久,云南省青委改派“老王”“王同志”即胡昌治负责领导同济党小组。在胡昌治的领导下,同济地下党小组开始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刘光琚也被发展入党[34]。1939年8月,况礼文通知刘光琚:经过组织审查,宋鸿鼎、宋鸿鼐已被列为发展对象,请刘光踞具体负责发展入党。当月底,宋鸿鼎、宋鸿鼐就被发展入党[35]。后来,医学院汪润人、宋文英也被相继发展入党[36],这样,同济党员人数达到了9名。1940年夏,同济9名党员组成了3个小组:况礼文、薛崇本、肖庆熹;汪润人、任天润、宋文英;刘光琚、宋鸿鼎、宋鸿鼐。上级党组织指定况礼文、汪润人、刘光琚3人分别为各党小组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支部雏形,但支部尚未正式成立,日常工作由况礼文负责与胡昌治单线联系,上级指示及各小组工作布置,均由况礼文向汪润人、刘光琚两人传达[37]。
虽然同济支部尚未正式成立,但中共云南省青委是将同济况礼文、汪润人、刘光琚3人核心小组作为一个领导组织来对待的[38]。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组织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曾记载:“同济大学有二个同志成立一个小组。”[39]
这个时候,在同济由上海迁至浙江金华时入党[40],曾任中共遂昌县小组组长、遂昌县大柘区区长的梁建明在遭通缉后也辗转回到了学校。因为在赣州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无人证明脱党原因,梁建明的党籍一直没能得到恢复。此外,因患肺病,梁建明经常卧病在床。但组织上对梁建明的表现还是认可的,所以胡昌治和况礼文曾一起到梁建明的病床前表示慰问,以使梁建明感到组织上对他的信任[41]。在校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正在附中读高二的王昌维于1939年6月离开昆明赴延安[42]。受阻后转至山西,在抗大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晋东南敌后战区八路军三大队三分队战地医院工作,1941年转移至辽县(今左权县)任战地记者[43]。医学院徐瑞芳于1940年夏离开学校到了重庆,辗转赴皖南泾县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捕,英勇牺牲[44]。工学院的陶亨咸复学后于1939年毕业,后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还曾任一机部总工程师、副部长等职。
当时,同济地下党的任务,一方面是结合抗战实际组织党员学习,另一方面是开展群众工作,包括加强对读书会、壁报、民众夜校、儿童剧团等的领导,深入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济的进步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45]。
三、中共同济地下支部的成立
党员数量的逐渐增加,战时服务团、儿童剧团、读书会等学生社团的存在及其影响,教育、团结了更多的同学,发展了进步力量,客观上也为党员发展工作乃至党支部的重新建立创造了条件。
1940年9月,胡昌治召集况礼文、刘光琚、汪润人3人开会。会议共有3项议程。一是由胡昌治报告国内外形势,传达上级领导指示。二是讨论工作,重点讨论、分析同济校方准备迁校四川的真实原因、校内斗争形势和对策。三是宣布,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同济党支部,由况礼文任支部书记,刘光琚、汪润人分任组织、宣传委员。此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在昆明期间中共同济支部的第一次支委会。一周后,胡昌治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支委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通报国内形势,分析校方和同学思想动态。会议讨论了迁校过程中党的工作方针,一致认为学校迁川已成定局,即便暴露也是徒劳,所以不宜搞反对迁校活动[46]。
多年后胡昌治回忆:“我在(云南)青委工作时期,除做宣传工作外,还代表青委领导联系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支部。支部书记是况礼文。该校初由我领导联系的党员极少,未成立支部,后发展到10人左右,成立了3个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组长中我记得的有刘光踞,其他两个组长的姓名已忘。因我除与况礼文单独在校外联系外也曾亲自到校内参加过几次组长会议,故对这些同志也认识。”[47]
因为物价飞涨、日机侵扰以及校区过于分散、管理困难等原因,从1940年初夏开始,同济校方就已经考虑迁校事宜。事实上,1940年11月15日,尚未动身迁往李庄的同济医学院前期学生胡津祥[48]、附设高职机械科四年级学生项瑞棠就遭日机扫射而死[49]。1940年10月,同济开始迁往四川宜宾李庄。这样,同济地下党支部成立仅仅半个月后[50],就开始随校迁移。因为经济窘迫,学校无法提供交通工具,况礼文、薛崇本、滕志超[51]等还千方百计,帮助部分同学解决了困难,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拥护[52]。宋鸿鼎、宋鸿鼐则不得不自找工作以筹措路费,迟迟才到李庄。作为工学院毕业班学生,刘光琚和几十名同学,七八名教师一起,在昆明东郊一寺庙中上课,1941年1月提前毕业。因为肺结核病日重,同学们将梁建明安排在昆明郊区一座道观内养病。1941年初,梁建明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乘飞机辗转到达李庄,1943年在宜宾病逝[53]。
最后,除刘光琚滞留昆明等待毕业外,况礼文等8名党员均随学校来到了李庄。汪润人抵达李庄后不久即返回上海治病后,一病不起,任慰农也在“皖南事变”后转移回云南工作,先后任职于昆华医院、陆军医院等单位,并重新加入党组织[54]。因为地下党组织及活动的特殊性,加上形势险恶,同济地下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42年夏初才转至四川李庄[55]。

表:昆明同济大学地下党员概况[56]
注释:
[1]胡昌治(1908—),原名胡敬修,江苏昆山人,东南大学毕业后在太仓师范学校、暨南大学实验中学任教,曾任上海正风中学校长。1938年春在四川万县入党,曾任中共万县县委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39年9月在云南省委工作,同年底赴上海在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2]项伯龙主编,《青春的步伐 解放前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运动史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68页。
[3]刘光踞关于同济学运史稿(初稿)的补充意见,第124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4]韩忠山:同济大学内迁期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片段,黄恩德主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内迁院校在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8页。
[5]《云南民国日报》1939年4月16日第4版,转引自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256页。
[6]《云南民国日报》1939年4月25日第4版,转引自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257~258页。
[7]《云南民国日报》1939年5月13日第4版,转引自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273页。
[8]昆明《中央日报》1939年5月22日第4版,转引自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279页。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1卷)》,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12月,第841页。
[10]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349页。
[11]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 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276~277页。
[12]王昌烈:同济学生运动史记忆片段,第211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5。
[13]张之伟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8~249页。
[14]解方逊、张自明、黄林,《徐守廉传略》,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5]昆明“一二·一”老同志合唱团编著,《民主革命时期云南创作歌曲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页。
[16]昆明“一二·一”老同志合唱团编,《李仁荪词作歌曲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6页。
[17]申波著,《穿行于田野与思考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87页。
[18]翁智远、屠听泉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1907—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19页。
[19]董林肯:回忆昆明儿童剧团,《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儿童文学研究(第6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94页。
[20]况礼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同济地下党工作的一段回忆,第141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21]翁智远、屠听泉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1907—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18页。
[22]刘光踞关于同济学运史稿(初稿)的补充意见,第124~126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23]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第112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刘光踞关于同济学运史稿(初稿)的补充意见,第125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24]徐瑞岳、徐荣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1页。
[25]任慰农:关于四十年代同济在四川期间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3.0001。
[26]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31~232页。
[27]昆明时期同济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2.0001。
[28]钱寿昌谈抗战期间同济地下党活动,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1。钱寿昌(1917—1970),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联中党支部书记。1942年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委员,负责联系李庄同济大学地下党。1945年起历任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川南工委副书记、宜宾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29]李法天、李奇谟:同济大学内迁回忆片断,黄恩德主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内迁院校在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0页。
[3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366页。
[31]毕业后曾在重庆工作。任慰农:关于四十年代同济在四川期间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3.0001。曾任成都军区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正军职离休干部,松潘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设计者之一。何光岳著,《中华姓氏源流史》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639页。
[32]况礼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同济地下党工作的一段回忆,第140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另,同济大学馆藏史料《解放前同济党组织情况调查报告》(档案号:2-1949-DW-1.0010)称:“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刘钟渊、梁建明等到同济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有误,梁建明非西南联大学生,因此不予采信。
[33]抗战时期同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第156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1。
[34]根据《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刘光踞入党时间为1940年7月;根据《刘光踞致同济大学“三史”编写组的信》(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刘光踞入党时间为1940年8月。但根据《三十年代校友座谈会纪要》(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6-2.0009),刘光踞入党时间为1939年。综合判断,刘光踞入党时间应为1939年。
[35]刘光踞:关于1940年在昆明建立同济支部的史实,第116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36]原文为5名。参见《三十年代校友座谈会纪要》,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6-2.0009。
[37]翁智远、屠听泉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1907—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18页;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第107~108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况礼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同济地下党工作的一段回忆,第140~141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据《关于1940年在昆明建立同济支部的史实》第116~117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新中国成立后,胡昌治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38]昆明时期同济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2.0001。
[39]“二个同志”系口语化、模糊表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党组织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25页。
[40]三十年代校友座谈会纪要,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6-2.0009;访朱惟善同志,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4.0005。
[41]昆明时期同济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2.0001。
[42]谢伯余校友致同济大学“三史”编写组的信,第106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8。
[43]王昌烈致同济大学“三史”编写组的信,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4-4.0001。
[44]中共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闽北党史人物(武夷山卷)》,2005年9月,第390页。
[45]翁智远、屠听泉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1907—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18页。
[46]刘光踞在这次回忆中否认了之前梁建明也是支部委员的说法。综合梁建明的健康状况和党籍恢复问题,予以采信。刘光踞:关于1940年在昆明建立同济支部的史实,第116~117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47]原文为“20人左右”“4个小组”,系记忆有误。原文称任慰农即任天润是党小组长,其实不然,已删除。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党组织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89~290页。
[48]顾炜、方恩约来信,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34.0001。
[49]《朝报》1940年11月16日:同济学生中弹陨命;王时炎:关于王瑞棠同学在昆明被日机射死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34.0004。
[50]刘光踞:关于1940年在昆明建立同济支部的史实,第116~118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51]1943年毕业于同济工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阳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副校长。贵州大学校史编写委员会编,《贵州工业大学分册(1958—2004)》,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93页。
[52]王昌烈:同济学生运动史记忆片段,第218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5。
[53]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第107~109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一说是1940年底。朱惟善回忆摘录,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8;刘光踞致同济大学“三史”编写组的信,第126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54]钱寿昌谈抗战期间同济地下党活动,第154~155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1。
[55]任慰农:关于四十年代同济在四川期间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3.0001;刘光踞:关于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同济地下党工作的一段回忆,第143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10。
[56]梁建明因党籍未恢复,本表未将其列入。
[57]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第107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任慰农《关于四十年代同济在四川期间地下党组织情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3.0001)认为肖庆熹毕业时间是1944年。这里以刘光踞的回忆为准。
[58]毕业后在昆明中央机械厂分厂工作(后为昆明机床厂)。昆明时期同济地下党组织情况,第13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112.0001。该厂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党组织关系转至云南省工委。关于昆明建党前后的学运,第107页,同济大学馆藏史料,档案号:2-ZT-XS15-6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