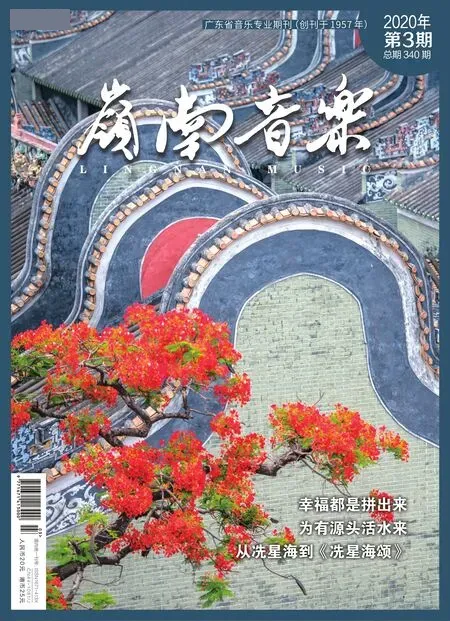古典的严谨与浪漫的自由碰撞出的奇异火花
——听陈必先贝多芬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
文|李思远
2020年1月18日晚,著名台湾旅德钢琴家陈必先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室内乐厅举行了纪念贝多芬诞辰两百五十周年的专场音乐会。贝多芬既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又是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启迪者。在时而如静水流深,时而若惊雷飞瀑的琴声中,古典的严谨与浪漫的自由交汇着,这一夜,观众的心灵为作曲家构筑形式的天才和其中蕴含的激情所震撼,亦被演奏家独具个性的二度创作所打动。
上半场的曲目安排别具匠心,是两首在创作风格上有鲜明对比的作品:贝多芬中期的G大调奏鸣曲(作品31之1)与后期的《六首小品集》(作品126),充分体现了贝多芬所处历史转折时期的音乐特征以及他在其中的引领作用。作品31之1是青年时期的作曲家向着古典奏鸣曲巅峰迈出的重要一步,作品126则标志着浪漫时期标题小品套曲的萌生。下半场的曲目是贝多芬晚期的经典代表作——32首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两首(作品110和111),这两首作品被公认是成熟钢琴艺术家的演奏技术、音乐表现和艺术修养的试金石。
陈必先对作品的骨干结构和速度统一性有着总体的把控,声部的层次和强弱清楚、细致,触键和踏板的运用必经仔细斟酌、功力深厚,音色丰富多变,对和声、旋律的走向也有着透彻的理解,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教科书式的严谨和古典的审美。但与此同时,她的演奏在表层节奏型、旋律乐句的节奏伸缩和左右手相互对齐等方面,又常常有其自由度颇大的个性化处理,这种严谨与自由的碰撞令人感到新颖,印象也特别深刻。
当晚陈必先女士对G大调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演奏诠释就很有特色。音乐整体有如弦乐四重奏的音响效果,乐章的中声部是持续的跳音,仿佛在模仿弦乐的拨弦奏法,右手是歌谣风的旋律,左手的低音肩负着和声发展的重任,所以低音有延长的需要。为了令这三个层次各司其职、互不干扰,陈必先表现出多样化的、扎实的指尖触键功底,华彩段的声音清晰剔透,连奏声音线条绵延致远,她有效地结合踩半踏板技术,让中声部的拨弦效果贯穿始终,一丝不苟地将声部层次处理得十分清晰。与此同时,右手起自颤音的高音旋律却如静静绽放的花朵,柔柔地伸展开美丽的花瓣,精灵似的以优雅的线条轻歌曼舞,在乐句之间随意而舒心地呼吸,完全不受局限于左手小节拍的束缚,不时与左手的节拍微微错开。让听众感觉演奏者像难舍父母怀抱却又渴望自我放飞的孩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游移。
作品126的六首曲子性格各异,要求演奏者时刻处于高度精神集中的状态当中,迅速应对技术的种种转变。陈必先的乐句处理有着说话语气般的自由灵动,对每一首的速度有合理的安排,而且她赋予每一曲甚至曲子里各个小乐段以鲜明的性格特点。比如第二首突然而热烈的情绪打断了第一首思想的遨游,在演奏技术上从抒情的连奏突然转变成清晰有力的断奏;又如第五首用弦乐四重奏的织体温馨而自由地歌唱着民谣,转瞬间被第六首快速而幽默的前奏惊醒。
陈必先演奏的贝多芬作品110第三乐章也可圈可点,演奏的技巧与作曲的手法配合默契,很好地表现了音乐的内涵。序奏于降B小调上缓慢地开始,节奏自由、速度多变的宣叙调以起伏跌宕的旋律线在深情地述说,片刻,经过降D(升C)小调转到了降A小调,在阴郁的和弦衬托下,右手轻轻地“唱”起悲叹之歌(“Arioso Dolente”)。这里先后出现的拥有六、七个降号的调性在古典音乐中是罕见的,其音响色彩压抑、暗哑。在演绎这段著名的悲歌时,陈必先再次运用了踩半层次的踏板,让左手的和声衬托贯穿不断,其缓慢细微的变化又清晰呈现,在不同的和弦之间没有丝毫的模糊重叠;而充满哀求叹息的右手旋律的音量则大大地超出左手,其歌唱性和自由的节奏伸缩达到极致,同时中声部的呼应仅隐约可听见,突出了高声部的独白效果。悲歌的第一个段落在平行的降C大调上,第二段开始就向降D小调离调,最后还是回到降A小调,内心郁结难舒。此时,深情的主题从低声部响起,中声部、高声部相继加入,这是一段三声部赋格,如同教堂的祈祷歌,此起彼伏。接着是悲歌在G小调的再现,然后赋格再现。再现的赋格主题是第一次出现时的倒置形式,陈必先用一种微弱而有穿透力的声音将这主题引出,逐步渐强的G大调和弦从G小调的悲歌中解脱出来,犹如希望的钟声一样慢慢逼近。她专注地聆听着自己手下各声部发出的声音,就像正在精耕细作的农人看着被霜打过的作物逐渐现出生机,音乐的意境变得悠远而宁静,那是万物复苏前的宁静,让人对风霜雪雨过后将要透出的第一缕阳光充满期待。终于,温暖和希望从演奏家的指尖汨汨流出,经过层层的铺垫和发展,全曲以积极和鼓舞人心的形象结束。
相对来说,陈必先所弹的作品111似乎与听者心目中的“贝多芬”更吻合。贝多芬这首最后的奏鸣曲只有相互对比极其强烈的两个乐章,第一乐章如狂风暴雨般庄严而激烈、热情而紧张;第二乐章则像清朗月夜那样静谧、圣洁。贝多芬的晚期创作常回归到巴罗克的复调、变奏等手法,这也明显体现在作品中。陈必先的诠释在速度处理上特点尤为鲜明,体现了她对全曲整体的严谨把控,第一乐章的引子比快板部分大概慢一倍,引子后面左手低音的32分音符颤音与快板部分的16分音符颤音几乎相等。在演奏变奏曲式的第二乐章时,依次出现的一个个变奏段落先是节奏不断加密,而速度节律则保持高度统一的,没有调整的余地,使结构十分严格紧凑。要应对这种变化,在技巧方面需要深厚的功力,在心理方面既要高度集中,又要耐心淡定来让音乐在稳定的速度中自然地展开。但在速度整体统一的基础上,陈必先还是对乐句的组织加了自己的伸缩处理,让音乐的“叙述性”更为突出。而正是她的一些富有个性的细节处理更容易让听者产生共鸣,如她弹奏的这个变奏曲乐章近尾声部分的高音长颤音,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音色纯净明亮,犹如照亮年迈的贝多芬灵魂的那一束光,那从天而降的希望,动人心弦。
在听音乐会的过程中,有时觉得陈必先在表现贝多芬,有时觉得她在表达自己,也有时感到两者合一了。让人同样感觉有时冲突,有时统一的,是她演奏中既古典又浪漫的诠释,及其所体现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对此开始不乏疑问和困惑,细想却又有所悟,这应该是陈必先对音乐作品、作曲家和二度创作自由有着自己深刻理解的一种反映。

陈必先曾说过:“不管弹谁的音乐,我一定发自内心尊敬作者,然后彻底研究这个人和其作品。”她提出,虽然我们今天不再像巴赫、贝多芬在他们的时代那样表达自己,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巴赫与贝多芬如何表达自己,而且演奏者有责任带领听众进入作品产生的时代、进入作曲家内心世界。①可见她并不认为演奏者应该表现自我。但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对古典音乐就应该一板一眼地按照乐谱演奏,似乎那样才是“严谨而正确”的,所有“自由”的演奏都不正确。但作曲家本人的演奏真的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吗?乐谱一写好就成为不可做任何改变的清规戒律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记得看过的一些书、文中提及贝多芬友人对其演奏的回忆,说是非常大胆而自由,速度变化不一,并没有完全遵循乐谱上的标记,而是每次演奏的细节处理都不一样,但又很合理很有说服力。车尔尼和申德勒等贝多芬的学生在描述自己老师演奏时也提到,贝多芬的演奏在作品总体速度和结构的把控是严谨统一的,但是很多细节上他会保留演奏的自由创作的空间,比如说在一个大渐强的尾部加上一个谱子上没有的突慢处理,又或者是沉思性的段落速度会有变化等②。密歇根大学的羽管键琴教授Edward Parmentier在一次博士风格研究必修课上说,“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他们都是浪漫自由,有艺术审美解放追求的人。自由浪漫是一种不断扩张艺术审美的创作冲动,和浪漫时期的浪漫不是同一个意思。”③这位精通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键盘作品的学者的话使我们明白,没有“自由浪漫气质”的演奏并非作曲家的本意。可见,陈必先的个性化诠释从精神上更接近贝多芬。
当然,由于无法与已故的作曲家直接交流,乐谱的确是演奏者与作曲家沟通的重要中介,而且谱子上如蛛丝马迹般的细节很多时候也是解开作品“密码”的关键。但是,乐谱其实无法完全记录音乐的各种细微变化和风味韵致,因此谨小慎微地按照乐谱的所有指示演奏,不对乐谱做任何超越、任何变通,这个中介就有可能变成障碍,局限了演奏者的思想和感悟,使演奏缺少情感张力,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陈必先所说:“节奏绝对不该只是数拍子,而要表现出音乐和演奏要说的话,不然音乐就是死的。”④
更重要的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都有其深层积淀和当下生发的丰富的思想和情感活动相伴随,而音乐创作与表演(尤其是表演)的过程更偏向于一种感性的创造,理性更多的是其观念基础。例如,贝多芬在创作当时规模最庞大,技巧最华丽的作品31之1的时候,已经有信心可以超越前人的创作,他赋予快-慢-快三个乐章的奏鸣曲以前所未有的对比鲜明的戏剧性表现。而陈必先严谨控制低声部和声节奏的稳定,却让高音旋律自由伸展的个性化演奏处理中,也许是无意的却很形象地反映了作曲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的心理活动。同时,这也未尝不是演奏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某种折射:九岁即以音乐天才身份前往德国科隆深造,曾在不少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曾与伦敦交响乐团、BBC英国广播交响乐团等国际著名乐团合作,并在德国、台湾等知名音乐学府任教的陈必先,年届七旬仍活跃在舞台上,她没有停下脚步,仍有着更高的艺术追求。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创作的另外三部作品,陈必先也许有着更多的共鸣,其中仍有着生生不息的斗志,但更增加了经过种种人生历练之后的精神的升华。作品110、作品111的最后部分,作品126之3的连续5个小节使用了延音踏板的结束句,还有几部作品中时常闪现的长颤音(贝多芬晚期钢琴作品的特征性手法之一)等,她的声音把控都稳定而细腻,音色如净化过似的澄明、晶莹,把曲子带到更深远的境界,从中能听到作曲家和演奏家对音乐、对世界的思考,对宇宙、对灿烂星空的敬畏和神往。
总之,从表面上看,古典与浪漫、严谨和自由、理性与感性似乎都是相悖的,而此次音乐会就展示出这些对立的两者也存在统一的可能性。贝多芬音乐中既古典又浪漫的风格,在陈必先严谨把控形式结构和自由展现美感深情的演奏中,碰撞出奇异的火花,令人难忘,给人启迪。由于火花的每一次闪耀都富有创意,又使人对演奏家的下一次音乐会充满期待。
注释:
①马克西米利安·卡克霍夫(Maximilian Kalkhof):陈必先专访《当我弹钢琴时,我处于一个完好的世界之中》,翻译:张君德(Günter Whittome),版权:歌德学院(台北)2018.7
②卡尔·车尔尼著.保尔·巴杜拉-斯柯达注释.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正确演绎[M].张奕明,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③Edward Parmentier是美国著名羽管键琴家,密歇根大学羽管键琴终身教授。此处出自笔者在上Parmentier教授的“巴洛克风格研究”的博士研讨课程时做的笔记。
④焦元溥.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贝多芬和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