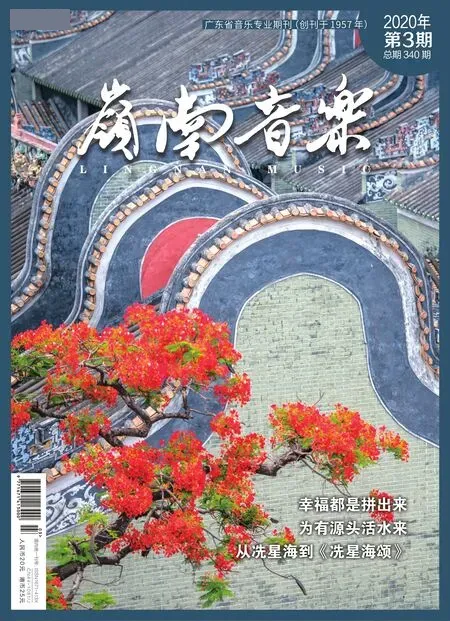现实题材民族器乐剧的创新研究
——以《扬帆大湾梦》为例
文|孙明浩 陈芳毅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品,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演的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梦》于2018年11月7日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演。该剧是广州市2018年重点立项的创新剧目,是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担任总策划,粤语相声表演艺术家黄俊英担任艺术指导,国家一级导演王佳纳担任总导演,著名音乐制作人隋晓峰担任作曲和指挥,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创作室编剧苏虎担任编剧,国家一级编导张瑀航担任舞蹈编导,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赵海担任舞美、灯光、视频设计,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方国良担任化妆造型的一支“强强联手”的主创团队。《扬帆大湾梦》是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的广州为背景,用民族器乐讲述广州市民的人生故事,带观众重温广州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作为民族器乐剧首次选择现实题材进行创作生产的尝试,该剧中所有对话、独白、旁白均由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完成,这种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得到了广州市民和文艺界的广泛认同,也受到了《央广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堪称是四十年来给广州市民带来的一次集体回忆。2018年12月,该剧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一、民族器乐剧选用现实题材创作的首次尝试
民族器乐剧是“以民族器乐作为表演主体来讲述完整戏剧故事的剧种”。[1]是民族器乐舞台表演的一种新的形式。2017年7月中央民族乐团创演了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之后在2018年4月重庆歌舞剧院创演的《大禹治水》,2018年5月上海音乐学院创演的《笛韵天籁》、南京市民族乐团创演的《桃花扇》,2018年8月湖南省歌舞剧院创演的《九歌》,2018年9月吴茜创演的《韵魂弦梦》,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共公演了7部民族器乐剧,并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一时间,民族器乐剧这种创新艺术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民族器乐剧在音乐创作、舞台戏剧表演和跨界融合上有了较大的创新,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并俨然成为民族器乐开拓演出市场的热门产品。在民族器乐剧如火如荼创作生产的同时有些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以往的器乐剧作品均以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为题材,而民族器乐剧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在真实生活素材和鲜活人物形象融于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如果民族器乐剧的创作始终脱离现实生活,必然因其曲高和寡而丧失生命活力。
现实题材根植于国人的生活情感,蕴藏着丰富的时代审美诉求。[2]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选择现实题材创作逐渐成为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自觉。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3],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当做历史的使命和责任。二是文艺作品中感人的形象和生动的剧情更贴合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具有对文艺审美鉴赏和评判的权利。随着人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文艺作品审美的鉴赏和评判也不断发生变化,趋向于追求现实生活中角色的喜怒哀乐和剧情的戏剧冲突。三是艺术创作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内在动力。当创作题材越接近现在时,越具有挑战性,而越有挑战性,就越有可能对当下社会文艺创作和未来文艺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和古代文人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道理不谋而合。面对这样的创作契机,传统艺术选用现实题材创作的剧目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精品。例如2019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的参评剧目中,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聚焦精准扶贫时代题材,讲述了农科院的助理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当第一书记扶贫济困的感人故事;河北梆子《李保国》通过李保国生命进程中的人生轨迹和精神片段,揭示出主人公李保国“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的灵魂高度和人生价值;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围绕农村虾稻产业发展这条主线,戏剧化地展现了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生故事,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乡村变化等等,这些传统艺术剧目在评比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民族器乐作为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追求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作品,是民族器乐剧发展一个必然阶段。现实题材的民族器乐剧《扬帆大湾梦》紧紧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源泉,以爱国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用普通老百姓的视野和经历去反映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对广州产生的深远影响,带出广州城市变迁的一幕幕光影图景,背后蕴藏着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憧憬,讴歌了广州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时代担当。
追求
民族器乐作为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追求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作品,是民族器乐剧发展一个必然阶段。
二、民族器乐剧在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中的困境
民族器乐剧在音乐性和戏剧性的构建上与歌剧之间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都是“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4]器乐剧虽然在语言文字的表情达意和故事直接叙述性上和歌剧有一些差异,但是在现实题材创作的基本规律与歌剧并无本质区别,换言之可以将民族器乐剧的创作看做为一种“无词歌剧”的创作过程。就创作的评价标准而言,两者在现实题材创作上都应以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的为评判标准。但是民族器乐剧在现实题材的创作过程相比歌剧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存在更多的困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实题材的器乐剧创作中如何体现历史性的思考。作为一部以改革开放40年为创作背景,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创新剧目,如何在剧中体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新成就、新变化、新问题,同时通过音乐叙事“语义延伸”的优越性,充分延展观众在剧情中对意境和情感“解读”的空间,从而巧妙地将观众引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去,促进观众对剧中人物情节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并在情感认同、艺术认同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思想认同和精神凝聚,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二是题材的创作如何把握器乐的艺术规律。民族器乐原本只注重音乐的演绎,现在却开始增加戏剧化的表演,这给剧目的创作增加了难度,现实题材的音乐创作一方面要考虑到民族器乐善于运用当地传统音乐文化素材和情感意境表达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民族器乐搬到舞台上进行戏剧化表演会受到乐器形制大小、音色个性化差异、音域跨度窄和演奏姿势固定化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如何把握民族器乐艺术表达的规律,做到扬长避短,运用民族乐器有效表达出现实题材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特点是创作过程中的难点。
三是作品如何更加贴合观众的观赏需要。剧目的创新探索能否得到观众的观赏认可才是硬道理。“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民族器乐剧在为观众讲身边的故事时,如何体现鲜明的本土化音乐人物特点,做到旋律优美、主题鲜明,并能有机融合戏剧、舞蹈、视觉创达等元素,充分调动观众的视听联觉,给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带来艺术审美上的亲切感,愉悦感和认同感是关键。
三、用民族乐器讲好当代故事的实践创新
器乐剧《扬帆大湾梦》努力用民族乐器讲好当代故事,其实就是有效解决在现实题材创作过程中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问题,笔者认为实现“三性”有机统一就应该在解决该剧“说什么,谁来说、怎么说”的过程中体现。具体来讲“说什么”就是指剧中人物情节塑造和音乐语言表达;“谁来说”就是指为角色选择运用合适的民族乐器,“怎么说”就是指多元舞台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入。
1.人物情节塑造和音乐语言表达
在人物情节的塑造上,考虑到器乐剧和其他艺术剧目的最大差异就是全剧没有一句台词,在故事的直接叙事语义表达上会相对较弱,因此在剧情设计上通过聚焦到每个广州人记忆深处的标志性事件或场景来减轻剧目的叙述难度。例如海珠桥上的单车潮,西湖路的夜市,非典时期的医院、广州地铁开通、广州金融CBD,这些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场景或事件可以迅速激发起观众的记忆点,为剧情的叙述作出了具体化的情景铺垫,让观众的观赏和想象有了明晰的方向,有效弥补剧情上的叙事性语义较弱的短板。该剧设计主要角色有四个,分别是男主角李嘉豪和其妻子曾佩仪、女儿李婉婷、侄子李中国。其中用两条剧情脉络来讲述整体故事,第一个脉络是从1979年到2003年,广州市民李嘉豪和妻子曾佩仪通过经历车潮相遇、灯光夜市、地铁开通、抗击非典等事件相识相知相守相别离的悲欢离合人物故事;第二个脉络是从1978年和在“逃港”失败与兄弟失散,以及2010年到2018年和回国侄子认亲、同逛花街、共同创业的故事。两条脉络最终融合成了9个情景故事,每一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互为铺垫,巧妙地将两代人的情感交织和广州的城市命运扭接在一起,使得整部剧的故事和情节塑造都合乎时代的逻辑,同时有较强戏剧冲突和鲜明的人物特点。

谱例1:主题旋律1

谱例1:主题旋律2

谱例2:主题1变形《夜市》柳琴的旋律

谱例3:主题2变形《春潮》竹笛的旋律
根据剧情和角色的设计特点,作曲家隋晓峰在音乐主题创作时更加突出了角色关系对话的旋律辨识度,音乐主题根据整部剧主要角色的对话关系来创作,以李嘉豪和妻子曾佩仪的对话音乐主题为例,剧中的《春潮》《夜市》《大爱》《花街》中都有两个角色的大量音乐对话,均是由两段主题旋律发展变化而来(谱例1),两位主角用乐器进行“独白”也是根据这两个主题进行创作的(谱例2、谱例3)。通过音符的增减、节奏的变化、调性的处理等方法让主题的旋律串联全剧,这样的音乐主题辨识度高,可听性强,为角色的鲜明个性化和形象化塑造提供了听觉印象的支持。同时作曲家创新使用“流行交响”的创作手法,即融合了管弦乐、流行乐、广东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等元素进行音乐创作,努力协调民族乐器、西洋乐器、电声乐器之间的音色和音律之间的差异,实现“和而不同”的音响效果。
2.角色选择最合适的表达乐器
以往来说,器乐演奏和戏剧表演本来是两个分开的行当,现在器乐演奏和戏剧表演要合成一个形象,让所有的人物表达都通过民族器乐来实现,实现民族器乐的话语体系和角色人物的特性趋向“人器合一”的境界。因此器乐是否符合角色的“可演奏性”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器乐的选择一定要遵循其艺术规律,也就是说,要综合考虑民族乐器在形制,构造、技术运用和舞台表演上等一系列艺术特征能否满足角色的年龄跨度、性格特点、性别差异、地域差异和角色搭配的需要。最终男主角李嘉豪选择乐器是笛萧类吹管乐器,妻子曾佩仪选择柳琴和中阮,侄子李中国选择高胡,女儿李婉婷选择大提琴。
其中作为整部剧人物的主线李嘉豪,选择笛萧类吹管乐器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笛萧类吹管乐器的种类繁多,包含笛子、箫、埙、葫芦丝、巴乌类等丰富乐器种类,这些乐器音色个性鲜明,适合不同的情景叙事表达,而上述的吹管乐吹奏的演奏方法基本一致,演奏家都可以快速掌握使用,且笛萧类吹管乐器体积轻巧,便于舞台携带表演,这为统一角色舞台上的各种表演调度提供充分可行性。例如第一幕《寻路》中,李嘉豪有大量的舞蹈和肢体动作来表现“逃港”过程中的惊心动魄,大量时间都是在动态表演转换时演奏乐器,有时甚至需要边舞蹈边演奏,这时候竹笛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夸张化表演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虽然这一幕只有一个主角单独来完成演奏,但丝毫不影响观众对这一幕舞台呈现效果的喜爱。二是笛箫作为广东音乐代表乐器之一,在听觉上有着和广州语言表达的高度契合,例如第六幕《归来》中以广东音乐的《狂欢》为音乐素材创作,当李嘉豪拿着笛子和永庆坊的街里街坊一起在榕树下演奏广东音乐,充分展示广州的本土音乐气质和文化背景。三是李嘉豪的表演贯穿了从20岁到60岁的时间跨度,选择从梆笛到曲笛再到低音大笛的音色转换符合李嘉豪剧中青年到老人的声音表达差异,语言表达的时空感明显加强。例如第三幕《夜市》和第七幕《花街》中都有一段同样的主题旋律,《夜市》中用G调梆笛演奏这段旋律,梆笛明亮的音色表达恋爱的懵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花街》中再是用G调低音大笛来演奏同样的旋律,声音低沉,厚重,更符合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对已故妻子的思念之情。
在其他角色的乐器选择上,综合考虑整体音响结构的合理性,按照现有民族乐团的基本乐器配置类型为基础,均衡调配各种民族乐器,让他们都能发挥各自的音乐的特点。例如在《夜市》中,将唢呐、二胡、古筝、萨克斯、马林巴、琵琶等乐器融入夜市的小贩角色,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在整体的共性音乐氛围中突出了每个角色的个性化音色特点。同时在《地铁》中融合了电声乐、架子鼓等乐器,为整部剧增添了现代气息。
3.多元舞台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入
多元舞台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入主要包含戏剧表演艺术、舞蹈表演艺术和视觉传达等方面。戏剧表演在剧中以两种形式体现,一种是有音乐演奏的戏剧表演,另一种是无音乐演奏的戏剧表演。这两种戏剧表演方式在舞台呈现上都有各自难度。对于有音乐演奏的戏剧表演来说如何协调好戏剧表演和器乐演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演奏过程如何不“出戏”或‘跳戏”,让演奏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中自然呈现,达到“予演奏于无形”的境界。另一种是无音乐演奏的戏剧表演,以第五场《大爱》为例,其中有接近3分钟的时间除了15秒的南箫演奏之外,其他时间均由李嘉豪的扮演者通过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完成无实物的戏剧表演,这种无台词的戏剧表演对于专业的戏剧演员难度都很大,更不用说器乐演奏员了,不说一句话要演绎出男主角在妻子染病离世后的悲痛欲绝和绝后重生,这让观众印象深刻。从整体来说,加入了戏剧表演的器乐演奏,在舞台上无疑是对器乐演奏的艺术化补充,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视听联觉。但同时对于器乐演奏员的要求就更高,需要大量的戏剧训练才能够实现。
二是舞蹈在该剧艺术表达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特别是在写实的情景很难表述的时候,用相对抽象的舞蹈语汇来帮助表现,为音乐的诠释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在该剧的舞蹈编排中,融入了大量的现代舞和霹雳舞的元素,例如《夜市》中的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表演,《大爱》中用白布将舞蹈演员完全包住,舞蹈演员在白布中奋力挣扎,表现SA RS病毒的白色笼罩等等。该剧的舞蹈演员是由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师生担任,舞蹈的身段和戏曲的步伐有效的穿插在剧情中,和演奏的表演相得益彰,融为一体。
三是视觉传达包含了舞美灯光和服装设计。舞美灯光是全覆式设计,整体的舞台风格体现结构主义,这种设计对于剧目中表现时空的快速抽象转换是非常有利的,本次在舞台没有采用的常规的正面投影,而是通过在结构中寻找影像的变化,调整剧情中所有需要表现的环境、情景,无论是投影还是LED屏幕都是舞美中间的一部分,已经有效的融入到道具之中,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能够很恰当的表达出来。例如改革开放前的“逃港”中用两层幕布3D投影来展现大海波涛汹涌的逼真效果。第二幕场《春潮》中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和海珠桥模型的搭建;第四幕《速度》中地铁运行的动画设计,第五幕《大爱》中医院的隔离区,第六幕《归来》的大榕树等等,这些实景和LED立体布景的视觉传达会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角色的服装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近40年服装改革史的时代印记,服装的色彩从黑白向彩色过渡,20世纪70年代的逃难的破旧的衣服,80年代的蓝裤子、白衬衫,90年代的喇叭裤,千禧年之后的精致西装,这些具有时代印记的服装同样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