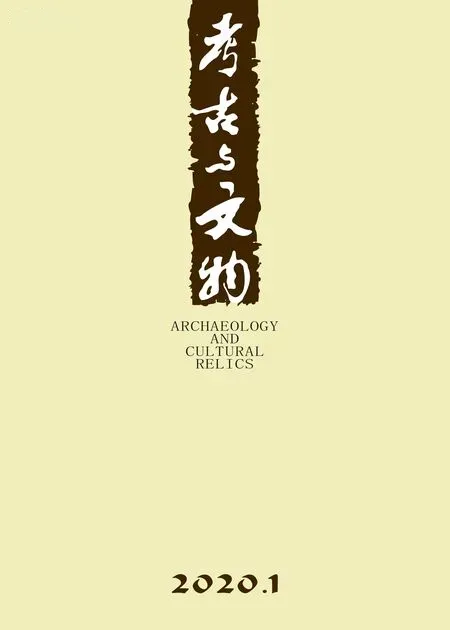试论宋元明时期闽北地区的仿龙泉青瓷
刘净贤
(故宫博物院)
福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瓷器产区。唐代以来[1],该地区凭借自身濒临海洋、港口发达的优势,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大量生产外销瓷。其产品种类多样,宋元时期以青瓷、青白瓷、黑釉瓷器为主,此外还有褐釉、黄釉、绿釉以及釉下褐彩等品种;明清时期则更为丰富,青花瓷、白瓷、青瓷、蓝釉瓷、黄釉瓷、酱釉瓷、黑釉瓷及五彩瓷、素三彩瓷等品种都有生产。
单就青瓷而言,南朝至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生产主要受越窑影响[2]。北宋晚期以后,闽地的青瓷生产转而受到新近崛起的龙泉窑的强烈影响,“以福建宋元以来的青瓷产品而论,基本上是仿龙泉窑的体系”[3]。福建青瓷的基本特征为多施半釉,釉色深浅不一,常采用刻划、篦划、篦点纹装饰。学界曾用“珠光青瓷”“同安窑系青瓷”“土龙泉”等概念来指代该类产品。有学者曾一一厘清这三个概念,指出“仿龙泉青瓷”的概念更为准确[4]。另有学者指出福建中部、南部沿海烧造的青瓷产品,实际上就是仿龙泉青瓷产品,并有所发展[5]。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同安窑系青瓷”就总体特征看,应属龙泉窑系的范畴[6]。“广义说来,闽江流域的所谓‘土龙泉’青瓷窑,应当也算是龙泉窑系的作品”[7]。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尽管是否要将福建青瓷纳入龙泉“窑系”[8]这一概念还有待商榷,但其仿龙泉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福建地区仿龙泉青瓷的窑址众多,不易梳理,本文拟在闽北(福建北部)地区的小范围内对宋元明时期仿龙泉青瓷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该地区亦是福建仿龙泉青瓷生产最为典型的地区。
一、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窑址分布概况
本文采用栗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中的区域划分,将福建地区的陶瓷生产划分为闽北(南平、三明地区),闽东(福州、宁德地区),闽南(漳州、厦门、泉州地区)三大格局[9]。这是唐、五代以来福建地区窑址发展逐渐形成的格局,在宋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但各区域的窑业内涵却有所区别[10]。
具体来说,闽北地区是指武夷山脉以南,闽江上游三大支流(建溪、富屯溪、沙溪)流经的地区[11],包括:松溪、政和、浦城、武夷山、建阳、建瓯、光泽、邵武、顺昌、建宁、泰宁、将乐、三明、沙县、南平等县市。
闽北地区仿烧龙泉青瓷的窑址(图一)主要包括: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半路窑,武夷山遇林亭窑,南平茶洋窑,建阳芦花坪窑、白马前窑、源头仔窑、碗窑、象山窑,顺昌河垱窑等。此外,浦城大口窑、碗窑,邵武大竹窑,顺昌连坑窑、谢屯窑,光泽下史源窑、茅店窑,将乐万全窑,尤溪半山窑也都有青釉瓷器的生产,只是龙泉青瓷的风格不太明显。上述窑址除浦城碗窑背窑以及建阳碗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外,其它所有窑址都烧造两种以上釉色品种的产品,甚至在有些窑口,青瓷并非其主流产品。如松溪回场窑除青瓷产品外,兼烧酱黄釉、黑釉产品;武夷山遇林亭窑黑釉产品占五分之三,青釉产品比例不及五分之二,此外该窑还生产少量白釉、青白釉产品;南平茶洋窑以黑釉、青釉、青白釉为大宗,兼有部分绿釉和釉下彩器。

图一 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窑址分布图
二、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举例及其生产时代
1.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举例及仿烧程度的差异
闽北地区对龙泉青瓷的仿烧主要表现在造型和装饰两个方面(图二、三、六、八~一〇、一二~一六)。仿龙泉青瓷的造型较为单调,主要为碗、盘、碟、杯等日用器皿,此外还有少量的瓶、炉类器物。在装饰方面,早期以刻划莲花、草叶纹、蕉叶纹为主,衬以篦点纹、篦划纹,晚期则多见印花纹样。
宋元明时期闽北地区青瓷窑场对龙泉青瓷的仿烧程度往往又是不同的,除造型、釉色、装烧等差异外,纹饰的繁、简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总体上看,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南平茶洋窑、顺昌河垱窑、建阳芦花坪窑、源头仔窑、碗窑在器物造型和装饰上与龙泉青瓷相似度较高。其中,松溪回场窑与龙泉窑的制瓷传统最为接近,部分产品甚至难以区分[12]。二者胎色均为灰白或浅灰色,釉色多为青黄色、青绿色,修足较为规整,施釉及底(其它窑场常施半釉),仅足内露胎。器物造型近似,装饰方法皆以内外壁双面刻划花为主,内壁刻划莲花、草叶纹,间以篦点、篦划纹,外壁刻划折扇纹。此外,回场窑生产的婴戏纹碗(图二,2)在闽北地区窑场中极为罕见,而婴戏题材在龙泉大窑、金村(图二,1)等窑场都有发现。在装烧方法方面,松溪回场窑除采用闽北绝大多数窑场普遍使用的漏斗形匣钵外,还大量采用M形匣钵装烧。M形匣钵是龙泉窑最常见的匣钵形制,而从目前发表的闽北窑址资料看,M形匣钵装烧方法除宋元时期的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元代的建阳源头仔窑、明代建阳碗窑有应用外,几乎不见于闽北地区的其他窑场,显然是受到了龙泉窑的强烈影响[13]。

图二 婴戏纹碗
闽北地区的仿龙泉青瓷还存在着纹饰简化现象。部分窑场的刻划花纹饰有所简略,但仍保留了大量龙泉青瓷的工艺元素,母题尚可分辨。这种现象在缠枝草叶纹饰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图三),如松溪回场窑除完整纹样(图三,5)外,还有以简笔刻划结合篦划纹勾勒的缠枝草叶图案(图三,6)。而以更简练的成组篦划纹表现的缠枝草叶纹在松溪回场窑(图四)及武夷山遇林亭窑(图三,7)等处都可见到。

图三 缠枝草叶纹碗
此外,部分窑口的装饰存在着极度简化及抽象化现象,仅保留少量龙泉青瓷的装饰技法及元素,即以成组篦划纹、“之”字形曲折篦点纹为装饰的主体,图案粗率,母题已经不可辨认。如南平茶洋窑部分碗类产品,内壁以几条简单的刻划线及稀疏的“之”字形篦点纹作为主题装饰,无法表现具体图案;武夷山遇林亭窑部分产品仅采用成组篦划纹,或刻划云状曲线纹及篦划纹组合装饰器物内壁,外壁或光素或刻划折扇纹[14]等简单的装饰手法,不再表现明确的题材(图五);浦城半路窑除生产纹饰较繁复的内壁刻划花卉纹、外壁刻划折扇纹的产品外,还有只在内壁划简单弧形篦划纹的器物,纹饰趋于简化;光泽下史源窑青瓷仅以数组弧曲的篦划线条装饰内壁;建阳白马前窑、光泽茅店窑址[15]生产只装饰多组“之”字形篦点纹的器物。
以上内容以装饰图案为主要依据,对闽北地区宋元时期青瓷器做出大略梳理,旨在阐明闽北地区仿烧龙泉青瓷面貌上的多样性以及仿烧程度的差异性。由于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多数窑址只做过调查,缺乏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闽北窑场产品的分期和特征还十分模糊。上述仿烧程度上的差异,不排除有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可能性。

图四 松溪回场窑出土的篦划简化缠枝草叶纹执壶

图五 武夷山遇林亭窑出土的青釉篦划纹碗
2.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的生产时代
闽北窑场典型的内外壁双面刻划花青瓷(图三、六)是较早的仿龙泉青瓷品种。就目前考古工作相对深入的龙泉窑情况看,金村、大窑以及龙泉东区的山头窑、大白岸等地都曾生产该类产品。根据现有的发掘调查报告,大窑发现的该类产品的生产时代定在北宋中期[16],金村的这类产品在元丰时期(1078~1085年)似已兴起[17],龙泉东区报告则认为该类产品出现在北宋晚期[18]。根据窑业交流的规律,与龙泉地区毗邻的闽北地区仿烧该类青瓷的年代当为与之同时或稍晚的北宋晚期。福建墓葬所出仿龙泉青瓷正可佐证这一推断,如闽北顺昌大坪林场墓出土的2件刻划缠枝草叶纹的青黄釉碗(图七),即为福建仿龙泉的典型代表[19]。据所出最晚钱币“元丰通宝”推测该墓时代很可能为元丰时期[20],属北宋晚期。从沉船资料看,沉没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镇的惹巴拉沉船(The Jepara Wreck)就装载有安溪、南安、同安以及推测为闽北浦城等窑口的仿龙泉青瓷产品。该船可能从福建泉州出发,目的地是惹巴拉(Jepara)、图班(Tuban)或者东爪哇的格雷西(Gresik)[21],沉船年代约为1130年前后的北宋末期[22]。惹巴拉沉船出水瓷器表明,至迟到北宋末年,闽北仿龙泉青瓷已销往东南亚。

图六 缠枝莲纹碗
南宋时期,闽北地区的仿龙泉青瓷生产仍然很发达,产品大量销往海外,福建福州平潭大练岛西南屿西南面发现的宋代沉船、福建莆田南日岛、湄洲湾海域的北土龟礁一号沉船、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1号沉船都出水有闽北窑场生产的仿龙泉青瓷,其时代集中在南宋早中期。
元代闽北的瓷业已不如宋代兴盛,略呈衰落之势,仅浦城碗窑背窑、大口窑、半路窑(图九,2)、建阳源头仔窑(图八;图九,3)、南平茶洋窑等几处窑场生产仿龙泉青瓷,这可能与福建沿海地区窑场的竞争有关。明代闽北仿龙泉的窑场仅建阳的碗窑(图一〇)、象山窑较为典型[23]。清代,闽北窑场改以烧制青花瓷为主。

图七 顺昌大坪林场墓出土的缠枝草叶纹碗
三、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窑场的分布规律
从中国古代窑址分布规律来看,河流对于窑业生产尤其是内陆地区的窑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河流不仅为瓷土的粉碎、淘洗、陈腐等工序提供水力,还是成品外运的通道。南方地区窑场选址往往依山傍水。在整个福建省范围内,相对于闽东、闽南地区濒临海洋的地理位置而言,闽北处于内陆地区,交通多依赖河道。闽北地区星罗棋布的窑场分布当与密集的水网有着密切的关系。
闽北地处闽江上游,境内分布着闽江上游的三条主要支流:建溪、富屯溪和沙溪,此三条支流在南平汇合为闽江,流经闽东地区,经福州入海。建溪、富屯溪又分别由若干细流交汇而成:松溪、南浦溪、崇阳溪汇入建溪;金溪在顺昌汇入富屯溪。闽北的主要县市就分布在这些大小支流上,有些更坐落在这些支流的交汇点上。兹按照逆时针方向、自上游至下游的顺序,简述各水系[24]如下(图一一):
松溪—建溪流域:松溪—建瓯—南平
南浦溪—建溪流域:浦城—建阳—建瓯—南平
崇阳溪—建溪流域:武夷山市—建阳—建瓯—南平
富屯溪流域:光泽—邵武—顺昌—南平
金溪—富屯溪流域:建宁—泰宁—将乐—顺昌—南平
沙溪流域:三明—沙县—南平
以上县市都有窑址分布,宋元时期尤为密集。闽北各县市窑场产品釉色种类多样,青釉、青白釉、黑釉最为常见,几乎各县市都生产两种以上釉色的产品。然而,若以仿龙泉青釉器物为关注点,分析各县市仿龙泉青釉窑场数量、青釉产品所占比重、仿烧程度,则可大致归纳出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分布规律:

图八 建阳源头仔窑址出土印花梅花纹盏

图九 印花碗盘
松溪与南浦溪上游流域的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浦城半路窑等窑址的地理位置与龙泉窑址分布密集的浙江省龙泉市、庆元市紧邻,受龙泉窑影响最大,仿烧龙泉青瓷的程度最高。其中浦城碗窑背窑是闽北境内少见的以仿烧龙泉青釉器为主的窑场,并采用龙泉窑系统的M形匣钵;松溪回场窑青瓷甚至与龙泉青瓷难以区分,并同样采用了M形匣钵;浦城半路窑等也大量仿烧龙泉青釉。一般认为,浙江龙泉窑产品的外运是向东顺瓯江而下自温州出海,有学者指出向南经福建闽江下福州自闽江口出海也是有可能的[25]。那么,龙泉青瓷自龙泉、庆元一带南下闽江,必然要经由松溪或南浦溪至建溪水系,对该流域窑场的深刻影响不言而喻。

图一〇 洗式炉
崇阳溪流域及南浦溪下游流域的武夷山市—建阳一线发展出以建阳水吉为中心的著名黑釉瓷窑场,建阳诸窑、武夷山遇林亭窑都以生产黑釉产品著称。即便如此,遇林亭窑亦生产占总数近五分之二的仿龙泉青瓷产品。建阳芦花坪窑址在烧造黑瓷以前的晚唐、五代时期曾烧造青黄釉瓷器,而仿龙泉风格的青釉器与黑釉器同出于窑址第二层,推测仿龙泉青釉器的时代与黑釉器同时或稍晚,当在北宋中期以后或南宋之际[26]。此外,宋代建阳白马前窑址甚至以仿烧龙泉青釉器为主,兼烧青白釉及黑釉器物。元代建阳源头仔窑亦以生产内底印花卉、文字的仿龙泉青瓷居多(图九,3)。建阳碗窑、象山窑是闽北地区明代为数不多的仿龙泉窑场。以上窑场中,建阳芦花坪宋代窑场、源头仔元代窑场、碗窑明代窑场都是仿烧龙泉青瓷程度很高的窑场,后两个窑场甚至采用了福建地区少见的M形匣钵。可见,由于地缘接近,崇阳溪流域及南浦溪下游流域仍受到浙江龙泉窑、福建松溪、浦城仿龙泉窑场较强烈的影响。
富屯溪、金溪、沙溪流域地处福建省西北部,邻近江西省,更多地受到江西地区青白瓷制瓷传统的影响,龙泉青瓷在本地的影响则较薄弱。光泽下史源、茅店窑址以青白瓷的产量最大,质量最高,并兼烧青釉器物。青釉器物多光素或仅以简单的篦划线或篦点纹装饰,龙泉窑风格不明显。邵武大竹窑、青云窑青釉产品在装饰风格上亦少见龙泉窑因素。建宁澜溪窑址以生产青白瓷为主,兼烧少量青瓷、黑釉瓷、酱釉瓷,青白瓷质量最精。三明窑以烧造青白釉瓷为主,兼烧酱黑釉器,极少烧造青釉瓷[27]。沙县仅在近年发现金鸡山一处窑址,且生产青白瓷[28]。在整个富屯溪、金溪、沙溪流域范围内,唯有位于富屯溪、金溪下游汇合处的顺昌境内的河垱窑生产的青釉瓷器在纹饰风格方面很接近龙泉青瓷。这大概是由于顺昌地处下游,在地缘上更容易受到上述松溪流域、南浦溪流域及崇阳溪流域的仿龙泉窑场的影响。
上述闽北的大小支流均最终在南平交汇,汇入闽江,通往下游出海。南平宋元设驿,自古以来便是闽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宋元南平茶洋窑产品以黑釉、青釉、青白釉为大宗,兼有部分绿釉和釉下彩器,当是吸收了上游各窑的技术成分,并兼容了包括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吉州窑等诸多窑系的艺术风格。茶洋窑青釉器仿烧龙泉瓷程度较高,具有浓厚的龙泉青瓷装饰风格。
综上所述,龙泉青瓷对闽北各水系窑场的影响力大略呈逆时针方向由东向西递减:即靠近浙江一带的松溪流域与南浦溪流域窑场受到龙泉窑影响最为强烈,最接近龙泉青瓷风格;崇阳溪流域虽以黑瓷著称,但龙泉窑影响也广泛存在;富屯溪、金溪、沙溪流域虽亦生产青釉器,但龙泉风格已弱化,产品以青白瓷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受江西地区青白瓷影响更深远。这些水系最终交汇在南平,成就了南平茶洋窑包括龙泉风格青瓷在内的种类繁多的产品。
四、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与龙泉青瓷的区别及相关问题
(一)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与龙泉青瓷的区别
1.胎釉及修坯
闽北地区不同窑口胎、釉质量差别较大。有的窑口胎质细腻,胎色灰白,施釉及底,釉色晶莹光洁,釉色以青绿为主,还有青黄、黄褐等色泽,接近龙泉青瓷的胎釉特征。多数窑口则胎体厚重,胎色灰,釉色灰暗浑浊,外壁半釉,施釉线不规整,内底刮涩圈。浦城半路窑三号窑甚至内底全部刮釉以叠烧器物[29]。闽北地区青瓷多数修坯粗糙,底足平切,修足不规整,留有割坯痕和乳突。外壁施半釉及内底刮涩圈的做法似乎在宋代已较为普遍,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
龙泉青瓷,尤其是以大窑和金村为代表的龙泉窑中心窑场产品,在胎、釉质量及修坯利足方面要大大优于闽北青瓷。虽然部分早期产品胎质略为疏松,釉色不一,温度和气氛的控制还不够成熟,但器物均为施釉及底,仅圈足内无釉,基本未发现内底刮釉及涩圈现象。元代时,大窑等地虽出现了(内)外壁施半釉的器物,但这类器物皆为素面粗瓷,数量较少,绝非龙泉产品的主流。
2.器型
从器型看,除松溪回场窑较丰富外,闽北青瓷大多较为单调。器型以日用器为主,且以碗、盘、碟、钵、杯类圆器为大宗。此外还有少量随葬用福寿瓶(图一二)、谷仓罐。香炉等供器十分罕见,基本不见陈设类器物。
相比之下,龙泉青瓷器型异常丰富。不仅日用器形制多样,还有很多陈设器、香具、文房用品等等,如贯耳瓶、琮式瓶、盘口弦纹瓶、折肩瓶、吉字瓶、凤尾尊等陈设器,各式砚滴、水盂等文房用具,各式香炉。这些器物中不乏仿古铜器、玉器造型。此外,龙泉窑丰富的人物、动物瓷塑也是闽北窑场所不见的。
3.装饰
闽北青瓷以刻划花及篦点、篦划纹装饰为主(图三、六、一三~一六),还有少量圆器内底模印花卉、文字图案(图九),琢器外壁模印“福”“寿”字。装饰方法总体看较为单调。
龙泉窑南宋后期流行的浅浮雕式剔刻莲瓣纹,元代常见的折线弦纹、云鹤纹、龙凤纹、海浪纹等刻划图案,内模满印纹饰、褐色点彩、镂空、贴花、雕塑等各式装饰手法均不见于闽北各窑。
4.装烧
闽北窑场常见的窑具包括垫柱、垫饼、支钉、匣钵等。匣钵以漏斗形匣钵为主,平底筒形匣钵也较常见。而龙泉窑大量应用的M形匣钵仅见于宋元时期的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以及元代的建阳源头仔窑、明代的建阳碗窑。漏斗形匣钵的使用方法为单件器物仰烧,器物、匣钵间用泥垫饼间隔。M形匣钵内则多置两件器物叠烧,用支钉、支圈间隔。器物内底刮涩圈后明火叠烧于垫柱之上也是较为常见的装烧方法。

图一三 莲花纹碟

图一四 草叶纹碟

图一五 莲花纹碗
龙泉窑匣钵的使用在北宋中后期还不够普及,明火叠烧还较为常见。到了南宋前期,龙泉窑的中心窑场已普遍采用平底筒形匣钵及M形匣钵一匣一器装烧[30]。与闽北窑场只有粗泥垫饼及支钉作为间隔具的情况相比,龙泉窑的垫具、间隔具种类繁多:从早期的垫圈,到饼形、轴头形瓷质垫饼。薄俏的圜底或平底钵形瓷质“垫盖”,再到大小、形制不一的直口钵形垫具,以及各时期通用的粗泥垫饼。伴随着装烧方式的变革,各式间隔具、垫具应运而生,多数都以保证产品质量为最高追求,在制作窑具时往往不惜工本。
总体上看,闽北青瓷的装烧方法较为粗糙,为了追求产量,涩圈叠烧类器物较多。即使是质量相对较高、受龙泉窑影响最为强烈的松溪回场窑,其M形匣钵烧造的叠烧器物内底亦有支钉痕或涩圈。而这种情况在明中期以前龙泉窑的中心窑场是极为少见的。
(二)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的仿烧层次问题

图一六 蕉叶纹碗
从以上分析看,闽北多数窑场对龙泉青瓷的仿制基本表现在对器型、造型、釉色、装饰的简单模仿。即使在这些方面也并非全盘模仿,而是仅得其皮毛。而在体现窑业技术传承的核心领域—装烧方面则很少借鉴:闽北窑场但凡使用匣钵,则基本采用漏斗形匣钵。而漏斗形匣钵是建窑类型黑釉瓷及景德镇窑类型青白釉瓷器以及广东窑口常采用的典型窑具。采用龙泉窑常用的M形匣钵的窑场,仅局限在与龙泉毗邻的松溪、浦城、建阳等零星几处宋元明时期窑址。龙泉窑种类繁多的间隔具、垫具则丝毫未影响到闽北诸窑。由此可见,闽北仿龙泉青瓷仅停留在局部的、表面的较浅层次上,并非是从根本上的全面学习。
五、闽北窑场兼收并蓄的生产风格
纵观闽北窑场可以发现,诸窑都存在着技术上兼收并蓄、工艺上草率急就的特点。几乎每个窑场都兼烧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釉色的器物,有的甚至有不同釉色的产品叠烧现象,如光泽茅店茶窠山宋代窑址出土的青白釉—青釉—青白釉碗的叠烧粘连标本[31](图一七)。即使受龙泉窑影响最深的松溪回场窑,亦发现了青釉碗与建窑风格的黑釉碗叠烧粘连的标本[32]。同一窑场不同釉色的产品在造型、装饰、施釉以及装烧方面往往相通。如南平茶洋窑的折枝莲花纹折腹平底碟有青釉(图一三,4)和青白釉两个品种[33],而这类器物也是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图一三,1、2);顺昌河垱窑生产的青釉及青白釉碗盘类器物皆外壁施半釉,内底有叠烧涩圈[34];建阳白马前窑生产的青釉、青白釉、黑釉品种的碗、盘、碟类产品的内底都刮涩圈,采用叠烧法,有的还使用支钉[35]。总体看来,同时兼烧青釉瓷、黑釉和青白釉瓷的窑场,一般青白釉瓷器胎釉质量最好,修坯也较为精细,青釉居次,黑釉瓷胎质、修坯方面最差,如武夷山遇林亭窑[36]、浦城大口窑等。
六、闽北窑场仿龙泉青瓷的外销
福建地区窑场具有悠久的外销传统,其产品除少量供应本地市场外,主要目标市场为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
闽北地区窑场众多,几乎各县市都建有瓷窑,且一处窑场往往绵延数座山岗,生产规模巨大。这些窑场生产的包括仿龙泉青瓷在内的不计其数的产品,远远大于本地甚至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闽北仿龙泉青瓷必然要运销海外。其外销路线也是非常清楚:各窑产品沿闽江上游的大小支流,顺流而下进入闽江,最终经福州入海。从福州沿大陆边缘北上宁波港,可外销至日本等地。从福州沿海岸南下达南宋、元代时第一大港泉州,则可远销东南亚诸国甚至更远。部分产品还有可能从福州港直接出海。近年发现的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外销的例证有:

图一七 光泽茅店茶窠山宋代窑址出土的青白釉-青釉-青白釉碗的叠烧粘连标本
上海奉贤县曾出土过叠摞捆扎在一起的八百余件青釉瓷碗。这批碗胎色呈灰色,釉色豆青,有的闪黄或泛灰,多数素面无纹,少数外壁饰直线或斜线刻纹,内壁饰篦纹或花瓣纹,外壁施半釉,圈足露胎,有的内底有圈垫叠烧痕迹。发掘者推测器物出土地为宋代海岸线里护塘遗迹,产品可能来自浙江南部或福建北部地区[37]。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这批青瓷产自闽北的茶洋窑[38]。
福建福州海域平潭大练岛西南屿西南面发现的宋代沉船遗迹,出土了大量装饰有篦划莲花纹的青釉碗、盘、碟类器物,发掘者认为其与福建北部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的产品相似,年代为南宋早期[39]。
福建莆田南日岛、湄洲湾海域发现的北土龟礁一号沉船,沉没年代当在南宋早、中期,出水的青釉碗类产品初步推测为福建北部地区窑口的产品[40]。
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了大量瓷器,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及大批的福建窑口瓷器。其中折腹敞口盘(图一八)的造型、修足、内外壁纹饰与松溪回场窑出土的青釉盘(图一九)[41]一致,而弧腹侈口盘(图二〇)亦与松溪回场窑出土的青釉盘近似,且沉船出水的印有“吉”字的器物亦见于回场窑址。基本可以断定,该沉船中的这类器物来自闽北的松溪回场窑。据推测,华光礁1号沉船由泉州出发,驶往东南亚[42]。其沉没年代约为十二世纪中叶的南宋前期[43]。
此外,上文所述北宋末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惹巴拉沉船,更提供了东南亚出水的闽北仿龙泉青瓷的例证。
以上所列海塘及沉船遗迹出土的闽北地区仿龙泉青瓷,粗略勾勒出该类产品外运的航线。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更多沉船被发现,闽北仿龙泉青瓷外销的面貌将会更加清晰起来。

图一八 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的青瓷折腹敞口盘

图一九 松溪回场窑址出土的青釉盘

图二〇 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的青瓷弧腹侈口盘
七、小结
宋元明时期闽北的仿龙泉青瓷生产始于北宋晚期,宋代最盛,元代稍衰,明代则仅有零星几处窑场还在生产。闽北仿龙泉青瓷窑场沿水系分布,距离龙泉愈近,则受到龙泉窑的影响愈大;愈向西部,受到江西青白瓷的影响愈强。此外,闽北青瓷对龙泉瓷的仿烧仅停留在釉色、装饰、造型等表面层次上,而对体现窑业技术传承的核心领域—装烧方面则很少借鉴,仅是一种局部的、表面层次上的模仿,并非从根本上的全面学习。闽北仿龙泉青瓷主要为外销而生产,至迟在北宋末年,其产品已运销到东南亚地区,并且是南宋早中期的重要外销船货。
[1]如福州怀安窑唐、五代青瓷器发现于日本九州地区,可能也有少量销往东南亚。栗建安.福建古窑址考古五十年[C]//陈昌蔚纪念论文集(陶瓷).台北: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1:32.
[2]栗建安.福建地区的越窑系青瓷[C]//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79-88.
[3]栗建安.福建仿龙泉青瓷的几个问题[C]//东方博物(第三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81.
[4]同[3].
[5] 叶文程.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C]//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60-61.虽然叶文程只提到福建中部、南部沿海地区仿龙泉青瓷,但福建北部的仿龙泉青瓷生产是为学术界所公认的。
[6] 傅宋良,张家,谢道华.闽北陶瓷[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137.
[7] 蔡玫芬.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J].故宫文物月刊,2009(2).
[8]“窑系”的概念近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质疑,笔者也不赞同使用“龙泉窑系”的说法。
[9] 栗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C]//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177.
[10]同[1]:13.
[11] 赵嘉斌,吴春明.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26.
[12] 如栗建安在介绍西沙群岛光华礁1号沉船出水的精品青釉碗、盘时,指出龙泉窑、松溪回场窑皆有同型的器物,不易判别。栗建安.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发现陶瓷器的相关问题[C]//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52-253.
[13] 在宋代南方影响最广的青瓷窑场中,越窑、龙泉窑都使用M形匣钵。浙东越窑的匣钵形制较多样,包括各式钵形、筒形、M形、僧帽形匣钵,并且有的还配有匣钵盖,M形匣钵并非主流。且越窑在北宋中期以后趋于衰落,影响力减弱,不足以对遥远的闽北窑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浙西南的龙泉窑在北宋晚期以后发展迅速,元代窑场更是规模空前,对邻近的闽北窑场影响明显,其典型的M形匣钵不见于江西青白瓷窑场、福建黑釉窑场及广东窑场。宋元时期闽北松溪回场窑、浦城碗窑背窑、元代建阳源头仔窑、明代建阳碗窑使用M形匣钵的做法,显然是来自龙泉窑的影响。
[14] 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发掘报告[J].福建文博,2000(2).
[15] 林忠干.福建光泽茅店窑的瓷业成就[J].东南文化,1990(3).
[16] 朱伯谦.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C]//龙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4.该类产品主要出土于1960年发掘的杉树连山西北部山岗的T10。
[17] 张翔.龙泉金村古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C]//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90.该类产品主要出土于1960年发掘的位于16号窑址的T1②、T5③两个单位。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402-407.龙泉东区以大白岸金钟湾窑址(BY22)为代表的遗物是“迄今为止龙泉东区所能见到的最早青瓷器物”。
[19] 发掘者推测同墓所出的其他瓷器产于闽北地方窑口,故这两件青黄釉碗也极有可能是闽北窑口的产品。从器物特征看,这两件碗应属闽北仿龙泉产品。
[20] 曾凡.福建顺昌大坪林场宋墓[J].文物,1983(8).
[21] E.Edwards McKinnon.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Ceramics Cargoes[M].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2001.转引自项坤鹏.浅析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遗址概况、分期及相关问题分析[J].东南文化,2012(2).
[22] 该船出水大量铜钱,最晚为重和钱。见Atma Djuana,Edmund Edwards McKinnon. The Jepara Wreck[C]∥Pei-Kai Cheng: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Maritime Trade, 12th -15th Centuries.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H.K.)Ltd,2005:129,132-134.
[23] 姚祖涛,赵洪章.闽北古瓷窑址的发现和研究[J].福建文博,1990(2).
[24] 每条水系按照从上游到下游的顺序,依次列明有窑址分布的县市。
[25]同[12]:255.
[26] 叶文程.“建窑”初探[C]//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53-154.
[27] 王永平.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三明窑[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21.
[28] 赵玉兰,林建棋.沙县水南鸡金山宋代窑址调查简报[J].福建文博,2011(3).
[29] 陈寅龙,朱煜光.略论福建松浦古窑产品的类型与特点[J].福建文博,1996(2).
[30] 龙泉东区安福宋代窑场有使用M形匣钵、匣钵内叠烧多件坯件的做法,坯件间以泥饼或支钉间隔。
[31] 黄富莲.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光泽窑[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57.
[32] 林忠干,赵洪章.福建松溪唐宋瓷窑的探讨[C]//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105.
[33] 张文崟.南平茶洋窑几个问题的探讨[J].福建文博,1990(2).
[34] 陈建标,林长程.顺昌河垱宋窑调查[J].福建文博,1990(2).
[35]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161.
[36] a.武夷山市博物馆.福建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再考察[J].福建文博,1996(2).b.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发掘报告[J].福建文博,2000(2).
[37] 孙维昌.上海奉贤县发现大批宋瓷[J].文物,1987(9).
[38]同[33].
[39]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J].文物,2014(2).
[40] 根据出水年代最晚的铜钱“绍兴通宝”及器物特征,判断北土龟礁一号沉船的年代为南宋早、中期。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与发现[C]//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7。
[41]同[29].
[42]同[12]:270.
[43] 森達也.龍泉窯青瓷の編年研究—沈船と窖蔵資料を中心に-.会议幻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