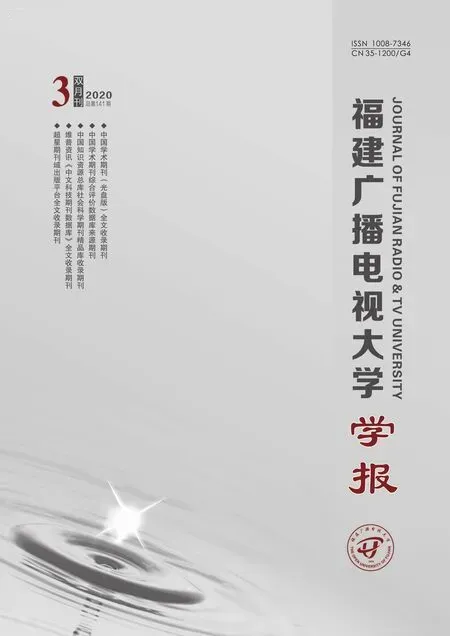回归与超越:从心中的山水到山水城市的营造
——论王澍和马岩松的建筑风格的同与异
林 平
(莆田学院,福建莆田,351100)
中国人居理想中的山水思想,是让人居环境直接融入自然环境中,并与之和谐相处;退而求其次,作为城市人居理想的园林思想,则是把大自然里的山水元素或意象,搬进园子、庭院中,通过模拟自然形成微缩的山水景观。作为在国际上知名的两位中国建筑师,王澍和马岩松的建筑风格都深深地刻上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思想的烙印。他们的作品风格独具,特征鲜明,可辨识度高,具有各自内在的关联性和统一性。
一、回归山水园林的理想:道法自然
(一)道法自然与人法自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然一词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为造化任运之自然,其二为天地万物之自然。正如推崇陶渊明的李白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既可以解释为由大自然雕琢出来的,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去除了人工雕琢的痕迹。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是人法自然——既是人对自然的仿效,又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中国人对自然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朴素的情感,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一种情感上的关联,在西方是没有这种概念的”。[1]在西方传统中,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发生情感联系,哪怕是人与作为人格神的上帝之间也能发生情感联系。而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并不直接发生情感联系。只有在当代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兴起之后,人们才开始清算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并认可人对环境、对自然单向性的责任关系,从而导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二)王澍的“大山法”与马岩松的“非线性”建筑
王澍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造园艺术中获取了大量的养分和灵感,他的建筑风格融入了对中国山水园林的思考。他认为,在西方,建筑一直享有面对自然的独立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建筑在山水自然中只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次要之物。他的建筑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中国新古典的风格,总体给人以黑黝黝、灰蒙蒙的雄浑大山般沉稳静谧的感觉。相对而言,人在建筑的面前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王澍在《造房子》一书中明确指出,宁波博物馆的设计就是用的“大山法”(见图1)。[2]
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曾专门提及建筑设计中圆形和方形的构图特征,并认为人工构筑物多为方形,而方形在自然界中却几乎不存在。[4]东西方建筑设计中的圆形结构,虽然不多,但并非没有,著名的有古罗马的斗兽场、印度的泰姬陵、北京的天坛,更别提中东穆斯林地区随处可见的半球形穹隆了。当代中国如杭州市的新地标建筑“日月同辉”——金球状的国际会议中心和月牙形的杭州大剧院,同样是圆球形建筑的典范。然而,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流线型建筑作品,却寥若晨星。但在年轻建筑师马岩松的作品里,却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他颇具识别度的建筑风格标签,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某种自然流畅、不拘一格的灵动感(见图2、图3)。建筑物起伏的轮廓曲线也给人以山峦一般的感觉。有人将马岩松与扎哈·哈迪德进行比较,把他们的建筑用颇为抽象的学术性术语归类为“非线性建筑”。[3]
如果说建筑物是山,那么山水中的水,又在哪里呢?建筑师的做法大多是把作品置于自然的山水之间,或者把活水引入园林。但在心中有山水的建筑师那里,山水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种意象,或是一种意境,未必要有真山真水。中国园林中的叠山理水,可以通过人工营造的假山、泉水、池水,营造山水氛围。而最典型的是日本“枯山水”的造园手法,仅仅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小品甚至是砖瓦白砂等模拟水的波纹或动感就足够了。究其源头,也是来自中国的园林思想。
(三)王澍建筑的阳刚之气和马岩松建筑的阴柔之美
王澍建筑的主色调也像大山一样,通常是灰黑色的。建筑的整体轮廓线线条是粗犷的、方块状的,充满阳刚之气。但在结构上、细节上却是纤细的,材质上尽量取用传统老旧的材料,像山体岩石或木质的纹理,这种反差较大的搭配,使作品展现出一股东方式的淡雅风韵,显得刚中有柔。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和杭州南宋御街的一些建筑,几乎都是这样的风格(见图4、图5)。
马岩松的建筑风格同样融入中国山水的意象。他的建筑给人以清新的山体的意象,从建筑的轮廓线上看,往往是浑圆光滑的,或婀娜或流动感十足,充满阴柔的曲线之美,整个建筑在整体上却不失简约明快、大线条的现代感。色彩选择上常常偏银灰色,显得更加清亮大气,更具现代气息乃至超现实主义式的未来感,有些作品中甚至能看到科幻电影《未来世界》《星球大战》的影子。
在马岩松那里,以钝化、曲线为特征的女性化的建筑造型,不仅是一种审美上的考量,也是对自然的妥协与和解,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还是对男性化建筑乃至男权社会的挑战。加拿大多伦多密西沙加市的梦露大厦直接就是用了一个性感女郎的名字(见图6)。但因其建筑多呈现大尺度、高密度的特点,又显得柔中带刚(见图7)。
总之,王澍的作品在继承中更老成些,更显森然的古意,而马岩松的作品在传承中更年轻态些,更具轻盈的现代感乃至未来感。如果用中国的阴阳鱼来比拟,我们可以说,王阳马阴,各擅胜场。
二、广义建筑学:聚焦山水城市和园林城市
(一)“四方域”与“三才”说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意识到技术进步对现代社会的肢解和冲击,提出了“天地人神”“四方域”的概念,指出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大有融合中西思想之意,因而受到中国这个“诗化国度”学界的广泛追捧。中国自古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也是钱学森先生提出“山水城市”理想的历史渊源之一。
在城市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今中国,正如吴良镛所倡导的“广义建筑学”那样,[4]王澍和马岩松他们并不满足于做一个狭隘的建筑师,而更愿意做一个广义的建筑师。王有杭州“南宋御街”,马有“北京2050”和“移动中国城”。有的虽然还只是图纸上的构想,但却为中国未来的山水城市建设指明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
(二)共同的山水城市的理念
王澍指出,“我把建筑做成山一样,建筑最重要的是隐蔽在里面。你走到跟前才会发现。它的入口很小。却像山一样庞大,几乎没有立面。它就是一个虚空,内部非常复杂”。[2]王澍的建筑也在尝试突破那种刻板的、千篇一律的四方形火柴盒结构,比如杭州南宋御街上的许多建筑,但基本上还是棱角分明的结构,马岩松流线型的建筑则与之风格迥异。
马岩松认为,山水城市的思想,也许才是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带给世界的进步。“山水城市就是将城市的密度与功能和山水意境结合起来,希望构建以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未来城市。”[1]在马岩松那里,构筑山水城市不是为了简单地把自然山水搬进城市,而是为了构筑我们心中理想的山水城市的意象,是追求“山非山、水非水”的意境,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话。[1]马岩松的建筑,其实是在西方先进科技的皮囊里装着一颗中国心,如广西北海市的北部湾1号,就是以桂林著名景点象鼻山为参照物的作品(见图8)。
两位建筑师从表面上看建筑风格迥异,实则有其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在传承中国古典山水园林理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却又在有意无意中拉开与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距离。在融入中国园林思想精髓的同时,借鉴西方现代建筑技术,营造与建筑周边环境更加协调的整体氛围。
(三)不同的建筑选材与建筑手法
在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上王澍更偏向于传统,而马岩松则更偏向于现代。换句话说,王希望通过传统建材如石砖瓦木的重新运用,凸显其粗粝古朴的质感,糅合现代简约的理念和传统的工艺手法进行创新性营造,从而搭建与传统的紧密关联,形式上更显古朴、更接地气;马则是在心中构筑起山水的意象,通过现代时尚光鲜亮丽的材料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更多地去与未来沟通,形式上更具梦幻般超越现实的未来感。
总之,他们都是在用各自的中国式的建筑语言,来应对裹挟着权力、资本和技术的机械现代主义对全世界发出的挑战。
三、超越传统与现代主义:未来的出路
(一)反思传统与现代主义
现代诗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对于诗人来说,“历史意识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5]对于建筑师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他们同样要思考如何沟通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正是为了更好地超越。回归历史、回归传统,不仅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重拾文化自信的表现。只有在这种前提下的创新,才不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不会在信息大爆炸的纷繁世界里,迷失未来的方向。
安藤忠雄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预制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建筑生产工业化”。[6]这必然妨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选择性。
马岩松曾明确表明:“就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造成的价值观,然而这个价值观也造成了现代主义建筑。”[1]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这种价值观造成了一个个机械的城市形态,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乃至矛盾对立。
(二)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
从现代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上看,老一辈的梁思成、林徽因还有吴良镛等人,他们更看重的是传统建筑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而新一代的代表如王澍、马岩松,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因此,选择他们俩为代表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知名度和成就,更是基于他们在中国建筑文化传承链条中所做的思考与创新。建筑师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思考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建筑乃至中国的城市建设,出路在哪里?
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洞察到的那样,代表自然的山水,其实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感情归宿和心灵寄托,俨然是中国人心目中堪比西方上帝的信仰。[7]这里对山水园林的回归,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回归,而是精神家园和情感层面上的回归,是回归到中国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与和谐关系上;这里的超越,也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在多少带着些焦虑不安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的召唤下,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指向了风驰电掣般扑面而来的、光辉耀眼的未来。
(三)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出路
两位建筑师同样关注未来,但看得出来,王更植根于传统,更注重朴实的价值,而马更超脱于现实,更仰仗科技的力量。在王澍看来,“未来的建筑学将以新的方式重新使城市、建筑、自然和诗歌、绘画形成一种不可分割、难以分类并密集混合的综合状态……传统一旦死亡,我们就没有未来”。[2]
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追求效益与效率,是否必然要牺牲理想?快与慢,是一对矛盾体。快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理想的打磨却需要时间、需要慢。方块建筑的简单、便利和实用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易于复制和工业化生产也是显而易见的。流线型、个性化的建筑,必然会给施工建造带来困难,从而降低了效率,增加了成本,这往往是资本和市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从吴良镛的北京菊儿胡同,到王澍的杭州南宋御街,再到马岩松的北京泡泡胡同(见图9),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马岩松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中绿地率和空地率不应该只算二维平面,而应该把三维立体中的空间都计算在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早在柯布西耶提出的建筑五要素里,就已经蕴含了立体空间的理念。如底层架空进行连续绿化以及顶层建空中花园等。这样做既可以保证城市在集约化要求下的高密度,又能鼓励人们推广立体绿化、空中绿化和屋顶绿化的积极性。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好想法真要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因其牵涉面太广,立法、行政、规划、城管、消防、园林、环保等方方面面都要顾及。这是王澍、马岩松他们永远解决不了的困局。当然,这还涉及到两位建筑师的作品能否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们的建筑形式能否得以推广的普适性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未来已来,在当今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建设浪潮中,城乡规划、城市环境设计和建筑等依然各为其主、各行其道,它们之间少有交集,更谈不上共商城市建设的百年大计了。城市建设的蓝图在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的手里,你描一笔我添一划,似乎永远是一幅未成形的、杂乱无章的涂鸦。只有什么时候当他们心平气和地围坐在同一张圆桌边,甚至他们身旁还坐着其他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政府官员、开发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区工作者、环保人士、普通市民……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把城市建设作为从总体到具体的一篮子工程来协商、协调和协作,那么,城市作为一个和谐整体的理想蓝图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山水城市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