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外国人和他们眼中的中国驴子
文_钱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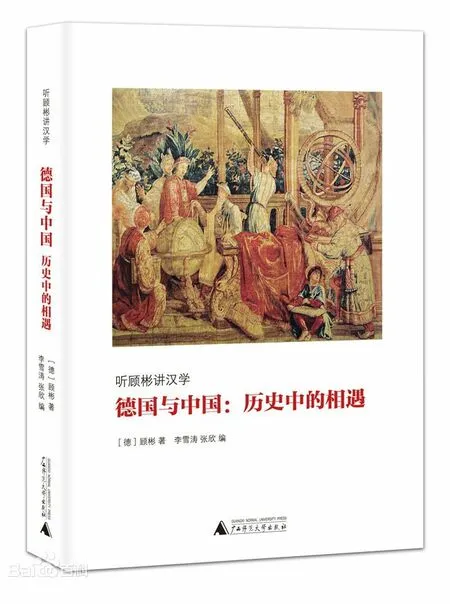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在他的著作《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中,讲述了一段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行奇遇。
1972年的一天,来华拍电影的安东尼奥尼游走于北京街头,无意中看到一头驴,大概当时的欧洲城市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畜力动物了,这位导演便顺手将它拍了下来。
没想到,这一行为引起了不小的重视,当时有人认为,驴没有什么好拍的,驴只代表落后。经过一番研究,安东尼奥尼不能继续在中国开展摄影工作,他被送回了国,而且不允许再来。
后来,顾彬本人也因在中国街头拍驴子被询问,对于像他和安东尼奥尼这样的外国文艺工作者,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应当正确、真实地反映中国。
顾彬讲的这两个故事收录在本书《布莱希特与中国》一章,他在文章开头开明宗义地说道:“近些时候,我常常阅读和研究布莱希特的诗歌,因为他受到了《道德经》的影响。”
他本来想研究中国文化对德国诗人的塑造,却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中国形象也可能是我们(指西方作者,笔者注)创造出来的,与中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些形象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于是接下来他讲了自己和安东尼奥尼与驴子的奇遇。
故事发生的年代,我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充满审慎,怕他们不了解自己,也怕他们了解得太多,更怕他们歪曲了自己。
然而在12年之后,随着时代更替,我们主动邀请了一批“批判资本主义非常深刻”的美国作家来华,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中美作家会议。这批“可靠的友好人士”包括托尼•莫里森、加里•斯奈德,以及大名鼎鼎的艾伦•金斯堡。
没想到,这场会议,最终也促成了另外一场奇遇——“金斯堡原本期望看到一个革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结果看到中国正在全面学习西方,感到不满,强烈要求要接触中国更淳朴的地方。”(《金斯堡1984年在保定:“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小小老百姓”》)于是,金斯堡选择在中国多呆两个月。
他深入大学和街头,尽可能详细地去了解这个他印象中的东方国度,所到之处,但有感触,便整理成诗句。但最让人不解的是,金斯堡的这次中国行,也与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保定的街上,他看到有很多驴车,甚至在大学校园里也看到了驴,于是他给驴写了一首诗,在里面尝试跟驴说话,给当时陪他游览的中国大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作者顾彬
金斯堡的中国行,赋予他许多灵感,在中国访问期间,他著作颇丰,写下了包括《读白居易抒怀》《北京偶感》《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等在内的大量诗句,并于回国后写下《中国记行》一文,发表在报纸上。
在《北京偶感》一诗中,金斯堡坦言:“我写诗,因为埃兹拉•庞德告诉西方青年诗人要关注中国的文字和书画……我写诗,因为庄子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人,因为老子说过水向山下流,因为孔子说过尊重老人……”
对于金斯堡笔下的中国形象,学者张剑的看法与顾彬十分相似:“他书写的是东方内容,探讨的是西方议题。因此金斯堡的中国仍然是想象的中国,是为特定目的建构的中国。”(《〈北京即兴〉、东方与抗议文化:解读艾伦•金斯堡的“中国作品”》)
那么,如果布莱希特和金斯堡写下的中国风物不是真正的中国形象,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形象呢?
近年来,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开始在中国走红,他们两位也倾心于中国形象,吉尔伯特在一首名为《冬夜》的诗里写道:“今夜我正在取水/猝不及防,当看到月亮/在我桶里,我醉心于/那些中国诗人/和他们无瑕的痛苦。”
而阿多尼斯,则将其2018年游历中国时的灵感写成50首诗,并结集成《桂花》在中国出版。在《永恒的无常》这首诗里,他写道:“在文学院,我常常看到/窗户在追随鲁迅的脚步,/看到鲁迅在阅读他的读者。”
这算不算真正的中国形象?
顾彬引用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话说:“哦,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两者没法相遇。”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也曾在其代表作《伊斯坦布尔》里引用过这句话,帕穆克自言,生长于地缘交汇的土耳其,他一生中都在感受两种文化的碰撞。
如果东西方无法相遇,为什么吉尔伯特和阿多尼斯能得到我们的认可?答案正是我们当初批评那位意大利导演的话:应当正确、真实地反映中国。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在面对中国这样的漫长文明时,只有西方作家的这些溢美之词,听上去才不会像是谄媚。
只是,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真实地反映自己?

安东尼奥尼

金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