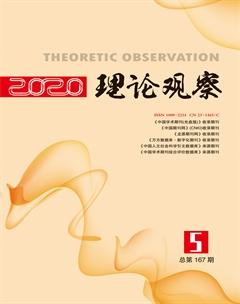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再完善
徐娜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义务;审查义务;网络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4 — 0118 — 03
一、问题的提出
(一)《民法典(草案)》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比较
首先,是完善了 “避风港”规则的通知规则。一是增加了错误通知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二是细化了权利人行使通知权的要件,即要求权利人在发出侵权通知同时应当提供其真实身份信息和初步证据。三是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转送通知和声明的义务。〔1〕《侵权责任法》对此并无规定,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即仅在网络用户主动要求提供通知内容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才会提供;而《草案》则明确转送通知和声明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
其次,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避风港”规则的反通知规则。《侵权责任法》第36条只规定了通知规则,没有规定反通知规则,司法解释也无具体规定,仅在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6条中有关著作权网络侵权时规定了反通知规则,造成了通知规则和反通知规则在立法层级上不统一。而《草案》第1196条增加了反通知规则,网络用户有权主张自己不存在侵权行为,该规定实质上是为了网络用户与权利人之间进行平等对抗提供途径。
最后,是扩大了“红旗规则”的主观适用要件。《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中“红旗规则”的主观要件为“知道”。有学者认为“知道”包含“应当知道”;〔2〕部分学者认为,若包含“应知”实质上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行为负有事先审查义务,这是不正确且无法做到的。〔3〕为了定分止争,《草案》第1197条则明确将“红旗规则”的主观要件扩展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无疑是扩大了“红旗”规则的适用范围,为权利人提供广泛的救济途径。
(二)《民法典(草案)》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掣肘
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或是收到侵权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损害扩大的情形下,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侵权损害远超过预防成本,则不能因为侵权信息过多而免除在未通知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4〕《草案》第1197条的规定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但是,在未通知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何种注意义务,《草案》未做明确规定。
网络侵权进入到已通知阶段,通知人和声明人提供侵权信息或者抗辩信息已经明晰,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初步证据具有审查义务,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积极、主动地审查初步证據的义务;如果有,当其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审查义务,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重新设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理论基础
(一)未通知阶段预防义务设定的必要性
1.权利行使之限度
有观点认为在网络上上传视频、音频等行为是自己的权利,如果在未通知阶段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预防义务会影响其言论自由,与推动网络信息自由发展的趋势相悖,可能会阻碍互联网发展。〔5〕“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根植于人的自然倾向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吧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6〕网络用户是有发表言论等自由,但其享有的自由不应当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并且未通知阶段的预防义务而不是对所有信息逐一核查,仅在特定情形下预防侵权,并不存在危害言论自由的可能性,设置预防义务是必要且合理的。
2.域外经验之镜鉴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著作权侵权并不负有审查义务,但是,在面临隐私保护和重复的、大规模侵权时,有责任去审查标准技术措施或者终止侵权人使用网络;《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但是当成员国为了监测和阻止非法活动可要求其预防或者终止侵权行为。〔7〕其实,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复制、发布以及传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该规定虽是从公法层面的规定,但也间接说明在私法层面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也有能力预防某些网络侵权行为发生。
(二)已通知阶段审查义务设定的合理性
1.遏制通知规则滥用
《草案》中明文规定网络用户应当对自己的身份信息以及发出的侵权通知或不侵权声明提供初步证据,但并未明确是否需要对初步证据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应当及时对初步证据进行审查。首先,《草案》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权利人提供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这实质上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审查权利人提供的初步证据的义务。其次,若仅审查权利人提供的初步证据,而不对未侵权声明加以审查,网络用户只有等待权利人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起诉的合理期限经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才会终止必要措施,此时,不侵权声明的本质无异于用户反馈机制,不仅浪费了网络用户收集关于未侵权声明初步证据的时间等成本、诱使权利人滥用侵权通知来拖延维权程序;还会导致权利人和网络用户间利益失衡,网络用户的正当权利无法得到主张,有失公平。
2.初步证据性质使然
对于已通知阶段进行审查的合理性基于审查初步证据负担较轻。一方面,审查对象明确,无需网络服务提供者再去收集证据,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依据危险源理论,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离侵权危险源更近,所以其对于网络侵权的类型、具体形式更加熟悉,更容易判断初步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而依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或者解除必要措施。鉴于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审查义务避免了审查结果的再周转带来的不便,节约成本,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重新设定
(一)未通知阶段预防义务的设定
1.预防义务设定应采用“善良家父”标准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具有专业的技术支撑,充足的网络经验,所以未通知阶段注意义务标准应当与其危险认知能力和预防控制能力相适应,建议以“善良家父”标准来设定未通知阶段的预防义务。“善良家父”标准是法国认定侵权责任承担的一种标准,其要求:“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8〕可见,“善良家父”不是一般谨慎的普通人,而是一个精明、谨慎如家父般的人,注意程度只有达到精明、勤谨家父的标准才可不成立过失,不承担责任。〔9〕具体到网络侵权,应当综合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水平、行为类型、权利客体情况来设定具体的预防义务。
2.具体设置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单纯提供某一种服务的甚少,将服务类型作为预防义务设定的考量因素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未通知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义务的设定应当考虑其技术水平、行为类型以及权利客体。
首先,由于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实力存在差异,而技术水平与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侵权行为发生的能力密切相关。技术水平越高,对侵权行为的预防控制能力越强,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的预防义务越高。
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义务的设置需要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类型来设定。网络服务体用这行为类型主要包括以下: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关键词销售以及设置榜单等。针对上述行为类型的预防义务设定应当根据人为干预因素具体衡量。对网络内容干预越多,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义务越高;反之,预防义务则越低。〔10〕例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通常都是网络交易信息内容的制作者,并从交易信息中直接获利,故其预防义务更高。提供关键词销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可能实施重复侵权的主体或是对极易被侵权的热播作品,应当相应地提高预防义务。在“爱奇艺诉今日头条关于《老九门》独播权”一案,因为涉案作品是国家发布预警通知的热播剧,今日头条应当提高其预防义务的标准,并且本案中网络用户上传的内容直接使用了电视剧名称,并有“福利”、“抢先看”等字眼,侵权信息极为明显,通过关键词搜索很容易被发现并阻止上传,故认定今日头条侵权。
网络侵权类型各异,不同权利客体的侵权判断难度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以判断侵权难度为标准,判断侵权难度越高则预防义务则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判定网络用户是否侵犯专利权等通常需要具有专业人士的专业技术背景支撑,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不具备相应的素质,所以设置高标准的预防义务不符合经济效益;相对于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肖像权等判定则更容易,预防义务标准设定的越高,网络侵权的可能性越低。
(二)已通知阶段审查义务的设定
1.审查义务应采用“权利、义务对等”标准
审查义务的设置应当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本身的利益与直接受其影响的网络行业的发展,过重的审查义务不仅会使得该审查义务形同虚设,同时也会抑制网络经济的整体发展。“权利、义务对等”标准要求網络服务提供者在已通知阶段负有的审查义务以其享有的权利为限。在已通知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有采取或者终止必要措施的权利,所以审查义务不宜过重,不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扮演法官角色,来履行“裁判”的职责。
2.具体设置
应当先进行身份信息审查。因为网络空间通常具有虚拟性,考虑到权利人或者网络用户真实身份可能难以认定,增加了认定侵权主体的难度,所以应当先就权利人和网络用户所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查,审查通知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等材料是否齐全。当身份信息缺乏必要材料的,造成难以确认真实身份,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终止或者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并且有权拒绝转送通知或者声明。但是,允许权利人或者网络用户再次补充或者更改材料。
身份信息被认证后,进行审查初步证据。初步证据的审查范围应当仅限于通知人和声明人提供的内容,对于侵权通知,应当提供“侵权证明,账号、用户名等能够定位侵权网络用户的信息、侵权内容链接等可以定位侵权内容的信息、构成侵权的证明材料(如书面说明)等,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还应当包括权属证明,如权利证书等。”〔11〕针对未侵权提供的初步证明材料因具体的侵权类型不同,所以提出的抗辩理由也不具有类型化,应当结合具体情形提供有力的未侵权证据。初步证据的证明力只要达到证明侵权不存在的盖然性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可自主决定是否对疑似侵权链接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对于缺少必要证明材料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认定该侵权通知抑或未侵权声明无效,进而拒绝传送,且采取或者解除必要措施。
四、结语
伴随着网络科技水平的发展,网络传播速度加快,互动性与开放性也愈来愈强,网络侵权影响力极大,确保在不阻碍网络发展的前提下,应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分为未通知阶段的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审查义务,为其各自设置相应的标准,加强对网络侵权事前防范和事后保障力度,平衡各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
〔参 考 文 献〕
〔1〕 杨立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则检视〔J〕.法学论坛,2019,(03):89-100.
〔2〕 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3):123-132.
〔3〕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理解与解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02):03-10.
〔4〕 梁志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法规制模式〔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02):100-108.
〔5〕 崔国斌.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J〕.法学研究,2013,(04):138-159.
〔6〕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305.
〔7〕 谢光旗.普遍与特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审查义务〔J〕.西部法学评论,2013,(03):71-77.
〔8〕 罗结珍.法国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5.
〔9〕 刘桦.“合理人标准”在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中的适用研究〔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81-85+90.
〔10〕 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01): 78-88.
〔11〕 宁园.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证明材料审查义务的设定〔J〕.科技与法律,2019,(05):88-94.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