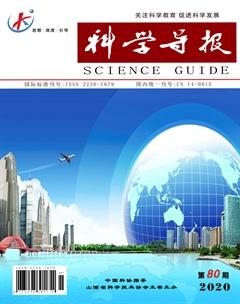温故而知新
【摘 要】“温故而知新”是每一位学子都应秉承的求学原则,如今中国舞蹈作品的创作数量已达顶峰,但质量是否也匹配顶峰之高却有待商榷。埋头苦苦创作之余回顾经典,用当下视角品鉴“故作”,或许会有“知新”待以开启。以《红河谷序》为例,突破了少数民族舞蹈只为抒情的局限,在苏自红的手中成为谱写家国大义的法宝。通过对其深度阐释,求得“巨人肩膀”之上更高远的发展。
【关键词】《红河谷序》;中华民族共同体;军民一家亲
一、“存异”但守“求同”情
男子群舞《红河谷序》是2004年苏自红老师带领学生去青海玉树采风后所编创的经典作品,它不同于之前创作的《牛背摇篮》是对轻松活泼的藏族小女孩生活的灵动刻画,《红河谷序》传颂的更多是家国情怀,将最终的主题升华到引领民族精神的更高层面。从藏族老阿爸救助小红军的情节中渲染出伟大的民族情与军民情。
(一)形象“求异”
苏自红老师在编创中选用的主角双方分别是来自藏族地区的老阿爸,与非藏族的红军小战士。“存异”首先便表现在人员配置上的民族归属不同,藏族阿爸长期生活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藏族文化的塑造下呈现出身材魁梧的外貌与包容仁爱的性格气质,而红军小战士作为“他者”在长征的路途中进入到藏区,因身材较为娇小,加之恶劣陌生的自然环境而身负重伤。二者在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凝练直观地弥补了舞蹈“拙于叙事”的弊端,在有限的剧目时间中为观众交代了人物双方的所属背景;其次,藏族阿爸的“老”,与红军战士的“小”同为“存异”,他们之间的距离除了民族的差异外还有年龄的老幼,藏族老阿爸的温情与救护之恩在红军小战士的稚嫩与幼小下显得更为深厚与感人,由此一种父爱如山的情感与气质便油然而生,这种情感不需要过多的诉说与谱写,仅仅从形象设置对比中便可显现。在彼此的衬托下,藏族阿爸象征着藏族人民的朴实与仁厚,红军小战士也展现出革命战士不分老幼坚持抗战的决心与抱负。因此,其中“求异”的目的便是为了在丰富舞蹈剧情需要的同时,表现出不同民族在战争面前守望相助,超出了民族文化信仰的界限,在更高一层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凝结一心。
(二)情感“求同”
“存异”之后便是为了更好地“求同”。无论是藏族老阿爸还是红军小战士,他们虽是舞蹈作品中创作的角色之一,但是背后的象征意义却不仅限于舞台呈现的老幼互助的形象之上。藏族老阿爸是对藏区无数帮助红军长征的民众形象的凝结,他们是藏族人更是中国人,他们居住于青藏高原之上,他们更是居住于中国的领土之上,他们与红军战士之间割不断的是五千年来的血脉相承,理不清的是中华民族自史以来的历史征程,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归属与凝结点——中国。
二、《红河谷序》中形式对内容的反哺
舞蹈的构成要素总是以内容与形式为搭建点,如果内容是舞蹈作品呈现的血肉精神,那么形式便是撑起整个主题的骨骼构架,因此对于一个完整的舞蹈作品来说,形式要服从于主题内容的安排,但是又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毕竟形式是外部呈现,是观众探知作品的切入点,对深入了解作品的内容与精神起到了指导与引领作用。
(一)双线结构的交相配合
《红河谷序》的结构可以看做是两条主线通过交织达到交响效果,一线是以藏族老阿爸與红军小战士构成的双人线,主要以故事情节的方式贯穿始终;二线是以男子群舞所塑造的群舞背景线,主要是衬托和渲染双人一线。群舞背景线是以辅线或是虚线为结构缠绕于双人舞的实线之上。在引子与第一段中群舞的背景虚线是对外部环境的塑造,引子部分以横向“S”线型表现雪域高原的连绵起伏,真实再现了青藏高原之上的地势艰险;第一段中群舞线又化身为暴风雪与洪水穿插于双人舞之中,为双人舞中老阿爸与小红军动作上的“聚合”提供了分离条件,更在情感中渲染出在老阿爸在恶劣自然环境下救助小红军的伟大精神,将西藏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以群舞辅线的形式勾勒的栩栩如生,虽是辅线但不可或缺。
第二段中的群舞辅线一方面化身为牦牛的形象,交代剧情环境已是回到了牧区的安全地带;另一方面也是双人舞内心情感的外化,在脱离危险后整个语境的轻松与欢快不仅通过双人舞进行展现,更多的还需要借助群舞的整体氛围进行加强,让重获新生的激动之情通过群舞力量传递到舞台的每一个角落,达到观众与演员、观众与编导在舞蹈作品形式之上的对于作品精神的契合。因此在以交代故事情节与宣扬主题精神的双人舞实线之上交织缠绕着对于外部形象与内在心理情感的外化虚线,二者在交相配合之中充分发挥了结构形式在《红河谷序》中的独具匠心。
(二)力结构对内容的阐释
“说到人类的行为,其运动具有的表现性质总是与他们传达的意义绑定着。”[1],因此理解与阐释主题与人物活动的基础便是从运动的表现性质,也就是动作作为出发点。动作是舞蹈的元素构成,是形成舞蹈的最小组成单位,也是最为繁杂与基础的部分。
1.老阿爸救助小红军
在老阿爸救助小红军部分,场景设置是在自然环境险恶的青藏高原之上,地势崎岖,空气稀薄,暴风雪的侵扰等都是外部条件对这对老弱搭配身体极限的挑战。开场第一个双人舞接触便是小红军战士“挂”在老阿爸的后背上,身体重心以及动作的力走向都处于下坠状态,而老阿爸双脚坚实踏地,手握双拳,脊椎直立,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向上“支”起小红军,虽然造型中的动作属于静止状态,但是力走向清晰明确,负伤小战士向下的力被老阿爸向上的对抗力所撑起,以确保二人屹立于高原之上,不惧自然与危难,由此通过表层的力结构反射出情节与人物的开场设定。接下来的救助舞段中,多是以二人的托举为主,红军小战士多以“靠”、“倚”、“趟”、“滚”等力走向向下的动作诠释自身的虚弱与对老阿爸急切的需要,老阿爸的动作成为二者双人舞中的主力与主动部分,根据情节对人物的设定,老阿爸的动作多是以“拉”、“抗”、“背”、“搀”等为主,动作的力走向持续向上且力度较大,如此才可以与小战士所表现的表层力结构动作的搭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完成对小战士的救助情节。
除此之外,两者之中还有一种隐性的吸引力是二者可以完美配合的关键,这种吸引力是透过二者心理间的互动而反射于动作的表层力结构之中。老阿爸一心想要救助小红军,小红军也一心想要求得救助,这是人性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所做出的正常生理反应,尽管由于各种外部条件使得老阿爸与小红军战士的双人舞一次次被分割又拼命的聚合到一起,以及小红军因负伤而呈现出与老阿爸相反的力结构走向,但是二者心理的隐性吸力却依然成为二者可以合力形成双人舞接触的动力之一。这种隐性的吸引力像磁铁一般,尽管外部环境艰险,使得二者相互分离的阻力再大,可是隐性的磁场力却为二者合力相触提供了合理的心理解释,呈现出人性最深处对“善”的渴求以及对“生”的希望。
2.老阿爸安抚小红军
第二段的场景设定回到了藏族同胞的生活区,第二舞段相较于第一舞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背景音乐从慷慨激昂的悲歌式伴奏改为悦耳的钢琴独奏,动作的幅度与力度也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据情节设定可知此段是对红军小战士心灵的抚慰,因此动作表现为脚尖轻点地,双手慢慢张开向空中旋转,以及藏族舞蹈中常出现的典型撩手等动作为主。在第二舞段中较少出现双人舞的接触技巧,双人舞由第一段力的不断聚合变为二者分别以各自独立的力为支撑各自行动,但是二者之间依旧存在着互动关系,例如小红军模仿老阿爸跳起藏区传统舞蹈,以及小红军俏皮的缠绕在老阿爸身边等等。此时的力由第一段隐性的“吸引力”变为“伴随力”,小红军对老阿爸依赖的心理力始终跟着老阿爸而随动,贴合了主题对于人物情感与关系的设定。
《红河谷序》中的动作通过“反哺”内容,更加明确了其中人物形象的设定以及段落之间所形成的强烈的差异对比,在舞蹈作品仅限的时间中充分交代了人物性格、事件发展,同时还从心理学角度呼吁关注遭受重大创伤人群的心理建设等,并且突出了民间舞蹈的心理治疗优势,最终将主题中心高度落在了军民一家亲、民族团结互助走向美好生活的政治高度之上。充分诠释了动作来源于生活情节,却又在艺术创作中“反哺”情节的创作手法,使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达到了新的创作领域与高度。
三、“以小见大”的主题升华
舞蹈艺术自古以来除了在形式上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视听觉盛宴以外,对于人们思想的集大成以及社会精神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当下舞蹈作品的选题日益成为决定舞蹈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主题立意新颖、激发观众的兴趣,同时还要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通过舞蹈这种艺术形式传播当下社会倡导的思想意识,以一种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的规范引领民众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红河谷序》在主题的设定方面统筹兼顾,即从微观生活而入,从宏观社会价值而出,做到了群众思想与国家意志的集合统一。
(一)藏族阿爸红军战士的“小”情
从微观直面主题我们最先感触到的是老阿爸奋不顾身在雪域高原极其危险的自然条件下救助受伤的小战士,老阿爸伟大的慈父光辉在舞台之上屹立不倒,这样的父爱超越了亲属与血缘关系,是藏族民众一心求佛向善的感召力迫使他们在危机面前临危不惧,爱与包容飞跃世界屋脊蔓延于整个中华大地。大自然之下人类的渺小与无助与老阿爸舍生忘死的精神形成了反差性对比,在雪山映衬的小小的身躯后是无边无际的爱与善的光辉应和着他,“藏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向他们致敬。
从舞蹈选题出发,老阿爸救助小红军或许不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在中国民族百年的奋斗史上出现过无数感天动地的事件都值得我们顶礼膜拜。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小”情在艺术作品创作中突破了观众心中的情感防线,在人们内心深处藏匿的爱与包容上撕开了一条口,观众的真情流露与作品的主体相会贯通,这来自于民众生活的“小”情与“小”爱成为最终猎取观众好评的关键支点。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情
《红河谷序》的主题与人物设定皆非巧合,而是故意为之。为何不是父与子?而是老阿爸和小红军;为何不是同属藏族的老阿爸与小孩童?而是藏族老阿爸与红军小战士,这是苏自红老师将家国情怀之“大”情注入于“小”角色之中后赋予的意义所在。藏族老阿爸与红军小战士的组合一方面是汉藏两族相扶相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例证,不需要多么宏伟的宣言还是保证,不需要政治色彩的过多渲染,只是最简单、质朴的相携之情便成为群众的表率,用肢体语言感化着藏、汉两族以及众多少数民族同胞凝结一心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藏族老阿爸与红军小战士除了跨越民族的差异性之外,他们身份归属中的群众与士兵是另外一层象征意义,军民的团结互助一直是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群众是国家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才可结成最有力的盾牌。在此苏自红老师一反传统作品中“兵领导民”、“兵解放民”的创作思路,而是让“民救助兵”,这种翻转磨平了民众与军队在普通意识上带给我们的强弱差异,更加突出的是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协作,将军与民紧紧地捏合在一起,突破界限差异,在更高的国家精神意志层面达到统一,这不仅为文艺创作的主题立意提供了新的反结构构思,更是刷新了群众对于红色革命舞蹈的新认识。面对于文艺受众仍是广大群众,这种新思路更加激发民众当家做主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军民协调共同发展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意义所在。
(三)峥嵘岁月走向黄金时代
《红河谷序》从开篇第一段的老阿爸在艰险环境的重重阻击之下救助小红军,到第二段的藏族牧区内安抚小红军,助他重建生活信心,奔向美好生活。这看似是对小红军从肉体到心灵的救护,实则在挖掘更深层涵义便可知其后也隐喻着中国从弱到强不断奋斗的艰辛历史。第一段中的“雪山”、“洪水”、“暴风雪”等自然灾害的符号都指向的是中国革命一路走来遇到的各种磨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制决策与勇于献身精神的引领下我们才可化险为夷。在《红河谷序》安静美好的牧区生活下隐喻着当下生活的幸福与美好,但是在第二舞段小红军与老战士的交流互动中同时告诫我们要牢记历史与每一位为建设新中国而辛苦付出的人。如果说小战士是对革命中国的隐喻,那么老阿爸就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伟人与英雄。
最后红军小战士两次在和缓的乐声中敬礼,坚定的眼神注视着远方,凝望着新中国美好的未来,他的祈盼与祝福不仅仅属于他,而是全中国对新生一代共产党人所给予的希望,青年一代终将接过建设新中国的火炬,奔跑着属于他们的时代。结尾处老阿爸托起手指远方的小红军,那是老一辈的革命者托起了中国的新希望,他预示着每一代的新星都应当负重前行,在祖祖辈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做出属于自己时代的丰功伟绩,开创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
站在今天回观《红河谷序》,它的创作历程又成为我们今天凝望的历史。在商品时代下去品味《红河谷序》更加意味深长,时间的浪潮淘洗着它,而经典就是在大浪过后依旧亮眼的明珠,始终为当下的舞蹈艺术创作提供着指导实践意义。如今,众多新创的舞蹈作品像是售卖的商品,外表光鲜亮丽,试图通过制造视觉的饕餮盛宴来弥补自身文化精神内涵的空洞与匮乏,浮躁与快节奏成为当下每一个城市人的通病。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上,“多”、“快”日益成为艺术输出的标准范式,无顾于百姓与人民,在自己的臆想中“闭门造车”,作品与社会群众严重脱节,无数作品被编导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那么,如何让中国舞蹈艺术走出困局?或许只有走下“象牙塔”,舞進群众内心才能让舞蹈艺术重获新生,在群众中找到艺术应当获得的价值与标准,让文化自信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的驱动力。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2]朴永光.《舞蹈文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注释:
①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
徐嘉怡(1996.02.12),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舞蹈学,研究方向:舞蹈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