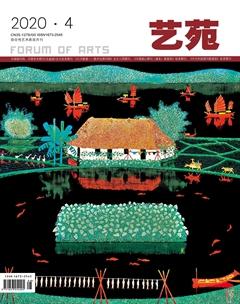家国观念与文化认同:国产“年代剧”《老酒馆》的文化分析
【摘要】自21世纪伊始的《大宅门》之后,逐渐出现一批基于清末民初时期,从一个家庭、家族、行业的兴衰等角度進行史诗书写来映射整个时代变迁过程的“年代剧”。也正是因为清末民初的动荡多变格局和民族存亡之际的历史背景,使这个时期成为表现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典型题材的蓄水池。本文试图以2019年国产“年代剧”《老酒馆》为例分析“年代剧”所具有的史诗风格、平民英雄、家国同构、个体集体的复调弥合等的典型特质。
【关键词】 年代剧;《老酒馆》;文化认同;家国同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年代剧”的概念最初产生于港台影视行业中,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末,具体是从服装上像区别于当时正火热的“古装剧”和“时装剧”,也就是从服饰的古代传统和现代新式的角度来区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年代剧”从服装上指的就是从古代传统的古装到现代新式服装的过渡阶段。从时间上划分,广电总局将剧集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年代剧”的表现内容对应近代时期,具体来讲的时间段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虽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事件划分上有所重叠,但在内容表达上各有倾向,虽然都是表达家国命运,但“年代剧”更具生活烟火气息和史诗风格的交叠色彩。“年代剧将家族内部男女情感纠葛与家族跌宕命运融于特定时空跨度的历史长河之中,通过多层次、相互关联的情节线展现特定时代的人物情感与家国情怀,满足多层次受众群体的观赏需求。”[1]20因此,“年代剧”中的史诗与传奇风格的编年体叙事、家国同构的深度情感指向和悲壮格局,以及个体精神与集体价值的复调狂欢,是营造出观众群体对“想象性共同体”认同的内在文化逻辑和生成机制。
《老酒馆》讲述了以陈怀海为领头人一帮人因为妻离子散的意外而被迫落脚日伪政府统治下的大连,经营“山东老酒馆”谋生计,作为一个典型空间“大连街、老酒馆”成为了各色典型人物、各方信息汇聚的焦点,呈现了1928年到1949年家国命运的风云变幻,其中的人情味、民族义、国家感等价值指向是唤起后现代社会下观众内心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意义生成机制。
一、史诗和传奇特质与平民英雄像下的价值认同
史诗风格是“年代剧”叙事风格的典型特质。所谓“史诗”是指一种严肃庄重的叙事长诗体裁,一般是歌颂叙述民间传奇、英雄事迹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的典型文化符号就是民族、国家、宗教等等,以此凝聚集体性的精神意志,具有仪式和认同的等典型文化属性,最初的史诗就是在仪式活动过程中口口相传来完成对其的继承发扬。如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等。可以说“年代剧”就是放在电视上的视觉图像化了的影像史诗。《老酒馆》中当陈怀海一众人开业“山东老酒馆”之后,以人物的命运走向、人物关系的发展、各个事件的串联等等完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变迁的描摹。作为“近代题材”的一种,“年代剧”虽然关乎历史,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历史只是“年代剧”的背景,“传奇”才是它的内核。[2]54“年代剧”中的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了清末民初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段时间中动荡不安、内外交困的家国命运和在动乱中逐渐以小喻大、献身救国的平民或草根英雄形象。《闯关东》中的朱开山;《大宅门》中白景琦、白颖宇;《大染坊》中的陈寿亭;《走西口》中的田青等无不是个人的事业线索与国家民族的史诗线索互文呼应,在见证家族和事业的兴衰也是国运的兴衰,由此传递出一种史诗传奇的崇高悲壮感。
《老酒馆》也不例外,剧中陈怀海是一个打破了“克里斯马式英雄形象”的平民化、草根化、身份化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嫉恶如仇、深明大义、重情坚韧,不惧危难,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当民间抗日英雄“老北风”被日本追杀,逃至老酒馆时,陈怀海不惧引火上身将其藏在菜窖里,之后再老警察暗中帮助下有惊无险地逃出城去;他帮助马旅长戒掉烟瘾、接济钱粮,赶去土地庙救他、将其藏在炕柜里保其安全,用情和义打动马旅长再次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之后与日本浪人决斗、痛斥满清遗风,并在谷三妹的配合下将“老酒馆”变成地下交通站,让其女儿成为抗日交通员。一系列故事情节体现出英雄式的形象塑造,剧中其余的贺义堂、老警察、谷三妹、三爷、杜先生、老二两、金小手等人物共同的一点就是有底线和原则,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呈现出恰切的价值指向。“民族和身份认同,主要来自于一种文化心理认同。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机器维护其政治统一,另一方面,作为想象共同体,它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确保其文化统一。”[3]469而一个文艺作品正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年代剧”通过家国和民族的史诗传奇叙事,将晚清民国时期国际国内的动乱格局复现在荧屏上,在观众观看互动过程中共完成民族和身份认同的意义生产,看剧的过程中观众被纳入到电视仪式中,完成意义的共享。人物在故事中实则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的存在,性格是能够表征出符号所之的文化指征。“年代剧”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往往能历时性地呼应着集体的兴衰浮沉,映射出整个现实生活和时代气度的宏观变迁。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年代剧”在具体的时空内容上并非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但是其透过历史背景、人物性格和情节走向而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时代风貌与当下社会同频共振,从价值内核上来说是对当下社会出现的多元危机状态的一种弥补和释缓。剧中男主角陈怀海以及其余各个人物的命运走向其实与当前工业化的消费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体奋斗和不稳定状态暗暗契合。从最开始的被排挤、被人下黑手影响经营,到逐渐获得越来的越多的顾客、邻友的认可,再到空间转换为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并在最终走向抗日救国的崇高情怀指向,这一连串的人物命运转折、英雄形象的价值演替和意义生成,正与在市场经济社会语境中个体沉浮且最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诉求相一致,基于此获得价值认同。
二、家国同构的互文共鸣与本体安全
“以家喻国、家国同构”的创作理念在《桃花扇》《红楼梦》等古典戏曲、小说中就已存在。“年代剧”中无论是从最初的《大宅门》,到之后《闯关东》《走西口》《乔家大院》《金粉世家》《京华烟云》《大染坊》《老农民》《和平饭店》《正阳门下》《芝麻胡同》《楼外楼》《老中医》等都是以商业或家族的兴衰和国运之间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互文效应。中华民族具有很深刻的家国情怀,“家庭—家族—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从内里上来讲,与包含的宗法制度和礼制秩序其实是一致的,从最初的商周时期国家的起源就是“家天下”的观念。而家国情怀的深刻互文呈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和“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效应,由此在具体的艺术形态和作品内容中,我国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化叙事的典型文化特质和美学追求。“年代剧”作为具有深刻民族文化内涵的媒介叙事艺术形态能够召唤出观众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感。詹姆斯·凯瑞认为:“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有关……传播的仪式观旨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而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7而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一系列具有价值指向性的通约符号所建构民族和身份认同的过程。《老酒馆》剧中将“个人史”“酒馆史”和“国家史”结合起来,以家喻国、以小见大,体现出“年代剧”对“时间”在表象上基本解构的流动的同时,对于历史叙事的设计和铺排的内在话语建构逻辑。1956年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之后,山东老酒馆改名为“国强饭店”;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实行全民所有制,再次易名成为“红旗大酒店”;“文革”时期改名为“防修饭店”;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应和时代,改名为“环球美食中心”;到了2013年的现代化社会后,改回“山东老酒馆”。店名的变迁和更替也表征出每个时代的特色,建构出家国同构的时代语境。《老酒馆》作为近年现象级的国产“年代剧”之一,不仅是对历史语境的复现,还是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主观艺术化的升华,是对历史观修订的一种尝试。家国同构的叙事过程中彰显出更深一层的文化主旨,建构出虚拟同在的电视空间,召唤出观众群体中类似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价值和思想观念,不仅指向剧中的历史语境,更会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而照拂当下。
在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中,每个成员因为工业化、消费化的文化语境而被异化为社会机器运行过程中一个原件,进入到一种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导致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的缺位,由此会产生诸如“怀旧、复古”的典型后现代个人情结。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中说道:“怀旧是一种创造性的情绪,也是医治时代心理症候的偏方。”[5]399可以说,“年代剧”中所展现出来的“家国同构”和“民族—国家情怀”就是对现代性不安全创伤的一种慰藉,也是在集体无意识层面的通过情感的召唤和补充将过去的历史置换为指向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期冀。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愈加强烈,愈加能够感受到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年代剧”体现出的以家喻国的创作理念非常契合现代观众的期待心理,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年代剧”侧重观察普通人物跨越历史时空的世俗生活,书写不曾被革命、战争岁月所割断的凡俗个体的欲望与营生。以一种动荡的个体记忆与经验方式,慢慢折射出乱世浮生的张皇失措与社会主体性危机。[6]61
三、个体—集体的复调与错位叙事的私人情感
(一)个人—集体的复调弥合
剧中通过多个典型人物的塑造,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的演进过程中体现了该剧内容在现代化社会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复调弥合。酒馆掌柜陈怀海和民间高手金小手之间多次过招,后者在被暗中“剪衣角、沾白灰”等之后自愧不如。由此金小手感慨道:“自己看了大半辈子戏,没想到自己也在戏里。”金小手自恃清高,本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却被陈怀海的以德报怨和仗义出手而打动,明确表示对陈怀海个人品格和他所代表的酒馆集体价值的叹服,二人随即结为异姓兄弟、互示敬重,在之后的剧情中危难的时刻二人也都曾为对方出手救急。陈怀海这个人物的崇高、悲壮的英雄气概象征的是集体性的宏观性的民族精神,但是却是从最细节、细腻的情感流露中体现出来的;在叙事伦理中也凸显出来这个人物的善良、正义、有担当、有魄力、敢于正视非正义。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剧中充分地展示出人物“不惹事、不怕事”和“敬人者恒敬之”的人际关系。
老二两在剧中是陈怀海等人的长辈身份,为表对其尊重老酒馆赠送菜品,但老二两拒绝赠送,并且说不能占小便宜,否则会吃大亏。老二两的角色设定外在上来看很像鲁迅笔下在咸亨酒店吃酒的孔乙己,但是不同的是在内在的情感设定上,老二两是一个宁折不弯的角色:他堅决不受嗟来之食、每次喝酒只喝一个小时、提醒陈怀海等人做生意要讲求诚信、拒绝酒馆众人为其雇车而坚持走路回家、坚持登门捧场,等等。虽然他颓败潦倒、年迈体衰、腿脚不便,但这种气度和风骨才是这个人物的符号价值,这是一种非功利的重情义轻利益的呈现,也正是目前消费化社会中所缺失的处世原则。此外,陈怀海在伙计们都担心赊账要不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们要尊重每一个客人,评价那爷不是不讲原则的人,他视磨刀匠与常规客人一样将其请入酒馆;而那爷教贺义堂做生意,可以赊账,先把人气拢住,等等。
上述的这些在剧中所体现出来的每个人物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是中华民族集体性的文化品格的日常化书写,也就是在各种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之间的缝合过程中完成对意识形态表征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效果。剧中个体的典型性格的讲述是外显的,但是宏大的集体叙事的内在特征是被遮蔽隐匿的,但是就是在合二为一的过程中,回归到了生命体验的终极关怀,诉诸更深刻一层的伦理意味和哲学反思。
(二)错位叙事下的私人情感
剧中陈怀海和谷三妹之间从初次意外相识,到二人共同为抗日救国将老酒馆置换为日常世俗空间和地下交通站特殊空间的双重空间,之后二人组成家庭。错位叙述诉诸于发现,而不仅仅是表现,以反真实的姿态追问内在的真实,探索被遮蔽的真实,这是其最重要的现代性特质。[7]“错位叙述”的方式将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过程与显示日常中的常规伦理逻辑像悖逆,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心理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逆向、错乱的情感关系脉络抽丝剥茧式地揭露出真实的人物性格,更重要的是在“年代剧”中将从两性爱情中反映出宏观时代语境。
在《老酒馆》中陈怀海和谷三妹之间的情感发展过程是一个个意外促成。而桦子和小尊之间的爱情线的“错位”更为明显。在桦子和小尊的婚礼上,陈怀海只办了一桌酒席,请来了酒馆的老朋友们。陈怀海向小尊和桦子介绍客人时,小尊正好遇到和金小手一起来的董叔,他就是当年暗杀吉田的地下党之一,小尊立刻吓得面如土色。之后,在海边,小尊坦然承认了是自己的出卖让日特分子吉田将小棉袄杀害,而董叔在当时被日特分子暗杀时仓皇逃出,现如今小尊和日特的密谋过程大白于众人。小尊问桦子:“是否爱过自己?”当桦子说完时,小尊便纵身入海,以死谢罪。学者李泽厚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说:“所谓历史本体,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但这活生生的个体的人总是出生、生活在一定的时空条件的群体之中,总是‘活在世上‘与他人同在。”[8]这种“个体—集体”的复合的情感指征使得《老酒馆》中的男女之间的私人情感以超验的错位方式置换出社会变革。
四、结语
国产“年代剧”作为具有典型特征的电视剧作品类型,从其表现的时空维度与具体内容来看,既无须像主旋律作品那样承载较大比例的政治任务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又可以在国家和民族的维度上真切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及对社会的反思意识;既无须像历史题材电视剧那样受到沉重的历史真实压力的制约,又无须像现实题材电视剧那样接受观众的严苛真实性的评判。基于这样的策略选择,“年代剧”在主流作品与大众文化之间找到了某种现实的平衡点和切入口,在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崛起,成为一类现象级电视剧作品。
参考文献:
[1]朱静雯,欧阳宏生.2019年历史题材电视剧述评[J].中国电视,2020(5).
[2]张宗伟,齐峥峥.“年代剧”述略[J].当代电影,2009(8).
[3]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斯維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6]卢蓉.浮世生活·欲望消费·女性模式——现代性视野下“年代剧”中的文学改编价值初论[J].当代电影,2009(8).
[7]张晓现.复调与中国当代小说[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8]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张鹤炀,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