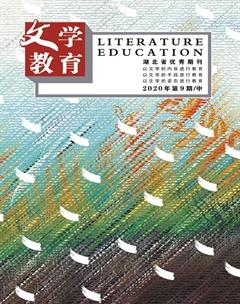论朱英诞诗歌中的“追寻”书写
内容摘要:“追寻”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书写类型,这种书写往往能穿越历史的长河在文学长廊中留下动人心弦的精神闪光点,朱英诞的“追寻”书写亦是如此,作者在诗歌的海洋中执着地寻找“真诗”,并以此为基点建立独特的诗学理想,同时,朱英诞以“梦”的幻想性为“追寻”书写插上想象腾飞的翅膀,让诗人得以在文学的世界中圆梦“母亲”与“江南”,孜孜不倦的“追寻”姿态让朱英诞思考自我与存在,从而抵达精神的家园与理想的彼岸。
关键词:朱英诞;追寻;真诗;存在
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追寻”有了不解之缘,整部文学史可以说是作家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不懈的寻找真善美、为寻找理想家园而不懈进步的历史,执着的追寻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对于隐没的诗人朱英诞来说,他在诗歌中的寻找更是如此。他的夫人陈翠芬曾说到:“整整半个世纪的日日夜夜,他的灵魂沉浸在诗的海洋里,不为名利,不计荣辱,读书,写诗,如醉如痴地钻研是他的最大乐趣。”[1]327正是这种苦苦追寻的执着精神,诗人建构了饱含个体生命感性体验的诗歌王国与艺术花园。在艺术的王国中,朱英诞寻找到了母亲,慰藉了自幼失母的隐痛:“青天老是蜷卧着/我也轻轻入梦/夜的深处是母亲,”[2]寻找到了故土家园,抚平了漂泊游子的淡淡哀愁:“寻找着乡愁的旅途/梦在裸体上漫步,”寻找到了精神的乐园,安抚了孤寂、凄苦的诗人灵魂,“历尽了崎岖的波折/我寻找着乌有之乡”,同时,朱英诞以“梦”的幻想形式为诗歌的“追寻”主题增添丰富的含义,可以说,追寻在朱英诞的诗歌中,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因此,本篇论文从朱英诞诗歌的“追寻”书写入手,以期阐释这一主题在诗歌中的含义,从而为朱英诞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一.寻找真诗—在艺术花园中构建诗学理想
朱英诞曾说:“诗,夹着田野的气息,如春风而夏雨,秋风而冬雪,点缀了我的一生,生命的四季”[3]160,如此发自生命本能的真诚热爱足以令每代读者动容。作为“废名圈”的诗人,朱英诞的一生可谓平平无奇、默默无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疏于时代与文坛主流的诗人,却留给我们将近三千多首诗歌。在朱英诞的诗歌中,“真诗”是其诗学理念的核心内容,主要指诗人真实地表达感性体验的所观、所思、所感,真挚地抒发感情。在诗人的诗学天地中,物物皆可歌咏,事事皆可抒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皆是诗意:有“才有可爱的梦/便下了快雪/如一匹快马/无籁轻轻的/驰过夜间”(《大雪散文诗》)中描绘雪花的活泼可爱;也有“凄凉如一片秋之叶的人/人影子如风/徐徐走过”(《秋日》)中抒怀寂寥悲秋之感;更有“我每每疑惑,这是梦呢/如果不是有着花木的香味/而且灯火逐渐稀少里/繁星格外的明亮了”(《沉默者》)的智性深思。在真诗的执着书写下,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如雪花、院落、晨光等之物,它们或可爱或破落或温暖,这些平凡之物经过作者陌生化的描绘,每一个都透露着诗性的光芒。不仅如此,朱英诞还在诗歌中真挚地表达情感,将个体生命的感性体验——思母、悲秋之感注入诗歌中,从而与人类的普遍情感之间产生了共鸣,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与情感深度。
对于“真诗”的不懈追寻,使得朱英诞在艺术的花园中建构自己的诗学理想。朱英诞一生创作了三千多首新诗,在这不断的诗歌耕耘中,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与指导性的诗歌理念。面对早期新诗的“稚拙”,他力主诗歌的自由与新鲜,提出新诗就是“内容是‘真诗,形式是散文”的自由诗的诗学观念。他之于新诗创作,不仅有持久的创作力,而且还有敏锐的鉴赏力。对于新诗独特的审美旨趣与艺术坚持反过来成就他“门庭冷落”但“怡然自得”的诗歌园地。在诗歌中,诗人将自己的生命与诗歌划等同,在诗性王国中追寻到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于“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朱英诞来说,诗歌赋予他超越现实生活的力量,让他得以挣脱现实的纠葛,走向人类生存更高的境界——在艺术的王国中找到灵魂的栖息地。因此,面向新诗,朱英诞从“真诗”的追寻为基点,建构起属于自己独特的诗学理想与艺术花园,并在诗歌的海洋中,安放灵魂,找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二.以梦为马—用幻想的形式来执着追寻
“梦”意象是朱英诞诗歌中最常用的意象之一,诗人借助“梦”意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朦胧、奇妙的幻想世界,同时,“梦”是承载幻想的最佳形式,诗人借助这一形式在文学的世界圆梦“母亲”与“江南”。
在朱英诞三千多首诗歌中,“梦”意象随处可见,可以说“梦”意象贯穿了朱英诞诗歌创作生涯的始终,朱光潜曾说:“意象是诗人性格与情趣的返照”[4]42,可以说,“梦”意象的幻想性是最适宜表现诗人沉默冥想的精神气质的意象类型。诗人借助“梦”自由地穿梭在幻境与现实之间,为我们塑造一个梦幻的世界,这里有温柔美丽的海上绮梦,也有春日美梦的轻盈灵动;有对曾经美梦的苦苦追寻,也有梦醒回归现实的怅然若失。在(《枕上作》)中,诗人这样写到:“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儿是我的家/游子是他乡的点缀/故里的情形将又是一番。”诗篇用“我”宣泄真实情感,诗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如一张白纸般纯洁无瑕,而纯洁的圣女有她圣神的归宿——天堂,但诗人自己却怅然若失,苦于不知道哪兒是我的家,如何才能回到故乡,重温故土中熟悉的场景呢?只有在睡梦中,在梦境这一切才能实现,不仅如此,梦还能将诗人带到另一个远方,在那里一切都很美好。
“梦”意象的运用在朱英诞的诗歌中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诗人之所以能执着地寻找“真诗”并建构属于自己的诗学理想,凭借的正是“梦”这一幻想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让朱英诞沉醉其中的,与其说是梦的内容,不如说是梦的形式。在诗歌《如梦》中,诗人这样写到:“有人说,人生如梦/梦?就是那些没有必要对谁述说的……不说起,却也易忘却/忘却?我也整整记得的就是这个忘却啊,梦又何妨。”“梦”虽说是一个缥缈玄幻的存在,一个无法言说的存在,但“梦”的主人却能清晰的理解梦,它是心灵的歌曲,精神的回声,因而诗人不能忘却,在诗歌的下半部分,诗人将现实与梦相联系,指出梦是现实的隐喻。另一方面,诗人凭借“梦”这一幻想的形式得以在文学的世界中圆梦“母亲”与“江南”。联系朱英诞的生平,我们可知,诗人九岁丧母,母爱的缺失是他一生的隐痛,诗人将人生中唯一的一篇自传《梅花依旧》献给母亲,足以可见作者对于母亲终生的怀念之情。国家不幸诗家幸,稍许安慰的是,文学的补偿功能得以让诗人与天人永隔的母亲在诗歌的王国中得以“相见”,“青天老是蜷卧着/我也轻轻入梦夜的深处是母亲”(《纪念早逝的母亲》),作者只有在“梦”中才能与母亲重逢团圆,“然而,年轻的母亲/永远年轻的母亲/你为什么永远在徘徊”(《杨柳春风——怀念母亲》),可悲的是,因为母亲的早逝,作者记忆中的母亲“永远年轻”,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动而自然衰老,因而作者在诗歌中发出这样的惊叹:“二十九年的惊人的过去/呵母亲,你在那里/母亲在那里/呵母亲,你并不是你”(《一日祭母亲》)。朱英诞的多首怀母诗抒发了对母亲的真切追思,这样密集的情感倾诉表现出诗人对母亲的苦苦追寻。然而,只有凭借着梦这一幻想的形式,只有在诗性王国中,天人永隔的母亲与诗人才能重逢,诗人才能追寻到记忆的母亲,才能宽慰诗人身世凄苦之感。
朱英诞诗歌中的“怀乡”诗亦是如此。朱英诞在其自传中这样说道:“我常自嘻,谓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个人却生长于津沽与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摩诘云:‘江南江北送君归,不幸,我却从未到过江南,更不必说江北的如皋”[5]542。诗人从未到达过江南江北,但可以借助“梦”这一幻想形式,重温江南山水的温柔美好,“窗口如梦着江南了/千山和万水一家家/小小的梦的乌篷船”(《夜窗》)。朱英诞还把江南、江北作为家园寄托游子的深情怀念,“我将愿望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死于怀乡病/时间渴望我们的平原和语言/哀愁着以致于死”(《乐园放逐——梦回天北望江南》)。“死于怀乡病”表明了诗人对于江南故土的真挚思念,然而,对于一生未到过江南的诗人来说,好像只有“梦”这一幻想形式,诗人才能回到美好的江南故土,才能安抚孤寂、漂泊的诗人灵魂。而“江南”对于朱英诞来说,具有双重的意味,一方面是诗人的故乡,它寄托了游子的缕缕乡愁,另一方面,江南也是诗人从而到达的远方,“我将永望着江南,远眺天空。”对于诗人来说,远方是梦想的家园,理想的彼岸,但生活是一种现时态的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生存境遇,“远方”却存在于现实之外,是现实的人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对远方的求索是一场了无终期的艰难的追寻,是对诗人心理、意志与忍耐的双重考验,但孜孜不倦追寻“江南”的朱英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诗人一生笔耕不辍、在诗歌王国中执着书写就是对此考验最好的说明。
不管是对“真诗”的执着追寻,还是在诗性王国中追寻母亲与故土江南,朱英诞这一孜孜不倦的追寻姿态定能穿越历史长河打动每一时代的读者,追寻这一行动本身就极具意义价值,更不用说朱英诞常态化的追寻。可以说,人类正是因为追寻才能抵制虚无,避免沉沦,拒绝平庸,从而走向崇高。人类从伊甸园掉落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人类不懈追寻的宿命,然而,也正是这种追寻的需求,人类才得以不断地克服困难,为寻找美好家园而不懈奋斗,人类存在才有所谓的意义与价值,朱英诞的追寻书写可以说与人类追寻命运的一个投射与剪影,从而容易与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对于个体生命的朱英诞来说,在诗歌的海洋中不懈追寻,让诗人與母亲得以团圆并重回江南故土,从而安慰漂泊游子的缕缕乡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追寻“真诗”的过程建构起属于自己独特的诗学理想,从而在艺术的花园中找到自我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1]朱英诞.冬叶冬花集[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
[2]王泽龙.朱英诞集第二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3]朱英诞.朱英诞诗文选:弥斋散文·无春斋诗[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4]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泽龙.朱英诞集·散文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作者介绍:段杰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