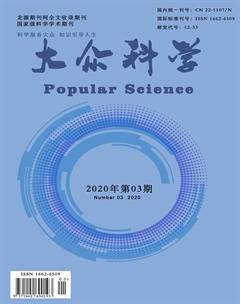浅析散文英译中“否定”之妙译
廖越英 杨丰仪
摘 要:散文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一环,一直深受各国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以2019年重印版张培基先生译作《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部分文本为例,浅析正反译法、含否定意义的词、句所采用的翻译技巧等在该散文英译版本中的表达效果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散文英译;否定转移;正反译
散文以其文辞优美而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其情感内核也同样重要。要将中国散文之神韵恰如其分地拿捏好,传达好,“字字对应翻译”显然缺乏适用性。正所谓散文“形散而神聚”,散文中的“神”在翻译过程中极其重要,因而也是难译之处。本文将基于《做一个战士》、《梦》等翻译为例,从翻译美学的解读视角,从否定转移、正反译两方面来具体分析“否定”之妙译。
否定式表达虽为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但在表情达意方面独具魅力:一方面,鉴于中文英文这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表达习惯、文化背景上的区别,否定式表达中的“正反译”可以提供翻译中的“逆向思维”法,符合目的语使用者的逻辑思维习惯,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另一方面,把握好否定修饰词的细微使用差别,能使译者更加精确地传递情感,恰如其分地保留原文的“神”,并且有时与恰当的修辞手法搭配使用,能创造出绝妙的表达效果。同时,中英两种语言中的否定表达具有一定的区别,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好“否定”的译法尤显重要。
一、否定转移
散文中的叙事性散文分为两类,偏重于记事与偏重于记人。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谈到,在对描述对象的总体情志的把握中,首先要把“凝神观照”的中心放在客观对象的形象、意象、意境体验上,然后从语言(从整体到局部)入手,将一点一滴的体验汇集到中心。可见,在偏重于记人的翻译中,译者需要精读、深读原文,把握人物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不同的翻译手段来准确勾勒人物特点。”
在巴金先生所著散文《做一个战士》中,有这样一句话:“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联系文本可以得知,“战士”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极强的意志力与崇高的精神信仰,英勇无畏,付出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来追逐着光明,而这句看似简单的“不知道妥协”该如何译才能表达出其坚忍不拔的特质呢?倘若字字对应译为“He do not know how to compromise”,则与原意完全不符,表达的是“战士不知道(要怎么做出)妥协(这一动作行为)”,涉及到的是施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問题,闹出误译的笑话。在理解了原句的意义之后,笔者脑海中自动译为“He never compromises.”,而张培基先生对此文的英译版本为“He knows no compromise.”,此句短小精悍,却能有雷霆万钧之力,效果要明显高于“He does not compromise”或“He never compromise” :“does not”与“never”均是对谓语动词的否定,强调的是战士这一主体的动作行为的“是”还是“否”,换言之,这是战士的选择(妥协还是不妥协);而“He knows no compromise.”则是将否定转移到了名词compromise上,否定宾语,即,直接否定了“妥协”这一举措的可行性,强调感更重,在最靠近之处否定“compromise”远比将否定前移至动词处更加有力量,使得战士的视死如归、坚毅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正反译
正反译法作为一种常见的翻译手段,可以确保译文语义明晰,文从字顺,而正反译法在实践中分为两种。
一种是反说正译。在《木匠老陈》一文的开头中有一句“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灭。”,张培基先生将原文中的否定副词短语“不会消灭”正译为“withstand”,即“抵挡;禁得起”,全句译为“Some memories will withstand the wear and tear of time.”,此处的反说正译在传达文章深层含义上效果极佳。原文中的“磨洗”一词表现了年岁渐长的沧桑感,但“记忆不会消灭”更倾向于客观的叙事;而“withstand”一词将“不会消灭”正译为“承受(时间的磨洗)”,将读者的眼光聚焦到“记忆的深刻性”上,使读者更能体会到那份关于木匠老陈的记忆根深蒂固,以致于经过数十年的风吹日晒依然能清晰,并带有一定的拟人化修辞效果,相较于平铺直叙一句“记忆没有消失”,更加有感染力,挖掘出了“记忆”这一事物的情感内涵,表达更加深刻、精确。
另一种是正说反译。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中的翻译审美移情要旨中写道:“译者应该沿情(原文之情)而表,做到文辞相应,情境相切,以译文造原文之境,以译文托原文之情。”,作为一篇伤感的悼怀之作,《梦》中有这样一句话:“然而睁开眼睛,我只是一个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声。”梦中亲切地陪伴在身侧的父亲、梦中美好的场景都在梦醒的一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孑然一身生活的世界,心中只留下怅然与失落。”张培基先生将此中心情熔铸在他的译文中:“When I opened my eyes, I found that I was all by myself and nothing was heard except the pit-a-pat of rain drops.”。原文“只留下”被译成一个双重否定句“nothing except(除…之外再无)”而不是“only(只有)”,在这一英译版本中,读者读到第一处否定“nothing(什么都不剩)”时,仿佛全世界都无比空洞,只留一个孑然一身的、失去了父亲的身影在读者眼前,紧接着的“except(除了)”好像给了读者一丝慰藉,原来作者并不是一无所有,而后文那句滴滴答答的雨声揭晓了答案,让读者在短暂的希冀过后感受到落差,有了更深的悲哀:原以为作者的世界孤独到别无一物,却发现仅有的、能陪伴作者的,也不过是细细密密的雨声;若将此句按照字面意思译为“I could only heard rain drops”,则仅仅表达“我所听到的只有雨声”,叙事虽有凄凉之感,却远不如否定译法来得动人。“nothing was heard except the rain drops” 比“I could only heard rain drops” 的情感渲染效果更加强,在这一“有”和“无”的对比中,否定的使用使得文本感情的传达更加强烈,更能打动人心。
散文英译任重道远,但不论使用何种翻译手段,译者最基础的任务便是读通、读懂、读透原文。将中国散文译为英语,既要考虑目的语的思维与语言表达特点,懂得充分利用“否定”的妙译思路来传达深层情感,并不断提高自身文学素养与翻译水平,促进中国散文与各国散文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2]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
2018年长沙市科技局项目:长沙语言景观英译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kc1809052)。